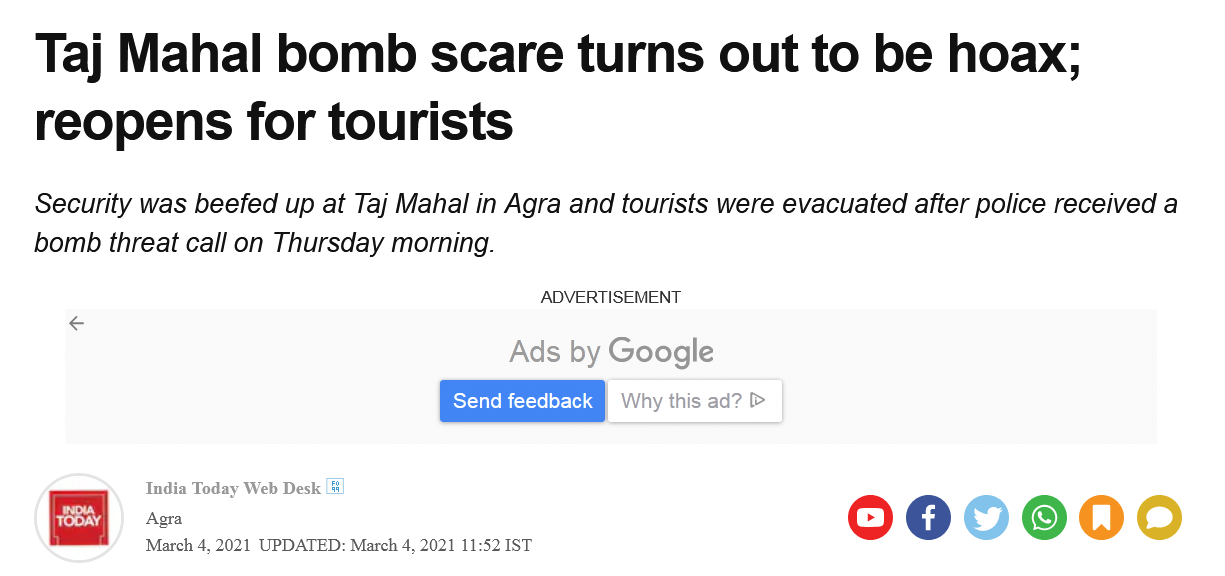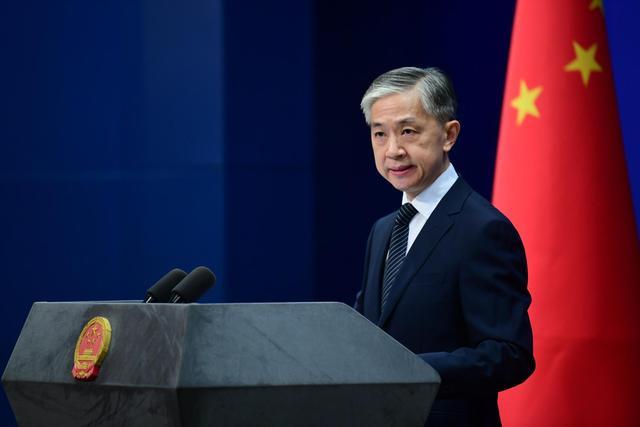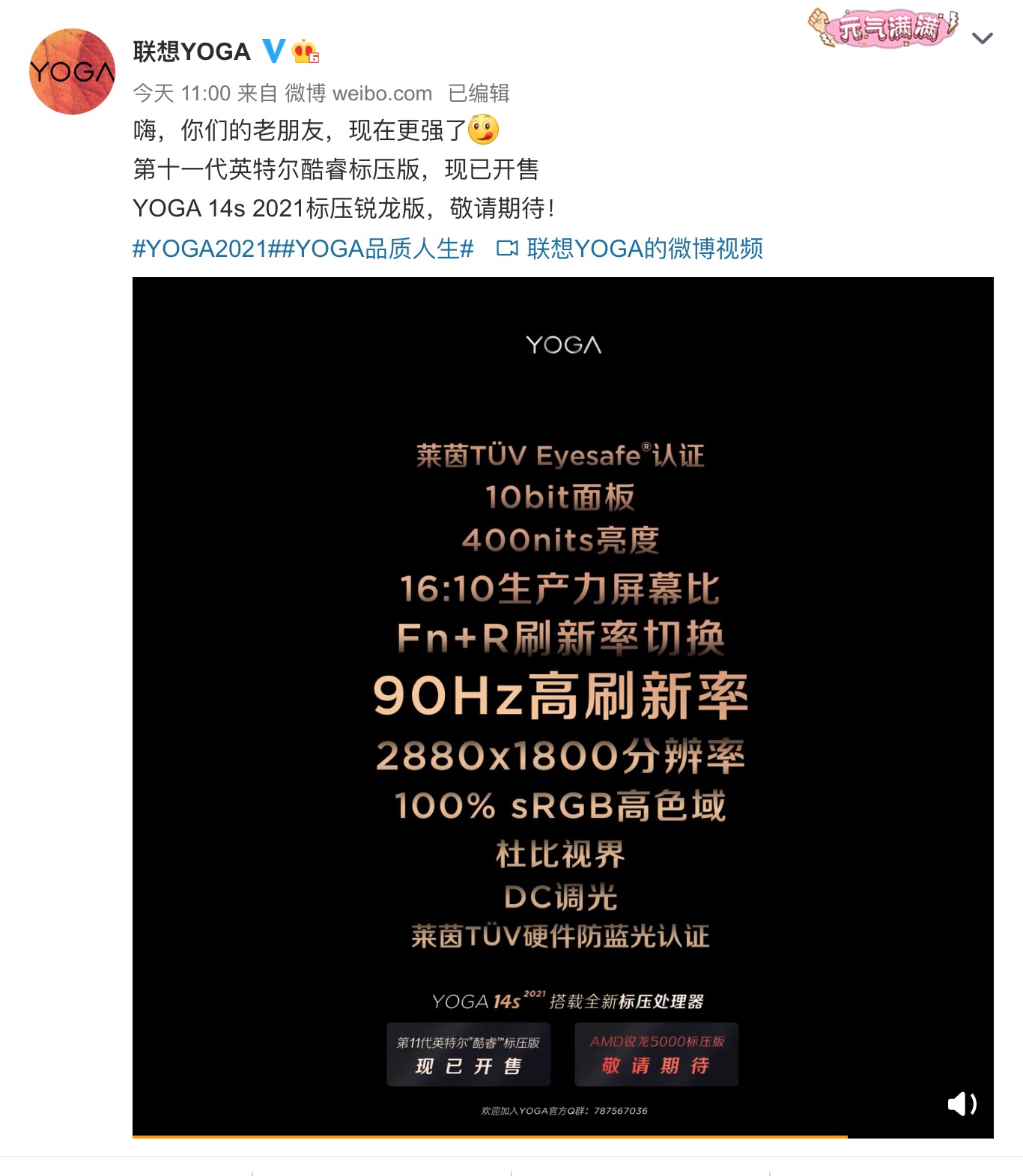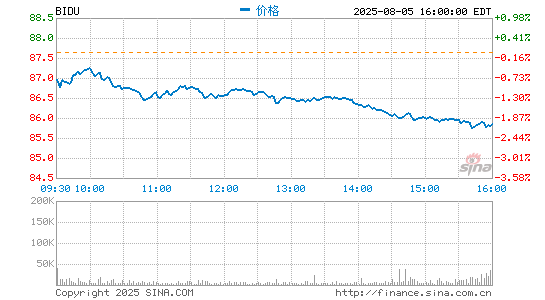原标题:从韦伯的“天职”到格雷伯的“狗屁工作”,我们如何认识工作与人的关系?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疫情期间,人们的工作形态也受到了影响,有人需要冒着更大的危险工作,有人习惯待在家中远程工作,有人则面临着裁员和降薪的风险。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Pissarides)在2020年的世界科学家大会上所说,疫情会改变工作形态,这种变化对某些人来说并不友好——未来对人工的依赖将远远小于对资本的依赖,因为工作自动化的加速会减少对人工劳动力的依赖。
如果说疫情暴露并加剧了本就存在的问题,那么我们也需要再次追问工作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你做的究竟是什么工作?又秉持着什么样的信念?这样的信念是否无懈可击?一方面,我们知道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曾经声称,世界上百分之四十的工作都是狗屁工作;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追溯马克斯·韦伯所谓“天职观”的来源,而将这二者结合来看,颇有意味。
什么是“狗屁工作”
2020年去世的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在他的著作《狗屁工作》中做出定义,称所谓“狗屁工作”就是“一个人必须每天做这份工作,但是他/她却认为这份工作是无意义的”。其概念核心在于虚伪和欺骗,包括对外的声张和自我欺骗,其中自我欺骗更为重要——只要工作者私下认为这份工作是荒唐的、无用的,就足以令这份工作被称为“狗屁”。
格雷伯也说明,狗屁工作是那些没有实际用途、缺了这些工作世界也能正常运转的工作,但与人们通常的印象不同,狗屁工作未必与公家单位的工作等同,因为私人企业同样存在官僚化和效率低下问题——如果说前苏联体制产生了冗余的蓝领工人,而出于精简化管理需求,资本主义制度制造了更多的案牍工作和白领工作。同时,狗屁工作也并不一定就是女性倾向做的职业,在当前就业环境下,女性从事的经常是低薪、重复度高的工作,却可能是护士等社会必不可少的职业。为了进一步阐明狗屁工作的范围,格雷伯举出了极端例子,有的工作像是“黑手党打手”,因为从事者心怀赤诚的信念,不存在欺骗之意,也不领取固定薪资,不能称之为狗屁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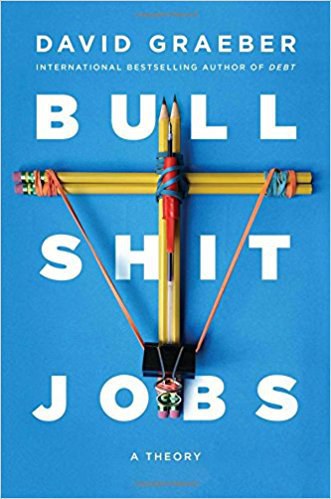
DavidGraeber
Simon & Schuster 2018
格雷柏将狗屁工作分成几类,其中就包括为了让自己上级感觉重要的“马屁精”(flunkies),比如宾馆门童、电梯操作员以及某些无事可做的前台接待员,他认为这是类似封建残余的工作;另一类是让下属感觉自己不重要的任务大师(taskmaster),他们负责分配以及监督狗屁工作;还有富有侵略性甚至有害性的“打手”(goons),这包括电话销售、广告、公关和公司法务,他们需要帮助教育顾客产生需求,再诱使人们为此买单。有意思的是,格雷伯对于公关的讽刺极为强烈,他说不知道牛津大学为什么需要聘请公关部确保“最好大学”的地位,如果公关能让牛津大学地位不保,这才能证明他们工作的力度,但这同样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这三类工作之外,还有为系统本不应有的错讹而存在的“胶带型工作”(duct tapers),他们要跟在上级和其他更重要的人后面收拾烂摊子;以及循规蹈矩的“勾框型工作”(box tickers),要求别人勾选表格按流程办事就是他们的工作,虽然他们明明知道完成表格并不能实现单位声称的目标。当然,这些狗屁工作类型也可以彼此混合的形式存在。
为什么钱多事少不是好工作
格雷伯指出,市面上有百分之四十的工作属于狗屁工作。比这个统计数字更重要的是,他要求人们认识到,并非钱多事少的工作就是最好的工作,缺乏责任与信念感的狗屁工作会磨损人们的尊严。人们需要在工作中寻找意义(end),意义的缺失会使人不知所措。他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中对苦役犯劳动处境的一段议论,阐释了什么是工作中的自由以及什么是不自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他见证的事实是,即使对死刑犯来说,也有强制的劳动和自由的劳动的区分;苦役犯大部分是熟练的工匠,他们会将自己的产品卖给当地人挣些小钱——虽然这在原则上是被禁止的,但能够支撑他们在监狱里活下去,赋予他们自我支配和道德自主的感受,而强制性的劳动则是具有毁灭性的:
格雷伯试图论述的正是,感受到工作的目的并且去做,就是最大的自由,而“摸鱼”“无实物表演”“装作自己在忙”的工作事实上是最大的无尊严和不自由。这与人们以往基于功利主义的人性假设——作为理性人,人性本能地追求利益最大化,因此无所事事还有收入是理想工作——完全不同。在他看来,人类生来就想要对世界施加影响,从婴儿时期人类就会展现出对于影响周围事物的喜悦,格雷伯引用德国心理学家卡尔·谷鲁斯(Karl Groos)1901年的发现“人类乐见于自己成为事物的原因”以证明自己的观点。从反面来看,失去影响事物的能力会造成心理的创伤(trauma of failed influence)。用他的话说就是,不能对世界施加影响的人事实上已经不再存在(“A human being unable to have meaningful impact on the world ceases to exist”),所以从事狗屁工作,尤其是被人监督、被人迫使的狗屁工作,会让人不快乐。
《狗屁工作》中的一个例子颇为有趣:一个蓝领工人家庭出身的学生,习惯了看到父辈凭借劳动直接产出成果,比如生产、修理物件,所以在读完大学从事白领工作之后感到无所适从。要求诚实的劳动、看得到劳动成果,而不是卷入自我欺骗式的、被迫强制的空虚劳作,这是格雷伯讨论的核心之一。
我们不应当把格雷伯对狗屁工作的反对,看成是他对某些工作种类的私人的反感情绪。在讨论19世纪美国消费主义文化兴起的著作《欲望之地》中,哥伦比亚大学荣休教授、历史学者威廉·林奇回顾公关和经纪人工作如何重塑了美国人的生活(在格雷伯笔下,这些工作大概会被归类为狗屁工作中的“打手”类型),也指出了这些工作中“伪”的性质。比如20世纪20年代最重要的人物伯奈斯就曾被评价为“伪事件”的制造者,他的成功公关案例包括通过制造媒体事件将天鹅绒和性感魅力以及巴黎、纽约的精致捆绑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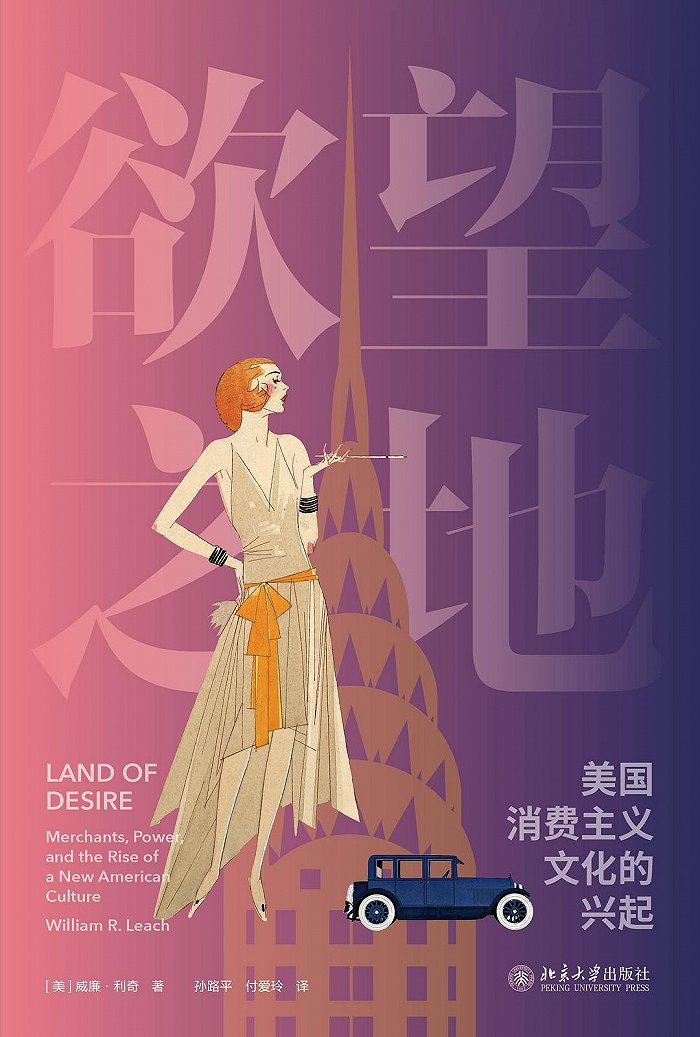
《欲望之地:美国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
[美] 威廉·利奇 著 孙路平 付爱玲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年
以《有闲阶级论》著名的经济学家凡勃仑也曾反对经纪人的工作,其理由和格雷伯竟有些相似。凡勃仑认为,包括投资银行家、地产经纪人、广告商在内的经纪人没有从事生产劳动,只是靠买卖他人的欲望来赚钱,将经济活动从制造有用的商品转向赚钱和获取利润,这些人对工艺一无所知,却对利润、营业额和愿望的复杂性了若指掌。至于金融手段和推销技巧,也是一门欺骗的艺术,因为这门艺术诱使顾客产生根本不存在的欲望,再靠售卖这些欲望赚钱。
“天职观”的来源
格雷伯讨论了当代种种工作及其虚伪之处,倡导人们应当从事自己能够做的工作,而这种要求真诚的态度令人想起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中提出的“天职观”:人们将工作视为天职,并终此一生为工作奉献。韦伯写道,个人感觉到对本职工作的责任,而且能感觉到职业活动的内容,正是资本主义文化的社会伦理最有代表性的特征,资本主义的伦理观在经济生活中取得了主导地位,并教育出了它所需要的经济主体——企业家与工人。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
[德] 马克斯·韦伯 著 袁志英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9年
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有胆大的投机者和冒险家,也有占有巨多金钱的金主,但这都不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主体。所谓的经济主体是那些“在冷酷无情的生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既精打细算又敢作敢当的人”,他们具有稳健节制、诚实可靠、敏锐精明的特质,全身心地投入到事业中去。为事业永久操劳是他们生活的必要,也是活着的唯一动机。
值得琢磨的问题正在于,“人为事业活着,而并非事业为人存在”的生活方式出现了。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经济劳动并非以赚到更多钱为目的,为了赚钱而劳作会被认为“拜金”甚至是可鄙的,同时也是非理性的;而在资本主义时代,这却成为了指导纲领,也为新式企业家的生活提供了伦理基础。韦伯强调,所谓资本主义的变革并不来自金钱的不断投入,而来自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准备。
韦伯将这种观念追溯至宗教传统。与“天职”(calling)相关的宗教概念是神交付的使命,而职业这个词与宗教改革紧密相关。职业一词的现代来源是《圣经》的译文,路德在译文中首次使用了贴合现代意义的“职业”一词。韦伯指出,路德的“天职”将人们履行世俗义务视为道德实践的最高内容,但因为不主张营业活动,所以对现代意义的“职业”影响有限。
如果转向加尔文教派和其他清教教派,我们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启发。概括来说,加尔文教派的教义相信,世间发生的一切,若有什么意义可言,也只在于它是彰显神荣耀的手段,只有一小部分人会被选中获得永生。对此韦伯评价说,“如此悲壮的不近人情的教义,势必会对信奉它的人造成严重的后果,尤其是让各人内心产生一种空前的孤寂感。”而重点在于,加尔文教派提出人们可以通过世俗职业劳动来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从而获得“灵魂救赎”。世间所有事物的存在都是因为神,所以现世的职业任务也是神赋予的,完成这些任务也具有为神而非为人的性质,“即一种服务于合理建构我们周遭社会秩序的目的。”由此,世俗的职业变成驱散宗教不安的最恰当手段,劳动成为有效地抵制一切诱惑的方法。在韦伯看来,固定职业具有禁欲的意义,也为近代专业化劳动分工提供了伦理依据,职业劳动进一步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人生观在人群当中扩散。
“上班骗局”
一方面是大卫·格雷伯提倡的基于诚实劳动和真诚信念的工作,另一方面是马克斯·韦伯追溯的从不近人情的教义产生的“天职观”,两者之间很难说没有关系。格雷伯倡导的工作态度,更像是鼓励诚实地追求符合个人天性的天职,而他反对的狗屁工作是对于将劳作视为目的、将赚钱当作目标本身的反省,尤其是将工作的人当做完全的理性人的批判,而这正是加尔文教派的重要影响之一。韦伯写道,加尔文教派信徒生活在难以缓和的紧张之中,无法摆脱也无法借助他力,需要在每一个时刻、每一个行动中将个人从自然状态提升到恩宠状态,至此人们的生活变得完全理性化了,实践不再无计划和无系统,而形成了一套可行的理性方案,资本主义时代意志坚硬如钢铁的商人就是加尔文教派圣徒的当代版本。
鼓励人们追求自己的志向这点不难理解,而后面一点更值得思考。卷入经济体之中,将劳作和赚钱视为目的本身,会存在什么问题?上世纪70年代末,陈映真创作了“华盛顿大楼”系列小说,包括《夜行货车》《上班族的一日》《云》等篇目,以跨国公司的上班族为主角,讲述了台北“华盛顿大楼”里发生的故事。在此系列小说里,陈映真提出了“上班,是个大大的骗局”的口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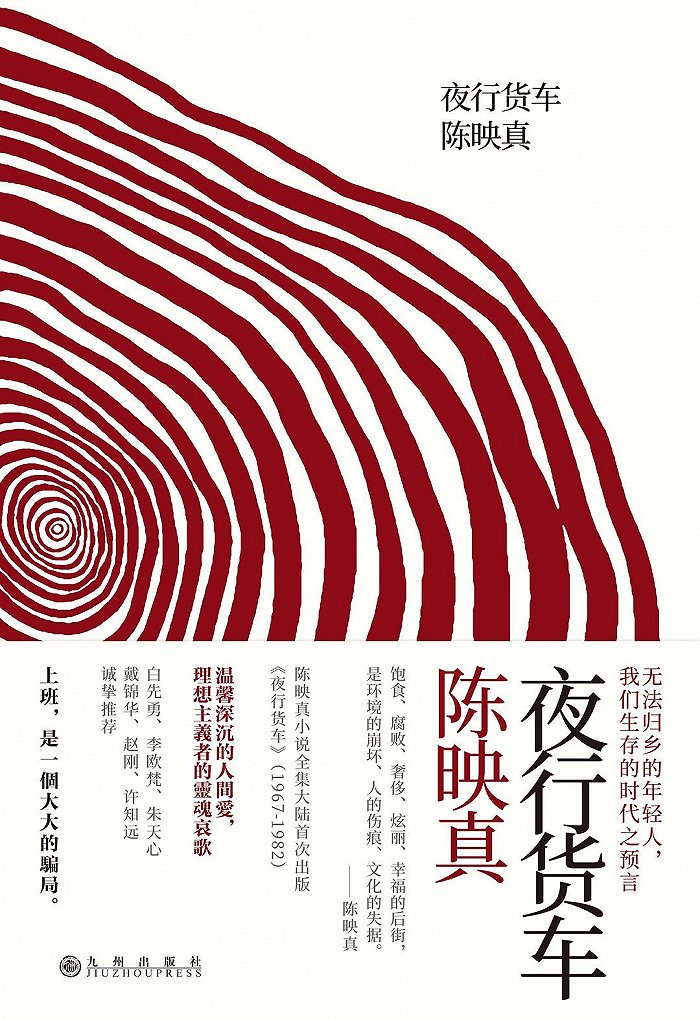
《夜行火车》陈映真 著
理想国·九州出版社 2020年
小说家陈映真对工作的洞察,正与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类似,也点出了理论之外的个体工作中的悲喜。“华盛顿大楼”系列故事中的主角抱着老老实实等待升迁的想法,然而现实并不按照他规划好的那样发生:有一位想要做经理到已经魔怔,将当上manager作为至高无上的人生目标,另一位一路升迁顺利、眼见着要跳进那间独立的办公室,突然中途受阻,一怒之下要挟上司辞职。
就像加尔文教派无法摆脱紧张状态、必须身处争取救赎的路径之中一样,在人人都要上班的时代,公司经济体之外的生活几乎消失了,当工作中的情感成为个人意义的唯一的来源,对工作的热爱也变成他/她精疲力尽的缘由。陈映真笔下的小说主角想要离开他的工作环境和公司,然而不管是待在家中还是乘坐公交,或是跟朋友电话聊天,他都发现自己的社会角色消失了,脱离公司之网他根本无处可去。“他忽然感到仿佛被整个世界所抛弃了的孤单。他这才想到:这一整个世界,仿佛早已绵密地组织到一个他无从理解的巨大、强力的机械里,从而随着它分秒不停地、不假辞色地转动。”说出辞职之后,他感觉到自己早已落在“重重的生活的,驱使每一个人去上班、下班的无形的巨大网罟之中,难于动弹”。
将陈映真的小说与格雷伯和韦伯结合来看,它们似乎指出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当就业环境不再如人所愿,当天职观(或者变体信仰“你应当热爱你的工作”)无处不在,身处其中的人们是否将被工作湮没——而即使是狗屁工作,人也难以动弹更遑论逃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