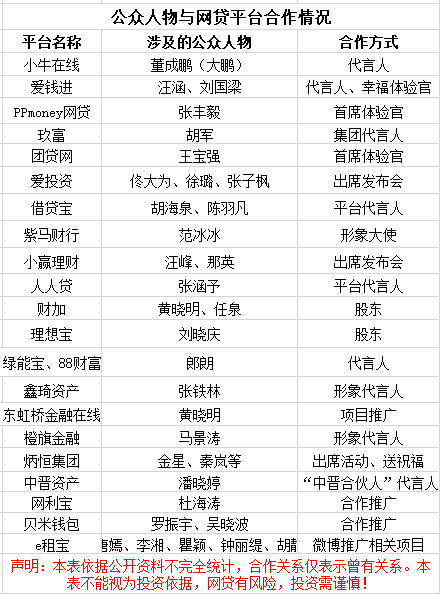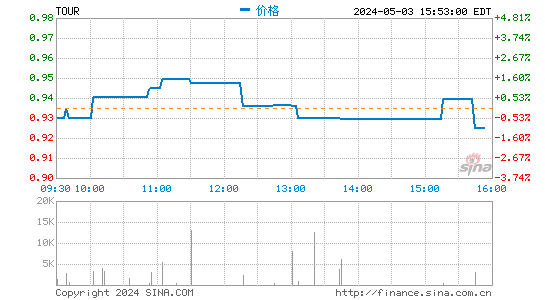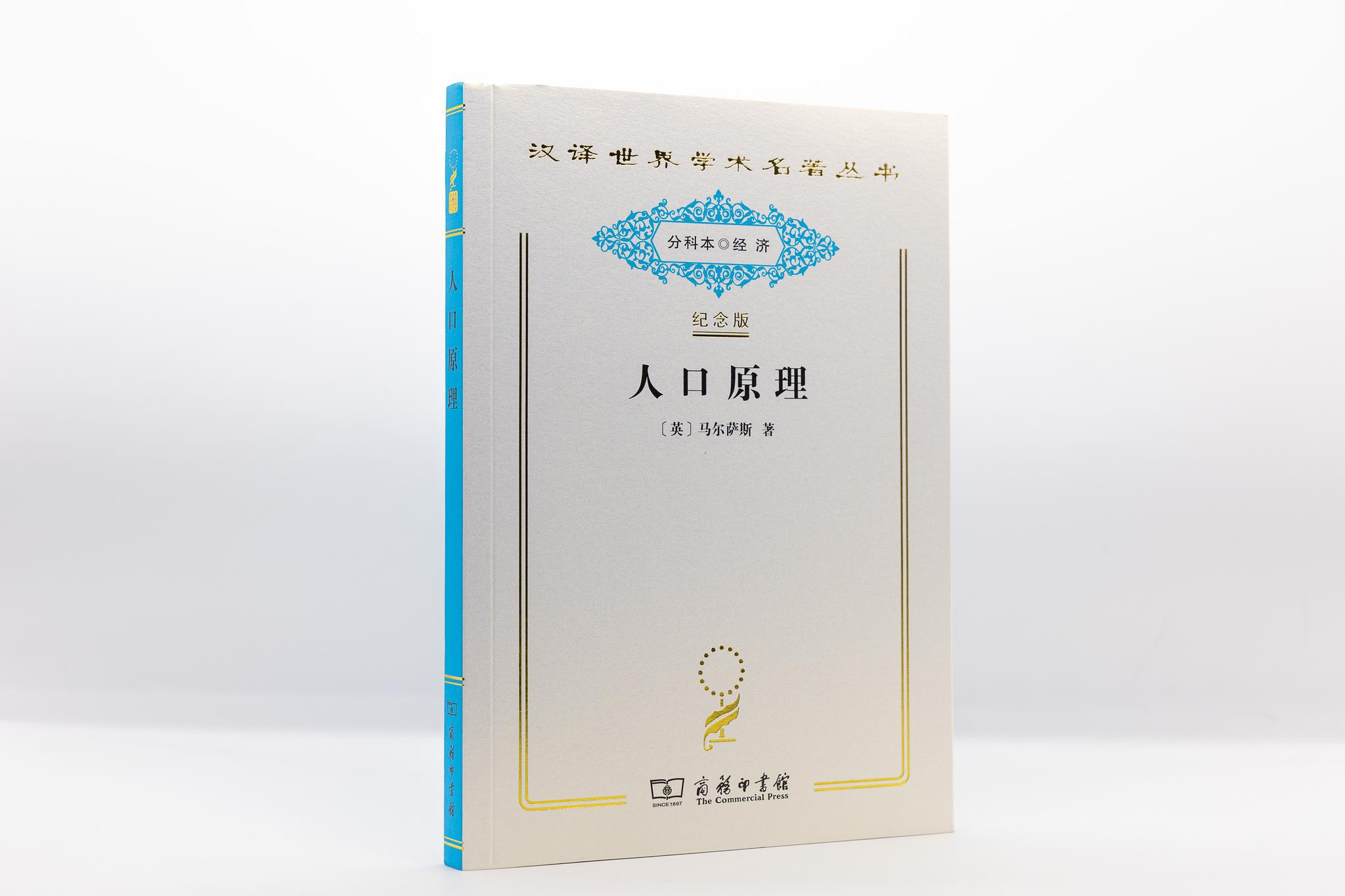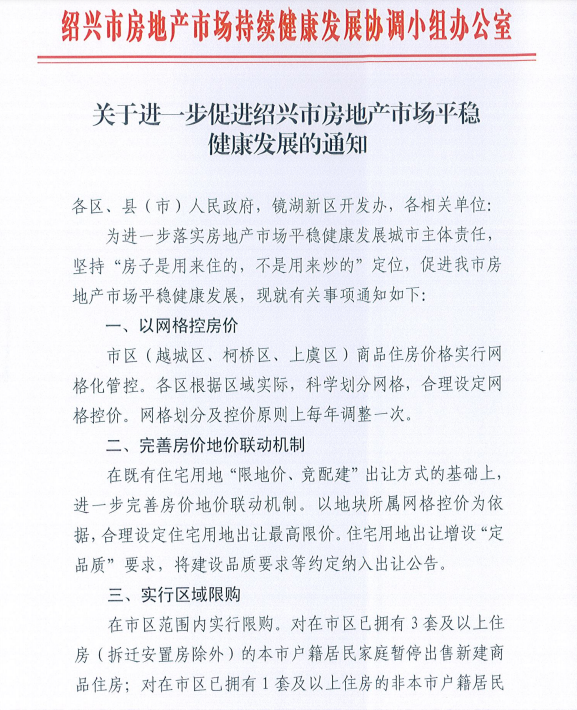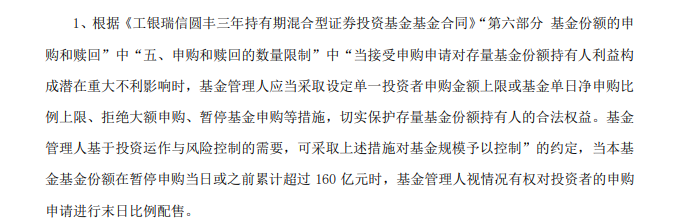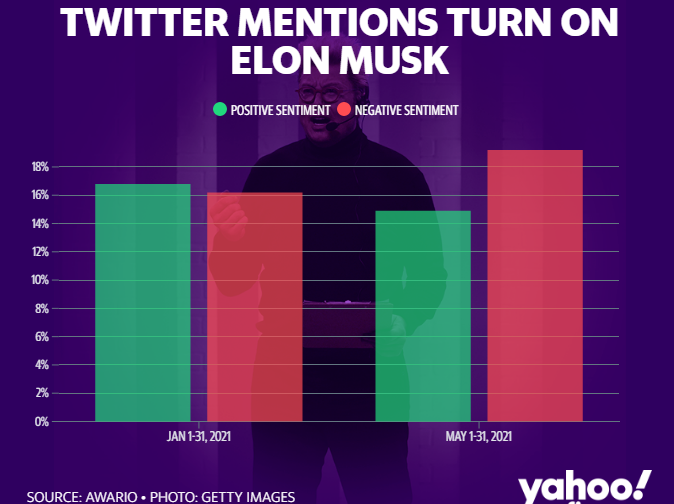原标题: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④|做好中国的国际传播需要更多研究和人才
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我国在设置全球议程和讲好中国故事两个方面,虽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也仍然存在改善空间。
比如,第一、目前的成绩主要体现在“硬领域”(区域经济和地缘政治),在其他“软领域”(思想、文化、价值观等)的议程设置和故事讲述较少;第二、传播对象多为海外商人、企业家和IT从业者,针对海外普通公众的项目较少;第三、周期性和项目性成果较多,缺乏持续和稳定的影响机制;第四、传播方式仍主要“以我为主”,宣传意图明显,容易激发国外受众的戒备和逆反;第五、议程设置和讲述故事的主体以国家级媒体“旗舰”和“航母”为主,传播效果有边际效应递减的趋势;第六、国际传播实践缺乏政策性强,理论指导弱;第七、高端国际传播人才较为稀缺。
如何做好我国在新时期的国际传播?我认为可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提高专业水平
我国的国际传播又被称为“对外传播”或“对外宣传”,其政策性常常大于专业性,在实践中政策和经验指导多于科学和规律指导,这样常常造成国际传播从业者只知道要做,但不知道怎么做(how),更不知道为什么(why)要这样或那样做。
例如,中国文化的谦虚、礼貌和温和早已广为世界人们所知晓,国际受众也并不缺乏区分礼貌和粗鲁的能力。我国新闻发言人和外交官在跨文化情境中的强语言(power speech)与弱语言(powerless speech)使用,其效果如何?需要研究。
“强语言”指在对话中一方占据主导地位,体现为较多打断、命令、质问等,但强语言并不等于粗鲁无礼(rudeness),而也可以表现为自信而礼貌;“弱语言”指对话中一方处于配合和合作地位,语气多为商讨性和回应式,但弱语言并不等于软弱无力,也可以表现为谦逊而坚定(civility)。弱语言还可以被发言人策略性地利,例如用“个人故事”提升观点的真实性和“自置低位”来表现出我们对国际沟通的在乎(caring)和善意(goodwill),进而获得观众好感,提升国家形象。
又如,我们听到 “狗”一词(所指)时,脑子里会想到该种动物(能指),但同时也会激活一种将“能指”和“所指”关联起来的一种“关系”(即皮尔士所说的“解释项”)。在不同文化中,与“狗”一词相关的“联想关系”各不相同,例如,中国人和美国人对“狗”(dog)这个词有不同的的联想,而恰恰是这些不同的联想导致了跨文化沟通中的误解——你用狗表示可爱和亲密,我则认为是表示讥讽和侮辱。国际传播研究者应该关注和研究这样的误解。
二、需要更多的国际传播主体和更多的人际传播
中国的绝大多数国际传播,是借助大众媒体或网络媒体进行的。大众传播一对多,实施容易,威力强大,但是通过大众媒体进行国际传播,却对国际受众有较大的宰制性,效果较差。
因此,如果过多地依赖大众传播,国际传播往往会沦落为单向的独白,造成资源浪费。套用广告从业者的一句话:投入到以大众媒介为主的国际传播中的大量资源,至少有一半被浪费了,但我们不知道是如何被浪费的,也不知道被浪费在何处。
相关实证研究也证明了基于大众媒介的国际传播,效果已经越来越差。如美国传播学者策尔纳观察了9个主要穆斯林国家中反美情绪的根源,发现对于观看西方新闻的阿拉伯观众,观看时间越长,对美态度越负面。他对此给出的建议是,用面对面的人际交往补充大众媒体的单向宣传,创造本土语境让穆斯林受众能与代表美国声音的人士进行直接交流和对话,对重要议题展开讨论。
有鉴于此,中国的国际传播,应该大量增加大众传播媒介之外的传播主体并采纳更多的人际传播。
中国的国际传播曾经历过“人际传播1.0时代”(来华传教士与中国人之间)、大众传播时代和互联网传播时代三个阶段。目前,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民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国际视野的扩大和国际交往的深化,人际传播(包括以互联网为中介的人际传播,例如“网红”)的重要性越来越出,使得国际传播已经 进入“人际传播2.0时代”。
中国还可以大量增加地方机构型国际传播主体,例如在中国有条件的城市推出一些小而美的新型外宣媒体,一个例子是上海的“第六声”(Sixthtone.com)。“第六声”有意要与中国现有外宣媒体形成差异,试图展现在这个正在快速现代化的庞大国家中的普通人的声音,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传播中国。运行5年多来,它默默耕耘,静水深流,做出了投入小,效果好的国际传播成绩。
三、 动真格大批量培养高端国际传播人才
我国对国际传播的投入不少,但多用在可见的设施设备和海外拓展上,对于人才培养的投入虽有增加,但远远还不够。
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要加大人才培养投入力度,而且要着力大批量培养顶尖国际传播从业者,尤其强化他们的高端对话能力。这种能力指传播从业者经由多方位、系统的和强化训练后在受到高关注度的国际场合,具有的一种高超的,能调动自身具备的一切经验、技能和知识综合漂亮地应对挑战、表达观点和立场的能力。
目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已经参与了我国高端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但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培养机制不能受制于现有的人才培养机制,而要突破现有框架,特事特办;人才来源也要放眼全国乃至世界,保证其精英化,以一当十,而不能全是虾兵蟹将;在培养过程中要投入资源,报以信任,给予权力并尊重其相对自主性。在信息泛滥、利益交葛的国际传播环境中,具有高端对话能力,国家立场坚定又充满个性魅力的意见领袖属于稀缺品,他们的培养需要清晰的思路、创新的模式和大量资源的有效投入。
四、 辩证看待国际传播的效果及其与现实的关系
最后,我们要辩证地看待国际传播效果的好与坏,以及国际传播与国家现实之间的关系。
首先,人类个体之间的相互隔阂是绝对的,相互理解是相对的。传播的价值不在于达致人与人心灵之间的融合,而只不过是为了实现外在行动上协调合作去达致一些能达致的目标,底线是不至于陷入“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
由浸淫在不同语言和文化中的个体组成的国家之间也是如此,而不同的国家利益进一步加剧了这种隔阂。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说,我们哀叹交流总是失真和失真,那是因为我们将交流的目标竖得太高,将其作为相互融合来追求而导致的。与此类似,我们要认识到,基于不同语言文化、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国际传播中的差异、误解、故障和失败其实并非能完全剔除,它们本身就是常态而不是例外。
既然我们无法完全剔除差异,那就只能接受差异并努力从中获得最大的收益。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将自己建设成一个国家强盛、人民幸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伟大民族。如果我们的这一追求能被他国理解,这自然会令我们愉快,但如果不被他国理解,我们锐意进取,行稳致远,其实也并无大碍。
其次,在国际传播中,我们要相信“信息的唯物论”(information materialism)而不是“传播的决定论(communication determinism),认识到影响其效果的最终因素并非传播,而是传播所基于的现实,并努力通过改进现实来提升传播效果。
从19世纪晚期以来,各种媒介技术层出不穷,人类的音容笑貌开始被媒介技术中介化,到1920年代,大众媒介(mass media)在美国首次出现。随后,人们对日益复杂的客观世界的认识便开始越来越多地通过大众媒介,以至于将其等同于前者。这不免让人类开始迷信传播的威力,认为仅仅通过它就能够操纵人们“脑中的图景”,甚至操纵现实本身。
鲍德里亚指出,工业化时代是符号复制现实,信息社会是符号复制符号,从而将人类社会带入“拟像”(或“后真相”)时代。诚然,媒介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建构现实,但媒介终究不是现实。因此,我们要记住,在国际传播中,现实始终是第一性的,传播始终是第二性的。(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