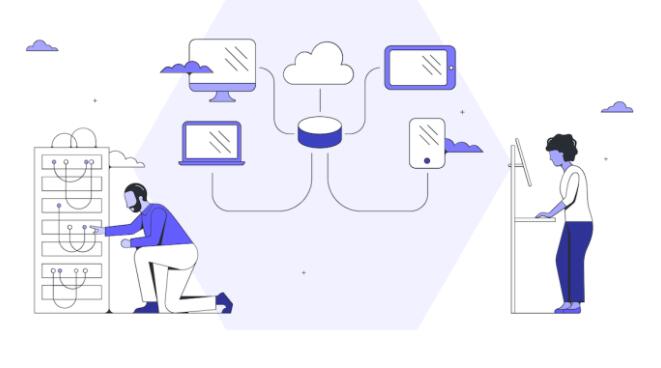新浪科技讯 北京时间10月29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2018年,斯蒂芬·戈斯林和他的团队花了数月时间搜索了从帕丽斯·希尔顿到奥普拉·温弗瑞等一些最富有名人的社交媒体资料。这位来自瑞典林奈大学的旅游学教授试图寻找有关这些富人飞行里程的证据。
答案是惊人的。根据戈斯林的计算,世界上最知名的环保倡导者之一比尔·盖茨在2017年一共乘坐了59次航班,飞行距离约343500公里,相当于环球飞行8次以上,产生了1600多吨温室气体(相当于105个美国人的年平均排放量)。
戈斯林的目的是试图揭示这些超级富豪的个人消费水平,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往往被隐藏了起来。巧合的是,他的研究正好赶上了一场日益壮大的环保运动,而在这场运动中,个体的责任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乘坐飞机出行是碳消耗最密集的形式之一,成为了这种责任的象征,你的碳足迹越大,你的道德责任就越大。
过去几十年来,全球性的不平等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从2008年金融危机到新冠疫情,再到气候变化日益严重的影响,破坏性的事件往往首先对最贫穷的人群造成最严重的打击。然而,在有关如何解决不平等问题的辩论中,过度消费往往被忽视,你所超出的每一份额,都意味着必须有人放弃(一些东西)。其结果是,社会上最富有的人巨大的碳足迹巩固了不平等,威胁着世界抵御灾难性气候变化的能力。
统计数字令人吃惊。根据2020年的一份报告,2015年全球约一半的碳排放来自全球最富有的10%的人口;其中前1%的人口的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的15%,几乎是世界上最贫穷的50%人口的两倍,后者的排放量仅为7%。尽管贫穷人口对气候变化的责任最小,但他们将首当其冲地感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随着富人们快速地消耗剩余的“碳预算”——在本世纪末导致全球变暖不超过1.5摄氏度的情况下所能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他们“正在挤压底层50%的人口的排放空间,导致他们实际上无法满足生存的需求”。
《碳不平等:气候变化中最富有者的角色》一书的作者达里奥·肯纳创造了“污染精英”(polluter elite)这个词,用来形容社会上那些广泛投资化石燃料、并因其高碳生活方式对气候产生强烈影响的最富有人群。然而,尽管污染精英具有与人数不成比例的影响,但所谓“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则涵盖了更广泛的人群。

当我们想到“富人”时,我们可能会想到拥有私人飞机和多座豪宅的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
但38000美元的收入就足以让一个人跻身世界上最富有的10%,而109000美元的收入则足以让一个人跻身世界上最富有的1%。
就目前情况来看,富裕国家的大多数人的消费方式正在加速气候灾难。根据研究数据,如果将进口商品的排放量考虑在内,那么英国人均每年的碳排放量为8.5吨,而加拿大高达14.2吨。加拿大是该研究所调查的国家中人均碳排放量最高的国家。为了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到2050年,年人均碳排放量需要大幅下降到0.7吨。
个人消费是一个棘手的话题,并可能很快演变成一场老生常谈的辩论,即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是取决于个人行动,还是政府和企业的系统性变革。
其实这是错误的二分法,生活方式并非存在于真空中,而是由环境塑造的。人们生活在几乎不可持续的现存政治和经济体制当中。但是,如果不着手改变我们社会中最富有、污染最严重的那些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所拥有的权力,我们就无法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以航空为例,只要你乘坐飞机,你就属于全球的精英阶层。世界上超过90%的人从未坐过飞机,而仅1%的世界人口就贡献了50%的飞行碳排放。从遍布全球的商业精英,到将旅行视为个人品牌一部分的名人,他们的行为都赋予了高碳生活方式一种成功的色彩,变得令人向往。

除了飞机,运动型多功能汽车(SUV)也已经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除了接送总统、商界领袖和名人,城市中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家庭也选择了这种车型,尽管它们对环境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2019年,SUV占全球汽车销量的42%,并成为2020年唯一排放量上升的车型。由于这一年购买SUV的人数增加,有效地抵消了电动汽车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大房子是另一个消费热点。在最近发表的一项关于富人在加剧气候变化中的作用的研究中,对住房的选择意味着声望和社会地位,在欧洲,近11%的住房碳排放来自于拥有大户型(且通常是多套)住房的前1%的排放者。
不过,过去几年来,社会舆论开始发生变化。在瑞典,环保行动帮助激发了“flygskam”(在瑞典语中意为“飞行耻辱”)的概念。这一概念促使人们开始反思自己究竟应该乘坐多少次飞机。2018年,从瑞典机场起飞的乘客数量下降了4%,这在全球乘客数量增长的背景下是相当罕见的。
新冠肺炎疫情也大幅减少了商务旅行,证明视频通话可以取代面对面的会议。彭博社的一项调查发现,84%的企业计划在疫情后减少出差支出。
人们也开始考虑饮食方式的影响,这促使植物性肉类和奶制品公司成长迅速,这不是来自法令或政府政策的要求,而只是企业看到市场正在发生变化。
然而,对于我们所处的紧急状态而言,这些变化都太缓慢了。我们正在经历气候变化的临界点,物种正在灭绝,问题的关键在于速度,为此政府有必要采取行动。
对频繁飞行和肉类过度消费等不可持续行为有针对性地征税,可以帮助人们更快地转向低碳行为;如果惩罚污染行为和让许多人受益的投资之间存在直接联系的话,效果更为明显。
例如,“飞行常客税”的收益可以投资于更便宜甚至免费的公共交通系统,“豪宅税”的收入可以用于房屋隔热,从而降低(因为缺钱而无法给住房取暖的)能源贫困水平。然而,问题又来了,最富有的国家能否简单地消化这些成本,并继续像以前一样生活下去。

一个更激进的想法是个人碳限额(personal carbon allowance,简称PCA),即每个人都被分配一个平等的、可交易的碳限额。如果有人想要排放更多的二氧化碳,就必须购买别人不需要的配额。在爱尔兰、法国和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都已经探索了各自的PCA模式。2018年,英国政府分析了PCA的可行性,但得出的结论是,PCA成本太高,难以管理,不太可能被社会接受。
不过,根据最近的一项研究分析,在气候紧急情况和疫情——可以迫使人们以集体利益的名义接受一定的个人限制——的背景下,PCA可能是一项值得重新考虑的政策。
PCA是有一定吸引力的,因为它确实清楚地表明了我们的人均权利是什么。但这是将责任个人化的极端版本,最终可能会不公平地惩罚那些在公共交通选择很少的地区居住的人。
另一个越来越受欢迎的政策理念是“选择调整”(choice editing),即政府一开始就限制私人飞机或大型游艇等碳密集型产品进入市场。这个理念本质上是提供低碳选择,其中许多已经存在,可以填补市场的缺口。
选择调整可能听起来很激进,但并不新颖。例如,英国政府以公共安全为由,使用选择调整的方式,禁止销售枪支或无安全带汽车。今年4月一份有关行为改变的报告总结道:“消除不可持续行为比从一开始就阻止不可持续产品进入市场要困难得多。”
然而,即使应对气候变化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许多政府仍在有关行为改变的政策上犹豫不决,担心这些政策会在政治上导致选票减少,也会让富人感到不快。最富有的人通过游说和巨额捐款对政府拥有控制权,这让他们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可以稀释气候行动,并影响所有人的选择。换句话说,我们原本有机会选择另一种更加光明的未来,但每一天,这一未来都被不断否定。
对于所有针对消费者行为的政策,如果最终没有足够的基础设施能让人们过上低碳生活,就很难降低排放。要建设一个更可持续的社会,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不仅仅是减少私人飞机和豪华游艇。
一些政府正在进行重大改革。为了达到减排目标,部分国家政府已经暂停了对新道路建设的投资,荷兰则提议将牲畜数量减少30%以减少污染,英国一些城市的议会已经开始建造节能型社会住房。
另一些政策则瞄准了广告在推动不可持续消费方面的影响。继巴西圣保罗和印度金奈等城市禁止或严格限制SUV的户外广告牌之后,阿姆斯特丹在2021年禁止了SUV和廉价短途航班等排放密集型产品的广告。
但这真的不够,人类的行动是如此缓慢,时间已经所剩无几。政府需要彻底改造基础设施,将可持续性放在政策的核心。这意味着建立快速、广泛和负担得起的公共交通网络;发展脱碳电力;建设更密集、隔热性能更好的房屋;禁止使用燃油汽车;以及考虑实行每周四天工作制等一系列措施。
政府和富人对社会规则具有巨大的影响,他们也可以帮助改变“气候行动完全是关于个人自由和生活质量损失”的说法。那些被证明对环境更可持续的事物,几乎总是更有利于我们自身的福祉和社会凝聚力。
少开越野车和汽油动力汽车可以提高空气质量,减少空气污染造成的死亡;每周四天工作制可以更好地平衡工作和生活,让父母有更多的家庭时间,承担更少的育儿成本。人们消费的原因有很多,比如为了满足生活的需求,为了表达情感,为了良好的感觉,抑或是因为他们受到了广告或社会期望的压力。
很少有人真正反思自己的消费。这些都是非常深奥的问题:我是谁?我需要什么才能过上美好的生活?个人行动不足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内疚和羞愧也无济于事,但选择和行动也同样重要。(任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