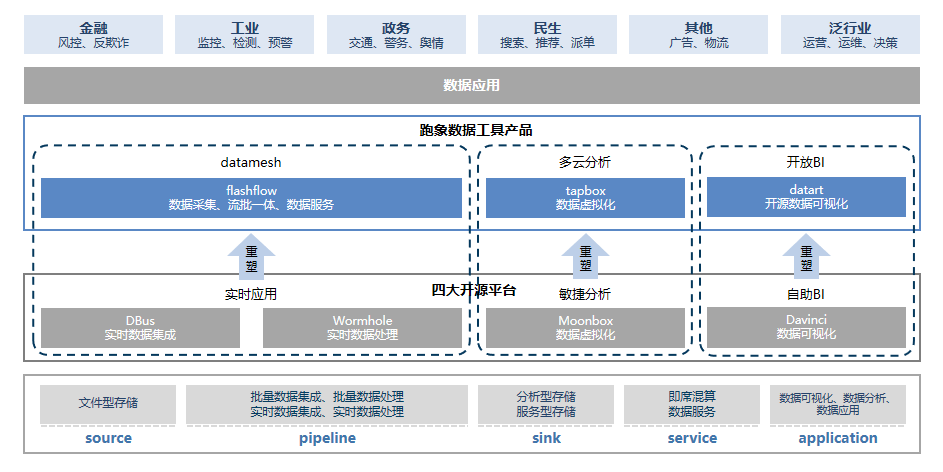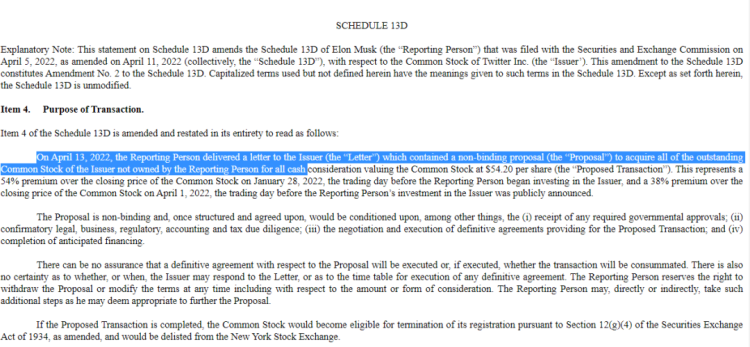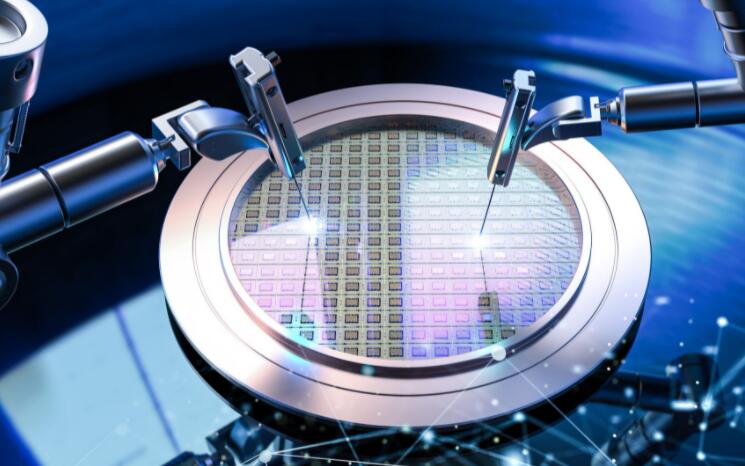●魏学光
生活在吐鲁番的人们,有些年份躲过了雨,有些年份躲过了雪,但是从来没有躲过风。没人能躲得了风,人的一生注定要经历一些风,经历无数的风,才算是完整的一生。
风是不速之客,请或不请,它都会来。该来的时候来,不该来的时候它也会来,它不在乎人们的意志,也不在乎人们对它的差评,没有什么人,也没有什么抱怨和力量阻挡得了它。
火洲吐鲁番四周高山环抱,上升的热气被下沉的冷气紧紧地裹住,百里火焰山俨然一颗巨大的仙丹,在这火洲的火炉里长久地冶炼。有热必有风,地面和天空的冷热气流,如仇人,如宿敌,从春至夏,从夏至秋,它俩捉对厮杀,杀得天昏地暗。当上升的气流败北溃不成军时,便卷起炙人的焚风,扫荡火洲大地。
新疆的七大风区,有四大风区分布在火洲吐鲁番。东面的是百里风区;西面是三十里风区,与乌鲁木齐的达坂城风区紧紧相连。从东到西有3个风口,分别从大河沿、小草湖、通沟3个方向直逼吐鲁番全境。
交河故城所在地雅尔乃孜沟自古就是著名风线。风出大河沿,如脱缰野马,势不可挡,横扫吐鲁番西北角,通过雅尔乃孜沟口再次扑向艾丁湖,所到之处飞沙走石,一片狼藉。
大风就是命令,我的工作职责是应急救援。因为工作的原因,我曾数次冲入暴风中救人。在小草湖、大河沿312国道,每当暴风肆虐,那些经过的大小车辆只能在此避风避险。随着风势越来越大,狂风吹起黄沙走石,轮番袭击这些毫无准备的人们。在寒冷和暴风中,我和战友肩并肩,手拉手,高举手电,一次次向前冲锋,在戈壁滩上四处寻找他们,把他们救出并送到安全地带。
在吐鲁番,我一次次经历着风,感受着风,体味着风,我能感受并分辨出它们是大漠风、戈壁风、焚风、微风还是飓风……我能看得清楚它们来自哪里,吹向何方。它们恣意地咆哮着、奔腾着、撕扯着,似乎正在摧毁些什么,也似乎在重塑些什么。古往今来,它便漠视一切尘世间的软弱、苍白、浮躁,而倾心于刚毅、果敢、厚重。
大风过后,留下的都是沧桑岁月的痕迹。风线上的树永远都长不直,树干是歪的,那些虬枝乱桠横七竖八;那些迎风面的树皮被风刀蚀刻,如海浪拍打的礁石千疮百孔;杂草和枝叶都被风刮起埋进了沙丘。那些大风刮过,刮走的也必然有刮走的理由;刮不走,留下的都是有分量的东西。比如人,比如历史文化遗产——交河故城、高昌故城。前者是世界上最美的废墟,活着的庞贝;后者是大唐遗梦,“翻版的长安”。
风谙熟艺术。千百万年来,它精雕细琢着吐鲁番,盆地里第四纪冰缘区冻土层和霜沙层的风凌石,比水蚀的奇石要奇、要峻、要透、要秀,还有古朴的光泽和风雨沧桑的韵味。水蚀往往使石头失去原有的模样,只是一味地浑圆,风蚀则磨掉了石的棱角,留下了石的骨骼和皱褶。故而水蚀石圆润,风蚀石既灵动苍秀又通透巍峭,具清、拙、古、怪之意;皱、透、漏、瘦之形,真是美不胜收。
风起沙扬,被风吹走的是黄沙,留在地表的是戈壁,每个沟壑和岩块都留有风的痕迹,这些被风吹成的平行的深沟,都是来去无踪的风的杰作。白杨河雅丹地貌、南湖大海道雅丹地貌和盘吉尔怪石林,以雄奇、粗犷、古朴而名闻天下。
风在自然面前威猛、霸气,从来都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但人与天斗与地斗与风斗的力量同样也不可小觑。1961年5月31日,一场持续16小时的12级以上大风摧枯拉朽,重创火洲家园。人们惊恐、错愕后,痛定思痛,纷纷从废墟中爬起,抡锹铲土,挥汗如雨,硬是在老风口上平行并列开挖五条渠道,在渠道两侧栽满树苗。风雨沧桑,五道“绿色长城”终于长成长大,如猛将壮士将“老风口”堵得结结实实。这就是吐鲁番“五道林”的来历,是人在风口前沿植树造林改变了风的走向。
风,从此时也对人产生了敬畏。
风刮完一场,接着又刮,风起沙行,浮尘蔽日,忧郁也好,烦躁也罢,人们别无选择,还得把日子过下去,过得跟风一样酣畅、爽快。
人们在风中栽瓜种果,收获甜蜜;人们在风中歌唱舞蹈,裙裾飞扬。他们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正如维吾尔谚语所言:“人出生后,除了死亡,其他事情都是在享受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