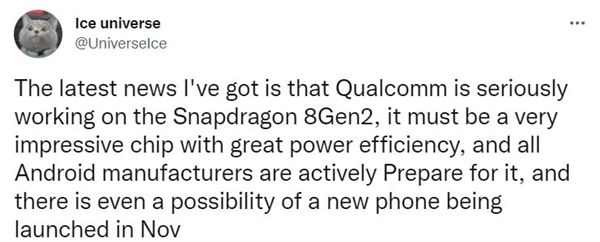来源:中国企业家公众号

克制和谨慎,比创新和突破还重要。
文|《中国企业家》记者 梁宵
头图来源|受访者
年过60岁,创立的两家公司相继被跨国巨头辉瑞、拜耳以累计数十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人生的下一步何去何从?
肖啸的决定是重启第三次创业。那是2016年,他自己拿出几百万元在上海租了实验室,招了几个“学生兵”。他还陆续辞去了国际药企顾问、UNC(北卡罗来纳大学)终身讲席教授的职务,放弃了在美国三十多年的积累,全力投入到中国基因治疗创新药领域。
这个不同于其他教授的经历打动了郑静,在此之前,她有过两次、加起来十年的创业历程,见惯的是一些拿着几张PPT就去找投资人要钱的创业者,以及那些创业之余还身兼数职的“海归”。“观察”肖啸一年后,她更觉得“这个人能处”,就正式加入,成为公司的联合创始人。
都是医药领域的连续创业者,他们知道创新药企“九死一生”的命途,尤其是罕见病用药研究投入之大,风险之高更让人“望而却步”,说是“九十九死一生”都不夸张,但他们决心要做“让中国老百姓买得起、用得上、而且治得好的药”;以至于带有一些理想主义的执拗,他们把公司命名为信念医药。
信念医药首个攻克的目标是血友病。因为最早发现于维多利亚女王的后代中,血友病又被称为“皇室病”,但诗意的比喻改变不了病痛残酷的本质:由于体内缺少凝血因子,患者任何一个不小心的磕碰都可能导致血流不止,甚至还会出现“自发性”出血,严重时危及生命,成为经不起任何碰撞的“玻璃人”。
根据测算,这样的患者在中国约有14万,全球约50万,常规通过注射凝血因子进行治疗,每年的治疗费用高达几万到几十万美元,持续终生;相比之下,基因治疗可以实现“一针治愈”,但费用动辄数百万美元——信念医药希望尽量降低这种创新疗法的用药成本。
在正式成立(2018年5月)后的第三年,信念医药越来越接近这个目标:2021年8月,公司自主研发的BBM-H901注射液成为国内第一个获批进入注册临床试验的血友病AAV基因治疗药物,12月完成中国首例B型血友病AAV基因治疗注册临床静脉给药,目前已经完成首批病人注射,进入到药物开发的临床二期,预计在2024年下半年到2025年上半年上市销售。
 来源:受访者
来源:受访者而今,这颗由信念播下的种子已经破土而出。未来,又能否冲破风雨、长成参天大树呢?

先发优势
或许要先解释一下什么是基因治疗?
简单地说,基因治疗就是将具有正常基因或治疗作用的DNA片段导入人体细胞,通过矫正患者原本的基因缺陷而实现治疗的目标,对于致病基因清晰而蛋白质水平难以成药的靶点具有独特优势——此前的生物医药技术在这方面则收效甚微。因此,财通证券在研究报告中指出,“如果把小分子药物、抗体药物称为生物医药的前两次革命,基因治疗将引领生物医药的第三次产业革命。”
2017年,首个基因治疗药物获得美国FDA批准,药物面向一种很罕见的遗传眼科病——Leber先天性黑蒙症,研发药企Spark也因此被罗氏制药以43亿美元收购;此后,推出脊髓性肌萎缩症(SMA)基因治疗药物Zolgensma的AvesXis被诺华制药相中,卖出了87亿美元的高价——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上市的基因治疗药物已有二三十种,但绝大部分都在欧美市场。
“基因治疗技术已经开发了三四十年,此前在临床实验上走了很多弯路,做了几千个实验,其中失败的也有很多。”肖啸表示,如今随着基因治疗生产和临床应用先进性和安全性不断提升,商业化的时代已经到来。
过去的35年,肖啸一直在美国从事AAV基因治疗的研发转化,他在博士毕业后加入初创公司,六七年后回到学校任教,同时从事科研成果转化工作,带领团队成功研发数十种AAV基因治疗药物及相关技术,并一路见证了基因治疗在美国的发展——这些经历让他能够跳出单纯的科学家视角去思考技术创新和产业应用。在一些行业会议上,他更喜欢和患者及其家属在一起,去观察小患者腿部的肌肉功能,问他们病情的发展状况和临床指征等,这些调研中的发现经常成为指导研发部门技术改进的要点。
作为一家生物技术公司的董事长而非实验室中的科学家,肖啸更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在商业化和临床应用的目标下,去推动研发创新;研究管线的选择也是如此。
“这也是纯粹的实验室研究和药品研发不同的地方,前者可以去尝试任何奇思妙想,但公司研发要控制风险,要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围绕一些管线集中推进。”肖啸说。信念医药将血友病列为首个研发管线,就是经过多方面市场调研做出的决定。首先血友病属于单基因病,“靶点”明确;另外中国差不多十几万患者,很少进行预防用药,基本上是出血后的应急用药,而目前血友病的相关用药已经进入了医保目录。“在当前中国的大环境下,血友病A和B是商业化可能性较大的两种罕见病。”
当然,也就无可避免地要应对“硬币”的另一面:这个领域的竞争尤其激烈。就在6月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刚刚受理了又一种B型血友病基因药物临床试验,而国内目前已有十来家研发血友病药物的基因治疗公司。
“竞争总会有,但信念医药在很多方面都保持了先发优势。”肖啸说。据公司介绍,作为国内首个获批进入注册临床试验的血友病AAV基因治疗药物,BBM-H901注射液技术创新性、安全性以及有效性甚至比国外产品还要好,临床试验开展的比国内同行要更早,临床数据已发表在国际杂志《柳叶刀·血液学》上,同时按照国际质量标准建设的生产基地即将在第三季度投入使用——这也是其他通过外包生产的公司短时间内难以比拟的优势。
同时,这些围绕血友病药品研发生产所进行的探索成果,可以进一步复用在更多药品管线的拓展中。目前信念医药在神经退行性疾病、关节炎、癌症、代谢疾病、眼科疾病、骨骼肌病、遗传性肌肉疾病、溶酶体贮积症等多个治疗领域都进行了研究布局,多个项目进入CDE新药临床试验申请(IND)和临床验证阶段。
“先用5~6年的时间把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创新在中国落地,上临床拿批件,然后再通过国产化降低成本。”郑静表示这也是信念医药早就确立好的“两步走”计划。
 郑静。来源:受访者
郑静。来源:受访者只不过,原本步步推进的构想,被突如其来的疫情一下子打乱了。

“被逼”长大
信念医药不得不做出调整。
过去的几年,由于基因治疗的全面创新性,国内市场缺乏成熟的供应链体系,所以很多国内创新药企都选择与全球大型供应商合作,相应的,也要承担在各个方面都受制于人的代价。这一方面导致了企业研发成本的居高难下:同样的东西国外只要10万美元,国内进口就要20万甚至30万美元;更重要的是货期难以保证,在美国下单,订货一周内就到了,但在中国,周期则会被拉长到几个月甚至半年。
实际上一开始,信念医药就确立了国产化的目标,但相对于眼下更紧迫的管线研发来说,国产化只能退居其次。不过,疫情的盘旋不去让形势陡然严峻起来,“如果一下子断供,对中国医药企业来说就是硬着陆。”郑静说当时公司就意识到“不能等,也不能靠”。
只能行动。疫情暴发后的这三年,在新药研发推进之外,信念医药最大的创新就是“国产化转换”,这涉及到整个药物研发生产中280多个关键工艺环节的设备、试剂、耗材。如今,其中3/4已经完成国产化替代,其余的1/4由于药物进入临床试验无法中途更改,但国产替代方案已经就绪——以应对可能发生的极端情况。这些调整一方面缓解了公司的全球供应链危机,同时更打破了国际供应商的长期价格垄断,推动了国内供应链上下游的能力共建,降低未来病人的用药成本。
“之前想的是管线研发和国产化分步走,现在‘两条腿’同时走,本来计划8~10年实现的战略目标,在这4年内同步实现了。”郑静自己都觉得难以置信,“回头来看,疫情对公司影响或许有好有坏,但我们尽可能地把危机中‘机’的效应放大。”
过去,“信念人”常自嘲“创业四年,抗疫三载”,但当创业的磕磕绊绊和疫情的反反复复交叠在一起,像密集的雨点一样击打下来的时候,他们才发现组织的韧性超出所有人的想象。而在这个过程中,肖啸担心过,却从未感到焦虑,归根到底,还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只要技术和临床数据过硬,就肯定能做起来”。
在郑静看来,肖啸有着那种“winner”(赢者)的心态,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的格局和视野,也决定了公司的未来发展。在创办信念医药之前,肖啸卖出过很多专利,创立并转让过公司,历经太多的事情,这些经历使他能聚焦到最主要的问题上,而对其他的都淡然处之。回顾过去的几年,肖啸坦言除了早期融资的时候有点紧张,“睡得不太好”之外,没有感觉到特别难的事情,更多的情况,都是在压力下解决问题,“被逼”去做转型。
就这样,信念医药“被逼”国产化,“被逼”建设生产线,“被逼”从一家生物技术公司成长为一家生物制药公司,“我们从源头发现开始,做到动物实验、临床验证性实验和注册,再做到一期临床、二期临床和三期临床,然后商业化生产上市,现在整个过程快走通了,发现自主平台和自建团队确实很重要。”就像肖啸说的,这些“投入”为信念医药筑起了愈加牢固的竞争壁垒。

创新,也克制
伴随着生物技术向生物制药的公司转型,信念医药的业务版图从研发到注册,再到商业化生产,组织的体量也迅速膨胀。四年间,团队从几个人扩容到300多人,到今年年底甚至会超过500人。
但本质上,这还是一家初创企业。
这一点郑静深有感触,在她看来,一家生物技术公司每个发展阶段都是从0到1的搭建,从最早的研发体系,到之后的药物生产,再到后面的临床实验以及商业化——每个阶段都需要从零开始的创新和突破。
这也就意味着,生物技术公司要始终保持组织活性,“要快速决策,要对大环境和不确定性作出快速应答以及灵活创新”,郑静说,这也是创新药企在大型跨国企业的规模和资本优势碾压下生存下来的唯一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