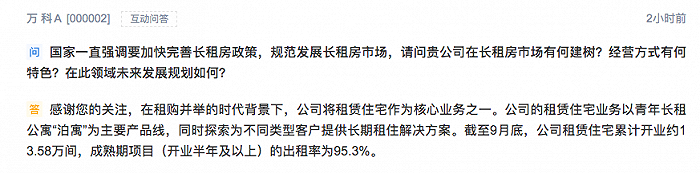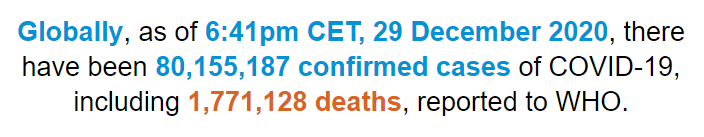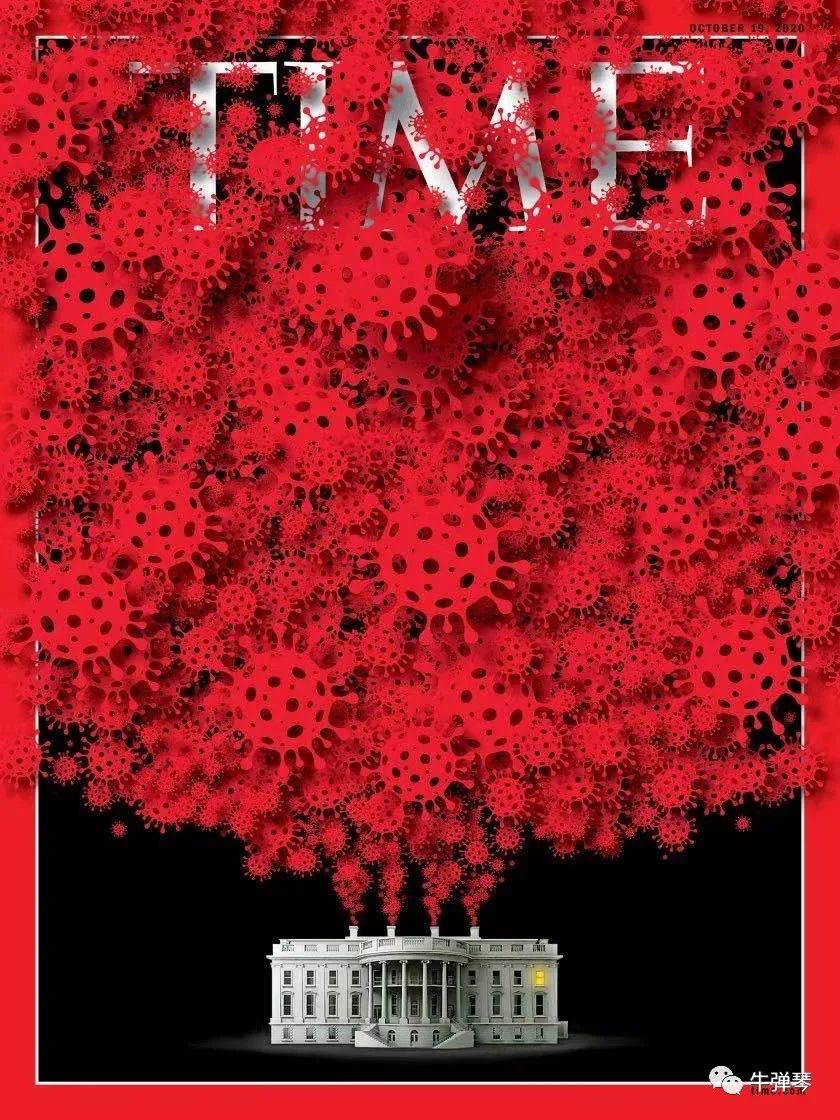两性的结合是物种克服不良基因配对的自然方式,而线粒体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两性的结合是物种克服不良基因配对的自然方式,而线粒体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新浪科技讯 北京时间12月30日消息,在任何一位生物学家看来,“性”可能都是一种浪费。这种行为十分昂贵:想想雄性孔雀为了吸引雌性与之交配,需要耗费多少能量,才能发育出如此壮观的尾羽。另一方面,有性繁殖的效率似乎很低,因为只允许我们将一半的基因传递给后代,而且物种中有一半的成员(雄性)不能生育后代。演化是无关感情的,因此这些代价必然意味着某种好处。通常的答案是,有性繁殖通过每一代的基因重组创造了新的基因组合,将有益突变与有害突变分离开来,并赋予物种一定程度的演化灵活性。“性”使基因保存在基因库中,这些基因今天可能没用,但未来可能就会拯救后代,使其免受瘟疫、瘟疫和寄生虫的侵袭。
这种论点可能是对的,但存在一个缺陷:有性生殖的好处往往是微妙的,需要繁殖几代之后才能显现出来,而它的代价却是沉重和直接的。为了完全理解“性”,我们需要一个解释,而这个解释可以追溯到早期复杂生物所生活的“原始汤”,以及它们所面临的即时生存压力。2019年,澳大利亚演化生物学家达米安·道林与同事贾斯汀·哈维尔德和马修·霍尔在《生物短评》(BioEssays)杂志上提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观点。他们基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单细胞细菌和古菌(都是原核生物)从不有性繁殖。它们有一些类似性的行为,包括通过身体接触来交换基因——有时被称为“细菌性行为”——但它们不会有性繁殖,而是通过分裂成两半来实现增殖。
性是更复杂的真核生物的特权。从变形虫到犰狳再到人类,在繁殖时都是通过减数分裂,形成染色体减半的配子(如精子和卵子),然后再结合形成一个新的生物体。红藻是化石记录中保存完好的最早的真核生物,可以追溯到12亿年前,也是已知最早的有性生殖的例子,化石中配子的存在证明了这一点。真核生物的典型特征是具有高度结构化的细胞,不仅含有细胞核,还包含细胞器——尤其是线粒体,这种奇妙的“生物电池”能为细胞提供赖以生存的能量。达米安·道林在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领导了一个研究小组,他说:“我们的论点很简单:真核生物都具有两个特征——线粒体和性——我们相信这其中存在某种被忽视的联系。”
这种联系的背后,是线粒体不仅仅是“细胞电池”这一事实。数十亿年前,线粒体实际上是独立的有机体。可以说,它们是人体不完全是“人”的一个例子。我们的肠道里充满了数万亿外来的细菌细胞;我们的DNA充斥着古老病毒的片段;甚至我们的细胞都可以认为是一团“原始汤”。科学家越来越认识到,许多疾病并不是外来的攻击,而是我们内部生态系统的失衡。以线粒体为例,这些细胞器包含自己特有且独立的DNA,可能会与细胞核DNA产生冲突。“直到不久前,科学界基本上都忽略了一个事实:我们每个细胞都有两个基因组,”达米安·道林说,“即我们自己的核基因组和线粒体基因组。”
线粒体基因组往往突变迅速,更容易与细胞核中的调节基因不同步,对生物体产生潜在的负面影响。道林认为,性的演化是细胞核与细胞内千变万化的基因突变保持同步的一种方式。他说:“产生能量的线粒体是早期真核生物的关键武器,它们以此建立的‘帝国’正处于危险之中,因为线粒体的突变太频繁了。”通过性,每一代真核生物都能构建新的基因型,并允许细胞核在出现问题时进行补偿。换言之,这是一种恢复平衡、修补内部分歧的方法。与性的其他好处不同的是,这一点对最早的真核生物和它们的后代都同样重要。
大约20亿年前,两种原核生物,或者说两种细菌在原始汤中游动,它们进行了一种可以被认为是“原始性行为”的活动。一个细菌入侵了另一个细菌,但二者都存活了下来,开启了新的故事篇章。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非凡的新生物体。这个入侵者——也就是被吃掉的那个细菌——在几百万年的时间里演化成了体积小但功能强大的线粒体,另一个细菌则可能演化成了更大的细胞核。
这种融合导致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共生现象。线粒体致力于产生能量,效率极高,以至于这个星球上的各个角落很快就出现了复杂生命的大爆发。但是,专门从事能量生产也有一定的代价:线粒体的氧化压力很高,会损害细胞器及其基因。因此,达米安·道林认为,线粒体DNA“注定会积累有害的突变”。快速突变似乎是自身具有DNA的细胞器的普遍问题,不仅会影响线粒体,有时还会影响叶绿体(植物中进行光合作用的细胞器,本身也曾是自由漂浮的细菌)。德国科隆马克斯·普朗克衰老生物学研究所的尼尔斯-戈兰·拉尔森最近的研究表明,线粒体复制在本质上就很容易出错(特化的生殖细胞除外)。
在今天各种各样的物种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线粒体的高突变率。在人体以及其他大多数动物体内,线粒体会不断分裂,而随着它们的分裂,其基因突变的速度比细胞核基因要快10到100倍。一个细胞不仅携带着数千个线粒体,而且每个线粒体都包含自身DNA的多个复本。因此,突变的绝对数量是非常惊人的。
 尽管线粒体基因组很小,但它对个体的生物化学和健康至关重要
尽管线粒体基因组很小,但它对个体的生物化学和健康至关重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大多数基因在经过数百万年的演化后,都脱离了线粒体,进入更为稳定的核基因组。今天的动物线粒体只有37个基因,全部用于产生能量。线粒体的大部分功能由核基因组中的1000多个基因调节并辅助。但是,放弃基因只能解决部分问题。当这37个基因衰退或改变时,细胞机器就会停止运转。除非调控线粒体的核基因能够适应这种变化,否则细胞就会生病甚至死亡。
2007年,达米安·道林和同事们研究了两组基因相互作用时会发生什么。在一项实验中,他们以四纹豆象(Callosobruchus maculatus)为研究对象,分为5个家系,培养23代。在一些家系中,线粒体和核基因组已经适应了协同工作。但当实验者在不同家系之间移植线粒体时,出现了精子活力下降的情况。道林和同事将这项研究扩展到了果蝇身上。他们培育了5个具有不同线粒体基因的果蝇家系,并研究了不同家系对核基因的影响。雌性果蝇几乎没有受到影响,只有7个核基因的活性发生了变化。但令人惊讶的是,雄性果蝇有1172个核基因受到影响,主要是在睾丸或精子腺。“当我看到这种效应对雄性的影响如此强烈时,我差点摔倒,”道林说,“这差不多占到雄性果蝇基因组的10%。”
雌性和雄性基因组的不同反应有一个自然的解释:线粒体纯粹是母亲的礼物。精子不会将线粒体传递下去;只有母亲的卵子才会携带这些细胞器。因此,携带有害线粒体突变的雌性往往会在繁殖之前死亡,将这些突变从基因库中清除出去。但是,如果这种突变伤害雄性而不伤害雌性,就会继续遗传下去。达米安·道林并不是唯一证明线粒体和细胞核之间存在深刻相互依赖关系的科学家。已有研究表明,这两个基因组的相互冲突会导致果蝇和海洋甲壳类动物的发育迟缓和生育力受损。
这两个基因组的不和谐也会影响人类。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的演化遗传学家丹·米什玛发现,线粒体和细胞核的冲突会导致具有某些遗传变异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增加患II型糖尿病的可能性。伦敦大学学院的神经科学家简·威廉·塔安曼表示,在阿拉伯-以色列裔和西班牙裔家庭中,单个线粒体突变就会导致遗传性耳聋。然而,在一些遗传了这种突变的人身上,核基因的突变反而能修复这一问题,可能是通过限制线粒体突变的影响,或者是直接进行补偿。在小鼠身上进行的实验也证实了这一点:新的核基因可以绕过线粒体的“失灵”,为耳蜗提供更多的能量,从而恢复听力。
科学家现在推测,一种遗传性的渐进性失明症(称为雷伯氏遗传性视神经萎缩症,简称LHON)的部分病因可能就是线粒体突变与核基因组之间的相互作用。长期以来,研究人员很困惑的一点是,这种形式的失明并不总是表现出同样的严重程度,甚至不是每个具有相同突变的人都会出现症状。例如,我国藏族人的线粒体DNA具有一种特殊的突变,似乎可以保护他们免受高海拔压力,从而防止这种失明;但在低海拔地区,人们可能更容易患这种病。这是怎么回事?是否可能与不同的核基因组背景有关?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的神经遗传学家瓦莱里奥·卡雷利对LHON的研究已经有20年,他说:“核基因组中有一系列很好的候选基因,它们可能会影响线粒体DNA,并解释这一现象。基因组测序越完整,我们对这个问题的了解就越透彻。”
“性”拯救了我们,这是一个物种从基因错配中恢复的最快方式。在有性生殖中,基因重组创造了适应各种变化——无论是来自外部还是内部——的新变种。“性是线粒体基因组和核基因组保持同步的唯一途径,”贾斯汀·哈维尔德说,“如果没有性,我们就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线粒体突变的积累会变快,而细胞核无法足够快地产生协同适应的突变。性通过相关的重组‘技巧’,允许真核生物从其基因组中获得更多的变异。”
除了重组基因,性还提供了一种新的演化方式。不健康的生物体不仅会因为环境压力而被淘汰,也会在争夺配偶时落于下风,这样的竞争也会出现在显微尺度下,那就是无数精子为了与卵子结合而展开的追逐。对线粒体来说,这种竞争也是一种考验,即使是最微小的不匹配也会导致淘汰。精细胞的中间部分充满了线粒体,为“赢家通吃”的阴道竞逐提供能量。“尽管线粒体基因组很小,但它对个体的生物化学和健康至关重要,”英格兰东安格利亚大学的生物学家马修·盖奇说,“以性选择方式进行的配偶选择和竞争,可以从两方面改善线粒体基因与核基因的匹配。首先是对雄性良好的线粒体功能进行选择;其次是选择出良好功能的精子,因为精子的受精能力严重依赖于良好的线粒体功能。”
为了检验马修·盖奇的理论,达米安·道林对不同物种进行了考察。从海藻到郁金香再到珊瑚,不同物种的线粒体突变率差别巨大。道林的理论预测是,线粒体突变率越高,该物种的成员需要交配的频率就越高。他认为有证据支持这一观点。几乎所有动物都具有很高的线粒体突变率,并且都需要有性繁殖,而植物在这两方面都更为温和。“许多陆生植物的线粒体突变率极低,事实上,很少有植物需要有性繁殖,”道林说,“它们几乎都可以在需要的时候进行有性繁殖,但也可以无性繁殖。”
 与性有关的突变:动物线粒体的突变率较高且需要有性繁殖,而植物很少需要有性繁殖,其线粒体突变率也较低
与性有关的突变:动物线粒体的突变率较高且需要有性繁殖,而植物很少需要有性繁殖,其线粒体突变率也较低其他研究者就不那么肯定了。伦敦大学学院的演化生物学家布拉姆·柯伊伯是道林新理论的支持者,但他希望看到更有说服力的证据。他说:“我们对各种生物体的线粒体突变率知之甚少。”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的生物学家大卫·罗伊·史密斯对此表示同意,他说:“尽管一般而言,动物的线粒体基因组突变比植物快得多,很快就会变得十分复杂。但最近的研究表明,对于单个植物,其线粒体基因组的突变率可以相差近三个数量级。”
布拉姆·柯伊伯希望对微孢子虫进行这方面的研究。这些微小的寄生虫属于真核生物(真菌界罗兹菌门),但在演化过程中失去了线粒体。“它们有性行为吗?”柯伊伯猜想,“如果有,会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与之相反的是蛭形轮虫,这是一种小型水生动物,具有线粒体,但不能有性繁殖。萨拉·奥托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理论生物学家,她的演化数学模型曾获得麦克阿瑟基金会奖。她担心这种轮虫会成为反驳道林新理论的特例,“有很多证据表明它们仍在进行无性的基因转移”。但她也表示,道林的观点可能是正确的,即有性生殖的演化是对不同生物形成共生关系,进而融合成真核生物这一过程的回应。她指出,由于被额外的膜包裹,“基因交换变得更罕见,以至于演化出有性生殖系统的优势变得足够强大,足以抵消其成本”。
这就强调了关于演化的一个更广泛的观点:生物之间的合作关系产生了变革的动力。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曾说:“伟大的生物学家林恩·马古利斯告诉我们,演化中的大多数重大飞跃都是来自于共生关系。”戴森涉猎了许多学科,并撰写了一部短篇杰作《生命的起源》(Origins of Life)。他解释道,当宿主被寄生生物入侵后,二者展开了缠斗,在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新的生命被意外地创造了出来。“宿主为共生体提供了生命支持,”戴森指出,“使共生体可以自由地演化,随机而迅速地获得或失去遗传能力。在极少数情况下,共生体会发明出新的结构,极大地改变宿主的生活方式。”
很显然,“性”非常符合“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这一要求。它带来了快感,也使孔雀长出了华丽的尾羽,并演变出了丰富多彩且异常精细的求偶仪式,而另一方面,它也具有破坏和修补生命的力量。有性生殖可能正是透过这种看似混乱的复杂性,避免了37个基因中的极小部分引起的更深层的混乱。(任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