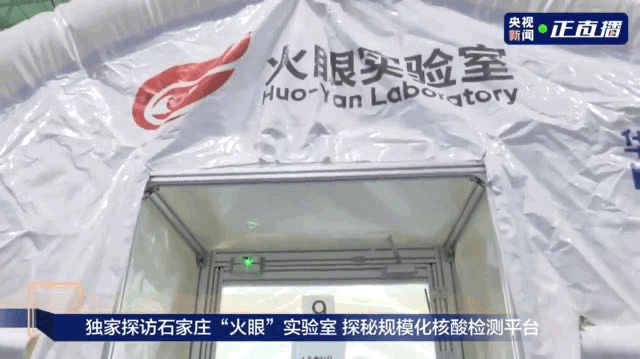原标题:六十一座“鬼城”之夜
最近一次从“鬼城”回来,“二打六”的成员黄海清对着工作室外发光的小鹿雕像,发了条朋友圈,“终于回到了人间,但又像极了梦里”。
2015年秋,由七名广东青年组成的“二打六”团队决定去睡“鬼城”。五年来,他们的足迹遍及中国三十多个城市的61座“鬼城”。
他们在鬼村落贴上红色门神,还在烂尾的别墅群泳池里放生了一条金鱼……空旷的“鬼城”生活和喧嚣的城市生活,哪种是实,哪种是虚,他们渐渐分不清楚。
百度搜索指数显示,从2013年开始,“鬼城”、“烂尾楼”逐渐成为公众关心的话题。超前规划的城市新区或资金链断裂的房产开发,可能造成大片的房屋空置或烂尾,他们被称为“鬼城”。
在“二打六”的展览中,一个来自“鬼城”的床单因为塑成了容器的形状,被观众投满了绿色的一元纸币。黄海清看到了,乐呵呵地说,这变成了一个聚宝盆。“二打六”不太在意别人的看法,创作是自由的,作品的意义也是自由的。对他们而言,睡“鬼城”这件事是用一个好玩的方式,记录下时代的变化。至于作品本身,开放给所有人言说。
【以下为“二打六”成员的口述】
侵入“鬼城”
第一次睡“鬼城”,我们特别兴奋。
当时是2015年的秋天,我们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喝着茶,吹水,聊天,过着神仙一样的生活。忽然间身边很多人要买房、结婚了,他们焦虑,我们也被影响,慢慢聊起了类似的话题。无意中有人说,最近不是有很多空城、“鬼城”、烂尾楼吗?我们天天在工作室里喝茶,去“鬼城”里喝茶不也很有意思吗?当时大家都三十岁左右,没有家庭压力,也没有买房的概念,在广州伍仙桥的工作室里自由自在,就是想着要做一些好玩的事情。
做作品是头脑和运气的结合。我们做了好几个月的功课,估算“鬼城”在哪,应该怎么做作品,但真的开车上路了,就不知道会碰见什么了。
第一个“鬼城”是在路上偶遇的,那是和化工厂隔了一条高速的村子。我们绕着村子走了一整圈,在里面几乎碰不到什么人。两个老人和几个骑摩托车的人经过我们,看了一下就走了。
我们就找地方搭帐篷、烧水、喝茶,然后坐着聊天。被一圈空房子围着做这样的事,有点古怪的错位感。
“鬼城”的夜晚很黑,周围的房子都不开灯,只剩下黑漆漆一片,有种可怕的安静,除了你自己,只能听到鸟叫虫叫,还有水声。
“鬼城”原本被造出来等着人居住,但植物替代了人侵入其中,我们在其中睡觉,就像在侵入一个不属于人的城市,总处于提心吊胆的状态。
在一个新开发区,我们这群入侵者就被盯上了。那里基础设施都很完善,公路也很辽阔,但看不到几辆车。到了晚上,所有的房间都没有灯光。
我们想尽可能感受这个城市,就没有固定一个点来睡觉,而是每天都转移一个地方,但当我们在空荡荡的大街上行走时,背后似乎总有一个目光——我们可能被一个当地人或者保安盯上了,这个目光提醒着我们,我们是这个城里的异数。 “二打六”团队
“二打六”团队这种远观的感受是我们想保持的。我们基本不会睡在“鬼城”的房子里,都在外面选一块地,搭帐篷睡觉——人如果睡在房子里,那就成了这里的居民。虽然在露天睡觉经常会遇到下雨或者下雪的天气,有时帐篷都渗水了,但我们还是比较坚持待在野外。
为什么一个本该住人的地方,人却显得格格不入?当人把视线投向“鬼城”,问题才会浮现。我们做过一个直播的作品,想让观众也参与到其中。当时我们在一个“鬼城”里安装了几个摄像头,另一端的显示器放在南京艺术展的展厅里。我们没有一个人在展览现场,全都在“鬼城”生活,吃饭,喝茶,睡觉,观众通过显示器,也会看到我们在“鬼城”的生活。
2016年,我们在艺术馆的空间里做了一个展览,把“鬼城”里面收集回来的砖在展厅砌成了一堵墙,它连接一个落地玻璃窗,中间空出了一块砖没有砌。趴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里面展览的电视在播出我们睡古城的场景。也是打破一堵墙,看到“鬼城”的含义。这是比较好玩的。
“鬼城”的人
在“鬼城”里,我们会海阔天空乱想,经常思考的一个概念是“居住”。谁会“住”在“鬼城”?
所谓的“鬼城”,其实就是没有人了。偶尔在“鬼城”里会碰到一些人,有的是周围来玩的居民,穿进来穿出去,想看看这里是什么样子;有的是想装修的业主,他们会坚持来几次,但大多因为没有水电而作罢;还有的“鬼城”是拆迁拆了一半的,丢下破落的墙体,所有人都走了,几年过去还是原来的样子。很少有人真正居住在这里。
有个地产项目原来是很豪华的别墅区,但后来因为开发商资金出现问题,就变成了一个烂尾楼。现在还住着一些老人家,他们在里面种菜、生活,但大部分的房子都是空的。虽然这是别墅区,但很多人可能是中产,用了半生的积蓄想要买个房子,遇到这样的事,钱就打了水漂。很多“鬼城”背后都有类似的故事,在有的烂尾楼里还能看到之前售楼部里的楼盘模型,那些模型都被砸坏了,可能也是发生了类似的矛盾。后来我们做了一个《养金鱼》的作品,就想思考这个问题。
当时我们尝试把一条金鱼转移到“鬼城”。城市的马路上有很多垃圾桶,我们在一个又一个垃圾桶里翻来翻去,找各种容器,矿泉水瓶、塑料袋、快餐盒……金鱼和水在这些容器里被倒来倒去,最后被转移到了一个“鬼城”里。那个“鬼城”是一个荒废的别墅区,里面有像游泳池一样的地方,蓄满了雨水,最后多了一条金鱼。
这条金鱼其实就像我们一样。我们从乡下到镇里读书,然后到一个地方工作、结婚、生子,地方换来换去,人折腾来折腾去,就这样过了一辈子,老了,也就回到了大自然。后来我们回去找过这条金鱼,它不见了。 行为艺术:养金鱼 二打六供图
行为艺术:养金鱼 二打六供图“鬼城”里没有人,当然也没有鬼。有一个所谓的“中国第一大鬼村落”,网上传得很玄。那个村子特别偏,山路十八弯的感觉,我们开车到了山顶,还要走四个小时才能下到山脚下。去到的时候已经是夜晚,村子里的建筑是明清时的式样,还有一个太师椅立在里面,有种灵异的氛围。
但其实鬼村里也没有鬼,村民慢慢搬出来以后,它自然而然就空了。去之前,我们就谋划好了要做一个贴门神的作品。门神是一个保家护宅的神,我们希望通过贴门神的方式给“鬼城”带来喜气,让它变得像有人守护,以后也能慢慢起变化。
事实上,真正在“鬼城”住过的,一个是农民工,还有就是各种昆虫。
“鬼城”里会碰到很多物件,鞋子、毛巾、小灵通,以前的墨镜,还有布娃娃,这些可能是农民工用过的一些物件。他们曾在这里建了好几年的房子,还带了老婆孩子来到这边,最后也不能留下来,人走了,只留下很多生活的痕迹。我们把他们的衣服鞋子之类的捡回来,给这些物件覆盖上水泥或者胶水,用雕塑的形式把它们再呈现出来。
在我们心里,这些农民工,或者为整个城市付出过血汗的人,是真正垒起城市的人。所以我们把这些物件变成一个纪念碑,做成一个系列叫《来自鬼城的礼物》。 “来自鬼城的礼物”物件除了建造它们的人,只有野生动物居住在这里。蜜蜂会在废弃的房子里筑巢,还有很多蚂蚁在里面生活。我们把这些虎头蜂、蚂蚁之类的昆虫也搜集回来,做成《来自鬼城的礼物》中的另一部分。也许它们才是“鬼城”的原住民。
“来自鬼城的礼物”物件除了建造它们的人,只有野生动物居住在这里。蜜蜂会在废弃的房子里筑巢,还有很多蚂蚁在里面生活。我们把这些虎头蜂、蚂蚁之类的昆虫也搜集回来,做成《来自鬼城的礼物》中的另一部分。也许它们才是“鬼城”的原住民。 “来自“鬼城”的礼物”农民工衣物
“来自“鬼城”的礼物”农民工衣物被建造的和被浪费的
“鬼城”的出现和城市快速发展息息相关。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里,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很多人从农村来到城市,城市的人口和需求激增,导致资源不断紧缺——但我们觉得很奇怪,如果说资源紧缺,为什么周围有那么多的浪费?城市在不停地变,人的需要也在不停地变,导致了很多新的焦虑,这些飞速变化的东西,我们想把它变成印记留下来。
在亚运之前,广州的城市环境不太好。我们的成员海清因为学的城市规划,去过很多楼盘的工地,当时管理没有那么好,漫天都是粉尘。秋冬季节特别干燥,出去走一圈回来鼻子里面都是黑的,人会特别难受。亚运之后环境好了很多,现在工地里所有车辆、工人,都必须清洗干净才能上路。但是当时的景象留在了我们记忆里。
后来我们想做一个作品来还原当时的城市,还有农民工建造房子的过程。我们想到原来用“鬼城”的砖砌过一堵墙,如果我们反过来,把一块来自“鬼城”的砖粉碎,再把灰尘收集起来,重新凝固一块,不就是城市的房子和道路拆了又建、建了又拆的凝缩吗?
于是我们在北京的美术馆里搭建了一个透明的玻璃房子,在里面做了一个行为艺术。我们五个人拿着一块在“鬼城”捡的砖,用切割机之类的工具把它粉碎了。粉碎的时候,整个空间都充满了灰尘,嘴里、鼻腔里都是。即使只隔着两个拳头的距离,我们都看不见彼此。等到尘埃落定,我们再把这些灰尘扫在一起,用凝合剂重新凝固了这块砖。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想模拟农民工建造城市时身处的环境,同时也通过重新雕塑,给这块来自“鬼城”的砖另一种生命。 行为艺术:来自“鬼城”的一块砖 二打六供图
行为艺术:来自“鬼城”的一块砖 二打六供图2016年我们一边继续着“鬼城”作品,一边把工作室搬到一个比较郊区的地方。那时共享单车正是爆发的时候,很多单车都被丢弃在了郊区周围。小黄、小蓝、小绿,乱七八糟的颜色躺了一地,还有的被丢到了河里。这些共享单车和“鬼城”一样,因为时代需要突然迸发出来,但实际的需求没有这么多,资源没有分配到真正需要的人身上,最后都成了一种浪费。
这些共享单车静静地躺在草地上、水泥地上,就像是死去的躯壳。后来我们找来一些裹尸袋,把它们裹好,运到了美术馆里展览。 裹好的共享单车 二打六供图
裹好的共享单车 二打六供图流动中的情感
“二打六”原来有七个人:刘奎纬、潘学城、林超文、陈艺儿、黄海清、黄秋霞、苇风。大家基本都从广东工业大学的美术学院毕业,是师兄妹、师兄弟的关系。10年前后,我们都在伍仙桥那边有自己的工作室,独立地在做作品,平时互相串门,喝茶,聊天,慢慢地变得像家人一样。
2015年我们去苏州做了一个叫“落地开花”的展览,结合当地的特色来做艺术作品。这次经历对我们而言是一次转变。
去之前我们搜集了很多资料,文字里都告诉我们苏州的文化厚度,历史意涵有多深远。我们带着这些印象,满街想找一些相关的材料来做作品,不认路,只好在公交车上问人,那些老人家听到了,不但给我们指路,还带着我们穿街过巷地找东西。这其实是很小的一件事,但在陌生的城市里,忽然遇到了这么热情的当地人,就觉得特别温暖。比起书里的文字,让我们印象更深刻的是那里的人。
这时我们发现,人对城市而言是这样重要。他们会受到城市氛围的影响,也会塑造一个城市的氛围。原来我们的创作是自我探索为主,这以后我们从对自身的关注延展出去,开始更关注社会和人的关系。
因为我们都是广东人,就想找一个粤语的词汇来做小组名字。“二打六”,在广东话里是跑龙套、香港影视剧里的“茄喱啡”(小角色)的意思,比较符合我们的心态。
在当时的广东艺术正统里,广东美术学院或华师的美术学院比较有话语权,但我们在广东工业大学,它的艺术学院成立时间很短,就不太被正统承认,像海清是广工美术学院的第一届学生。这种非正统艺术院校的出身也会导致我们的作品不太受人认可。
我们有点像城市发展里的小白鼠。小的时候很早就离开父母去了镇上读书,从农村到城市后,又眼见着它大拆大建。那时我们七零后的哥哥姐姐先出来城市,他们是第一批接触资源的人,此后就把资源握在手里了,他们的孩子也生活在物质条件比较好的时候。我们八零后虽然刚好处于改革开放三十年,但就像一个夹心层,一直在变动,一直在错过,有种边缘的心态。起“二打六”这个名字,就是想以自我嘲讽的方式来看待自己做的事情,虽然有些无厘头,但也是一种事实的反映。
突然涌现出来的城市和人是没有根的,这和“鬼城”的出现一脉相承。城市里的流动太快了,人的同情心、感情像是被磨掉了。原来我们在农村,对于“欺骗”没有概念,刚来城市时别人说什么都信。当时天桥上很多乞丐,他们抱着个小孩,在地上写自己没有饭吃,想讨个饭钱,我们自己还是学生,身上只有几十块,全都掏出来给他了。但是第二天过来一看,发现他还在那里做一样的事,那之后你就不再信任他和别的乞丐了。
这其实是一种病态的感受,对人的不信任变得正常了。老人在街上摔倒了你去扶他,反而害怕遭殃;在街上看到了流浪汉也不想再去帮他了;2016、17年的时候,我们搬迁工作室,新搬的工作室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屋子的框架,想着以后这就是我们长久住的地方,我们就手动搭工作室,搬了十几吨的木板,地板装修、水电装修都是我们自己来的,两年的时间几乎都搭进去了。但是后来房东说租金要上涨,原本合同里不涨租金的条款也没有用。我们学艺术的不会找律师,只好再次搬迁。
这件事暗合了我们睡“鬼城”的逻辑。工作室对我们而言,就是一个家。以前读书的时候,我们没有工作室,甚至会在学校的热水房里画画,同学都知道热水房里住了一个疯子。出来后我们就想着,有个地方能给我们画画,不用怕下雨天会淹了画册,回南天看着画作发霉,就好了。为了装修这个新工作室,我们整个身心都投入进去,但是到最后还是要离开。那时我们才知道,原来在伍仙桥的我们是一直生活在乌托邦的世界里,无忧无虑地过了十年,而这种生活是很容易被打乱的。
在种种变化中,很多东西都被消费掉了,不只是大拆大建过程中的物质损耗,还有很珍贵的感情。而我们几个人的相遇,就像是几个孤独的灵魂走到了一起,最后变成互相搀扶,彼此依赖。这些支持最后保证了我们自己的独立。大家一起睡“鬼城”,就是把信任的感受融入到了作品里。如果没有彼此,我们没有办法做这个作品。
其实做艺术的生活是很动荡的,经济来源无法保证,彼此也会遇到自己生活的规划。我们原来有七个人,后来因为工作室搬迁,有的人要结婚,要生小孩,在种种生活变故面前,就掉队了。陈艺儿最先因为家庭的原因离开,然后是秋霞和奎纬。
那时大家心理状态也非常矛盾,一方面觉得他们能找到自己的幸福,能离开也是一件好事,但自己心理上非常舍不得,也会想他们走了,“二打六”似乎就不完整了。但二打六也不是单纯的人的集合,它就像一个小社会,人来人往的,是对艺术的共同追求让我们扭结在一起,就算有人暂时离开,这种精神还在。
不会消失的“印记”
艺术这一行也没有想的那么高大上。对我们而言,选择它就是因为觉得做这个很快乐,做别的活也苦,做这个也苦,但是它让我们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一种自由的感受。
以前小的时候我们有人会很讨厌父亲,觉得他是一个权威的象征,你要我怎样,我就要怎样。但是越年长就越发现,自己的一个微笑、一个咳嗽,都和他一模一样,连样子也越来越像。祖祖辈辈要的东西似乎都是一样的,前人告诉他们要什么,他们就要什么,一代代都是循环。如果生活只能重复,那我过一天也就够了。
年轻的时候身边的讨论风气很热烈,就好像所有人都在问,我们是怎么来的,要怎么走?为了了解这个问题,超文在大学时候画过很多自画像,盯着它看,就是想知道这个人是干嘛的,太陌生了,完全不了解。我们画画,就是为了了解自己,是一种和自己相处的过程。
二打六成员黄海清自画像
这些自我探索还是在比较单纯的环境里的,出来后,我们逐渐想做点不一样的东西。创造是有压力的,比如绘画,你想到的东西可能都被画过了,但是行为不一样,真正用行为艺术的方式参与到社会事件里的人不多,我们就希望去做一下。
行为艺术是二战以后发展起来的一种艺术方式,博伊斯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从中国来说,许多人也是非常前辈的艺术家,他们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来实践行为艺术。
我们其实不能被归类为行为,更多的是一种行动作品。行为是固定一个点,夸张地做某件事,比如谢德庆,他就是固定一个点,一年内在固定的封闭空间中重复打卡,模仿城市人日常中的打卡行为。但是这个行为是不可能一直持续的。“二打六”不是固定在一个点,我们只是通过很长时间的重复做一件事——睡“鬼城”。这个事情可以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会说,要睡到世界上没有“鬼城”为止。 拓印“鬼城”墙体 二打六供图
拓印“鬼城”墙体 二打六供图 拓印墙体
拓印墙体比起我们的父辈,我们是更自由的,在面对世界时有更多的精神粮食,父辈没有那么多选择,他们要填温饱。但另一方面,这些更多的东西出现后,我们的压力更大了。过往每个人都有一个小房子,吃同样的东西,没有什么攀比,但是在现时代一百个人有一百种活法,人的差异忽然出现,就总会觉得有很大的落差。
它也变得太快,我们从农村来到城市,再回去的时候已经找不到童年的记忆了。我们小时候掏鸟蛋、抓蛇、弹波珠、拍公仔,这些痕迹都不见了。村子变成了一个躯壳,没有人,也没有精神,没有温度。所以我们给墙做拓印:不同年代建筑的房屋,墙体是不同的,90年代的墙很多都是一个个小瓷砖贴的,后来的墙就变成了水泥。那些小瓷片会随着时间,一块块地剥落,如果没有人住,这些墙缺少维护,更容易被侵蚀,小瓷片用手指轻轻一拨就掉下去了。水泥的墙体也会留下不同的印记。这些痕迹就是岁月。
下一步,我们计划做一个叫空心村的作品,记下村子的这段时空。
我们是这个时代脉络里出来的人,也一直在思考如何用艺术切入这个时代,提供一个理解的角度,留下一点印记,属于我们的,也是这个时代的印记。哪怕非常无厘头,只要我们心里觉得是好的,我们就满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