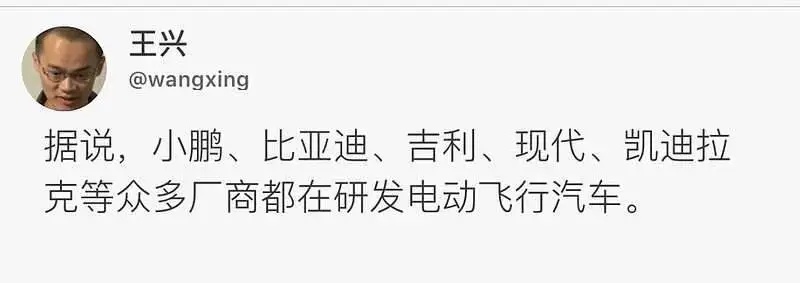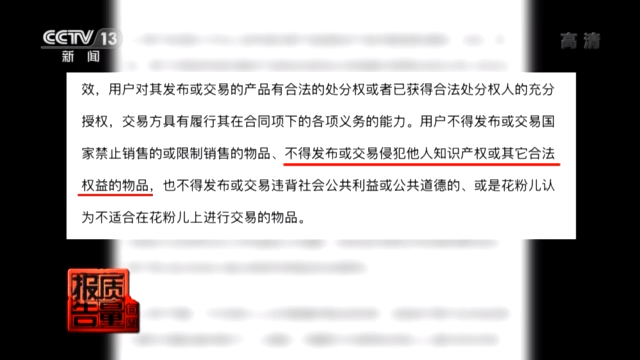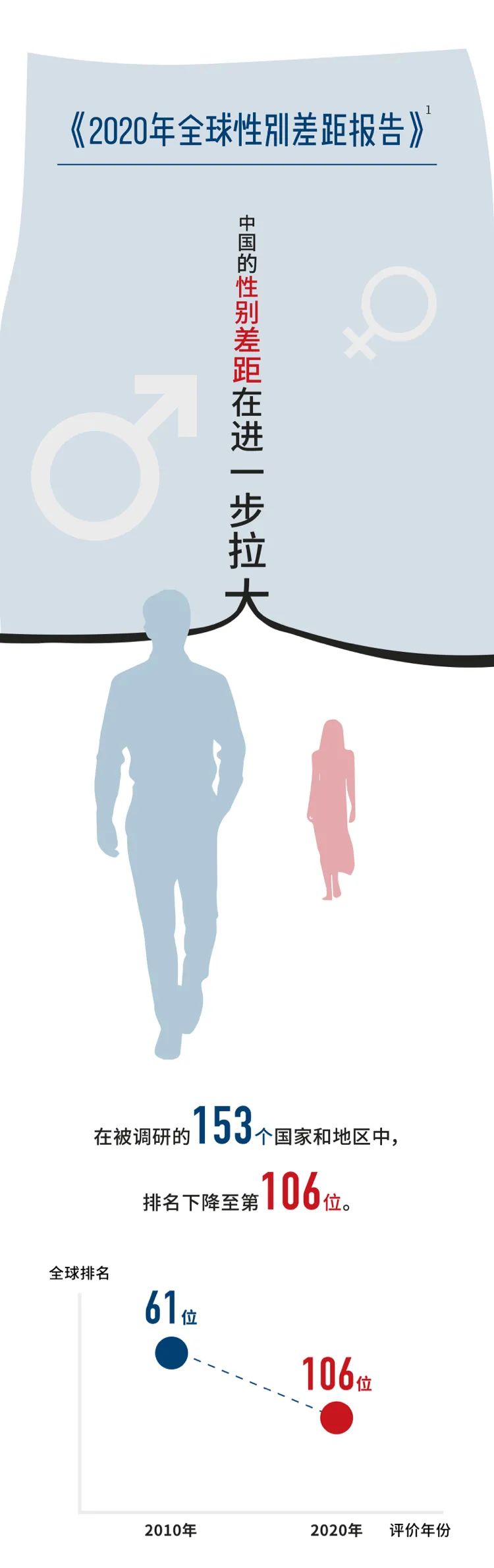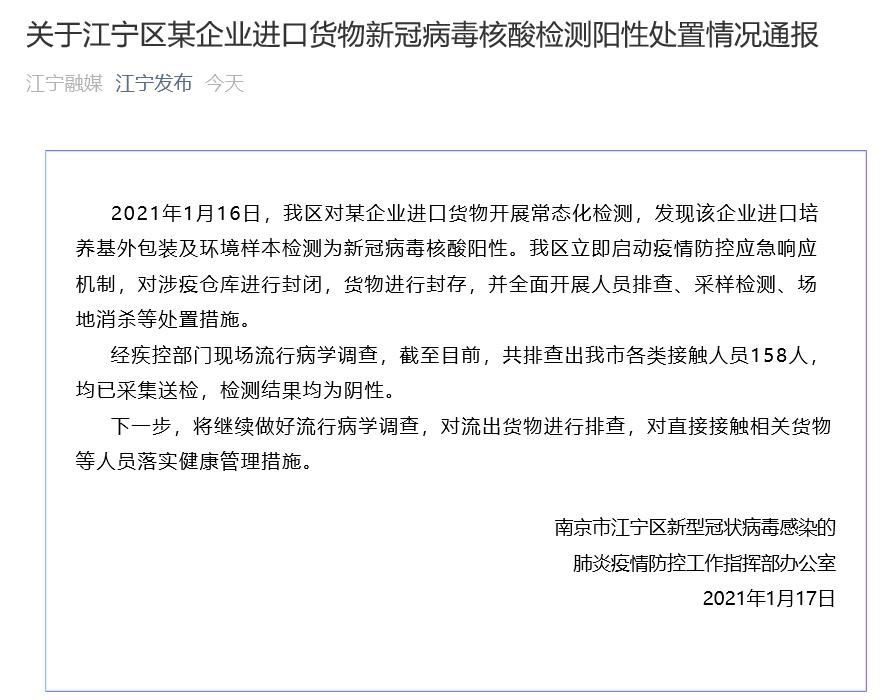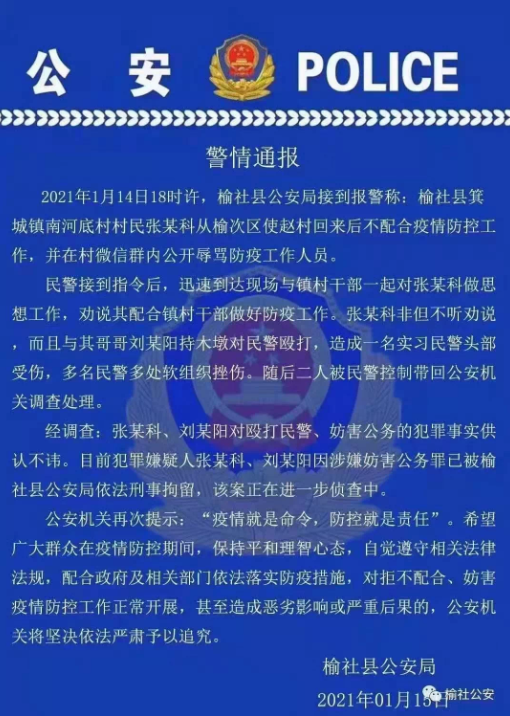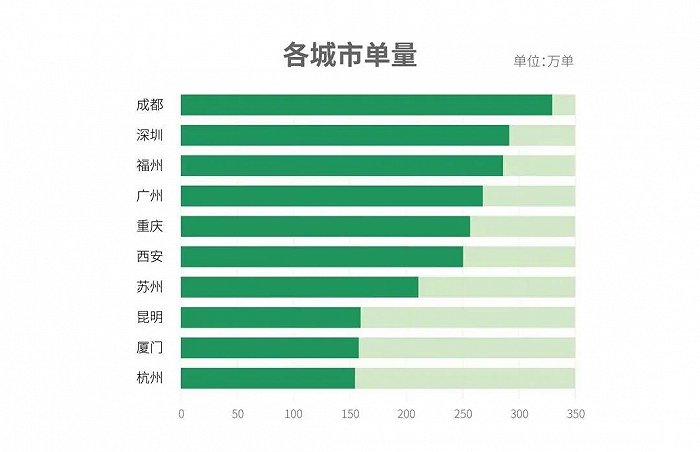原标题:贾宝兰:不一样的沈公
三联书店原总经理、《读书》杂志原主编沈昌文,于2021年1月10日清晨去世。几天以来,回忆与纪念文章很多,也有许多作者朋友询问,有的从国外发函表示悼念。
纪登奎的大公子纪坡民,得知沈公去世后,打电话去他家慰问;原国家环保局的牟广丰赋诗一首,还有著名艺术家高名潞从美国发来信函等等。这里把高名潞的信函摘录于此(注:信函由王明贤转来,他当时参与了现代艺术展的筹备工作):
“又一位知识界老先生作古了,感叹。当初找现代艺术展的主办单位,我到三联找沈昌文先生,很支持,所以,三联书店是在我给中国美术馆写的报告上第一个盖章的单位,他又让《读书》盖了章。从90年代就没有再见到过。存者且偷生,逝者常已矣。”
这个展览很著名,影响很大,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第一个现代艺术展,具有里程碑意义。这里,可以看出沈公的魄力与担当。
沈公88岁生日时,海豚出版社原社长俞晓群委托三联书店原副总编辑汪家明带话,让我写篇文章,腹稿已经打好,但是看了吴彬的文章方才知道,那是一群年轻人要写写沈公的糗事,我很意外。我写不出那个活灵活现的沈公,我人木讷,当初沈公的许多幽默与滑稽我并没有领悟。文章没有写,我不知道沈公如何想,但我的确不是故意。
逝者为大。在沈公去世当天我接受了《深圳特区报》记者的采访,也接受了《财经》杂志这篇约稿,让逝者安息。
虽然我们从人民出版社开始就是同事,但是真正接触沈公、在他手下工作是从1982年开始,到他1996年退休,时间长达14年。他留给我的印象很独特。
突出的印象是自嘲自讽,自贬自损。自喻为不良老人;自嘲自己就是小学毕业,除此之外,上过形形色色的补习学校,上海人称之为 “野鸡学堂”。辍学期间,在一家首饰店学徒,上海人称“小赤佬”。经常这样自嘲的一个人,1949年 3月考进人民出版社工作。从校对、领导秘书,到编辑、编辑室主任。1980年他到《读书》杂志,历任编务、副主编、主编。1986年任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1993年他不再担任总经理,一心主编《读书》至1996年。
沈公很勤奋。在人民出版社期间,他自学日语、俄语和英语,翻译出版了《书刊成本计算》《控诉法西斯》《列宁给全世界妇女的遗教》《阿多拉茨基选集》(部分)等多部俄语译作,退休后更是一发而不可收,先后出版了《阁楼人语》《书商的旧梦》《最后的晚餐》《八十溯往》《也无风雨也无晴》,还有他本人收藏的影印本通信集《师承集》。这些书籍,记录了他的人生轨迹和出版经历,我们可以从个人的历史中看出大的历史轨迹。
沈公担任《读书》主编期间,每期刊末的“编后絮语”(后结集为《阁楼人语》)是一道风景线,河南大学刘炳善称其“几十年来看过的杂志”,编后记“写得很有特色,是鲁迅,胡风,现在又加上你的大作”。
关于《读书》的办刊风格,是一直争论的问题。1994年第四期的“编辑室日志”题为《后饮酌·后学术·后刊物》,其中有这样一段关于编辑方针的话:
“后学术”大都产生于“后饮酌”,编成者则为一“后刊物”,即不合时尚之刊物。“后现代”废弃时尚,《读书》虽有一定方针,但不欲处处“随时俱进”,从这一点说,途径约略相似。三个“后”生拉硬扯地汇合在一起,吾人于《读书》之宗旨及运作,或可稍稍有会与心焉!然则,“后饮酌”可理解为“混吃混喝”;“后学术”不免被讥为“学术性”不足;至于“后刊物”,虽然“后”字不甚雅驯,但是并非自甘落后,也就算了。
《读书》不追时尚,不赶潮流,不人云亦云;所讨论问题,或为经过沉淀之后的思考,或者引领思想,除了创刊号上的《读书无禁区》,还有关于股份制的思考、关于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对话,都引领思想风气之先。
沈公向来提倡深入浅出,开门见山。文章不要开头就从盘古开天地讲起。于此,陈原也有这样一段话,废除空话、俗话、套话;不要穿靴戴帽等等。长此以往,《读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行文风格,有人称为《读书》体。《读书》的思想性,特殊的文体,为读者所喜闻乐见,使其发行量屡创新高,1996年,沈公退休时印数达13万之多。著名作家、评论家王蒙曰,“可以不读书,不可以不读《读书》”。
沈公喜欢吃,读书的编辑们经常与作者吃饭,上至高级饭店,下至脏兮兮的小饭馆,甚至他在办公室也用脏兮兮的锅,做出一锅美味的红豆沙汤、煲仔饭、罗宋汤等。他“拉拢”作者与下级的方式就是吃。他把“后饮酌”喻为“混吃混喝”。但他明确提到:文人、编辑之小酌,所重者应在“后饮酌”,而不在饮酌本身。“后饮酌”者,事后对席间传来信息之思考、整理、领会。更所要者,是席间的催稿、逼债。非如此,哪里能办成一个刊物?“编后絮语”和“编辑室日志”处处充斥着他的办刊思想、与作者的互动方式。靠吃来催稿、逼债屡试不败!
沈公在“后饮酌”时结下广泛的人脉,这包括作者、读者、朋友。他主编的“新世纪万有文库”和《万象》杂志,就是靠他的铁粉俞晓群和陆灏的支持,这使他退休后的生活更自在、更丰富。他的《八十溯往》与《八八沈公》都记载着俞晓群、陆浩等对沈公的爱戴。
沈公很有智慧——生活的智慧,政治的智慧。除了性格因素,他的个人生活经历,他亲历的历次运动,使他对问题与事情处理方式的把握游刃有余,我辈远远不及。《读书》创刊于1979年,上世纪80年代,人心思变,但是在变与不变之间,如何变,《读书》不可能不触及。从影印本《师承集》里我们可以感受到《读书》曾经历过的顺与不顺,但无论遇到什么问题,《读书》都波澜不惊地应对了下来。这里,胡乔木1983年7月29日的一个讲话起了关键的作用,他说,《读书》“编得不错,我也喜欢看”。
看《师承集》有些打不住了。匆忙成此文字,是为悼念前辈沈公。
(作者为《读书》杂志前执行主编,编辑:臧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