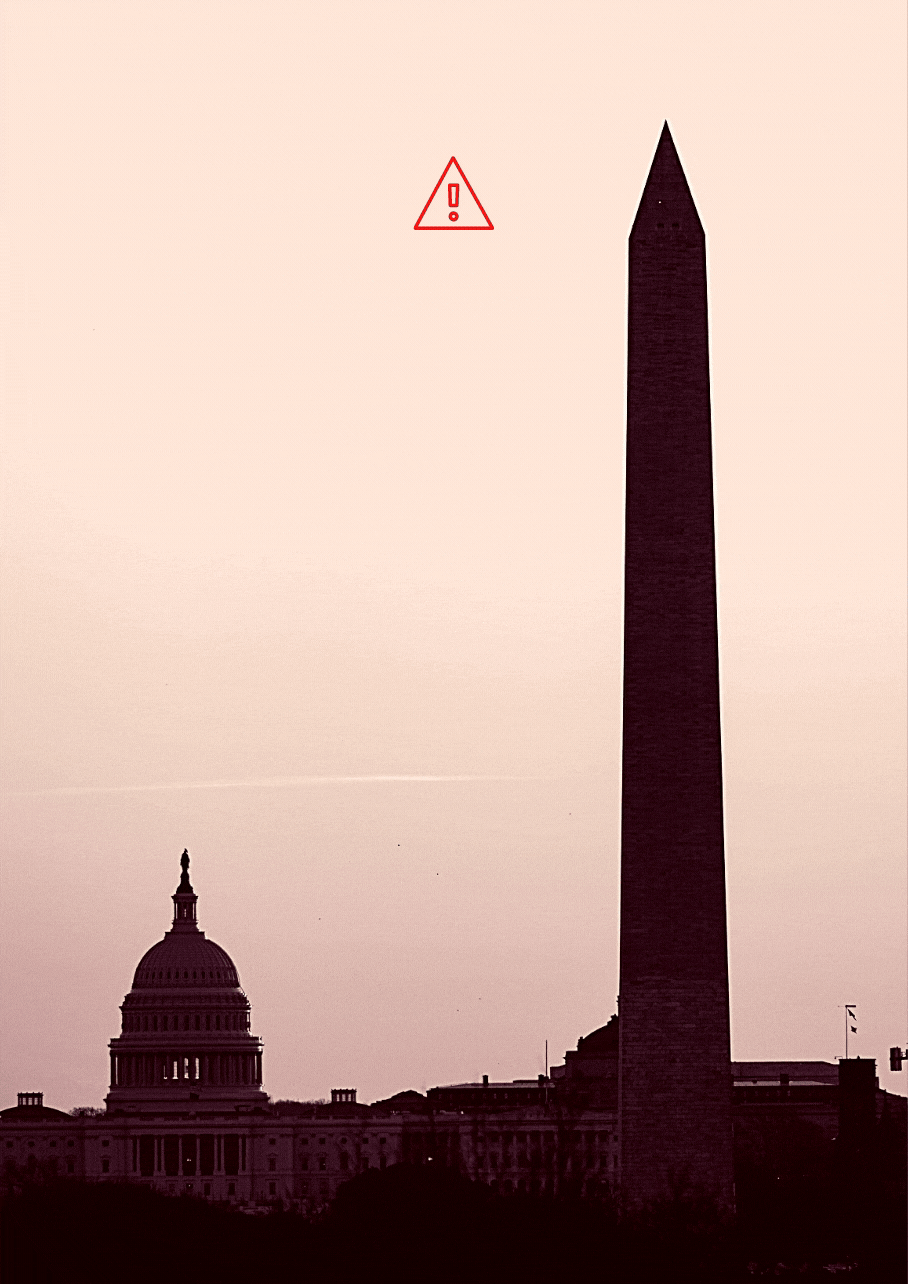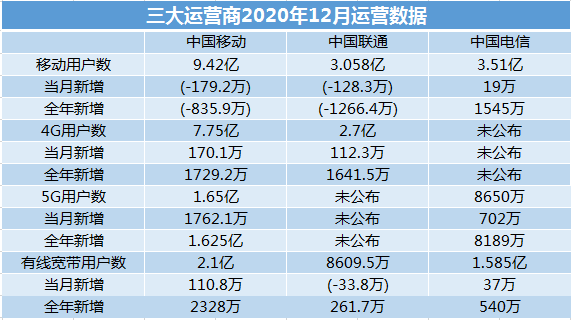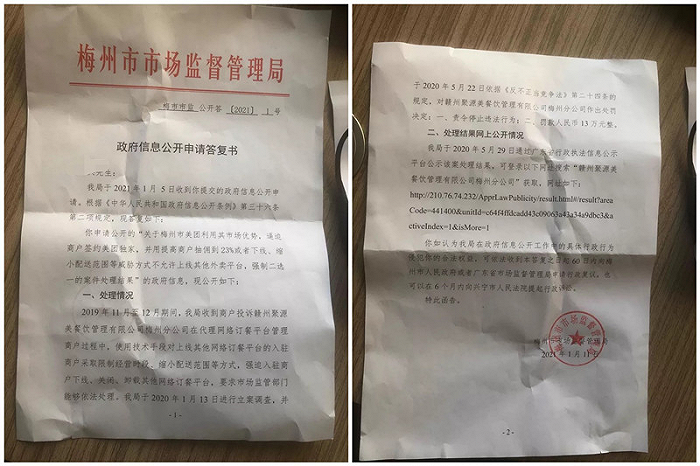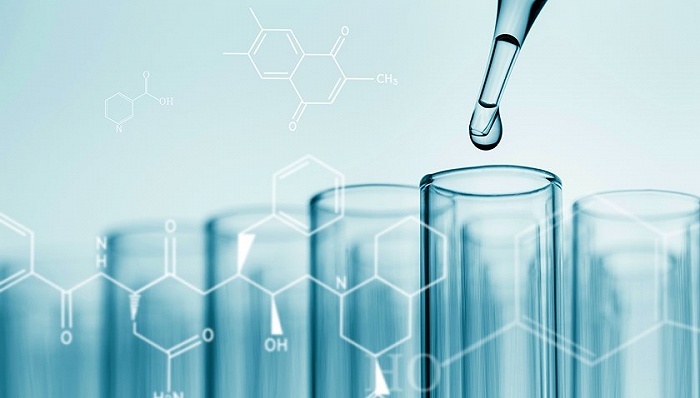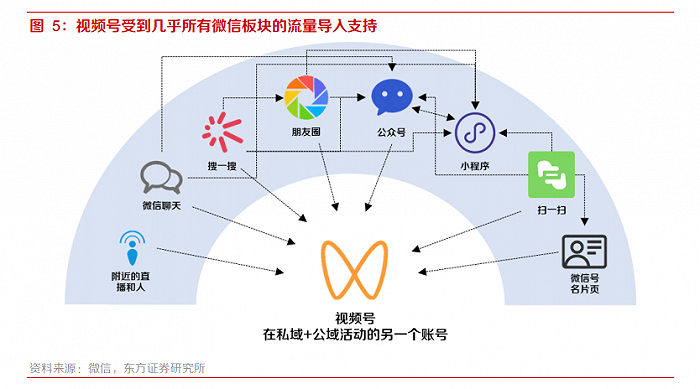原标题:许知远:流行不再让我脸红
原创 竺晶莹 虎嗅APP 虎嗅机动资讯组作品
虎嗅机动资讯组作品作者 | 竺晶莹
题图 | 受访者提供
我一直以为,许知远很出名。
在过去几个月中,我采访了他三次。
十月,阿那亚,单向街15周年,许知远作为主角,被众星捧月。
十二月,北京单向空间,他的办公室更像一个书房,被两面触到天花板的大书架包围,一眼扫去,有几部书脊上印着李鸿章、陈寅恪的名字。许知远的书架多被清末民初的中国近代史名人所“霸占”:“我在写梁启超,有很多资料要查。”桌上也摞着几叠书,外加一个银质托盘,上头错落有致地码着几瓶开过封的威士忌。
十一月,国贸,渣打银行对面的一间bar,爵士乐奏得热闹,许知远和老友叙旧。那天他喝得清淡,铜杯里是伏特加兑了姜汁啤酒和青柠汁的Moscow mule。谈话间,我总怀疑会有人认出他来,结果倒也并没有。看来他还不至于出名到被打扰的程度,又或许周围这些金融人不爱《十三邀》。
流行,从来都是有限度的。换个圈子,或许就是寂寂无名。许知远越来越不在意流行与否了。年轻时他或许带有偏见地认为流行与严肃对立。但他近来倒也不会再为流行而感到脸红,因为看到了将精英话语体系传递给大众的可能性。
掩埋虚荣
“我首先更接受,自己是个写作者。”
从出版《那些忧伤的年轻人》起,到今日将四季《十三邀》集结成册,许知远不变的是,一直将写作奉为第一要事,他目前在写《梁启超传》第二卷。
乔治·奥威尔在《我为何写作》一文中,归纳了驱动人们写作的四大原因——纯粹的自我主义(sheer egoism,也译作利己主义)、审美情趣、历史冲动、政治目的。 英国作家、记者乔治·奥威尔 / 图片来源:Google
英国作家、记者乔治·奥威尔 / 图片来源:Google强烈的自我是许多作家或记者动笔的最初冲动。奥威尔写道:(写作者)希望以机敏的形象示人,被谈论,被铭记……假装自我主义不是写作的动因,是虚伪的。他指出,多数人在三十岁以后就放弃了个人抱负,但写作者属于那些有天赋且任性地要将自我贯彻到底的少数人。
“严肃作家大致上比记者更加虚荣,更加以自我为中心,即使他们对于金钱更淡漠。” 奥威尔下此定论。
作家和记者,这两个身份许知远兼而有之,那他的虚荣也是双份的吗?在这个问题上,许知远够诚实,坦言年轻时虚荣在事业的推动中占比很大,但随着年龄增长,在忙碌中他似乎忘了虚荣的存在,也意识到有更广阔的事物比自我更重要。
“更年轻的时候,那种虚荣、冲动是很大的,(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现在自己明显更忙碌,所以更少想这个问题了。当然你不知道会不会ego仍然是很重要的,但它会减少一些。因为你确实不断意识到,这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比ego重要得多。甚至当你丢掉这个ego,可能是更美好的。但当然你很难丢掉,一些时候遗忘掉甚至掩埋掉、遮蔽掉它,很重要。”
许知远正在发生的转变是——你想追求的价值和事业应该比你的ego更重要,世界上确实有很多更高尚的目的,更强有力的志向,高于你的个人实现,而且你的个人时间应该为这个价值做某种贡献。
他不再那么强调自我,却将责任感挂在了嘴边。“为往圣继绝学”的理想正在许知远的行动中上演,尽管他表示这么说实在言重了。张载的寄望虽说是每一代中国读书人的梦想,但从当下的语境来看,确实略显宏大。但很显然,许知远认为有责任来传承精英文化体系。他表示自己受惠于过去名家的思想和情感,于是也有责任把这些思想、情感传承给下一代,不管以写作还是影像的方式来传递。
“我花了这么多心力写梁启超,这当然也是某种意义上被个人ego所驱动,因为你要写一本大书。但同时更重要的是,你觉得这套近代知识分子的传统是重要的。你应该为它的继续传承,添一点砖瓦或者加一点燃料,这也是你的责任。”
正视流行
许知远最初的理想是成为专栏作家,在这种自由度极高、个人化风格强烈的文体里挥斥方遒。北大毕业之初,他就在《经济观察报》专栏中讨论国际事务,之后亦是FT中文网多年的专栏作家。可惜“专栏”在中国的语境里夭折了。但许知远将《十三邀》看作视频专栏,那仍是他个人化的表达,尽管视频更偏向于包含导演摄像剪辑在内的集体创作。
《十三邀》的确让许知远更流行了。
采访五条人时,海鲜大排档的老板认出许知远来,谈论《十三邀》这个节目给他带来了新的价值和感受。“如果你的支言片语能够对别人有某种启发,这是很美好的事情,所以对我来说很温暖。” 若流行真给他带来什么“红利”的话,这是头一桩,因为这个节目真的影响到了不同圈层的人。 许知远与五条人对话 / 图片来源:《十三邀》
许知远与五条人对话 / 图片来源:《十三邀》不过,流行也意味着争议。《十三邀》首季甫一面世时,许知远曾被视为笨拙的提问者,且过于理想主义。他本人却离这些争议比较遥远,全因自己不生活在网络上,没有微博账号,甚至从来不看剪辑后的节目。许知远不在乎公众对于节目的评价,也无法控制评论,更无意迎合。
制作《十三邀》首要的目的是——“我们对个人好奇心的一种探索满足,然后理解一种更大的思想边界的冲动和欲望。” 尽管对节目的效果和反响,许知远并不在意,但他认为自己对交流本身有责任。“这个交流尽量要开阔、绵长、有更多的内容含量,我的交流本身要真诚。”
流行与严肃有时会被视为一种对立。《那些忧伤的年轻人》2006年再版的序中,许知远表示自己依然期待这本书卖得像周杰伦的唱片那么多,而不会有埃德蒙·威尔逊式的担心,这位批评家曾经觉得他的书——平装本销量太大,“大得足以使一个严肃的作家害臊”。
今天的许知远对销量和影响力没有那么大的渴求,流行对于他而言只是副产品。这种对于流行不褒不贬的态度或许是他变得更沉稳后的产物。
相比于流行,许知远更渴望建立起一个文化系统。“我们缺乏精英文化系统,这个系统基本上都瓦解了。我始终希望在一个相对有限的读者范围里写作,他们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系统。但是中国现在没有这样的一个系统,我们甚至在慢慢想去建立这样一个小小的文化系统。”
《十三邀》不失为建造这个文化系统的方式之一,尤其它经常游走在流行与严肃之间,让学院的观点有机会走向大众。比如项飙与许倬云这两期节目在去年受到了较多的关注。项飙作为人类学家,对当下科技社会提出了“附近的消失”等敏锐的观察。许倬云则多年来在海外潜心延续着中华文化的基因,让人看到温柔敦厚的风采。无疑,该节目在获得影响力后拓展了对话的边界。 许知远对话人类学家项飙,谈及当代时间感的扭曲 / 图片来源:《十三邀》
许知远对话人类学家项飙,谈及当代时间感的扭曲 / 图片来源:《十三邀》本着多样性的原则,《十三邀》的嘉宾跨越学术、文化、娱乐、商业界。有别于一般的访谈节目,这更像是许知远带着自己的观点和个性,在不同的时空中进入对话状态。他始终觉得,这个节目是他记者身份的延续。
“我依然觉得我就是个记者、采访者。记者是最好的职业,你可以进入不同体验,可以迅速地有一种特权,进入别人生活的特权。” 他认为,提问者对于这个社会非常关键,如果一个社会不对自身提出问题,这个社会就僵化了,堕落了。
在制作这档节目时,许知远的参照样本是BBC节目主持人Clive James,也是主持CNN《未知之旅》的Anthony Bourdain,前者身兼作家、诗人、学者数职,后者在全球寻味之旅中结合当地历史文化来诠释食物。时至今日,许知远仍被这些电视人所影响着,他统称大家为“探索者”。 波登和奥巴马在越南喝啤酒 / 图片来源:Google
波登和奥巴马在越南喝啤酒 / 图片来源:Google许知远前阵子在探索王宝强。《十三邀》的访谈时间在不断拉长,从最初的几小时到第五季制作时的两三天。因为人和人之间见面需要预热,通常在两小时后,真正的谈话才开始发生。许知远也重视空间对人的思想的塑造。他前往王宝强的故乡邢台,期待理解这位演员少年时的成长,以及为何要逃离那个空间。
甚至谈话已经不再是这个节目的唯一形式了,体验更为重要。为了寻找担任群演的感受,许知远真的去演戏了。早上四点钟起床,却已经到得晚了,然后一直在等待,因为群演很多时候就是在等待,他跟年轻的群演们聊天,对这个行业产生更多的理解。又好比他去采访赖声川时,体验了即兴戏剧,他称这种非头脑性的行为会帮助人理解很多东西。
“这种理解不是智力上的,而是一种感受型的。做这个节目可能让我感到最强的一种变化,就是我对感受型的越来越重视,很多东西不是你思想上理解就足够,你要在情感上,甚至在身体上理解一件事情,比如早起是一个身体反应,是巨大的疲倦。”
有时在节目中,会发现许知远跟相似行业的人聊得更尽兴,但他认为这种区别在于即时满足和延迟满足。同行业的人,由于受过相似训练,当那一刻有碰撞和共鸣时, 是多年彼此积累的碰撞。与不同行业的人对话,也许你只是最近去理解了这件事,没有很深的感受,但它会启发你,可能过段时间就变得更深入起来了。
《十三邀》也在往海外走。2020年12月20日,傅高义(Ezra Vogel)离世,许知远此前与这位研究东亚问题极深的美国学者已有过一次交谈,本计划再访,却成为了未竟的对话。同年12月12日,英国间谍小说家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辞世,这也是许知远想去拜访的作家,他好奇一个间谍大师的世界是什么样的,遗憾再无机会。
扮演商人
许知远一直在回避商人这个角色,但从他和朋友在2005年创立单向街开始,这个身份就避无可避了。
《十三邀》让许知远从文化圈进入了大众视野,尽管这种流行跟他的生活没有直接关系,但他认为,这给书店带来了变化,单向街作为一个品牌,获得了更好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书店不易做。尤其是疫情期间,单向街受到了重大冲击,他们推出预售会员卡,我身边有不少朋友购入。书店的业态很脆弱,困难时期没有现金流,十分令人焦虑。但这次预售给了单向街很大鼓舞,也让许知远意识到单向街足够有号召力。所以他更感有义务把这个品牌和空间持续下去。
他认为,很多人没有把单向当作一个单纯的书店,大家喜欢的是这样一种理念的存在,作为一个活跃的精神因子存在于这里。因此他甚为感激,也想要把它做得更有商业价值,但许知远仍感到训练商业能力是个很艰难的过程。
对于书店这个生态,他期待见到更多独特的书店可以让该行业更有魅力。然而这个愿望从商业角度来看略显天真,毕竟现今的书店更多只能靠贩卖文创或打造IP来勉力支撑。单向街算是其中幸运的了。
抛开商业逻辑不讲,许知远对于书店的寄望始终是漂亮的:“我们不喜欢书店作为一种悲情的存在或者作为一种防卫的姿态,我们希望它很自然、自由,但同时它是很自信的,对自己有拓展性。” 单向街在2020年15岁了。在他眼中,这将会是一件不朽的事。
他总是守护着一些传统,比如书店比如文字。事实上,《十三邀》的出版像是商业行为,将影像转变为文字,不是一种重复或冗余吗?许知远对此的回应是,节目经过剪辑丢失了一些内容,文字还原了更原本的对话。
或许他也觉得这个解释不够有说服力,便引用了艺术家徐冰的一段话:书真是人类最好的创造。一个由N层纸张形成的方形体积,当人们拿在手里翻动时奇迹就会出现……《十三邀》里这些散落在“空气”中的“思想”,如今被收纳在这个方形体积里,真像是一代人文化情感的寄托之物。
但延续不朽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在许知远身上表现为忙碌。他要写作、看书、主持节目、出席活动、接受访问……“我好像进入相对比较平静的时期了,但同时我不喜欢自己的状态,我觉得太忙碌了,过分忙碌,忙碌会使人单调,会使人匮乏,我在想以怎么样的方式来拒绝忙碌,而且忙碌会使人接受惯性。”
成为商人,意味着更大的责任,因为要考虑背后的整个团队。同时也喻示着巨大的身不由己。于是,许知远的手机屏幕时不时就亮了起来,总有新的信息不断涌入。
在“对话的精神”论坛中,许知远曾提及剑桥晚宴时的餐桌礼仪,至少要跟你周边的人热络对话,尽管有时是虚伪的。他为现今大家在餐桌上对着手机而感到遗憾,但他自己却也逐渐被手机捆绑。 单向街15周年在阿那亚举办的论坛 / 图片来源:单向街
单向街15周年在阿那亚举办的论坛 / 图片来源:单向街有次访谈前,许知远问我借充电宝,大概他理所当然地觉得一个年轻人应该离不了这些物品。但我愣了下,因为我从来没有这些东西,我甚至不会在谈话或吃饭时拿出手机。
反倒是许知远在这个科技时代变得越来越忙,在多重身份下,手机就像一个追踪器,随时可以追到他。屏幕又亮了,他边说不好意思边看了一眼,而不是选择将手机翻面不理会。终究是身份越多,自由越少。
如对本稿件有异议或投诉,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