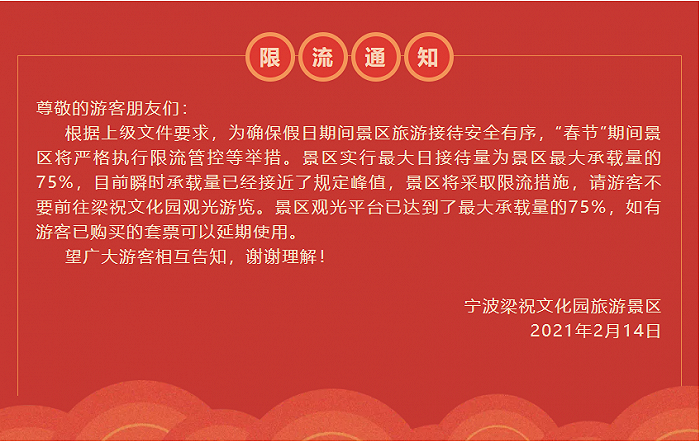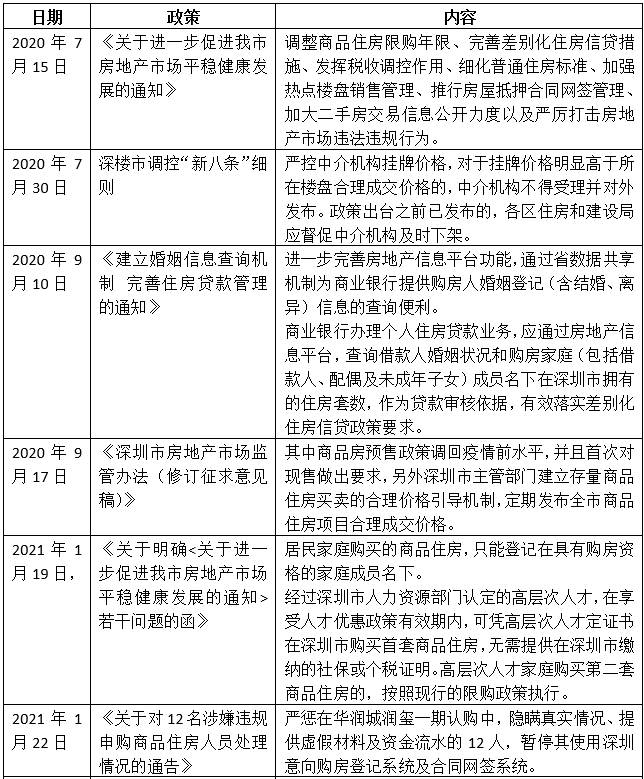原标题:反垄断维护的是公平竞争秩序,而非个别竞争者私利
近期,中国加强了对互联网行业的反垄断审查与监管力度。《反垄断法》正在面临新一轮的修改完善,相关执法机构也积极出台了《禁止垄断协议暂行规定》《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暂行规定》《经营者集中审查暂行规定》《经营者反垄断合规指南》等多部规章或指南,最近颁布的《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下称《反垄断指南》)更是引发各方关注。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相关部门将对互联网等新经济业态法律适用问题作出更加具体的、合理的和有针对性的规定,增强反垄断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和可预期性,为市场经营主体划定更加清晰的行为边界。
界定“相关市场”应综合考量
依照学界传统共识,评价某经营活动是否构成反垄断法需要加以规制的行为,通常需要首先界定被诉行为人是否在相关市场中具有支配地位。对于“相关市场”,现行《反垄断法》只是给出了其含义,即经营者在一定时期内就特定商品或者服务进行竞争的商品范围和地域范围,却并未给出明确的界定方法和标准。
传统的做法通常是采用“假定垄断者测试”,即思考一个商品市场上的假定垄断者是否可以通过小幅的、显著的和非暂时的涨价来获利。如果可以获利,则该市场将遭受反竞争损害,对此进行反垄断规制便是合适的;如果涨价导致消费者转向其他替代品或减少购入量,则该市场不是反垄断法意义上的相关市场。
但已有学者指出,这种静态、刻板的方法并不能完全套用于技术快速革新迭代、产品或服务类别高度混合的互联网领域。一个社交软件或内容分享APP,完全可以同时是电商平台或立刻转化为电商平台,故仅仅根据其主营业务来划分相关市场,或是评判原被告是否存在“竞争关系”的固有观念应当修正了。
同样地,以互联网为代表的高科技企业之间并非传统意义上商品价格的竞争。相反,常常是一家企业依靠技术的“网络效应”和“路径依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独占鳌头,接着又因出现了一种足以重新定义整个行业的崭新技术,而被另一家企业“大跨越”地取代。某家高科技企业在短期内占有较高的乃至绝对的市场份额,并不能就此得出这是个缺乏竞争的垄断局面之结论,只要对科技创新开放,那它就是高度竞争化的市场。
正因为如此,2021年2月7日公布的《反垄断指南》也明确指出:“平台经济业务类型复杂、竞争动态多变,界定平台经济领域相关商品市场和相关地域市场需要遵循《反垄断法》和《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相关市场界定的指南》所确定的一般原则,同时考虑平台经济的特点,结合个案进行具体分析。”
《反垄断指南》第四条“相关市场界定”中指出:“可以根据平台一边的商品界定相关商品市场;也可以根据平台所涉及的多边商品,分别界定多个相关商品市场,并考虑各相关商品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当该平台存在的跨平台网络效应能够给平台经营者施加足够的竞争约束时,可以根据该平台整体界定相关商品市场。”
由此可见,在网络平台经济领域界定“相关市场”是一件相当复杂而艰难的事,必须充分考虑互联网技术特征和商业模式,基于个案中涉及的多种因素审慎分析、综合考量。这一思路和方法同样适用于评判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中。虽然现行《反垄断法》规定,可以根据经营者在相关市场所占份额(比如一个经营者占50%以上的市场份额)推定其具有支配地位,但这种推定仅适用于特定情形,且是可以被相反证据推翻的。
恰恰由于互联网行业的复杂性,反垄断执法部门和法院才尝试使用一些更加灵活、综合的考量方法。如在著名的“3Q大战”案中,最高人民法院终审指出:“互联网环境下的竞争存在高度动态的特征,相关市场的边界远不如传统领域那样清晰,在此情况下,更不能高估市场份额的指示作用,而应更多地关注市场进入、经营者的市场行为、对竞争的影响等有助于判断市场支配地位的具体事实和证据。”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于2020年初公布的《<反垄断法>修改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中也明确提出,认定互联网领域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应当考虑网络效应、规模经济、锁定效应、掌握和处理相关数据的能力等因素,而不能仅仅依靠静态的市场份额指标。《反垄断指南》则更加扩充为“经营者的市场份额以及相关市场竞争状况”“经营者控制市场的能力”“经营者的财力和技术条件”“其他经营者对该经营者在交易上的依赖程度”“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的难易程度”等多重考量因素和认定视角。
“合理推定”原则评判是否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互联网领域的竞争态势给传统的反垄断执法观念和操作方式都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但有一点是不变的,即其最终的评判标准还是要回归和立足于反垄断法的制定宗旨——其维护的是整个公平竞争秩序,而不是个别竞争者的私利。优胜劣汰、此消彼长、借助正当手段损人(竞争对手)利己,本来就是市场常态。反垄断法旨在保障消费者及公共利益,促进社会整体福利,如果公益没有遭受损害,则没有反垄断法的适用空间。
有人提出,虽然某些互联网产品是私人投资、商业模式和技术创新的结果,但事实上已经成为国内某个领域的必需设施。的确,“必需设施”是反垄断法上一个历史悠久的理论,其是指当一个设施被认定为“必需”或“核心”后,设施的拥有者就负有在一定程度上以合理条件开放该设施供竞争对手使用的义务。但到底什么样的设施才应当被认定为是必需的或核心的,有无明确统一的判断标准,是反垄断法学术界和实践者一直争论不休的话题。
有研究者指出,界定“必需设施”与界定“相关市场”并无显著差别,其本质都是经济分析与后果主义考量,即评估独占某设施给潜在竞争者造成的进入市场障碍,是长期的还是暂时的,其严重性如何;强制要求开放该设施会多大程度抑制投资和创新,拒绝开放是否存在正当理由。
《反垄断指南》指明:“认定相关平台是否构成必需设施,一般需要综合考虑该平台占有数据情况、其他平台的可替代性、是否存在潜在可用平台、发展竞争性平台的可行性、交易相对人对该平台的依赖程度、开放平台对该平台经营者可能造成的影响等因素。”“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拒绝交易可能具有以下正当理由:(一)因不可抗力等客观原因无法进行交易;(二)因交易相对人原因,影响交易安全;(三)与交易相对人交易将使平台经营者利益发生不当减损;(四)交易相对人明确表示或者实际不遵守公平、合理、无歧视的平台规则;(五)能够证明行为具有正当性的其他理由。”
以排他交易为例,在早期的反垄断法观念和实践中,法院一开始对纵向排他交易采取了非常严苛的态度,比如在历史上著名的标准石油(Standard Oil)案(1911)和标准时尚(Standard Fashion)案(1922)中,美国法院采用了类似于“本身违法”原则来判定排他性交易的正当性,理由是排他性交易引起了下游零售市场的圈定,构成对现有竞争对手和潜在竞争对手的排挤。
但以博克(Bork)为代表的法经济学“芝加哥学派”对该司法见解提出了质疑,主张排他性交易是有效率的。在其经典论著《反垄断悖论》中,博克反问道:既然排他性交易限制了下游企业的经营自由,损害了其利益,那为什么他会同意签署该契约呢?——这被后人冠之以著名的“芝加哥纵向疑问”。
西方国家最开始也认为企业的优势(如市场份额较高)本就是件坏事,其必然排除或限制竞争,故应采取“本身违法”原则予以规制。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法经济学强有力的分析论证充分揭示了市场竞争的复杂性,反垄断执法机构和法院逐步放弃了起初机械片面的“本身违法”原则,转为宽严相济的观念与举措,如采纳了从社会经济发展现实考虑的豁免制度,确立了正当性评判的“合理推定”原则等等。
所谓“本身违法”原则,指只要行为或状态满足反垄断法描述的外在表现(如达到市场支配地位、构成实质性的市场圈定等)即受规制,无需考虑个案具体情况加以权衡。所谓“合理推定”原则,指不能仅凭行为或状态的外在表现予以认定,而应当根据个案具体情况,由执法部门或反垄断诉讼中的原告举证证明被诉行为存在排除、限制竞争,损害消费者等公共利益的后果。
在“合理推定”原则下,反垄断执法部门和法院更加倚重实际数据及经济逻辑来评估被诉行为的竞争损害效应和效率促进效应,这通常包含如下步骤:首先,分析排他性交易是否引起了足够的竞争损害;其次,考虑排他性交易是否存在提升竞争效率、促进销售努力、保证专用投资或激励技术创新等积极效应;最后,以消费者及社会总福利是否增减为标准综合权衡竞争损害和效率促进两个相反的效应从而得出结论。
在司法裁判中,对于是否构成对市场支配地位的“滥用”,仍然是一个需要综合考量和审慎评判的问题。
由《反垄断法》第十七条可知,只有在“没有正当理由”的前提下,限定交易才属于应当被规制的垄断行为。虽然立法者并未对“正当理由”作明确界定及列举,但结合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不难看出,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效率、促进了技术创新和市场竞争,增进了消费者及社会总福利等等都属于正当理由的范畴。
可见,中国反垄断法同样采取了“合理推定”原则,而不是“本身违法”原则,来评判经营者是否“滥用”了其市场支配地位。换句话说,到底排他性交易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依赖原被告双方的充分举证。
综上所言,分析和评价互联网平台领域的竞争状态,有助于我们深入思考反垄断法的内在机理和价值目标,避免对个别概念、规则的机械解读与断章取义。
恰如美国法官波斯纳(Richard Allen Posner)所言:“新经济领域的企业为了达到网络效果,往往会以优惠的条件来吸引用户。在其步入垄断的过程中,不仅消费者福利增加,而且技术创新速度也在加快,市场竞争加剧……在新经济行业中,虽然在创新过程中可能出现一系列使利润达到最大化的暂时性垄断,但是由此产生的社会收益要远远超过短期垄断价格所产生的社会成本”。
对于一些由技术创新和市场演进带来的新的经营策略、商业模式或竞争手段,执法者不能拍脑袋或想当然,而应该冷静分析其内在机理,并对其采取一种更加包容审慎的态度,把目光放得更为长远。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