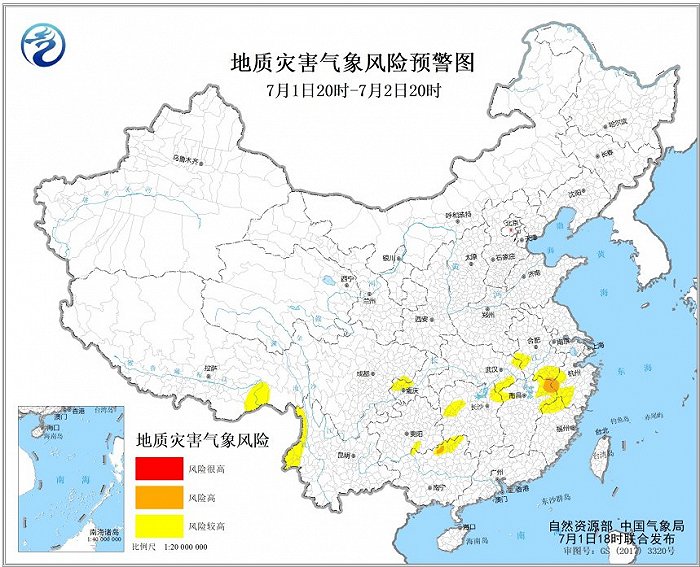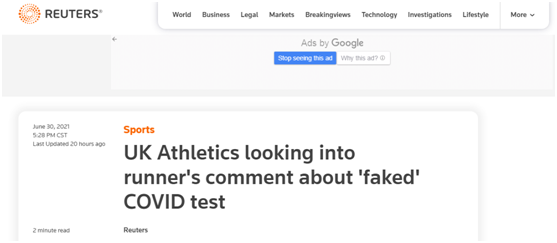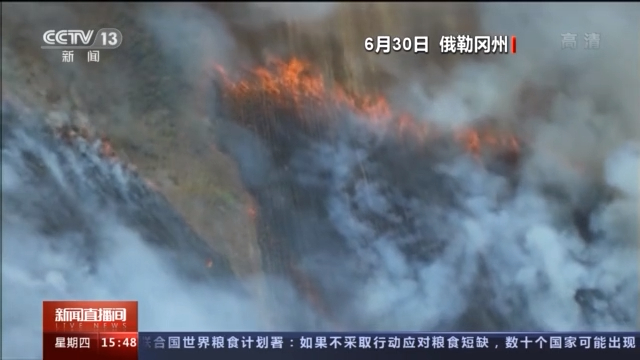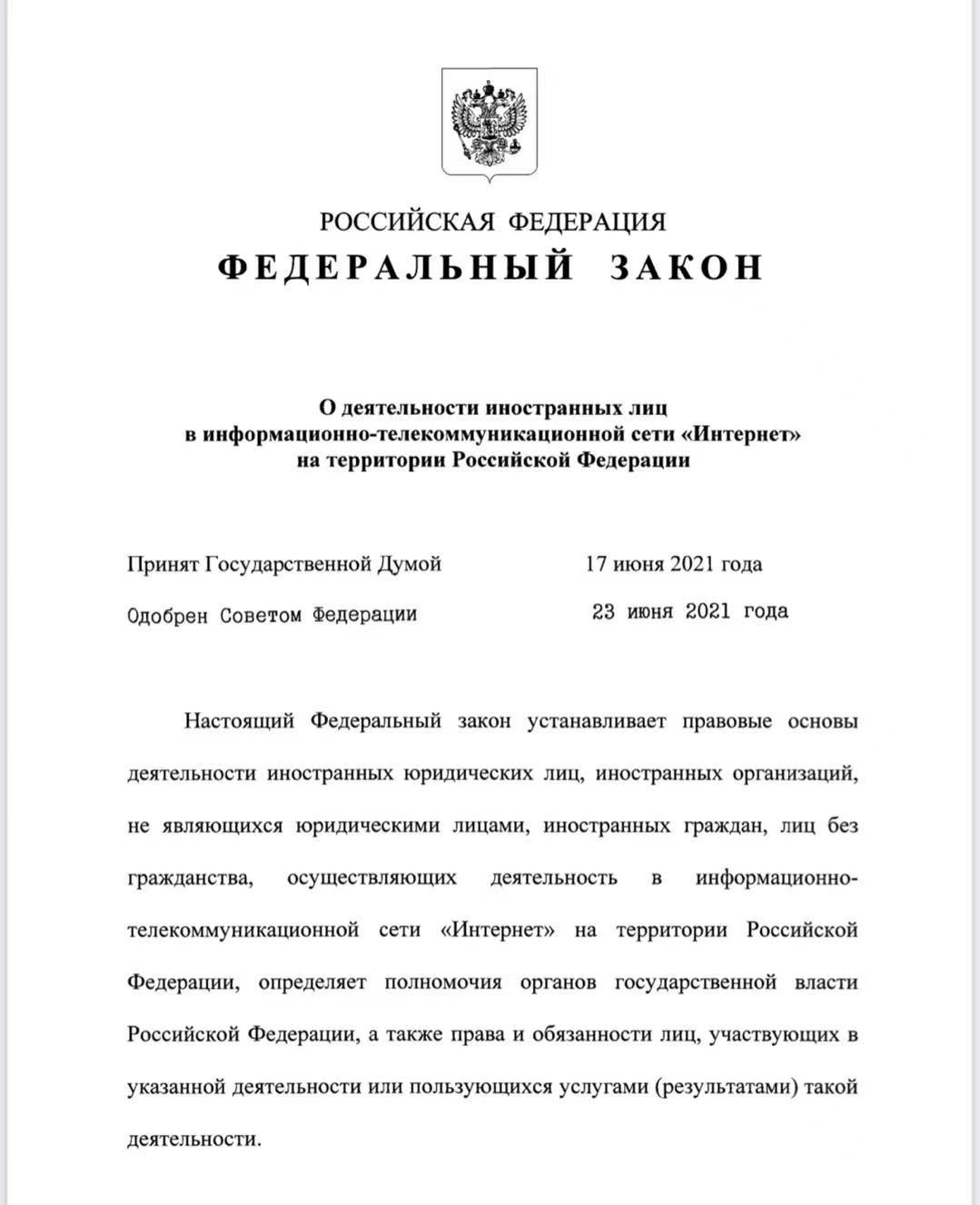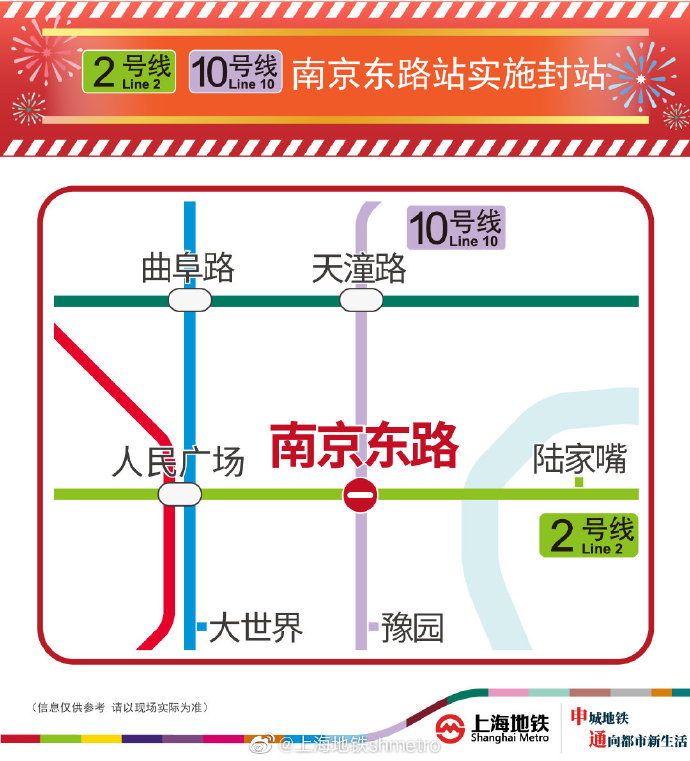原标题:在老家,奶奶与弟弟是一组的,我一个人一组
 “
“很可能从那一刻起她习得了,女孩是轻,男孩是重。女孩长成了妈妈、奶奶,每回身份的转换,她也亦步亦趋地临摹着前人留下来的法则。把姑姑放天平上,把堂姐们放天平上,最后,也把我给拎上了天平。于是,一批批的女孩,继承了血,更继承了这份自厌的遗情。细想真是凄凉,多像一笔无法抛弃继承的债务。
”
位于釜山的海东龙宫寺,自入口起,有一百零八阶。参观路线为拾级而下,再沿着原路返回。路边的石壁里,有一尊佛像,得男佛。与我同行的母亲注视着佛像,半晌,她小声建议,你摸一下吧。闻言,我心如突逢乱石投入,余波阵阵,但不好在异地吵架,我轻语,回程再说。
半小时后,我们又与那得男佛狭路相逢,场面又僵了,母亲的语气跟姿态都比上一回更低,摸一下,只是摸一下。我反问她,为什么。母亲结巴说,就只是……只是确保你将来生下一个男孩子吧。
我深呼吸,挤出一丝微笑,说,我们走吧。母亲牛似的不肯,拗声要求,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我没搭腔,转身低着头一阶一阶踩,母亲追上来,又质问,为什么不嘛?我回头看她,反问,我是女儿,你也是女儿,我们怎么可以这样,这对你公平吗?对我又公平吗?说完,我复往前走,母亲的声音在耳后响起,我只是希望你幸福,我知道这个社会上大家都说男女已经平等了,可是……可是没有儿子的女人,还是会被人说闲话的。母亲的话绊住了我,我再也无法往前一步,我心底雪亮,在某种程度上,母亲是在跟过去的自己说话。 我一生下来,评价两极。以父母而言,我是他们第一个孩子,简直挚爱。奶奶一得知我的性别,难掩沮丧。奶奶始终在盼着一个长孙,大伯夫妇生了两个女儿,他们累坏了,决意止住,奶奶只剩下二媳妇能寄望。母亲剖宫产的伤口还渗着组织液时,奶奶已经止不住关切,什么时候再生?
我一生下来,评价两极。以父母而言,我是他们第一个孩子,简直挚爱。奶奶一得知我的性别,难掩沮丧。奶奶始终在盼着一个长孙,大伯夫妇生了两个女儿,他们累坏了,决意止住,奶奶只剩下二媳妇能寄望。母亲剖宫产的伤口还渗着组织液时,奶奶已经止不住关切,什么时候再生?一年后,即使医生认为母亲伤口愈合的状况不佳,母亲的肚子还是大了起来。母亲不是不在意医嘱,只是人情在身后苦苦地追。奶奶告诉母亲,为了一个孙子,她不晓得在夜里惊醒、辗转反侧多少回。母亲觉得自己对奶奶的忧伤责无旁贷,她回到老家,找自己的母亲倾吐焦虑,两个女人惊惶地讨论,要怎么担保一个男孩呢,外婆说,去找妈祖吧,妈祖慈悲,会答应你的。
我问母亲,拈香时你想着什么。
母亲的答案老实得不可思议。害怕,她说,我好害怕。怕第二胎又是个女生,要再怀孕一次,肚子又要被划开,生你的时候伤口密合得不理想,我不认为我撑得过短时间内剖腹这么多次。
第二胎是个男孩。我有了一个弟弟,奶奶迎来她等待多年的长孙,母亲的苦难结束了。我后来把这过程告诉朋友们,回响热烈,那些女儿告诉我,类似的故事在她们家中也搬演过。没有产下儿子,让母亲被责怪,而身为女儿的她们,也共享了那份羞耻感。
其中有个故事十分立体:朋友的父亲是独子,底下三个女儿。一日祖父跟邻居吵架,邻居气急之下,脱口而出“你就是阴德不足,才没有孙子”,祖父气得转身走进家屋,找着媳妇,也就是朋友的母亲,暴雨似的恶骂。朋友说,要在那种处境下不发疯,得很自制。她的母亲竟还有力气去爱这些女儿。她敬佩着母亲的自制,也惊愕人们可以这么不自制。有时候,人类的无知实在放荡。
我一直以为这叙事会随着岁月流转而化为前尘,人们日后谈起这段,会以一种白头宫女话从前的姿态:“很久很久以前,女人的地位系之于生育。”直到这几年,见人议论某位女星就是因为积德不足才生了三个女儿。我才明白,即使校园的生物课已指出孩子性别的决定机制,知识却阻止不了人类渴望逞欲的心。 再回头去说童年吧。两位堂姐的衣角是我紧紧抓握的一切。弟弟出生后,我基本上归堂姐们管,奶奶总舍不得弟弟,去哪儿都抱着他,弟弟安睡了,就在他身旁守候。我跟堂姐睡下后,奶奶牵着弟弟,漫步至邻近的柑仔店,弟弟挑他喜欢的玩具。我跟两位堂姐,我们这些女孩,一起玩大伯母买的玩具,印象中,玩得倒也开心。未曾有人抗议,为什么他有,我没有,我们跟着接受了,他是奶奶等了好多年的男生,而我们不是。想想这真是让人感伤,我们就这么领教了。像是学习,走物为狗,翔物为鸟,在街上裸裎着肚腹的为猫,被人渴望的存在为儿子。而我们以上皆非。
再回头去说童年吧。两位堂姐的衣角是我紧紧抓握的一切。弟弟出生后,我基本上归堂姐们管,奶奶总舍不得弟弟,去哪儿都抱着他,弟弟安睡了,就在他身旁守候。我跟堂姐睡下后,奶奶牵着弟弟,漫步至邻近的柑仔店,弟弟挑他喜欢的玩具。我跟两位堂姐,我们这些女孩,一起玩大伯母买的玩具,印象中,玩得倒也开心。未曾有人抗议,为什么他有,我没有,我们跟着接受了,他是奶奶等了好多年的男生,而我们不是。想想这真是让人感伤,我们就这么领教了。像是学习,走物为狗,翔物为鸟,在街上裸裎着肚腹的为猫,被人渴望的存在为儿子。而我们以上皆非。奶奶难道不爱我及堂姐吗?我相信她也是爱的。根据我的巨大门牙,奶奶给了我绝对足够的营养,但,基于某种她也无法厘清的机制,她格外宝爱着会带着丈夫姓氏走下去的那个男孩。
堂姐们去上学后,我显得孤独。奶奶与弟弟是一组的,我一个人一组。父母北上看我,我一副郁郁不乐的模样。母亲要父亲去跟奶奶商量,一番揪心的长谈后,我跟弟弟回到父母身边。我很少想起奶奶,倒是常想起两个堂姐,到后期,她们更像是我的照顾者,做我的玩伴,给我编发,带我去买布丁,也跟我一起经受着被至亲冷落的微微黯淡。
母亲后来问我,为什么你不喜欢在奶奶家?我告诉她,因为奶奶都只看弟弟,不看我。对于一个还没上小学的孩童而言,尚且不懂得使用“偏心”这两个字,只能借由现象的描述来让母亲明白:在奶奶家,我无法得到注视。母亲说奶奶时常打电话给她,抱怨我喜欢攀爬到高处,像是冰箱上,她时常要警惕我的跌落。奶奶认为,我是很难带的小孩,很不乖。母亲在多年后回忆着奶奶对我的评价,我听了却满腹惆怅,那些机巧的小动作,可能是一个孩童对于主要照顾者的拙劣示爱:看我,看我,我在这里啊。
奶奶还在很年轻,年轻到难以想象自己有一天会成为奶奶的时候,我猜也曾被谁放在天平一端上,并且沮丧地发现指针的震颤渺乎其微。很可能从那一刻起她习得了,女孩是轻,男孩是重。女孩长成了妈妈、奶奶,每回身份的转换,她也亦步亦趋地临摹着前人留下来的法则。把姑姑放天平上,把堂姐们放天平上,最后,也把我给拎上了天平。于是,一批批的女孩,继承了血,更继承了这份自厌的遗情。细想真是凄凉,多像一笔无法抛弃继承的债务。
朋友近日怀孕了,是个男孩,众多道贺词中,她最受不了的莫过于“一举得男”“喜获麟儿”。她知道自己被赞美了,但她还想不出来自己做了什么好事,像是,怀了一个男孩而不是女孩吗?另一个朋友怀孕了,是个女孩,她察觉得到,大家都在尝试着抚慰她,以任何语句。女儿贴心。女儿懂事。儿子长大了会跟女朋友走,可是女儿不会,女儿恋家。这么多理由,只让她觉得寂寞,爱一个人,怎么会需要这么多理由?仿佛我们在讨论一个略有瑕疵的存在,必须一再游说,才让人勉强喜爱。更让她隐伤的是,懂事,贴心。她想到自己,这些特质其实都会压垮一个人。
在家庭中,女儿被期待着扮演一个柔软小棉袄的角色,微笑,没棱角,察言观色,说话甜蜜且每一句都让人想紧紧相拥。女儿们也是照顾者,照顾小孩、伴侣、自己的父母、伴侣的父母。懂事,贴心,恋家。她们从来不被鼓励走出家门。我曾想过,若交给女儿一纸舆图,悄悄引诱她,她是否也会渴望离开?到底是恋家,还是外头的世界虽广阔,却也在漫漫排挤着女儿们?朋友的结论是,单从我们对于生男生女的祝福,方知晓终究我们还是在为偏见服务,只是服务的过程中,我们至少制造了快乐。 回到得男佛的问题。只要伸出手,轻轻一个抚触,我跟母亲可以不必在穿梭的游客面前上演相互为难的戏码。但,为什么不呢?是什么在抗拒着这种无关紧要的指令,还是说,一切并没有表面上的无关紧要?我怎么可以祝福自己,向神祈祷,请确保给我一个男孩。好让我得以逃过没有儿子的女人所将遭逢的命运。我看着母亲,意识到有时候人事倾圮,我们只能跟着长斜身躯,但,为什么不伸手挑衅、媚行一回?罢了,罢了。懂事,贴心,不要怪母亲,她也被吓坏了。懂事,贴心,把别人的为难化成自己的为难,女儿们擅长这么做,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也期待自己的女儿们模仿她们这么做。
回到得男佛的问题。只要伸出手,轻轻一个抚触,我跟母亲可以不必在穿梭的游客面前上演相互为难的戏码。但,为什么不呢?是什么在抗拒着这种无关紧要的指令,还是说,一切并没有表面上的无关紧要?我怎么可以祝福自己,向神祈祷,请确保给我一个男孩。好让我得以逃过没有儿子的女人所将遭逢的命运。我看着母亲,意识到有时候人事倾圮,我们只能跟着长斜身躯,但,为什么不伸手挑衅、媚行一回?罢了,罢了。懂事,贴心,不要怪母亲,她也被吓坏了。懂事,贴心,把别人的为难化成自己的为难,女儿们擅长这么做,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也期待自己的女儿们模仿她们这么做。我突然间觉得,这么苦涩的游戏,神佛有情,恐怕也想说,别玩了,没看见玩的人都这样不愉快吗?我没有再说话,把话题移走,导游在等我们了。我跟母亲在海气弥漫的阶梯继续前行,突然她说,对不起,你说得对,我不应该要求你做这件事。我说,没事了,我们快去会合吧。
我听见胸腔内巨大的回声,那道声音说:不怪你了,若去除人世纷扰,我相信你可以更专心地珍惜你的性别。不生气了,因为我清楚,你老家餐桌上的鸡腿跟蛋,从来也不属于你。
本文节选自 《可是我偏偏不喜欢》
《可是我偏偏不喜欢》作者: 吴晓乐
出版社: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品方: 磨铁·大鱼读品
出版年: 2020-11-12
编辑 | 啾啾
主编 | 魏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