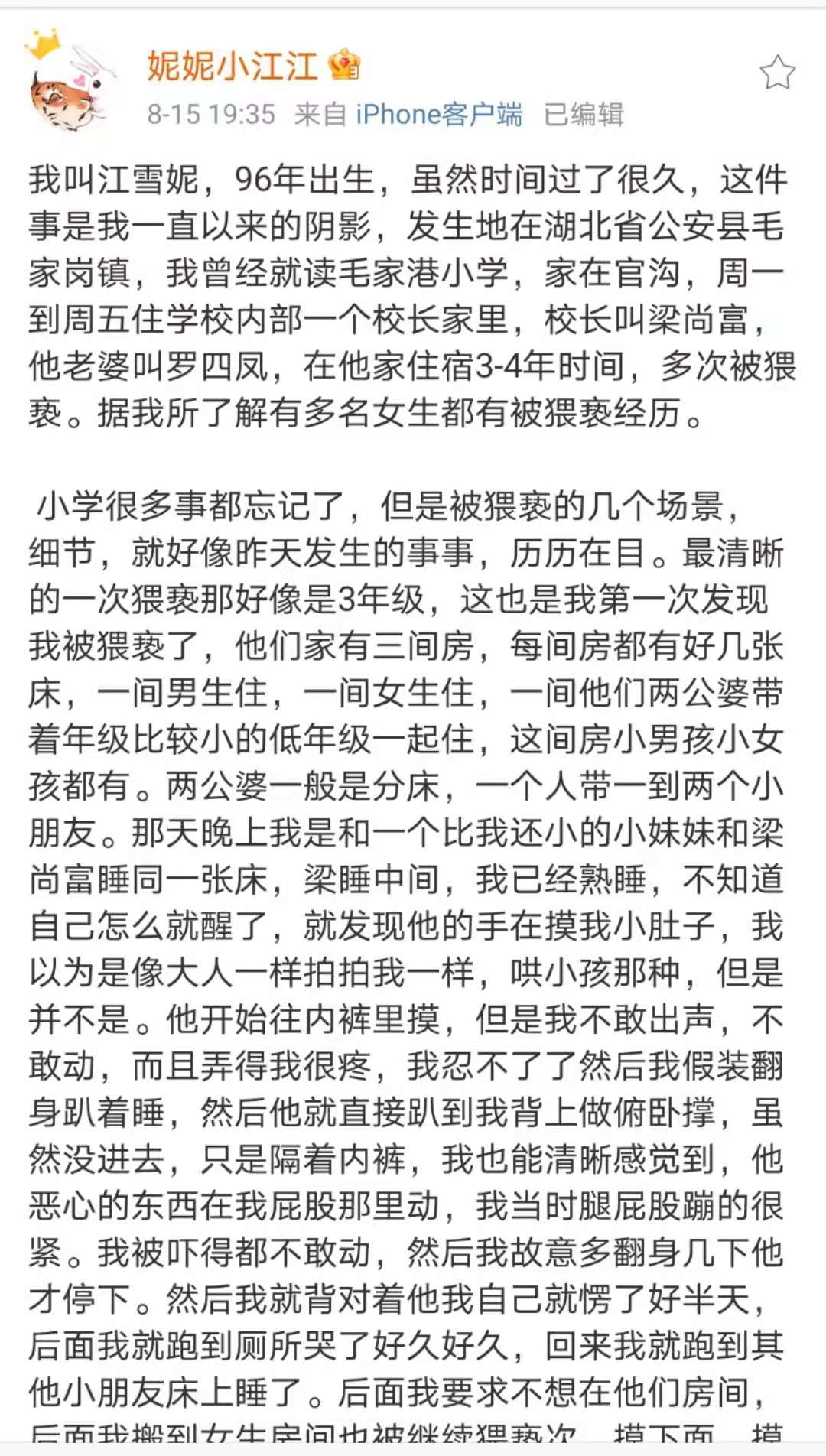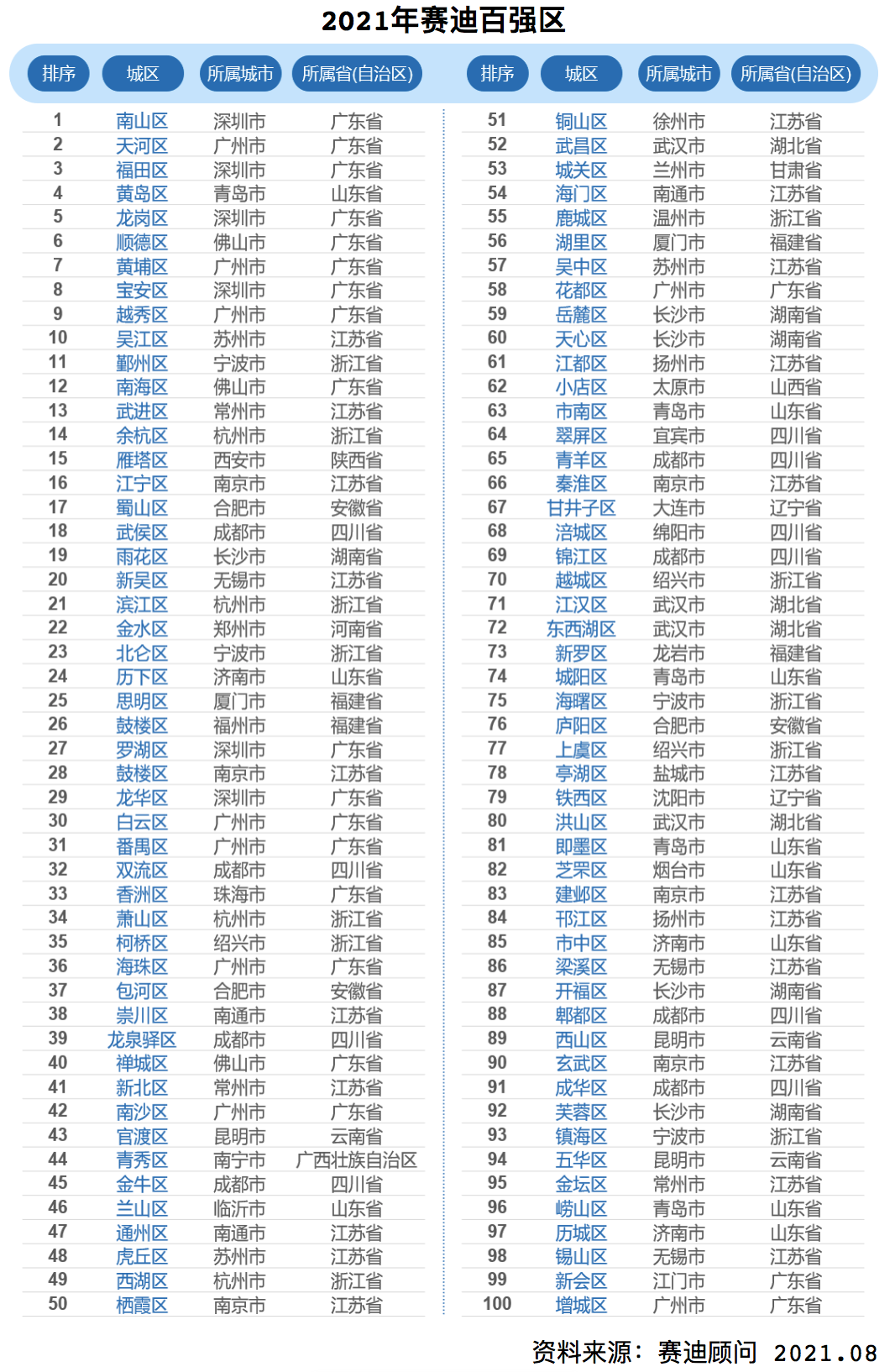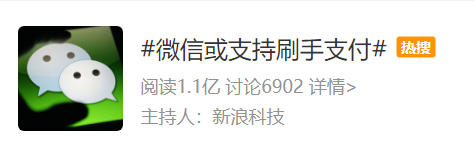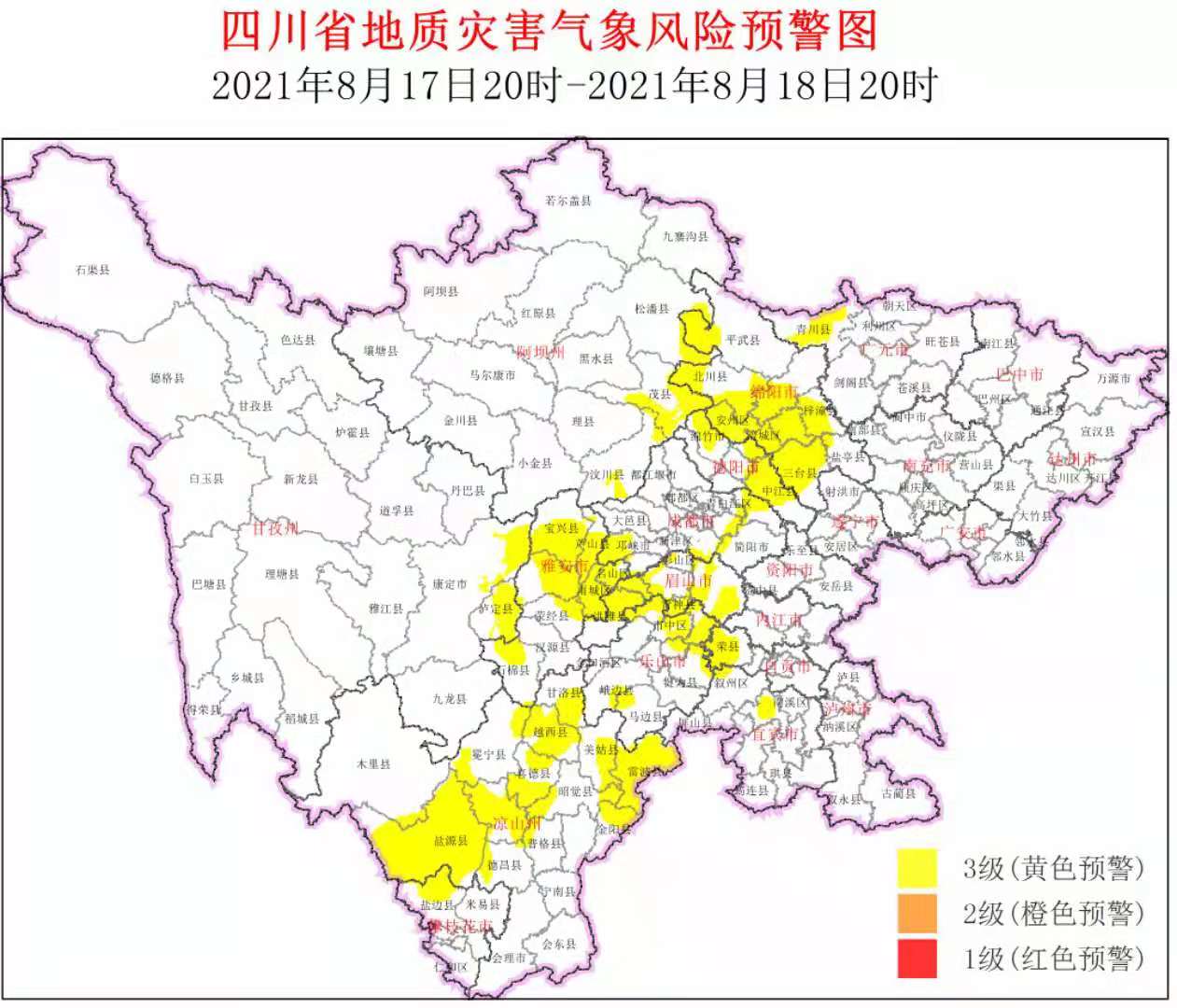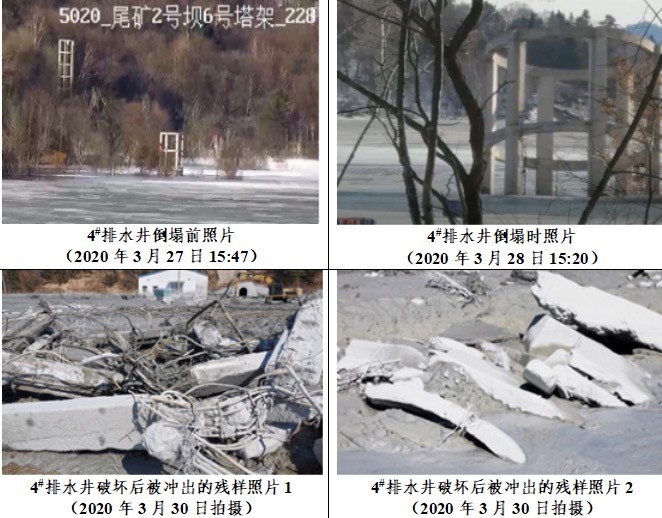来源:豹变
作者/陈晓妍
编辑/邢昀
在奥维德的《变形记》中,美杜莎在雅典娜神庙中被海神波塞冬强暴。因为丧失贞洁,美杜莎反而遭到雅典娜的惩罚,一头漂亮的头发化成蛇身,与她对视的人会变成石头。无法与外界联系,美杜莎成为彻底的女妖,被男性“英雄”珀尔修斯砍下头颅。
现代社会里,“美杜莎”依然是性侵受害者处境的隐喻。
8月中旬开始,“阿里女员工被侵害”案件点燃舆论,职场中的性侵害、性骚扰事件再度成为关注焦点。根据济南公安8月14日的通报,阿里巴巴集团王某文、济南华联超市张某涉嫌强制猥亵犯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职场性骚扰如同房间里的大象,明明普遍存在,一览无余,但往往被有意忽略。
在外界看来,互联网大厂本是文化价值观更成熟,更尊重员工、以人为本的现代公司,也是其他企业学习模仿的榜样,但即使在这样的公司里,职场人面临的性侵犯危机也从未解除。在关注度更低的中小企业,职场性骚扰以更隐蔽的方式进行着。
身处险境,敢于站出来说不的人少之又少。
阿里女员工在被侵害之后,尚且需要以食堂发传单这种极端方式,才能引起高层关注,推动事情进展。对于其他有相同遭遇的人来说,更是求助无门、维权艰难。迈过勇气这一关,只不过是维权的起点。很多人事后才发现,举报之后,更多棘手的问题也会随之浮现。
而更多人考虑到个人安全、职业和声誉,在遭性骚扰后选择隐忍。
也是8月中旬,上市公司金花股份董事长“性侵扰”女秘书事件历时一年有了终篇。从爆出来的劳动仲裁来看,2020年8月21日出差时,金花股份董事长张朝阳在酒店房间内,对女秘书做出搂抱行为,女秘书挣脱跑出房间。
针对该员工的维权,金花股份安排其带薪休假。然而从2020年10月起,金花股份停发了该员工的工资,断缴了社保。最终这名被侵害的女员工提出辞职,通过劳动仲裁途径讨要工资和社保。
吕孝权是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从业13年来,他接触了很多案例,职场性侵犯很少会有直接的肢体暴力,甚至连胁迫手段也比较少。更多的是利用隐形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对被害人施加压力。
虽然吕孝权看到女性维权意识越来越强,但在缺乏社会系统资源支持的情况下,站在维权道路上的女性,总是显得孤立无援。
举报经理性骚扰,因为证据不足,第二天他就被放了出来
林云 文员
2020年8月,我入职贵阳观山湖区一家高端精品酒店。33岁的客房经理是我的直属上司,我担任客房文员,同时也是他的助理。平时,我们就在同一间没有监控器的办公室办公。客房经理有女朋友,起初,我完全没想过职场性骚扰会发生在我身上。
他开始夸我“身材不错”时,我就感到有些不太对劲。有时候弯腰收拾东西,他就会盯着我看,说“姿势诱人”。我感到被冒犯,让他不要开这种低级玩笑。但他并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常常在说话时碰我的腰,把手搭在我肩上,说替我“胸部按摩”,甚至站在办公室过道用下体蹭我。我立马变了脸色,警告他不要动手动脚。他一点也不在意,反而回应我:“那你对我动手动脚啊!”
我恶心极了,向职位更高的总经理举报了上司。一位房务女总监也找我了解情况,又追问我是不是本地人,家住哪里,在哪里上学。我很疑惑,举报上司性骚扰,为什么要打探我的背景?后来,我才反应过来,她想知道我是不是本地人。如果是孤身一人在外的女孩,那么问题就更好处理。

举报之后,客房经理签了一份处分,并且向我道歉。那份纸质处分只是纸质版的口头警告,保证下次不再犯,甚至没有在公司里公开,这件事就算了结了。我很生气,问女总监为什么不劝退客房经理?她却回应我,“作为管理者不会偏袒任何一方”“规章制度的制定不以你个人意见为准”。
同为女性,她的处理方式让我寒心。当时,那位女总监刚刚上任,很多业务,都要依靠客房经理这种工作多年的老员工。经理甚至没有被调离,第二天,他依旧与我一起办公。
办公室里常常只有我和他两个人,我每天都过得很压抑,担心他报复我。酒店里有很多空房,而经理手里有任何房间的钥匙,那些都是无人监管的死角。我每天都惶恐不安,生怕他对我做些什么。在这家酒店里,没人在乎一个普通女员工的安全。得到处分之后,他开始要求我每天提前半个小时上班,也没法按时下班。工作太累,他就挑衅我,让我离职走人。
但在我找其他工作时,客房经理又会在背景调查时说我的坏话。有一家公司的HR本来很热情,跟他聊完之后,对我的态度突然变得冷漠。
经理有时会拿走客人遗留下来的安全套。有一次,他又骚扰我,问我喜不喜欢用安全套。我被彻底激怒了,只好报警。客房经理被叫到派出所,但我只有一张处分单,没有更多关于这件事的视频和音频作为证据。
女总监很快也来了,先是问我:“这件事能不能和解?”又威胁我,如果不答应,公司就不会再聘用我。女总监带来两个主管,他们当中没人目睹过骚扰现场,但都替他做了证。因为证据不足,经理第二天就被放了出来。
看着他们若无其事地走出派出所,我再也忍不住,在路上哭了。第二天,我没有再去上班,害怕经理再次报复我,同时也对公司彻底失望。在举报上司性骚扰之后,我成了被针对的对象。被侵犯的人一旦保持沉默,这件事就和没发生过一样。
但我告诉自己,绝对不能这么做。我向人事部门递交了离职证明,女总监立刻签了字。回寝室收拾行李时,女总监突然闯到我宿舍,问我要不要赔偿?所谓的“赔偿”,其实就是封口费。她怕我受了气离开公司,会曝光他们。我不想要赔偿,只想要公道,也不想让其他女同事遇到这样的上司。
离职那天,我在公司一个一百多人的大群里发布了那份处分单。人事连忙回复消息,说经理只是在开玩笑,随后解散了群聊。
离开公司的时候,人事向我保证,一定会处罚经理。但二十多天过去,我没有等到任何消息,经理也还是照常在公司工作。
我忍无可忍,第一次在朋友圈公开曝光了这件事。女总监威胁我,要给我寄律师函,我回复她:“奉陪到底。”
更多人知道了这件事后,经理没有颜面在公司继续待下去。在曝光的第二天下午,经理就离职了。朋友圈也不再更新。
我所做的种种努力,仅仅是让他离开了这家公司。他具体到了哪一家酒店任职?还会不会骚扰其他公司的女员工?这些我都不得而知。
遭遇老板性骚扰,我要办离职,财务全程守着我,不让我与其他同事接触
夏婷 互联网工作人员
刚到那家创业公司应聘,是我最开心的一天。老板曾是互联网行业一款爆款产品的负责人,名气很大。听我想做出一款自己的产品,他对我说:“公司就缺你这样有想法的人”。我踌躇满志,不介意从其他岗位做起,也接受了要频繁到海外出差的要求。
我太兴奋,忽视了一些现在看来很重要的细节。在咖啡馆里,老板故意贬低“Me too”运动,认为是因为钱没谈拢,女人借此发起网络暴力报复男性。

入职不久,我被安排和老板一起到国外出差,他常开黄色玩笑,我觉得不舒服,女同事却跟着笑。有一次,他当众说想与某个女明星上床,等同事不在,就对我说:“你长得像那个明星。”
一股恶心的感觉上涌,但我立马反省自己,是不是太过敏感。回国路上,我故意当着他的面与男朋友视频聊天。回国之后,他竟借此打压我,说我只顾着与男朋友聊天,没有事业心。又声称阅人无数,一眼看出我这种员工没法培养。我慌了,陷入对自己工作能力的怀疑中。他看出了这一点,改变态度,劝我拿出决心,尤其要信任他。
第二次出差,他趁机拍我的腿,听到我说不喜欢与男性有肢体接触,就告诉我,这是心理疾病,人要学会“脱敏”。接下来两天,他把出差形容成我们的“蜜月”,让我与他“结合”,提高后代的智商。我很害怕,每天回到酒店房间,就偷偷一个人哭。他一脸无所谓,嫌我开不起玩笑。
有一次,我们在外陪客户喝酒。凌晨四五点散场,他借着酒劲,让我陪他去洗手间,强行拖我去。我拼命挣扎,一个保安注意到我们,他又把我拉走,乘机摸我的胸部。我大叫着推开他,老板一直在装醉,最后,是客户们把我送回了酒店。
我告诉了家人,并发消息给当时兼顾人力工作的财务。她的第一反应不是安抚我,而是替老板找理由:“他一定是喝醉了”。接着又以公司创业不易,正面临融资为理由,说服我不要告诉别人。
我躺在床上一夜未眠,生怕老板又突然闯进我房里。回国后,我第一时间到公司办理离职,财务全程守着我,不让我与其他同事接触。
朋友鼓励我报案,但因为这件事是在国外发生,警察无法调取监控视频。老板每次都是当面骚扰我,并没有在我手机里留下任何证据,朋友告诉我,这个人肯定是惯犯。我们也只好就此作罢。
离职之后,我在家休息了一年多,想到工作就害怕。一位前同事联系我,在我之前,还有一位工作能力很强的女同事,被老板性侵犯之后离职,回老家结了婚。这再次打击了我,我同情那位女生,也理解她回归家庭的选择。职场性侵犯,就是对女性下达的驱逐令。
不愿离开的女性则会成为猎物,甚至共谋。那名财务其实也被老板骚扰过,在公司的庆功宴上,他趁财务不注意时搂抱过她。明知如此,她还是为老板到处招聘年轻的女员工。
一位与老板共事过的朋友发来消息,说自己曾经遭遇他的猥亵。她当下制止了他,但在那之后,合作依旧如故。我问她是怎么容忍的,她告诉我:“格局大一点就好了。”
顺应这个潜规则,就能得到更多的资源。那个瞬间,我有种错觉,好像做错事的反而是我。
举证困难,性暴力面前,受害者们都在孤军奋战
吕孝权 律师
2008年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就加入了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前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服务中心)。参加妇女权益法律援助、公益诉讼的工作已经有13年时间。
很多女性遇到职场性骚扰,都会隐忍不说。她们在一开始就面临很大的精神压力。选择维权,会不会造成二次伤害?隐私会不会泄露?获得的跟付出的是不是不成比例?甚至会不会面临“荡妇羞辱”?这样一来,有的咨询者会打退堂鼓,不再联系我们。
选择维权,要有足够有经验的律师帮助这些女性,还要有心理咨询师或者社工提供心理支持和感情陪伴。很可惜,目前来说,维权是缺乏社会系统资源支持的。面对强势的施害人,很多情况下,需要受害者独自面对,孤军奋战。
坚定维权的女性是值得钦佩的,但选择隐忍,或中途撤诉的女性,无论她们做出什么选择,都值得尊重和理解。
维权这条路上,从报案、立案、取证,再到胜诉、获得赔偿,每一步都很困难。
最难的是取证。目前,绝大多数案子都是按“民事侵权案”处理的,谁主张谁举证,举证的责任都在原告身上。但性骚扰案件跟民事侵权案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性骚扰通常是发生在一个私密空间里的,有高度的隐私性和隐蔽性。而且受害人跟施害人之间的地位是不对等的,是弱者跟强者的关系,很多职场性侵犯很少会有直接的肢体暴力,甚至连胁迫手段也比较少。更多的是利用这种隐形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对被害人施加压力,让她不敢反抗。这种情况下,取证就变得很难。
每年通过电话、邮件咨询我们的人很多,但很多人拿到的证据都不充分。我们会帮忙分析维权路径的同时,也要告知她们所要面临的风险和后果。
有的被害人能留下一些证据,比如当时的110报警记录、电话录音、微信短信等聊天记录,或者是案发现场附近的监控视频。有的时候,我们判断这些证据相对来说已经是比较及时的,但指控能不能成立,还得看办案人员的认识。对证据标准的认定问题,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不同的办案人员的认识和处理可能都不一样。
2019年,中央美术学院的9 名女学生举报教授姚舜熙长期性骚扰、猥亵。这个案子是我们代理的。在几个举报的女生中,有一个叫小羊的女孩维权意识是最坚定的。她没有太多的直接证据,但间接证据还是不少的。我们当时初步评估,觉得这些证据大概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
但这件事的结果,大家也都知道了。因为办案人员认定证据不足,这个案子最终不了了之。这个案子,我至今都觉得很遗憾。基本上,维权案件败诉,都是因为证据不足。
如果说,我们还是遵从一般民事诉讼的规则,把举证的责任都推给受害人,那只能说明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这种案例的特殊性。
即使是通过重重阻碍,案件胜诉,但要让被害人获得足够的赔偿也很难。2010年,我们代理在深圳三木集团总裁强奸女员工的案件,法院以强奸罪判处苏三木有期徒刑4年,但受害人最后只获得的赔偿,只有4000多元。
目前给被害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一般是在2000到3000元之间。这个赔偿额,对于被害人身心方面抚慰能有多大效果?对施害人的法律威慑力又能有多少?
这是一个补充性的民事赔偿责任,而不是一个惩罚性的赔偿责任。
在美国,如果发生了职场性骚扰事件,企业可能需要对受害人进行赔偿,支付高昂的“惩罚性赔偿金”。
现在一些性骚扰案件广受关注,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趋势。但在围观的人中,有真正关注案件的,也有纯粹吃瓜、看热闹的,甚至也有想把水搅浑的。舆论环境很复杂。
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未经调查,号称“反转”的消息出现。把这个矛头指向女方,诬告双方存在情侣关系,给女方泼脏水。每次看到这些,我都会很愤怒。
我希望无论是媒体也好,公众也好,一定要聚焦案件本身,不要去聚焦某一个人。不要求指控者是“完美受害者”,挖举报人的隐私。举报人的处境已经很不容易,对于那些正在孤军奋战,或者还在观望,准备拿起法律武器的人来说,我们能做的,就是不要成为射向她们的一根箭。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