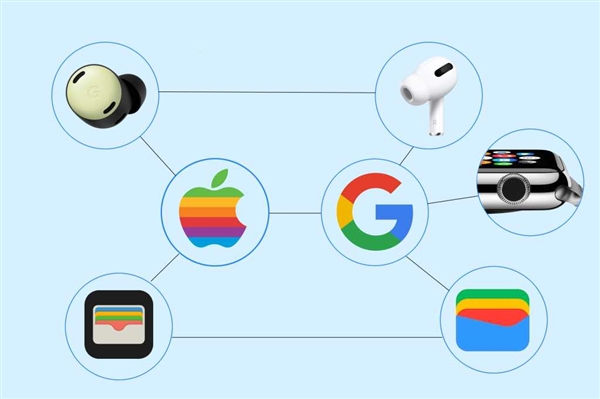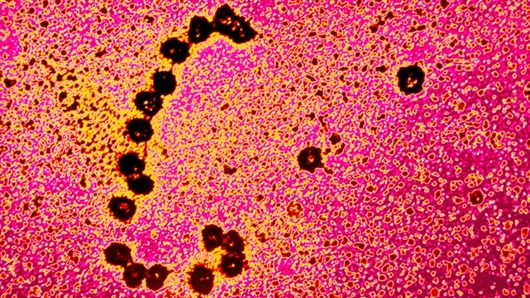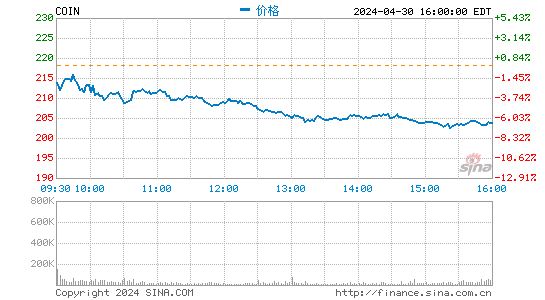●西洲
住在昭苏高原的时候,白天时间短,夏天每天只上7个小时的班。下班后的时间过于充足——小镇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又不会成天待在屋里,就出门散步。
初夏的时候喜欢去东边的矮山,野薄荷在石缝间、在草丛里、在牛马的蹄子下、在沿着雪水融化的黑土地生长,散发着异乡的风情——那确实是异乡的,我老家的薄荷不是这般模样:细小的叶子对生,一簇挨着一簇,等到夏末,就开同样是一簇一簇紫色的细碎微花,散发着迷离梦幻的馨香。
在山上远望,每一条光洁的水泥路都通往农田,每一条路两边都是瘦长光洁拥挤的杨树。那些杨树挤挤挨挨,每一棵都直立向上生长,好像终其一生都要探出头去往更高的天空中瞭望。杨树叶子小而密,被风吹翻的叶片泛着银白的光,像不知道什么花开在树梢。而四面都是遥远的雪山。雪山下,草原舒展,羊群点缀其上,河水蜿蜒——冰凉的雪水从遥远的山巅落下来。澄澈的蓝天下,油菜花盛开了,香紫苏盛开了,向日葵也盛开了。
天空蓝得像是另有一个幽蓝而明亮的星球在关注、拥抱着我们。向日葵明艳的黄,不同于油菜花拥挤而娇嫩的黄,一朵朵向日葵像一个个痴情骄傲又倔强的少女,站立在一望无际的蓝天下,一直蔓延到遥远的雪山脚下,越来越小的葵花像约好了似的,渐渐隐去形状、笑声和身影,只余一点淡淡的黄,只余一缕淡淡的绿,夹杂在棕色的秸秆上。
高原黄昏,凉爽宜人,散步的人们对这种晚景司空见惯,只有我像个城里人似的没见过此种世面。
安房直子写过一个名为《黄昏的向日葵》的童话故事。一朵向日葵爱上了每天从她身旁跑过的少年。因为过于执着,她变成了穿着鲜艳的黄衣服,戴着宽檐帽子、嘴唇闪闪发光的少女,在少年需要帮助的时候,指引着少年藏到一艘废弃的旧船里,并将追赶少年的人指向了另外的地方。夏日炎炎,晚风逐渐清凉,向日葵变成了女孩是向日葵的一个梦,还是向日葵真的就变成过一个穿着鲜艳黄衣服的女孩,就连向日葵自己也不知道。总之空荡荡的船里不见了躲藏的少年,夏天也结束了,向日葵呢?蔫了,枯萎了。
这是一个读来令我久久难忘又恍惚不安的故事,穿着艳黄衣服的向日葵女孩羞涩的心事,如昭苏夏日高远而幽蓝的夜空中蓝莹莹清泠泠的星星,在无尽的夜晚闪烁,忽隐又忽现。
小时候村里有人家在玉米地旁稀疏地种几棵向日葵,高高的艳丽葵花伸出碧绿的青纱帐。上学路上,远远就能望见“秀于林”的那几株向日葵,心里不停念叨:哼!等你结籽就去偷来!然而,也不过是心里想一想,路上看一看。不知道什么时候,那几朵向日葵从小圆笑脸变成大圆笑脸,再枯萎了黄色的花瓣,饱满了圆盘,再悄悄地只剩下光秃秃的秸秆在日渐饱满的玉米中间兀自摇晃——一定有人偷走了其中的一个花盘甚至所有的花盘。
一直惦记着等到向日葵成熟的时候去地里偷几个回来,同事们笑话我:这也值得用个“偷”字!你去拉一车,也没人拦你。
当然,这不是我们吃瓜子的食葵,不是小时候摇曳在玉米田中的向日葵,而是制油的油葵。夏天从乌鲁木齐乘坐火车到伊宁,路旁就有一片连着一片的油葵在火车的行进中缓慢后退。也有在一大片碧绿的田地中忽而亭亭的几棵、几十棵笑脸——那是去年的油葵地。
“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更无柳絮因风起,惟有葵花向日倾。”伏天里读司马光《客中初夏》,有种莫名的清爽之感,仿佛夏天还未到来,仿佛春之余韵犹存。就在余韵犹存中,盛开的向日葵花田渐渐远去,整个夏天也渐渐远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