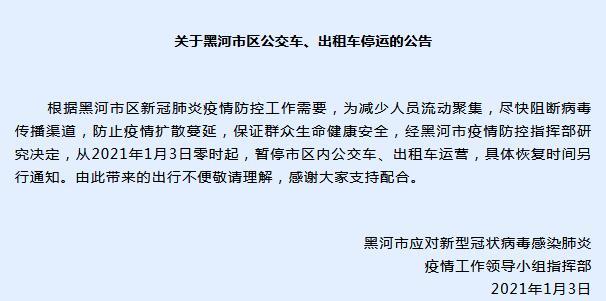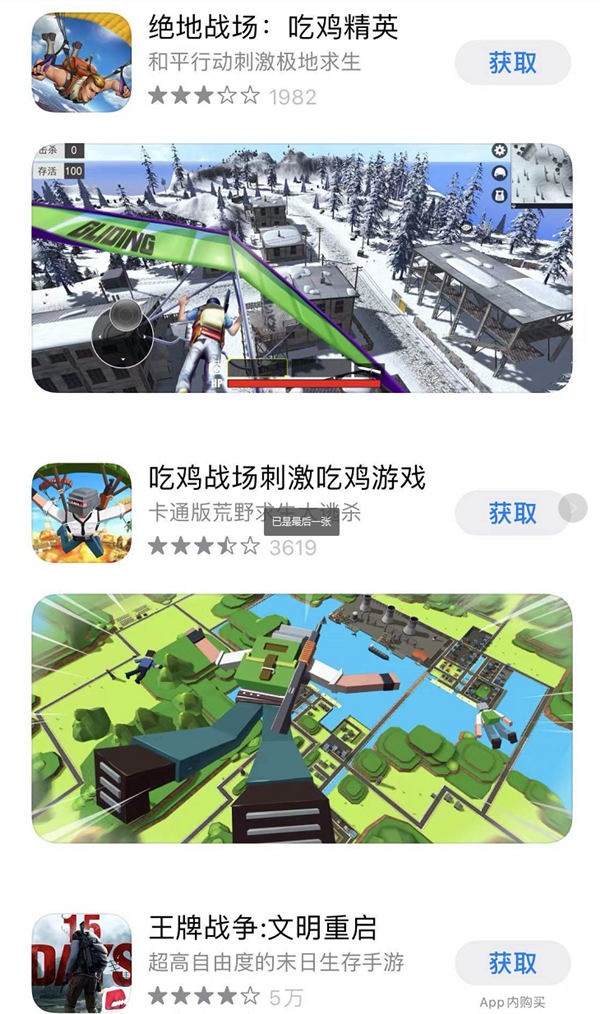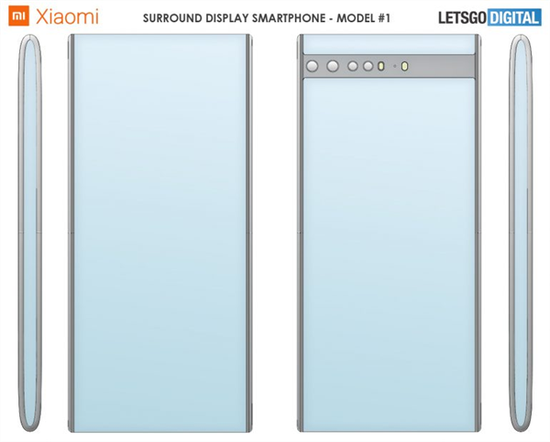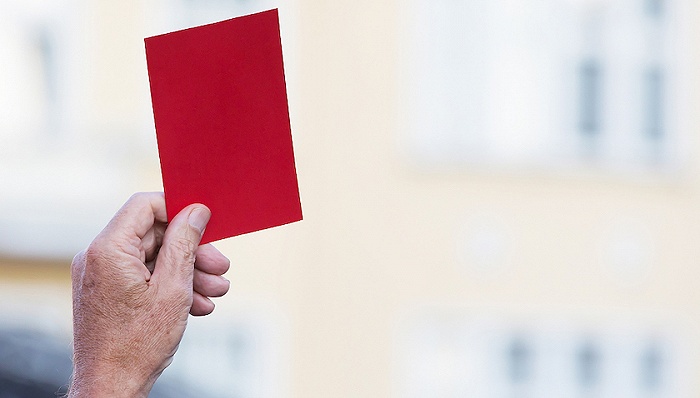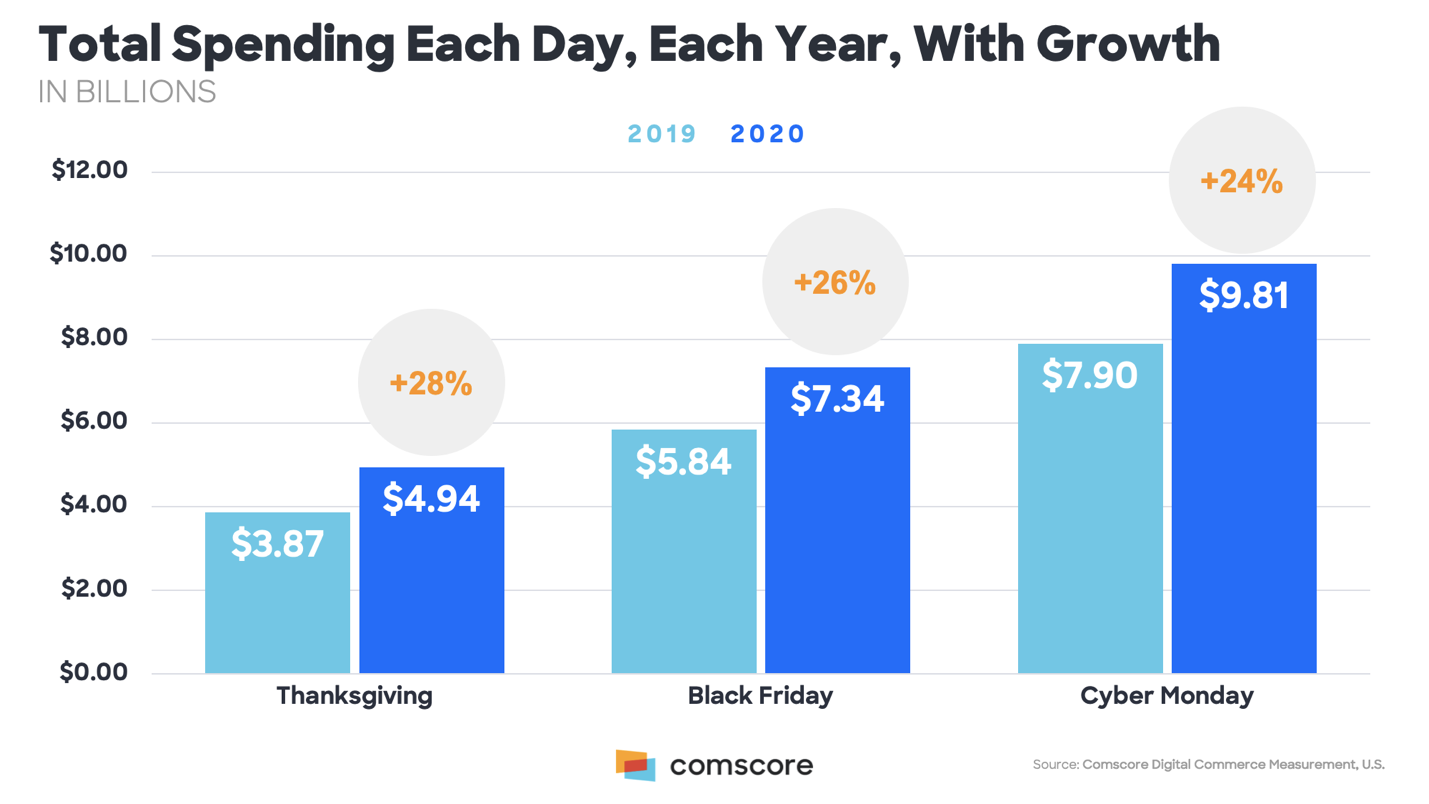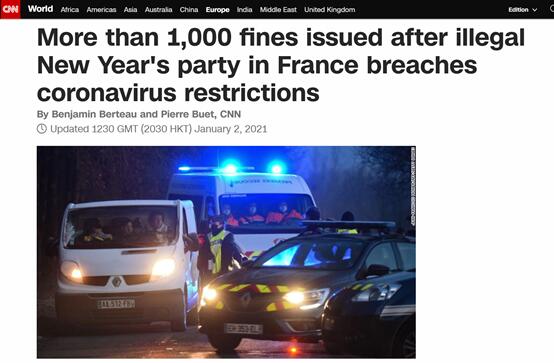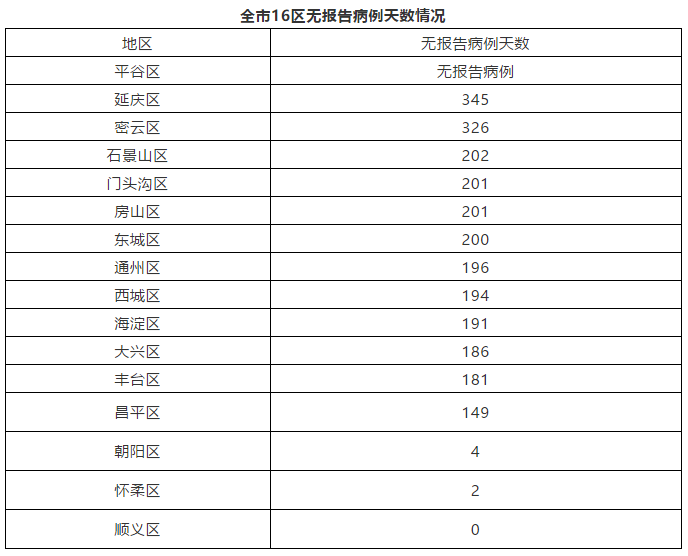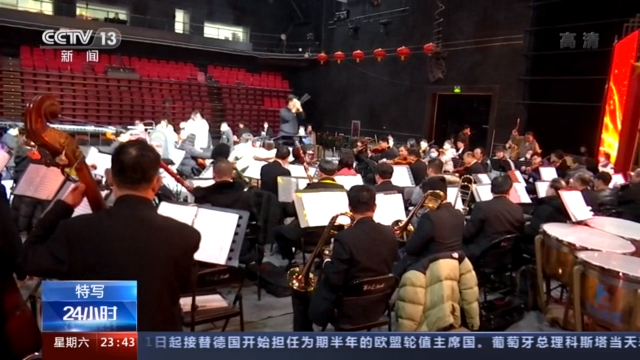原标题:合约城市:城市是一组合约关系网
笔者前次在《合约城市:城市化的另一条道路》(澎湃商学院,2020-12-01)一文中提及,政府负债建城不可持续,提高了我国金融体系的风险。要降低金融的系统性风险,需要从根本上改革我国城市化模式,合约城市是缓解公共债务压力的另一条城市化道路。本文指出:(1)城市是一组合约关系网;(2)政府凭借其强制力,是城市合约的重要组成部分;(3)城市合约结构的选择取决于具体的交易费用。
一、城市是一组合约关系网
城市是由拥有分立的产权的人群聚集而成的。这些产权所有者通过一系列合约构成密集的合约关系网。大量个体通过雇佣合约、购物合约、交通合约、税收合约、婚姻合约等多种多样的合约联系在一起。城市越密集,合约关系网就越密。城市化的过程,是人口由分散到聚集的过程,也是大量拥有分立产权的个体之间编织的合约网变得更加密集的过程。城市化的核心问题,是怎样有效地重新配置聚集而分立的产权。
如果没有规划限制,个体根据价格信号自发签订合约有效配置产权的前提,是产权清楚且缔约的交易费用较低。然而,产权完全清楚与交易费用为零的世界并不存在,政府通过行政力量配置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个体间缔约的交易费用。
但是,政府靠行政力量推行城市化也可能导致资源错配。几十万、上百万的市民有其生活的特殊知识,政府官员与规划专家难以掌握他们生活的全部信息,也无法完全预知未来。政府主导的城市化没有机会成本和债务破产的制约,从而缺少纠错机制。产权不清晰或交易费用不为零,并不意味着政府主导城市化是唯一的替代选择。合约城市就展示了另一种可能。
二、政府是城市合约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行政强制力影响政府合约边界
权利(权力)是资源要素,政府具备的核心要素是行政强制力。政府凭借其强制力,在城市生活的某些领域具有排他性的地位。例如,政府提供了司法税收等社会治理服务,包括法院及其法官、公安局及其警察、税务机关及其办事员等。在这些领域,个人及组织只能与政府缔约。
在另外一些领域中,政府通过提高准入的门槛,成为主要的缔约主体。例如,政府运营的公办学校是许多城市的主要教育机构。政府不但要提供土地、建设学校,而且学校的管理者与老师是有编制的、政府聘用的老师。政府不但与学校签订了界定土地权利的合约,也与学校的管理者及老师签订劳动聘用合约,并直接参与学校的管理运营。又如,多数城市的医院是公立的,政府直接与医务人员签订了劳动合约,并以此界定了医务人员的人力产权。在这些领域,虽然没有绝对地排斥民营企业的进入,但是因其高门槛,将大多数人力资源聚集在政府的行政安排之下。
(二)改革前的城市:政府是中心缔约人
当大量的经济活动与政府直接发生缔约关系,政府就成了合约关系网的中心,扮演了中心缔约人的角色。
在改革前,城市政府作为中心缔约人,与几乎所有的要素缔约,覆盖了整个城市的几乎所有合约。住房的建设开发、垃圾的清运、资金的信贷、交通的供应、教师的聘请、国企职工的雇佣等都是由政府通过合约来安排。也即,政府通过一系列以强制力背书的合约,界定与安排了土地、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劳力等一系列生产要素。这其中最关键的,是几乎所有居民都是政府雇员。政府作为中心缔约人,界定了人力资本及劳动力产权,将每个人与体制绑定在了一起。
(三)城市改革是城市合约关系网的重组
改革开放改变了政府作为中心缔约人的传统城市体制。大量农民及其子女进城,以及对民营经济的开放,在政府之外提供了新的可供选择的合约。新的合约安排提高了要素的报酬,使要素资源从与政府的合约中脱离,进入了市场交易。大量要素的市场交易催生了新的职业与市场平台,如各种住房中介、婚姻介绍所、担保信贷公司、建材市场、蔬菜市场等。今天,民营企业、民办学校、民营银行在城市中的数量越来越多。中心缔约人的缔约范围越来越小,要素自发的合约范围越来越大。城市的改革历程,是政府作为中心缔约人的合约边界逐渐缩小的过程。
三、城市合约结构的选择
(一)合约结构界定权责边界
城市有多种合约结构。有的城市的合约结构有中心缔约人,有的城市则更像一张扁平的网络,缺乏中心缔约人。例如,政府、国企、民企、村组织运营的城市,往往具有中心缔约人。但也有许多城市,例如自发生长的城中村,缺乏中心缔约人。
不同的合约结构,具有不同的利益分享和责任分担机制。政府运营的城市,政府及其平台公司承担了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投入,也获取了土地出让金等收益,并借助土地获取了大量融资。但是,如果政府经营的城市因欠债而破产,长期资不抵债,最终要靠向居民征税或通货膨胀来偿还债务,或者违约提高金融体系的风险。
民营企业运营的城市,民营企业承担了基础设施投入,分享了土地出让、租赁等收益。如果民营企业运营的城市破产,民营企业可能较难提供公共服务,对居民违约,但无法向居民征税,也搞不了通货膨胀。银行等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的融资也更加谨慎。
村庄就地城市化,缺乏地方政府协调提供的道路、地铁等公共服务。如果集体土地入市,村庄和村民可以直接分享土地出让收益,但也要承担前期的基础设施投入。村庄及村民可以利用集体土地及住房向银行进行抵押贷款,获得更多的收入。村民也要像城里居民买房一样,归还银行的贷款。
不同城市合约的融资机制不同。政府运营的城市依靠地方国企平台公司向银行借贷或在市场上发债。民营企业则多了上市融资的途径。国企平台公司的土地物业等资产的产权往往不够清楚,上市的难度更大。村庄有集体建设用地,但是目前土地入市及抵押融资的途径还不够畅通。
(二)协调成本影响合约结构
我国的土地产权较为分散,为土地资源的转让重组带来了较高的成本。农村的产权越分散,协调不同产权所有者的成本越高,与农民签订合约转让产权的成本就越高。集体土地流转的限制越多,与外来企业、居民签订厂房等租赁合约的成本就越高。
合约结构的不同,部分地反映了协调城市分散产权的方式不同。政府协调土地资源,依靠的是国家授予的合法强制力,民营企业(如成都蛟龙港)经营的城市依靠的是产权者之间的合约激励,村庄(如北京昌平郑各庄)经营的城市依托的是农村熟人社会的信任。
如果在某些地区,农村土地产权较分散,对土地流转的限制较严,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较多,以民营企业为中心缔约人的合约城市的交易费用较高,政府主导城市化的可能性就较大。如果在某些地区这些缔约成本较低,民营企业参与城市化的可能性就会较大,政府的边界会更小。哪种城市合约结构更可能出现,是当地的土地产权分散程度、对土地转让的限制、规划权的安排、土地出让收益的制度安排、融资成本等条件规定的总体交易费用最小化的结果。
(作者路乾为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中国土地制度与城市化、经济史等,著有专著《美国银行业开放史:从权利限制到权利开放》,论文《城市的合约性质——民营城市蛟龙港》、《土地财政是伟大的制度创新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