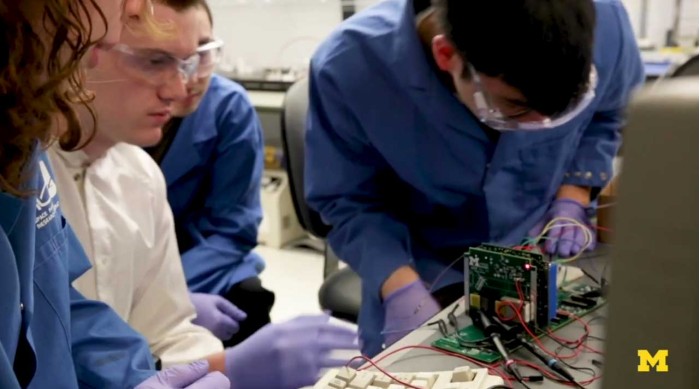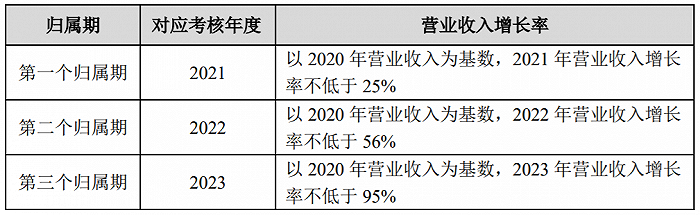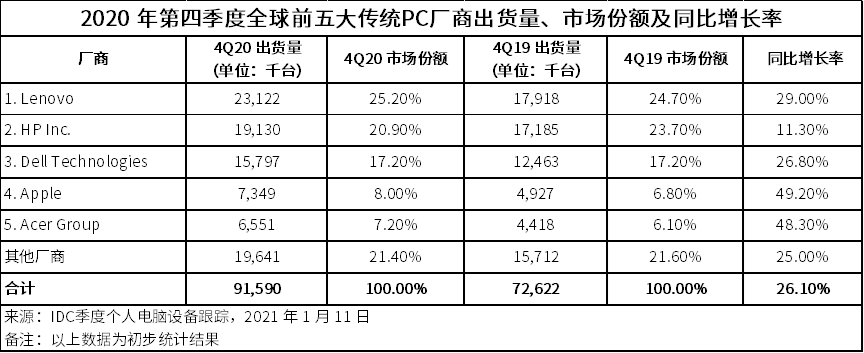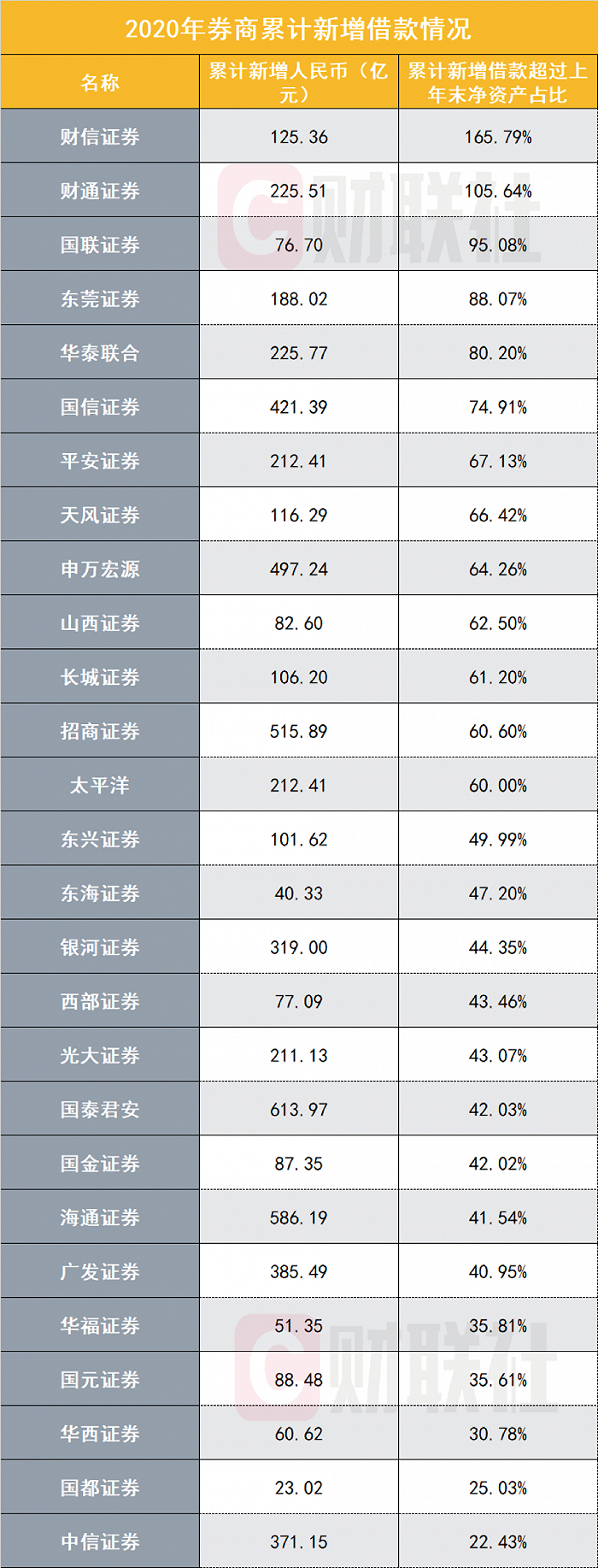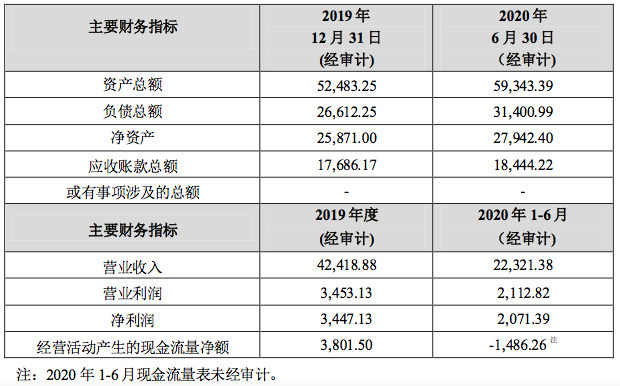直播中,英姐拿放大镜看手机屏幕上的文字。本文照片均由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杨海/摄
直播中,英姐拿放大镜看手机屏幕上的文字。本文照片均由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杨海/摄作者 杨海
见到英姐之前,我很难把她和“主播”这个职业联系起来。这个50岁的农妇,曾经以卖烤红薯为生。也许是常年在外摆摊的原因,她的皮肤粗糙,头发随意地拢到耳后。她身材瘦小,又总是穿着一件肥大的旧T恤,上面满是污渍。
她和老伴在2020年4月份从老家吉林省吉林市南下来到义乌北下朱村,成为一名带货主播。北下朱村不大,但足够包容。这里吸引着各种背景的创业者,有“颜值主播”,也有“才艺达人”,但更多的还是普通人,他们可能是农民、小商贩,或者毕业不久的大学生。
换句话说,北下朱是个草根创业者聚集的地方。那些受疫情影响,陷入困境的人们,被北下朱的造富神话吸引,希望能在这里完成咸鱼翻生,或者底层逆袭的故事。从这一点看,英姐和北下朱的其他创业者没什么两样。只不过,她更偏执。
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年,“直播带货”是个绝对的热词。上半年,不断刷新的成交量、明星和商业领袖的试水,似乎都在回应“万物可播”“全民可播”的口号,很多人都相信,一个现象级的商业模式又出现了。
那时的义乌,受疫情重创的国际商贸城比往常冷清不少,但仅相隔3公里的北下朱村却被一种热烈,甚至疯癫的气氛笼罩——每天下午,北下朱主街十字路口的主播们都会进入亢奋的状态,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夸张的表演,直到拍出一条满意的段子。接着往下走,你随便拐进一条巷子,都有可能遇到正举着商品,对着手机大声介绍的主播。
到了下半年,人们发现那些惊人的数据堆造出来的,可能是个泡沫。明星带货频频“翻车”,粉丝的消费热情开始降温,都让这个一路狂飙的行业逐渐回归正常。
英姐没工夫了解这些,她像台没有停止键的机器,不断运转。她总是很匆忙的样子,接受采访期间,有时碰面,她会一边快走一边打招呼,似乎没有什么能让她停下来。
有时分不清,她到底是精力充沛,还是在硬扛。她眼泡浮肿,大多时候声音都是沙哑的。她通常会直播到深夜1点左右,有时也会持续到凌晨三四点。最长的一次,她连续直播了18个小时。无论多晚休息,她一定会在早上7点起床,然后开始重复一天的工作——拍段子、剪视频、直播……
半年前,她在快手每天能卖出十几单商品,大概收入20元。这种状态持续几个月后,她加入了一个小型的MCN团队,换了直播平台,在抖音“二次创业”。
这次艰难的转向并没有给她带来太多变化,除了两次“一两千元”的“爆单”外,3个月来,她每天的出单量反而降到了个位数,“一般都到不了5单”。
“不到山穷水尽,我绝不回头。”她带着哭腔说。
可什么才是山穷水尽呢?英姐说,比起以往,北下朱也冷清了不少。熟人不断离开,十字路口也没以往那么热闹了。
两个月前,她的老伴去了江苏一家工厂,成了流水线工人。他和那些短暂落脚,又匆匆离开北下朱的创业者一样,被惨淡的业绩打败,对直播带货彻底失望,最后放弃“幻想”,回到了靠出卖体力吃饭的生活。
她把开支降到最低。每天22元的房租,2元电费,3元的共享单车车费,她一天只吃两顿饭——团队免费提供中午和晚上两顿盒饭。即便如此,她每天依旧入不敷出。
她终于相信了这个行业的逻辑,“不花钱买流量,就别想爆单”。现在,她指望着自己的某条视频忽然窜上热门,团队老板承诺过帮她“买流量”。

在北下朱就要一年了,英姐把心得、经验记满了快30个笔记本。但直到现在,她的作品很难称得上优秀。她虽然努力在介绍商品时加入一些故事,但看起来依然干瘪。
在一个抖音视频里,她讲述了自己初来北下朱时的经历。和那时相比,现在她还是原来的衣服,一样的表情,甚至连发型都没变。她就像一头倔强的驴子,无论如何努力,都是在原地绕圈。而在北下朱,没有变化是最可怕的事。
在这场商业游戏里,“头部主播、腰部主播”才有资格出现在各种行业报告和新闻报道中,这些像英姐一样的“脚部主播”甚至不值得一提。他们进场或者离开,成功或者失败,对行业都微不足道。
元旦那晚,英姐一个人在出租屋里大哭了一场。离家快一年了,她最担心自己的父母。两位老人都已经80多岁,父亲说过最大的愿望是看一眼西湖,她想在开春时赚够钱,帮父亲了却这个心愿——这是个不小的计划,她眼下的愿望是回东北老家过年,但还在为路费发愁。
支撑她继续留在北下朱的,还是对“爆单”的期望——那是指某条短视频或者某场直播忽然大火,带动商品冲到几万甚至几十万单的销量。英姐相信,她的尴尬和困境在这个机会到来时都会迎刃而解。她照常出现在北下朱的街道上,像闹钟一样准时,不管身边人来人往,或者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她把未来都押注在这个最大的新年愿望上,尽管她也不能确信它是否会真正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