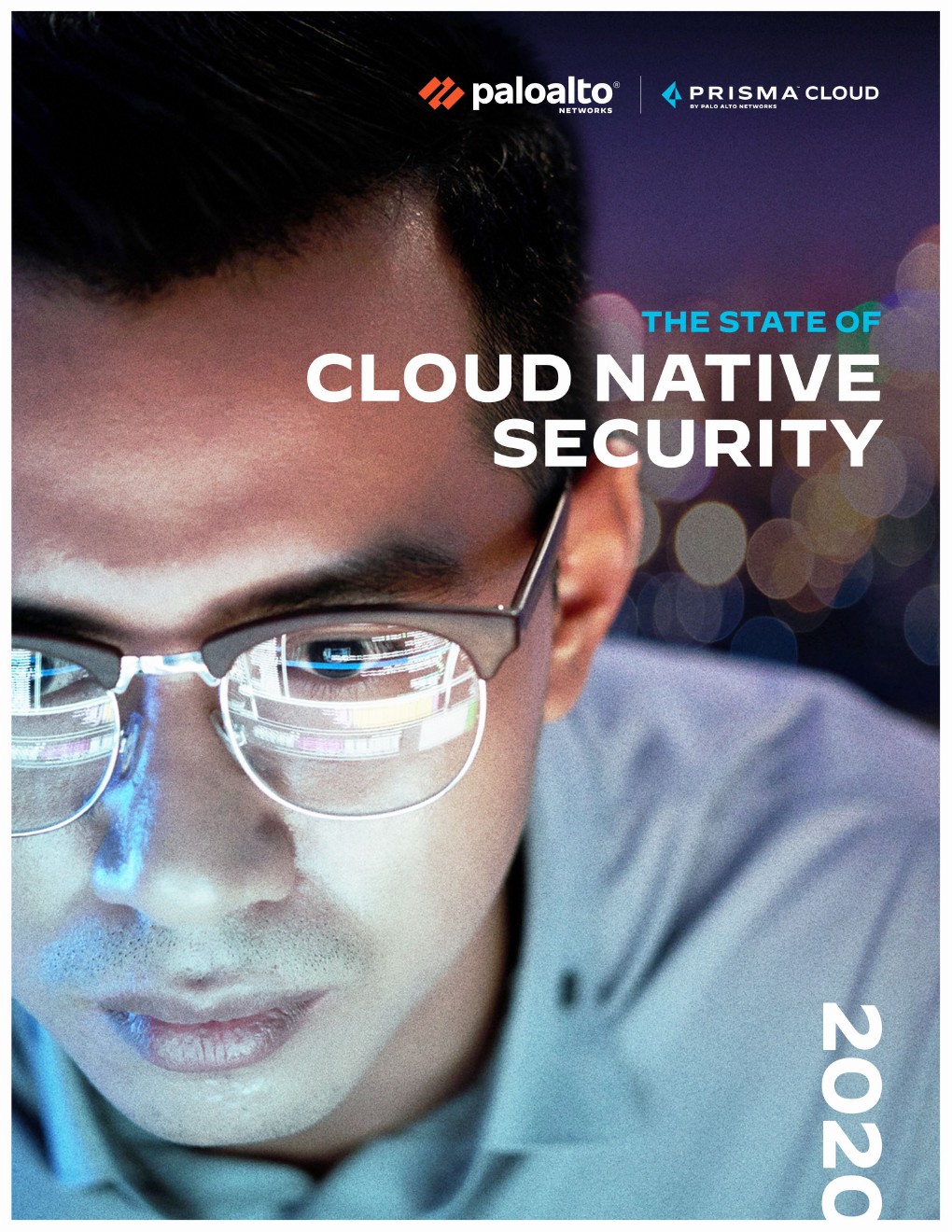原标题:保罗·策兰:我们互爱如罂粟和记忆 | 一诗一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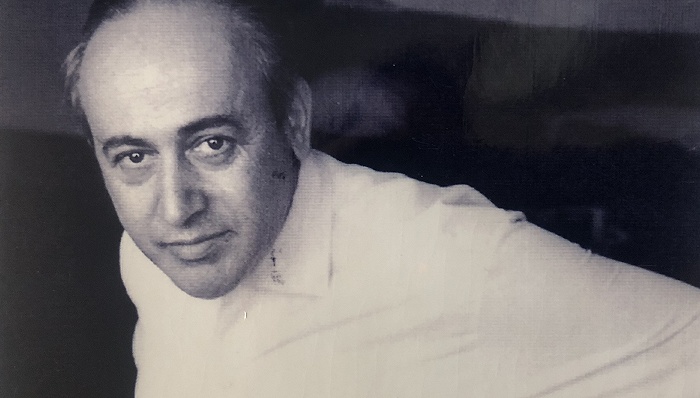 保罗·策兰(Paul Celan,1920—1970),德语犹太诗人。(图片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提供)
保罗·策兰(Paul Celan,1920—1970),德语犹太诗人。(图片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提供)保罗·策兰出生于泽诺维茨——一个有六百多年历史的、以德奥和犹太文化为主要基础的城市(1940年以后被并入苏联乌克兰共和国),他拥有一个正统的犹太教家庭,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在家中只说标准德语,青年时期就开始以德语写诗。然而,这种对德国语言文化身份的认同却被突如其来的战争彻底颠覆了。
1941年,德国侵入苏联,大肆焚毁犹太教堂。随后,四万多名犹太人被强行押送到集中营,其中就包括策兰的父母,策兰本人则被纳粹劳动营强征为苦力,在远离家乡的地方修筑公路和桥梁。就在当年秋天,策兰得到噩耗:他的父亲在集中营里死于斑疹伤寒,母亲因丧失劳动能力被纳粹枪杀。当1944年策兰从解散后的劳动营回到故乡时,他已失去一切。泽诺维茨的犹太人一大半惨遭屠杀,他童话般的家园成了乌有之乡。在极度悲伤之下,策兰离开家乡,经维也纳辗转流亡,最终定居在巴黎。
身处异乡的策兰并未因此被德国文学界遗忘。在当时已成为文学新星的女诗人巴赫曼的力荐下,策兰在流亡期间所写的诗歌被越来越多西德作家认可。1952年,策兰在西德正式出版了第一部诗集《罂粟与记忆》,诗集名出自策兰写给巴赫曼的《花冠》一诗:“我们互爱如罂粟和记忆。”罂粟是一种有毒的花,从中可以提炼鸦片,而鸦片是一种忘却、麻醉、阵痛的物质。“罂粟和记忆”是策兰前期创作中相当重要的两种对位性元素,它们隐喻了犹太人对其历史命运的共同心理。犹太人也想忘却历史,因为他们不想被奥斯维辛的可怕幽灵纠缠,但真正的忘却又是不可能的。策兰几乎一生都在书写、承继这种纠缠的伤痛。作为一个从大屠杀中有幸逃脱的人,策兰在诗中不止一次表达了他的愧疚感——比起活着,他更渴望加入死者的队列。
《罂粟与记忆》的出版在德语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尤其是其中的《死亡赋格》一诗,由于反映了奥斯维辛的苦难而成为战后具有纪念碑性质的时代之诗。策兰曾如此评价自己的诗歌创作:“在一切丧失之后只有语言留存下来,还可以把握。但是它必须穿过它自己的无回应,必须穿过可怕的沉默,穿过千百重谋杀言辞的黑暗。……它穿过它并重新展露自己,因为这一切而变得‘充实’。”此后,策兰的创作日趋深化、发展,出版了《言语栅栏》《无人玫瑰》《换气》《线太阳群》等多部重要诗集。他试着通过语言来确定自己的位置,勘探出自己的现实。
这一过程无疑需要巨大的勇气,因为它意味着诗人必须抵达毁灭的深处,而现实是残酷的。1970年4月,策兰因无法克服的精神创伤在巴黎投塞纳河自尽。日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灰烬的光辉》收录了策兰一生诗歌创作的精华,揭示了他的精神和艺术历程,也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痛苦而又卓异的心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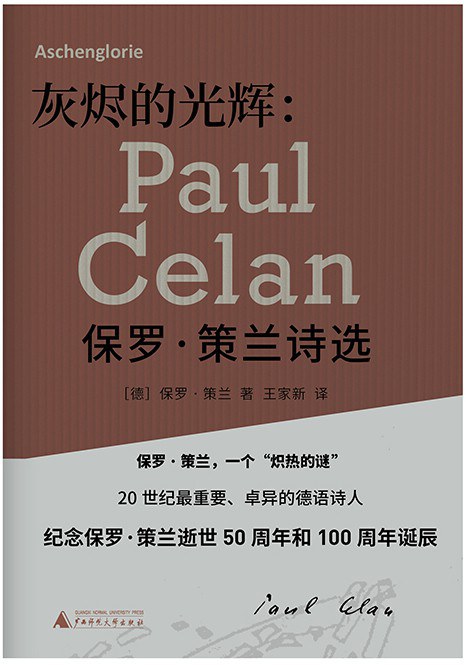
《灰烬的光辉:保罗·策兰诗选》
[德]保罗·策兰 著王家新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01
花冠
秋天从我手里吃它的叶子:我们是朋友。
从坚果里我们剥出时间并教它如何行走:
于是时间回到壳里。
在镜中是礼拜日,
在梦里被催眠,
嘴说出真实。
我的眼移落在我爱人的性上:
我们互看,
我们交换黑暗的词,
我们互爱如罂粟和记忆,
我们睡去像酒在贝壳里,
像海,在月亮的血的光线中。
我们在窗边拥抱,人们在街上望我们:
是时候了他们知道!
是石头到了开花的时候,
是不安的心脏跳动,
是时候成为时候的时候。
是时候了。
译注:
[1]《花冠》为策兰写给巴赫曼的一首诗。巴赫曼在给策兰的回信中说:“我常常在想,《花冠》是你最美的诗,是对一个瞬间的完美再现,那里的一切都将成为大理石,直到永远。”(《心的岁月:策兰、巴赫曼书信集》,芮虎、王家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死亡赋格
清晨的黑色牛奶我们傍晚喝
我们正午喝早上喝我们在夜里喝
我们喝呀我们喝
我们在空中掘一个坟墓躺在那里不拥挤
住在那屋里的男人他玩着蛇他写
他写当黄昏降临到德国你的金色头发呀玛格丽特
他写着步出门外而群星照耀着他
他打着呼哨唤出他的狼狗
他打着呼哨唤出他的犹太人让他们在地上掘个坟墓
他命令我们给舞蹈伴奏
清晨的黑色牛奶我们夜里喝
我们早上喝正午喝我们在傍晚喝
我们喝呀我们喝
住在那屋里的男人他玩着蛇他写
他写当黄昏降临到德国你的金色头发呀玛格丽特
你的灰烬头发苏拉米斯我们在风中掘个坟墓躺在那里不拥挤
他叫道朝地里更深地挖呀你们这些人你们另一些唱呀拉呀
他抓起腰带上的枪他挥舞着它他的眼睛是蓝色的
更深地挖呀你们这些人用铁锹你们另一些继续给我演奏
清晨的黑色牛奶我们夜里喝
我们正午喝早上喝我们在傍晚喝
我们喝呀我们喝你
住在那屋里的男人你的金色头发玛格丽特
你的灰烬头发苏拉米斯他玩着蛇
他叫道把死亡演奏得更甜蜜些死亡是从德国来的大师
他叫道更低沉一些拉你们的琴然后你们就会化为烟雾升向空中
然后在云彩里你们就有座坟墓躺在那里不拥挤
清晨的黑色牛奶我们在夜里喝
我们在正午喝死亡是一位从德国来的大师
我们在傍晚喝我们在早上喝我们喝你
死亡是一位从德国来的大师他的眼睛是蓝色的
他用铅弹射你他射得很准
住在那屋里的男人你的金色头发玛格丽特
他派出他的狼狗扑向我们他赠给我们一座空中的坟墓
他玩着蛇做着美梦死亡是一位从德国来的大师
你的金色头发玛格丽特
你的灰烬头发苏拉米斯
译注:
[1]据研究材料,该诗写于1945年前后,1947年译成罗马尼亚文在布加勒斯特初次发表时为《死亡探戈》,后来被策兰改为《死亡赋格》(“Todesfuge”)。而这一改动意义重大。它不仅把集中营里的屠杀与赋格音乐联系起来,而且把它与德国文化及其象征巴赫联系了起来,因而对德语读者首先就产生了一种惊骇作用。
[2] 玛格丽特(Margarete),在德国家喻户晓的歌德《浮士德》中女主人公的名字。
[3] 苏拉米斯(Shulamith),在《圣经》和希伯来歌曲中多次出现,犹太女子的象征。“你的灰烬头发苏拉米斯”,在原诗中,策兰用的不是“grau”(灰色),而是“aschen”(“灰”“灰烬”),这本身就含着极大的悲痛。全诗的重点,也正是“你的金色头发”与“你的灰烬头发”的“对位”。与此相对应,诗中的“他”和“我们”也都是在对这两种不同的头发进行诉说。“他”(集中营的纳粹看管)拥有一个迫害狂的全部邪恶本性,但这并不妨碍他像一个诗人那样“抒情”——在他对“金色头发”的咏叹里,不仅有令人肉麻的罗曼蒂克,还有着一种纳粹式的种族自我膜拜。
[4] “清晨的黑色牛奶……”这一句不仅是全诗的主题句,它在后来反复出现时奇特的时间顺序也应留意,据约翰·费尔斯蒂纳在《策兰评传》中提示,这里面还有着《圣经·创世记》的反响:“上帝称光为昼,称暗为夜。那里还有傍晚,还有早上:第一日”。而策兰对之的模仿可谓意味深长。这种模仿使“奥斯维辛”与一个神示的世界相对照,从而产生了更强烈的震撼力。
[5] 大师(Meister),既指精湛的能工巧匠,也指杰出艺术家、艺术巨匠。而“从德国来的大师”不仅擅长艺术,也擅长虐待人和杀人,他拥有绝对的权力。
一次旅行
这是一个使你风尘仆仆的时刻,
你在巴黎的房屋,成了你双手的祭坛,
你的黑眼睛,成为眼睛中最深的。
这是一个牧场,一队马等着你的心。
你骑上它而你的头发将被吹起——那是禁忌。
留在那里并挥手的人,不知道它。
数数杏仁
数数杏仁,
数数这些苦涩的并使你一直醒着的杏仁,
把我也数进去:
我曾寻找你的眼睛,当你睁开无人看你时,
我纺过那些秘密的线,
上面,你冥想的露珠
滑落进那些罐子,被言语守护,
无人之心找到他们的所在。
只有在那里你完全进入你自己的名字,
以切实的步伐进入自己,
自由地挥动锤子,在你沉默的钟匣里,
那听到的,向你靠近,
而死者的手臂围绕着你
于是你们三个漫步穿过黄昏。
让我变苦。
把我数进杏仁。
译注:
[1] 杏仁是苦涩的,犹太人逾越节吃的面饼要放一种苦草,以纪念祖先从埃及出来的苦难;至于“醒着”,德语的“杏仁”(Mandeln)和希伯来文的“清醒”发音很接近。变苦也就是变清醒,哪怕是痛苦地“醒着”。
[2] “无人”(Niemand),策兰诗歌中经常出现的一个重要指称。人们惯于把“无人”读解成“没有人”,但在策兰的诗中,“无人”往往已由一种否定性的陈述(“没有人”“没有任何人”)变成了一个“名词”:对一种更高存在的命名。约翰·费尔斯蒂纳在访谈《专注——灵魂的天然祷告》中称“无人”为策兰对上帝的“新定义”。这里的“无人之心”可理解为这样一种灵魂存在。
[3] “你们三个”有多种解释,在这里可以理解为诗人与死去的父母。策兰对父母的惨死一直怀有内疚感,认为自己未能保护住父母,另外,父母的死也给他带来了无限孤寂的孤儿感(策兰为独生子)。在这里他渴望加入死者的队列,回到父母那里,一起漫步穿过生与死的黄昏。
无论你搬起哪块石头
无论你搬起哪块石头——
你都会让那些
需要它保护的暴露出来:
现在他们赤裸着
变换着蜷缩之所。
无论你伐来哪棵树——
用来
做床架,在那上面
魂灵们再次聚集,
仿佛它们亘古如初
不会
发抖。
无论你说出哪个词——
你都有欠于
毁灭。
西伯利亚
弓弦之祈祷——你
不曾接受到,它们曾是,
你所想的,你的。
而从早先的星座中
乌鸦之天鹅悬挂:
以被侵蚀的眼睑裂隙,
一张脸站立——甚至就在
这些影子下。
那微小的,留在
冰风中的
铃铛
和你的
嘴中之白砾石:
也卡在
我的咽喉里,那千年——
色泽之岩石,心之岩石,
我也
露出铜绿
从我的唇上。
现在,碎石旷野尽头,
穿过蒲苇之海,
她领着我们的
青铜街巷,
那里,我躺下并向你说话,
以剥去皮的
手指。
译注:
[1]这应是一首献给曼德尔施塔姆的哀歌(实际上,策兰的整本诗集《无人玫瑰》就以“纪念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作为题献)。因为很难了解铁幕下苏联的真实情况,策兰想象曼德尔施塔姆有可能死于西伯利亚(曼德尔施塔姆实际上于1938年底死于押送至远东流放地的中转营里)。
[2] “乌鸦之天鹅”(Rabenschwan):策兰把“Rabe”(乌鸦)与“Schwan”(天鹅)拼在一起创造的一个意象。
你的梦
你被你自己的梦顶醒。
以开槽的词痕
十二次
螺旋形进入
它的犄角。
它发出的最后触顶。
向上摆渡——
在
垂直、窄狭的
日子裂隙里:
把
创伤的阅读运送过去。
纠缠的石头
纠缠的石头,
灰绿色,被释放到
墙角。
街头买来的红月亮
将那一小隅世界
照亮:
那就是
你。
在记忆的空白
挺立着专横的蜡烛
述说暴力。
本文诗歌选自《灰烬的光辉:保罗·策兰诗选》一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