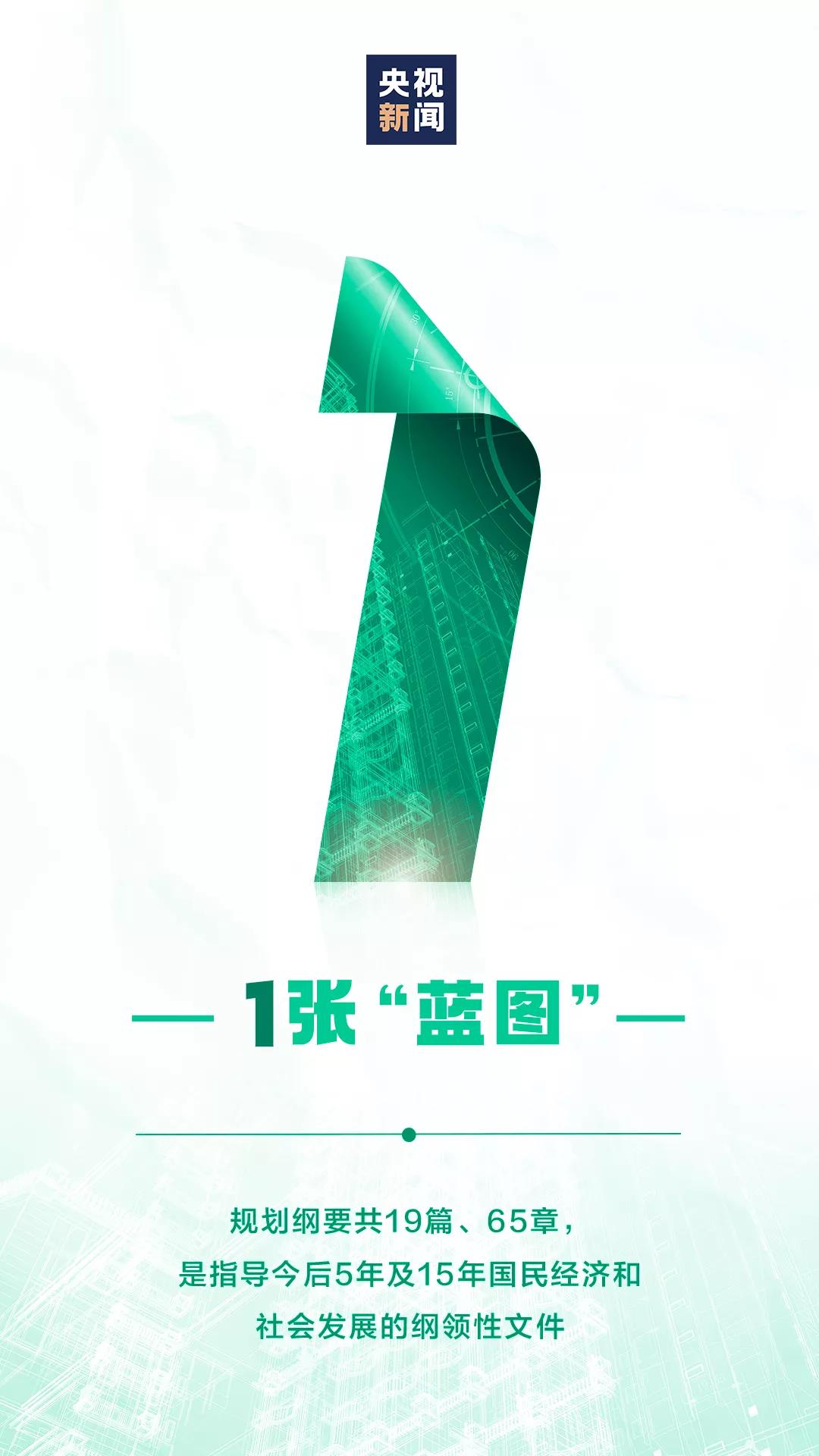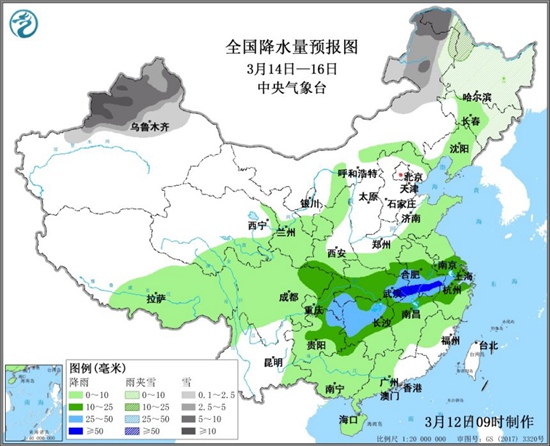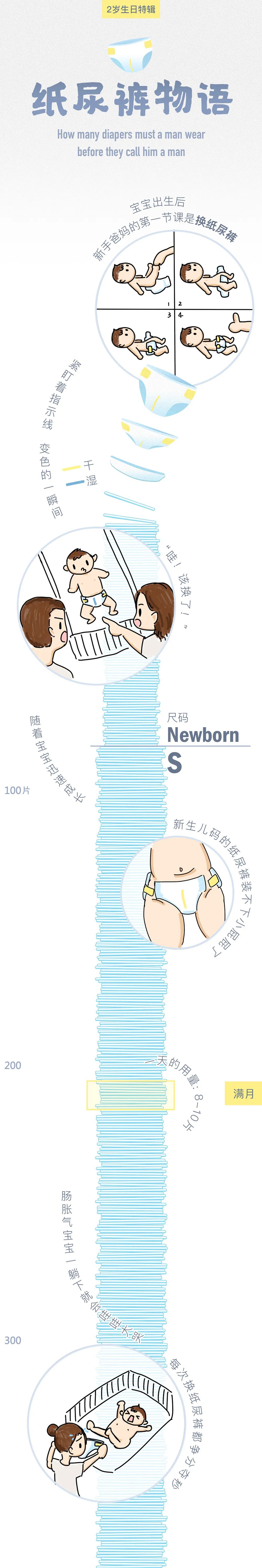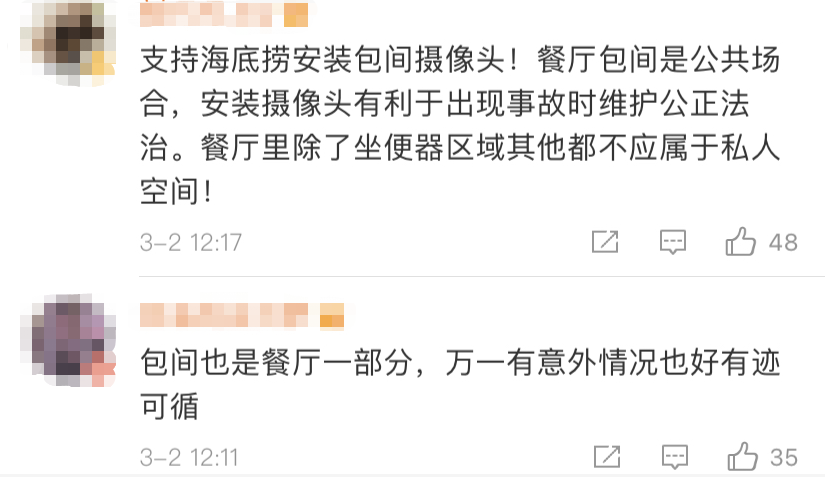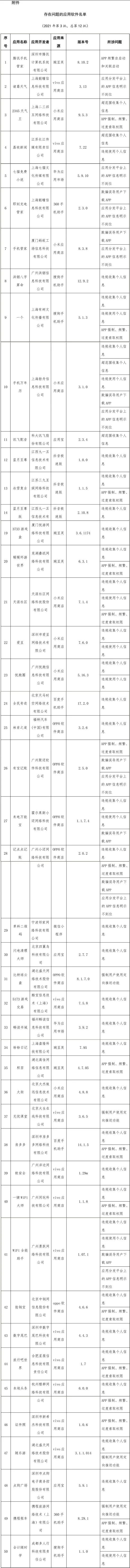“一个小小的病毒对人类文明的进程产生了影响”
问: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总结您过去一年的感受,会是什么词?
施一公:过去一年,如果我要选一个关键词,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不同寻常”。贯穿全年,大家特别关注的就是新冠疫情,疫情打乱了生活、学习、科研,甚至办企业等的节奏,整个社会、几乎每一个人,都受到疫情影响,确实是非同寻常。
中国政府很有作为,我们很快控制住了疫情,到2020年4月8日武汉就“解封”了。5月、6月学校开始开学、学生上课,线下上课就开始有了。
整体来讲,我觉得全世界受新冠疫情的冲击都非常大。有时候我会这样讲,一个小小的病毒对人类文明的进程产生了影响。我想这句话是不为过的,因为它把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把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交流方式、组织之间的交流方式、科学研究的合作方式都改变了。
“如果发挥自己的特长和积累,能够做一些事,让自己心里愉悦,可能是最关键的”
问:您2008年担任清华全职教授,从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到副校长,2018年又辞去清华大学副校长创办西湖大学,做出这些人生重大抉择时,您首先考虑的是什么?
施一公:实际这个过程是渐进的,绝对不是一晚上心血来潮,想了一晚上想明白了。在我从小到大的价值观、行为规范里,我一直觉得天生我材必有用,似乎总是要做点啥事,这点是非常明确的。我这辈子都没有觉得,我哪一天要找一份工作,要为工作担心,从来没有过。因为我觉得人如果成了衣食住行的奴隶的话,这辈子就太难受了。
在美国时,我博士一毕业就有点想回来,后来做了博士后又想回,但阴差阳错去了普林斯顿大学做老师,做教授,做了几年又想回,一直觉得为啥不回来呢?这种感觉很强烈。其实我自认为也算融入了美国的主流社会,去的学校是美国最顶尖的大学,教授职位也拿到了,和同事之间也相谈甚欢,在普林斯顿大学给本科生上课、给博士生也讲课。总的来讲,应该是进入了美国的主流社会,但这种(异国他乡的)感觉就是不一样,肯定是不一样。
有时候对我来讲,我怀疑是综合的,从我小时候、从河南、从驻马店、从我父母、从我的个人经历,你的骨子里有一种东西,觉得回来挺自然的。我回来不是一晚上的决定。当然了,当时清华大学相关负责人找我谈话的时候,确实第二天我就说,我全职回清华好了。
因为早就想这样做了,不存在作思想斗争、纠结半天,没有这个问题,心里一直觉得那么长时间终于要做这件事了,是一种期望、期待、期盼,觉得今后大有所为。做啥并不知道,不知道自己将来在清华能做到什么程度,但是觉得天生我材必有用,一定有很多东西可以做。
其实这个可能也比较难总结,对我而言,如果能发挥一些自己的特长,自己一些过去的积累,能够做一些事情,让自己心里愉悦,可能是最关键的。我想这样一个比较简单的做事出发点,应该说和我从清华大学辞去副校长,来到西湖大学,和一大批同道,一起来创办这所学校都是同样的考虑。
我觉得,对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一直处在改革发展中的国家,我们的科技、教育、对学生的培养、大学制度建设,其实也需要不断改革,才能适应国家的发展,才能让国家未来有更好的可能性。因为要应对未来的挑战,而这样的一个挑战、尝试需要有人去做。像我这样比较愿意折腾的人,愿意去离开现在的所有,去做一件新事情。
“你一定是回忆到多少年以前,当时有过多少困难,多少矛盾,多少心理失衡,多少焦虑,你才会刻骨铭心”
问:离开清华去创办西湖大学,是一种怎样的探索试验?
施一公: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朋友问我,一公你后不后悔?说有时候办一件事这么难。当然办大学肯定会有困难,因为它是一件新生事物,肯定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但当然不后悔。而且我鼓励我的同事,我告诉他们,我说你们想,如果过了5年,过了10年、20年,你回望这段历史的时候,说是轻轻松松、一帆风顺,你一定会觉得没意思,你一定是回忆到多少年以前,当时有过多少困难,多少矛盾,多少心理失衡,多少焦虑,你才会刻骨铭心,你才会觉得这辈子足了,知足了,你经历过了。
当然我自己从骨子里认为,我们做的事情不仅和国家的改革合拍,而且我们经常希望能往前走一步,为国家下一步改革铺路、探索,让国家下一步改革有据可依,看一看我们怎么做的,我们成功了,在哪儿成功,失败了,为什么,提供一个借鉴。中国这样的大国尤其需要这样的借鉴,就像我们做科学研究一样,你是不可能每一次试验都成功的。
像这种情况下,在科技和教育领域是需要一些探索的,而这样的探索特别适合一个小型大学去做。因为规模小,没有那么大的社会影响,但是因为小,又比较灵活,遇到一些问题相对容易解决,如果有一些东西做得不太对,也容易纠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在为国家做事,毫无疑问,我相信我的所有同道,他们骨子里都这样认为,是在为国家做事。
“一旦忘记了初心,不能按自己当时的理念、办学定位去做的话,那就失去意义了”
问:创办西湖大学2年多,探索试验最核心的点在哪里?
施一公:西湖大学首先办学定位,小而精、高起点、研究型。我们希望为国家探索新型大学治理制度,立足中国大地,符合中国国情,又符合国际化办学规律,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第二,我们希望在大学里探索一套适合中国国情,又鼓励创新的科技评价标准。第三,我们希望培养富有社会责任感的拔尖创新人才。
应该说西湖大学现在的发展和我们当时的理念,对大学的定位——“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等等是一致的,我们没有偏离我们的航向。对我们来讲,这样做原因太简单了,就是你一旦忘记了初心,不能按自己当时的理念、办学定位去做的话,西湖大学就失去意义了。它就不再是一个探索的主体,所以我们也在不断地提醒自己。
但是有一点我也要说,西湖大学从来不是要标新立异地去做事情,我们做事情绝对不会说在中国没有人做,所以我们要去做,这不是出发点。我们做事情一定是说在中国大地上,这样的事情首先符合我们的国情,其次符合国际化的规律,我们认为很合理,但是在中国还没有尝试,我们就可以去做,尝试一下在中国大地上,可不可以把一些事情做起来,能够让我们的教育系统,让我们整个社会,接受这样的一个新的做事方式、新的机制。
“办西湖大学不是为国家再增添几百篇论文,把我们的影响因子再往上冲一冲”
问:西湖大学在科研评价体系上做了哪些探索?
施一公:每一位入职的年轻人,年轻的博士生导师,我们都会跟他们讲,在西湖大学不需要有发文章的压力。因为办西湖大学不是为国家再增添几百篇论文,把我们的影响因子再往上冲一冲,都不是。
但是我们希望你在西湖大学能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在你的领域内,几年之后做出来的工作能自成一体。如果缺了你这份工作,你的领域会有一个缺口,不能自圆其说,中间发展过程会受冲击。如果这样,你就做对了,西湖大学会希望你留下来。如果做了六七年以后,你的工作虽然发了很多文章,影响因子、引用率也高,但说不出来哪项工作是你独特的工作。把你的文章全部隐去,在你的领域内,学术发展基本不受影响,那对不起了,西湖大学你可能就不太合适。
我们因为做小而精的大学,机制相对灵活。虽然有这样的规定,比如说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进来后6年,要对他进行评估,不好的要离开。但实际操作的时候,如果他能说服我们,我正在进行一项世界重大前沿课题,而且已经有了一定进展,我们会很实事求是(地评估)。如果通过学术委员会的评估,他确实是在坐冷板凳,全力以赴地探索,他一定会得到时间的延长。
“个人奋斗和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相吻合,是最好的一种结局”
问:您提到西湖大学一个根本任务是要培养富有社会责任感的拔尖创新人才。“拔尖创新人才”可能大家比较好理解,为什么这么强调“富有社会责任感”?
施一公:我每次说到培养什么样的学生时,都会特意加上“富有社会责任感”几个字。一个学生往前走,一定是靠个人奋斗。我们要认可个人奋斗,但个人奋斗和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是吻合的,只要吻合,相互之间形成彼此之间的融合,它就是很好的一种情况,是最好的一种结局。要教给学生实事求是、客观辨证看问题的能力,让学生自发地产生社会责任感。
“从最根本上来讲,我是一个科学家,不管工作有多忙,我一定会将科学研究坚持下去”
问:创办学校这几年,您自己的科学研究进展怎么样?
施一公:担任西湖大学校长,当然会影响我的科学研究,但这种影响是我心甘情愿意付出的代价。你看我用了“代价”两字,我想解释一下,首先对我而言,科学研究本身是一件非常愉悦的事情,但是这种愉悦只局限于自身。比如,每次和学生谈完课题我都有种满足感,哪怕是学生遇到问题、并没有进展,但是我提供了观点,与他进行了讨论,也是一种愉悦;如果学生有了突破,科研课题有了进展,我也是很愉悦。就是科学研究始终是一种自身的愉悦,我非常享受这种愉悦。
反过来讲,办大学会遇到一些问题、一些东西,一些事情,做的时候说心里话是有一些挑战的,做的过程可以说加个引号叫“痛苦”,很纠结,很痛苦,但是做好以后也是一种巨大的愉悦。而这样一件事情,虽然对自己在学术界的影响并没有帮助,但对一个国家的探索,一个教育、科技的改革探索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这是另外一种愉悦,我也是非常开心的。这两个在争我的时间,尤其是西湖大学成立以后。
过去两年,应该说我的科学研究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就是2018年10月到现在,心里是有一些纠结,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惆怅,我会觉得我今年(2020年)53岁了,如果我再多一点时间在实验室就好了,会有这种想法,经常会有。但是我也知道,有得必有失,你不过是在平衡一种得和另外一种失,哪个该得,哪个该失。所以我也不断地跟我的学生解释,也不断地在实验室内改进,或者是改变我与学生在实验室的一些科研沟通方式等等,更多用微信、语音、视频,用PPT线上交流等等。
我过去一年(2020年)发表的文章数量创了1995年以来的历史新低,过去25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文章荒”。如果不是新冠疫情让我的工作安排减缓一点节奏的话,会更荒。所以说新冠疫情期间我有两项事情做得多了,一个是跑步,一个是写文章、指导实验,科学研究得到一些恢复。
但是我也想说,从最根本上来讲,我是一个科学家,这是我最根本的属性。不管工作有多忙,我一定会将科学研究坚持下去,而且我也相信我的科学研究一定会有一些重大发现。因为这是我的灵气所在,我自己最专长的就是在科研过程中突然灵机一动,有新的想法出来,带着我的学生去验证,最后证明我是对的。这种情况在过去30年中不知道发生过多少次,我非常享受这个过程。所以说尽管受了一些影响,但是我觉得第一是值得的,第二我也尽力去弥补。
(采访整理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兰琳宗 韩思宁)
【采访札记】
步履不停 一心为公
见到施一公,是在2020年深冬的西湖大学。南国的校园里绿意不减,草木常青。
采访前几天,他刚刚在广州完成了自己的首场全程马拉松。采访当天,他穿了一双黑色运动鞋,手捧一杯咖啡,精神抖擞,笑容洋溢,热情地与我们一一握手。他告诉我们,昨天天气好又忍不住沿着铜鉴湖大道跑了两座山,跑步令他愉悦。
施一公的人生也恰如一场长跑:从留学到回国,从北京到杭州,无论人生“赛道”怎么转换,始终步履不停。在他看来,自己是一个比较愿意折腾的人,很情愿离开现在的所有,去做一件全新的事情。
“在我从小到大的价值观、行为规范里边,似乎总是要做点啥事,做啥不知道,但是觉得天生我材必有用”。这种“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做点啥事”的信念已经印成他生命的底色。“如果发挥自己的特长和积累,能够做一些事,能够让自己心里愉悦,可能是最关键的”,选择回国发展、离开清华到西湖大学都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这种选择和驱使背后是一种更大的人生格局和视野,是一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感和一以贯之的拳拳爱国心。他说,创办西湖大学,是想为国家教育领域下一步改革铺路、探索,“看一看我们怎么做的,我们成功了,在哪儿成功,失败了为什么,提供一个借鉴”。
每每谈及办学的根本任务,他都会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前加上一个词——“富有社会责任感”。他认为学生的个人奋斗值得认可,但个人奋斗和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是要吻合的,把个人奋斗融入国家事业是一种最好的结局。他希望学生们能够客观地、实事求是地、批判性地看问题,拥有独立思考能力和思辨能力,对社会纷繁的现象有自己清醒的理解,从而产生自发的社会责任感。
探索创新、攀登高峰,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问及压力大不大,施一公坦言一直有压力,“做的过程可以说加个引号叫‘痛苦’,但是做好以后也是一种巨大的愉悦”。肩负科学家和教育探索者的双重使命,这一路注定充满艰辛和不易,酸甜苦辣唯有身处其中方能知晓,但他表示从未后悔,言辞中流露的是坚毅和执着——
“你回望这段历史的时候,说是轻轻松松、一帆风顺,你一定会觉得没意思,你一定是回忆到多少年以前,当时有过多少困难,多少矛盾,多少心理失衡,多少焦虑,你才会刻骨铭心,你才会觉得这辈子足了,知足了,你经历过了。”(韩思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