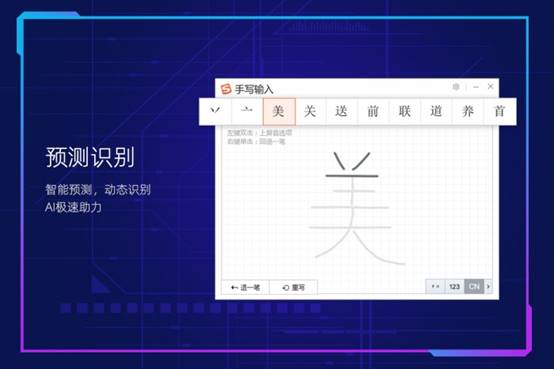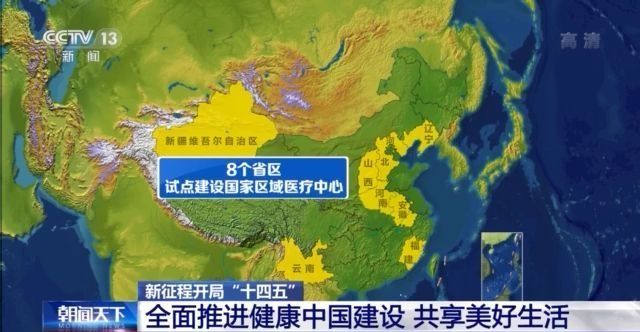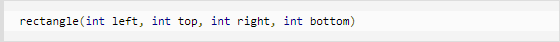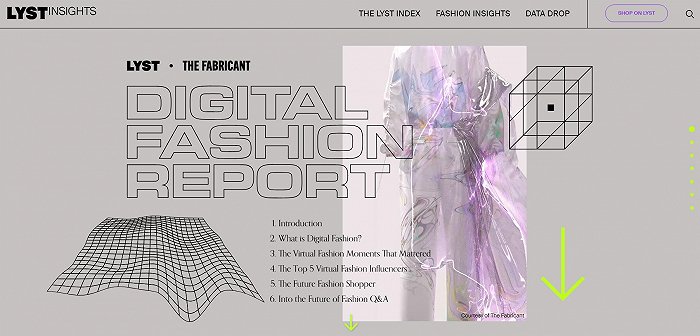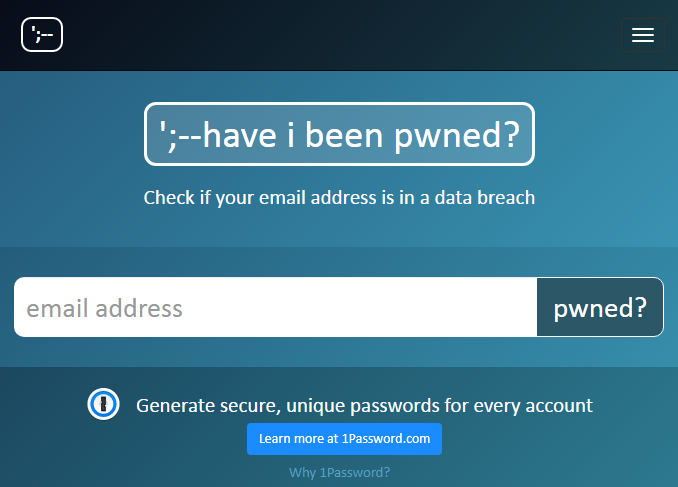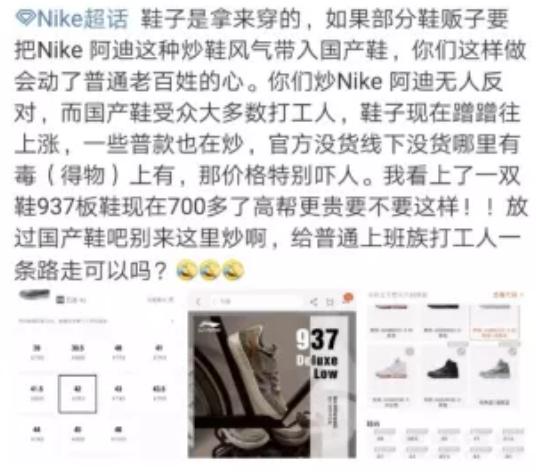原标题:【专访】历史学家赵冬梅:要建立更为精细的民族自豪感,而不是糊涂的民族自豪感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冬梅日前参加了一场题为“历史学家教你如何正确穿越”的直播活动,为渴望穿越到过去实现“人生逆袭”的现代人出谋划策。这位长期关注穿越文、影视剧等流行文化现象的宋史专家很实诚地告诫观众,历史学家即使对历史知识了若指掌,也只能帮助穿越者避免一些伤及性命的错误,无法确保成功,因为制度和文化是古代和现代的鸿沟。“我有一个悲观的想法,那就是现代人掌握的技术手段和能力要依托现有环境和位置才能发挥作用,”她说。
在最近出版的《法度与人心》一书中,赵冬梅开宗明义地指出了制度研究的意义。和许多当代中国人一样,赵冬梅对制度如何深刻纠缠日常生活有着切身的体察:幼时她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因没有户口而时刻面临失学的问题;来到北京后,粮票的重要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赵冬梅至今记得很清楚,她曾又渴又饿地经过北京一家国营粮店,店里有一个卖熟食的门市部,虽然口袋里有100多块钱,但因为没有粮票,她只能对着热腾腾的花卷干瞪眼。现世之人尚且如此,古人更甚——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升斗小民,个人及群体的身份、地位、活动空间乃至命运无不取决于制度。而当芸芸众生的命运交织到一起,就谱写了一个国家的命运。
从秦始皇统一全国到清朝覆灭的两千多年是中国历史上的帝制时代,赵冬梅将帝制中国作为一种国家类型考察其治理情况。与当今民族国家不同的是,帝制中国国家治理的探索是通过朝代与朝代的竞争实现的。尽管制度研究自古以来就是史学的重要目标,但现代历史学家具备独一无二的优势:首先,帝制时代已经结束,我们能够看到其制度成败的全部轨迹;其次,我们能跳脱出传统史学兴亡反思的窠臼,在一个更宏观的层面,思考国家政权历经朝代更迭却始终面临的治理问题,比如官僚的选任、士大夫与皇帝的关系、效率与公平的张力、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兵权的处理等。
“历史并不一直向前”是赵冬梅在《法度与人心》中得出的结论。北宋曾出现了帝制时期儒家政治的最好成绩——政策追求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平衡,批评纠错机制运行有效。但这种政治生态逐渐消失,在元代出现重大倒退,承认并敬畏天下苍生的“江山社稷”变成了皇室私产,强调人格平等的君臣关系沦为尊卑有别的主仆关系,士大夫的批评和监督不再被承认和重视,君主的专制与猜疑一路强化,直到1911年。
在研究制度变迁的同时,赵冬梅不曾忘记投身历史学的初心——对历史中人的命运的兴趣。她长期观察人与制度的互动——“制度会规训人,有权力的人又会改造制度,没有权力的人被逼急了也会反抗制度。”在写作面向公众的通俗历史读物时,她卸下学术写作的包袱,为读者讲起了隐没在历史长河中的小人物的故事。在同期出版的《人间烟火》一书中,她记录了张行婆的故事。这位生活在一千年前的女仆经历了平凡却伟大的一生——她被继母发卖却以德报怨,对故主人知恩图报,将儿女养大成人后离家修行守护庙产,司马光因其“忠孝节义”欣然为之做传。在赵冬梅看来,这些被命运辜负却活出生命的精彩与尊严的普通人,同样值得被历史学家言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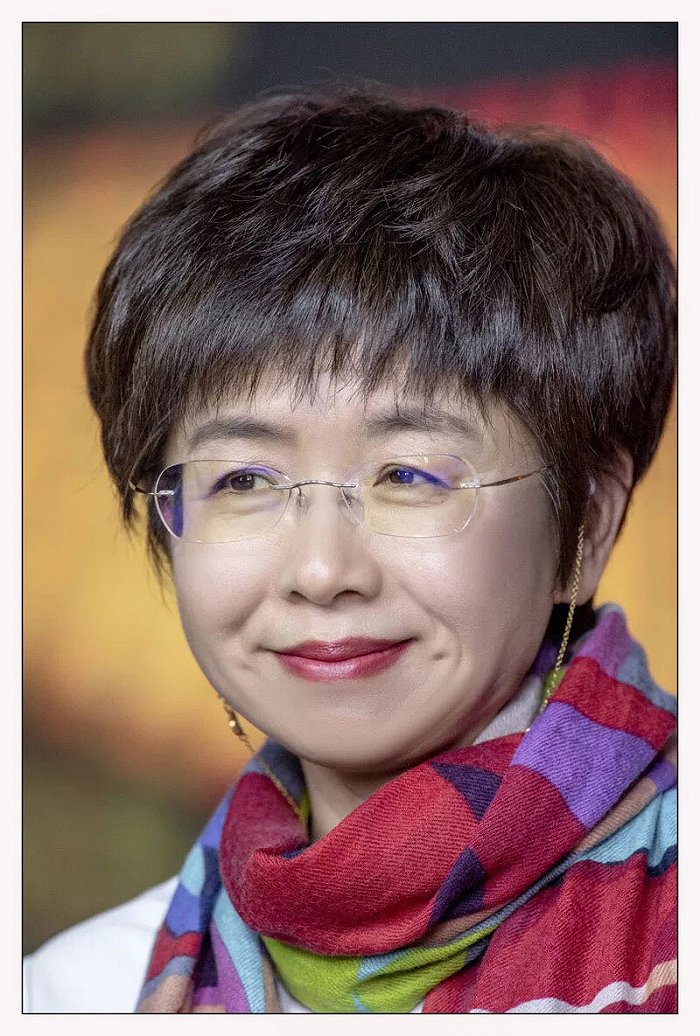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赵冬梅(图片来源:出版社供图)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赵冬梅(图片来源:出版社供图)01 穿越文是年轻人通往严肃知识的一个窗口
界面文化:你是我视野中最愿意在社交媒体上与公众交流、参与讨论流行文化的历史学家之一,这种面向大众言说的兴趣是怎么来的?
赵冬梅:传统史学有教化的功能,现代史学有教育的功能,历史知识还是要分享的。我的兴趣可能和个人机缘有关。当年受邀参加《百家讲坛》,我其实还比较抗拒,但当时的编辑跟我说,你学了那么多,应该和大众分享。这句话很打动我,跟我一贯对历史学的认知是契合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我可能会比普通的历史学者更积极一些。
当你面对观众的时候,其实是同时在做两件事:一是维持严肃学者的形象,二是面向公众的言说。两件事同时做会非常累,我知道个中辛苦。另外还有一层辛苦是不出来讲的学者所不知道的:面向大众言说需要在保持严肃性的同时具备通俗性,深入浅出其实更难。这些年的历史学在这方面的训练可能也不够,大部分学者没有这个训练。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会申明,在北大上课才是我最重要的本分,是我最重视的东西。大学里培养的是历史知识的爬梳能力,培养的是历史学的整理者和建树者;面向公众时是告诉他们你了解的一些东西,不需要思考如何把他们培养成历史工作者,但要让大众知道历史学的尊严在哪。
界面文化:你在《法度与人心》里写道,穿越文的风潮已经从汉唐转向了宋。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你是怎么看穿越文的?“穿越回宋代”反映了当代中国人怎样的欲望与焦虑?
赵冬梅:微博是我了解流行文化的重要窗口,我在微博上能够接触到一些宋粉和剧粉,比如《清平乐》和《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我还能接触到一些明星的粉丝,像是王凯粉。他们蛮认真的,问出来的问题证明他们认真读过书。当然,他们问的很多问题是专业历史学者无法作答的,但他们的态度确实令人钦佩。
我觉得当穿越文不止有清穿、汉穿和唐穿,还有宋穿,这确实是好事情。大家认识到宋朝是我们所向往的。在严肃学者看来似乎不登大雅之堂的穿越文是一种流行文化,也是年轻人通往严肃知识的一个窗口。至少我觉得,现在愿意穿回宋的人愿意了解宋朝,而且他们会知道宋朝和汉唐不一样——宋朝在中华文明史上是有特殊性的,这个就是很了不起的。再加上他们对具体知识的探索和爬梳,我觉得很可贵。
界面文化:去年你写过电视剧《清平乐》的评论文章,认为这是一部少见的对北宋朝堂关系有准确描述的电视剧。这些将时代背景指向宋的作品在国产剧中存在感变强,乃至出现了一种“大宋文艺复兴”的说法。你对此怎么看?在你的观察中,学界内外对宋朝的观感出现了怎样的变化?
赵冬梅:我觉得这种说法可以对接陈寅恪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的一个说法,他认为,当现代学术进来,中国学术将进入焕发新生的时代,这个新生机的走向如何、将来所指之境能够达到怎样的境界,我现在尚不能预言,但有一点是可以预测的,那必定是宋学的复兴。照你的说法,在陈先生说那句话的80年后,终于出现了苗头。
中国大陆学术界对宋是有一个再评价的,之前我们不太重视宋朝。宋朝人自己也说“积贫积弱”,宋朝是一个善于批评的时代,宋朝人对自己是很挑剔的。但近代以来学术界对宋朝的评价不高,这是政治环境的产物。1840年以来,我们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从那个时候过来的现代学术当然愿意看到一些积极的、对外扩张的朝代,像是汉武帝、唐太宗,甚至成吉思汗也会被拿来“壮一下胆色”,其实有一些“缺什么就要什么”的心态。
 《清平乐》剧照
《清平乐》剧照这些年对宋朝的再认识有域外的影响,即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在20世纪初提出的唐宋变革说,他认为宋代是近世的开始。这背后的逻辑是,东亚有一个自己特殊的现代发展节奏,它的速度和步伐和西方是不一样的。内藤的说法首先影响日本学界,然后在1950年代以后影响欧美学界,在域外掀起了研究宋朝的高潮。在海内,严复、钱穆、陈寅恪对宋朝早就有高度评价。陈先生的评价是“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这个评价是空前绝后的,但陈先生的研究方向在1950年代以后的中国大陆没有走下去。
中国大陆真正开始对宋朝评价更加出现逆转比较晚了,可能是在1990年代。我们最初是认识到,尽管宋朝积贫积弱,但在文化上,特别是文学史上的评价出现改变——文学史现在的定论是,唐诗和宋诗是各有千秋的。在多个方面,比如高雅文化、经济生活、城市发展,我们开始注意到宋朝在中华文明史上的特殊性。我斗胆说,如果从1990年代中期起算的话,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经历了1980年代的积累、开始经济起飞的时候。鸦片战争以来的那种屈辱感消失,就能以放松的心态反观中国历史,宋朝的美好就展现出来了。
此外还有一个认知的调转。传统史学站的是国家立场、皇帝立场,开疆扩土才是伟大的。和别人签订和平条约、不打仗了等等是不高级的,所以宋朝不高级——但19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史学界除国家立场以外还有了人民立场——而老百姓的立场是,“谁愿意打仗呢?”当我们开始注意到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这些方面,宋朝熠熠生辉。
界面文化:我的观察是史学中的“国家立场”从未完全消失。去年年底有另外一部历史剧《大秦赋》播出,也吸引了许多观众,而剧中对秦的政治制度有比较多正面描写,这一点也引起了一些争议。这是否也说明了我们目前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演变缺乏共识呢?
赵冬梅:我是研究宋史的,我最欣赏它的一点就是多元和宽容。所以我觉得存在不同意见其实是好事,但前提是大家彼此都愿意倾听,彼此都容忍对方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讲,意见不同才是好的,没必要全统一。
02 把帝制中国作为一种国家类型来看国家治理问题
界面文化:制度变迁研究应该是历史学自诞生起最关切的课题之一,相关研究应是汗牛充栋。对你来说,用《法度与人心》来重新阐述整个帝制中国的制度史的意义是什么?
赵冬梅:你说得很对,制度史研究确实在古代中国就有很丰厚的积累和悠久的历史。《汉书》中有《百官公卿表》,后来很多纪传体的史书里有《职官志》,唐代还出现了史上第一部政书《通典》,宋元时期有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清代还有《历代职官表》。但是古人看制度和今人看有不太一样的东西。现代中国历史学研究中,制度史是一个非常吃劲的地方,我们系的前辈邓广铭说过,治史的四把钥匙是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和目录学。邓先生说这个话,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立足于宋代。因为我们看到的大部分材料都是做官的人留下来的,记录的是和做官有关系的信息,如果你不懂职官就读不懂。
虽然制度史研究有丰厚的积累,但我做的不是制度史的阐述,我把帝制中国作为一种国家类型,来看它的治理。自从公元前221年帝制中国的国家类型建立以后,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是统一的,或至少是追求统一的,因此帝制中国国家治理的探索不像今天这样用国与国的竞争来实现,而是用朝代与朝代的竞争来实现——所有这些朝代在本质上都是帝制时期的王朝。因此,我把帝制时期的王朝政治作为一种政治类型,去看在国家治理当中,这样一种政治结构会遇到哪些问题。
帝制中国的核心目标是长治久安,但长治久安从未实现过。为什么?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问题,有一些问题是贯穿各个时代的,或者说贯穿各个时代的同类问题在不同的时代会表现为不同的形式,我希望以制度为线索去看朝廷国家的历史,这个和单讲兴衰不一样。传统史学直接看兴衰,看到的往往就是朝代更替之际——朝代更替的短时间内换了皇帝或出现了奸臣,其实没什么意思,新朝再建,问题还是一样的。我想要跳出来,有一个长时段的关照,看国家治理的问题。我希望从典章经制中看理乱兴衰:典章经制是制度,理乱兴衰是朝代更替的政治史,通常这两种叙述是不相干的,我现在要以一个为线索去看另外一个。这是《法度与人心》想做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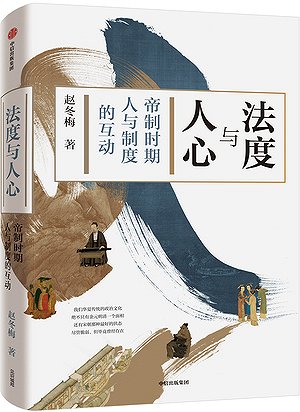
《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
赵冬梅 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1-1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有一些对传统史观的批评,比如过度关注“改朝换代”和君主的道德问题,缺乏系统性的反思。这是否和帝制中国一直以来缺乏“国际竞争”有关,即缺乏一个他者视角来反观自身?
赵冬梅:你说的是有道理的,没有一个外在的竞争者。对我的书,我有一点可以自信地说,我没有吹——华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就是东亚最发达的地方,我们是有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的;而且我们也能吸纳外来文化,但真正外来的、在文化上又足够强大到可以相互竞争的文明体,其实是没有的。
但另外一方面我个人觉得,(传统史观的缺陷)又和传统意识形态最核心的儒家思想比较强调道德有关。儒者走到最后就会走到“道德洁癖”的境地,司马光就是一个有道德洁癖的人。上午我和学生讨论学生的朱熹论文,朱熹不就说“我们是君子,君子和小人不能两立”?其实那些君子都没有什么用,还自称崇高。这些君子处在“上流无用”的状态,明末的那些东林党君子也是。上流无用,下流无耻。
实际上,宋代官员中,在上流无用和下流无耻之间还有一部分人,这也是中国传统人才观的另外一个主题——德和才。今天我们觉得最好的人才应该是德才兼备,但我觉得儒家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强调德行的时候,会认为有才的人会无德。就像现在有人会认为你有才,但面对大众去讲就证明你学问不怎么样(笑),其实两者不相干,是可以做到的。但最终就真的德和才分开了,所以我们缺乏这种东西(指不把德和才对立的心态)。
界面文化:这本书就像副标题所说,它指出了制度的变化会如何对人的生活造成影响,这是很多其他历史书很少去讨论的。
赵冬梅:我应该是一个不忘初心的人,永远对历史中人的命运感兴趣。因为如此,我进入了历史学。初学者会发现学古代史肯定要学制度,要做一些非常枯燥的研究,但是我在枯燥的研究里时刻没有忘记生活在制度中的人。我对制度的敏感和我对人与制度的关系的认识,是我从做博士论文《文武之间》的时候开始就有所体察的——制度会规训人,有权力的人又会改造制度,没有权力的人被逼急了也会反抗制度。
03 现代历史学特别缺少对个体生命的关照
界面文化:在《法度与人心》之外,你同期出版的著作还有《人间烟火》,后者更关注社会史或文化史。其实社会史和文化史应该算是历史学科内比较新的分支,目前国内的历史学家对这部分历史的研究的重视程度有多少?
赵冬梅:其实要说新也不算新,但始终处于不重要的地位。从世界范围来看,强调关注普通人生活的新史学很早就出现了。中国大陆学界开始关注是1980年代中期,只不过做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会非常不好意思地承认研究的只是历史的血肉,骨架还是政治史、军事史这些传统史学领域。
我的感觉是,社会史、文化史相关研究中能看到一些特别好的东西,比如说孙机先生的汉代物质生活史研究,还有关于舆服的研究。我在北大上的一门课叫做“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英文名“Everyday Life in Premodern China”才是我想说的,每年上课我都会和学生读孙机先生的研究。他能够通过帽子(幞头)的变迁,看到华夷交流,看到中华民族如何吸收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创造了新文化——它就体现在古代中国男子的冠上。孙机先生的研究特别经典,研究物质文化的演变能够显得很有意义,特别难得,但这种研究不太容易看得到。

《人间烟火:被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
赵冬梅 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1-4
我给学生上课的时候会把注意力放到物质生活条件的演变和个体的人身上。《人间烟火》里有张行婆的故事,她是司马光记录的一个婢女。这个故事属于正统历史学研究无法容纳的故事。我自己做过一点和军事管理有关的研究,我能看到的用法就是,因为张行婆的父亲是一个因为眼瞎退伍的老兵,学者会在谈到士兵需要不断体检的时候用到这条材料。我问过妇女史研究者是否用到过张行婆的材料,他们说有的,在证明妇女会在家修行的时候。但实际上,这么用这个材料的时候,这个人的生命就不存在了。
界面文化:她就成了一个典型。
赵冬梅:我觉得比典型还差一点。就用她生活中的一个小点,去证明某个制度存在过,这种叙述方式我觉得是很埋没人的,但它也是传统的那种不讲个人、没有感情的史学论述的必然之作。
传统史书中还有一篇《赵至传》,我在《人间烟火》里也用到了这个故事。武汉大学已故的魏晋南北朝史大家唐长孺先生写过赵至,他的视角是从《晋书·赵至传》看曹魏世家制度,也是拿这滴水去映照更大的制度。但他的文章特别有情,他有对这个人的同情。他很细致地描摹考证了赵至为什么要在16岁的时候开始逃亡,因为马上就要当兵了,他逃了几次。这些小人物生命中的细节通常是被认为不重要的,但唐先生花了力气去写,除了证明世家制度是一个如何残酷的制度之外,他还给了这个人生命的关照。这篇文章也是我在社会生活史的课上每年的必读材料。
对个体生命的关照,那种闪闪发光的人性的东西,是现代历史学特别缺少的东西。在写学术文章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写,可是这回面向大众,我就没有学术的包袱了——学术包袱就是你要有理论,要拔高意义。没这个包袱,我就把张行婆的故事完全按照个人的理解讲了出来。我真的没有想到,在喜马拉雅、微博上给我留言的朋友,特别多人为张行婆的命运着迷,特别佩服她和喜欢她。我能够把一千年前宋朝的一个女仆介绍给大家,大家这么喜欢她,这么爱她,觉得也很值得。
04历史构成了我们的基因,中华民族是一个“被时间祝福”的民族
界面文化:你在《人间烟火》中指出,在宋代之后,男性的成功道路越来越窄,于是男性也收窄了女性的路,“当男人开始接纳无条件的忠君,他们要求于女人的,就有了无条件的贞节。”这个观点和近年来中国社会性别规范的某种保守化趋势似乎有所呼应。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两性关系趋于紧张往往发生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中?
赵冬梅:如果简单粗暴地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在传统等级社会当中,君臣父子说的都是男人的关系,女人在此之下。自然压力是一点点往下走的,男人的空间小了之后肯定会压到女人身上。在现代社会,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现代社会涉及到就业,当初我们国家号召女性走出家门,其实是需要大量劳动力。美国也是如此,二战时塑造那种撸胳膊挽袖子的工人女性形象是出于国家需要,等到不需要的时候,女人就回家了。我觉得这里面有政策的因素、观念的因素,在国外还有宗教的因素,相对复杂。
回到现实的话,我个人是一个平等主义者。我觉得最理想的状态是,不管是什么性别,我们都是自由的,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人生,即男女两性的自由和平等。我想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还有女性不断争取宣传,我们能够创造一个更宽松的、两性都生活更愉快的环境。我这个人属于盲目乐观,尽管我能看到很悲观的状态,但我还是倾向于相信长远来看会好的,当然前提是我们需要为之努力。
界面文化:现代社会和帝制时期的一个根本性区别在于对“人人生而平等”的认识。但“平等”并不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思想传统推崇的理念,当然,你指出了儒家思想经过历代变迁已经和原意大相径庭。而今网络上有很多对儒学愚忠愚孝崇拜等级制的批判——特别是女性主义者会认为儒学就是“吃女人”——认为中国思想传统可能是一种历史包袱。你怎么看这种论调呢?
赵冬梅:我们对儒家思想肯定是有误解的。现在有一种要么一股脑地说要学国学,糊糊涂涂全盘接受的趋势,还有一种就是全面否定。我其实想做的一个努力是告诉大家过去不是铁板一块的存在,而是存在多种多样的元素。我们只有了解过去有什么,才可以考虑从中要什么。了解到过去的一些好东西,在心理上也是一种安慰吧。我希望建立一个更为精细的民族自豪感,而不是一个糊涂的民族自豪感。这个民族自豪感里要甄别,好的要吸收,不好的要摒弃,前提是你知道有好的和不好的。
我觉得你问的很好的一点是指出了传统时期的底层逻辑和今天是不一样的。古代是等级社会,是“忠臣出孝子之家”,因此当忠臣为国家服务的时候,对父母妻儿的照顾都是应该的,这是其中应有之义。但同时你要注意到,应有之义中的官员特权是明文规定的特权,除此之外的也是不合适不合理的,应当摒弃的。所以我反对的是机械地说古代有过什么,同样我也反对机械地说外国有过什么——任何一个社会要想正常运转,必须是顺应底层逻辑的。在等级社会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是君有君的权利,同时君有君的义务;臣有臣的权利,臣也有臣的义务。同时还有一套伦理结构,比如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是相互的关系。如果你承认这些,在这个逻辑关系里,按照孔子的说法就是“必也正名乎”。
我们要梳理这些权利义务,不应当是在这个方面采用这个逻辑,在那个方面采用另外一套逻辑,逻辑的顺畅其实就是孔子说的“正名”。名的系统可以是不同的,所构建的社会结构和伦理关系可以是不同的,但一个社会真正想要稳定良好地运作下去,“必也正名乎。”
界面文化:你在此前的采访中说,一个民族要走向未来,需要先真正了解我们的过去究竟有什么,而你想告诉大家的是,在我们的文化基因里有过好东西,但它未能延续。所以我们的文化基因是什么呢?
赵冬梅:我觉得我们的历史构成了我们的基因。中华民族其实是一个“被时间祝福”的民族,“Blessed by time”是一个英文的说法,可是我觉得这个说法很对。不管遭遇怎样的灾祸苦难,包括被异族征服,我们的文化核心依然还在——汉字所承载的东西,以及我们没有一个强烈排他的宗教。我们的文化内核(儒家思想)是开放包容的。不要再批评我们不开放不包容了,写作《法度与人心》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如果不把注意力只放在政府层面的话,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都是善于学习、有心胸能包纳同时也不失自我的。比如在海禁时代,东南沿海的渔民仍然不断前往海外,中国人走到哪就会把中华文化带到哪。我深深为这个文化感到骄傲和自豪,不是它没有毛病我才爱它,而是我了解它的好和不好,我更爱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