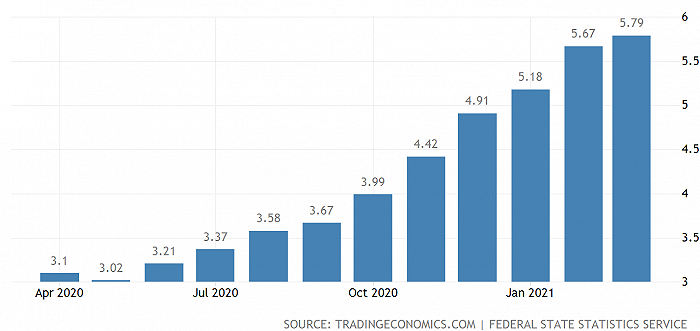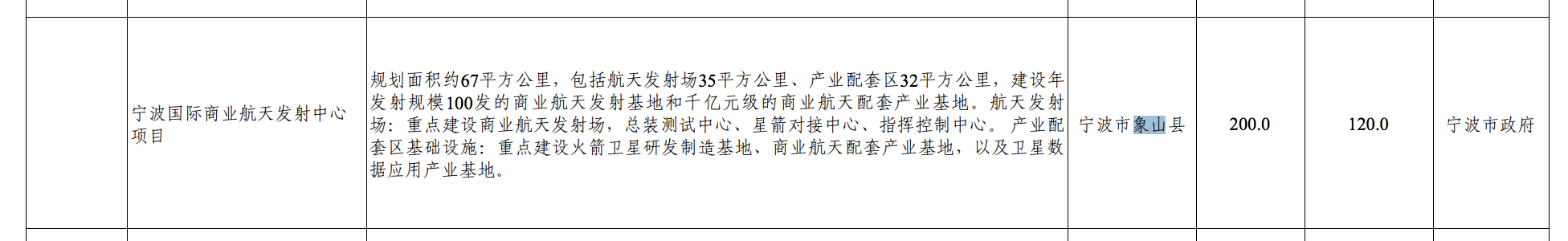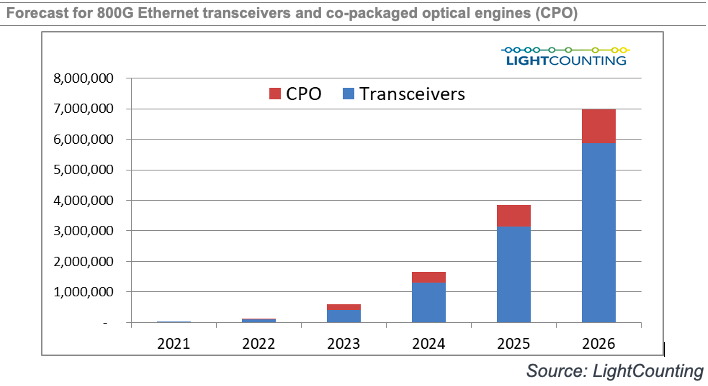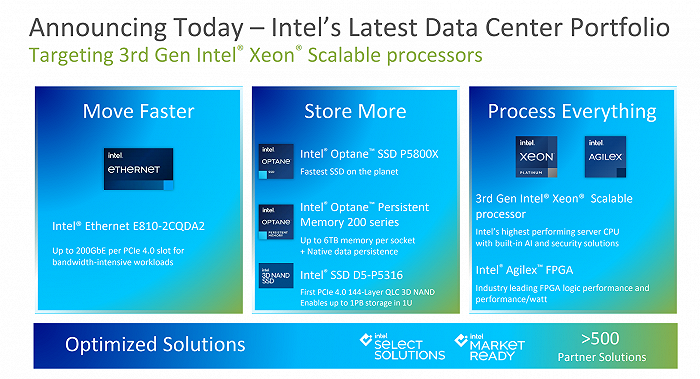19世纪30年代,达尔文乘“小猎犬”号舰进行了历时5年的环球航行,对动植物和地质结构等进行了大量的采集和观察,并于1859年出版了《物种起源》这一划时代的著作。
达尔文首次提出了“进化论”,证明物种的演化是通过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的方式实现的。进化论被恩格斯誉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不仅开创了生物学发展史上的新纪元,使进化论思想渗透到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而且引起了整个人类思想的巨大革命,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有着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然而,在达尔文的学术生涯中,一个人对他产生了深深的影响,可以说如果没有他的存在,达尔文可能就写不出《物种起源》这样家喻户晓的著作。这个对达尔文产生深远影响的人就是地质学家查尔斯·莱伊尔。

莱伊尔在苏格兰和英格兰长大,后就读于牛津大学,表面上是为了学习法律,然而他的思想不可阻挡地受到自然界的吸引,地质学很快就成了他钟爱的学科。在牛津大学,教他地质学知识的教授是威廉·巴克兰——英国第一位学院派地质学家,也是一位热衷相信灾变学说的人。巴克兰认为,挪亚时代的洪水是一系列灾难中距离我们最近的。在他看来,这一点再明显不过了:“在一个并非遥远的时代,发生过一场全球性的洪水,即使我们从未从《圣经》或其他权威人士那里听说过这样的事件,地质学本身也会帮助我们认识到,这样的灾难确实发生了。”年轻的莱伊尔受到他尊敬的导师的影响,加入了灾变论哲学的阵营。
1819年,莱伊尔从牛津大学毕业,搬到伦敦学习法律,但是他又一次受到石头和化石的引诱。不久,他开始周游欧洲,想亲眼看一下自己在科学报告中读到的东西。
回到英国后,他在伦敦以南大约40 英里的库克菲尔德镇的一个采石场里发现了奇怪的大骨头;在怀特岛看到白垩纪的海洋地层高高地耸立在海面之上,这是隆起的证据。他去了巴黎,交错出现的淡水沉积层和咸水沉积层让他感到惊奇,这些沉积物看起来似乎不是由突然的破坏造成的,而是由环境的温和变化造成的,灾变论无法解释这一点。

随后,莱伊尔游历革命后的法国南部,在那里看到清晰呈现地壳抬升和周期性的火山玄武岩与河砾石的(交)叠层结构。当向南去往意大利,莱伊尔的观念完全转变了。在临近那不勒斯海岸的伊斯基亚岛上,他发现海岸剧烈抬升的例证:悬崖高处发现了贝壳层。这种情况不应该发生。造山运动的过程被认为处于另一世代,却在此地出现了。旧有理论是错误的,他在最著名导师处学到的地质学理论是错误的。
莱伊尔意识到:地质学不仅是过去之事,而是正在发生之事。他继续在地中海地区游历,强化了自己对于地球的认知: 地球今天的运动与其过去具有联系, 其线索仍然存在;地球历史是连续的、可知的。莱伊尔迫不及待地发表了其关于地球(进化)的新理论。1830年7月,他出版了《地质学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第一卷,试图以目前地表运动为参考,阐明其早期演变。莱伊尔的观点凭借严谨逻辑、典雅表达而大行其道,其开放思想所造就的论断为大多数人所接受。通过其三卷本巨著,莱伊尔实质上终结了基于《圣经》的地质学理论,并且铸造出现在与过去牢不可破的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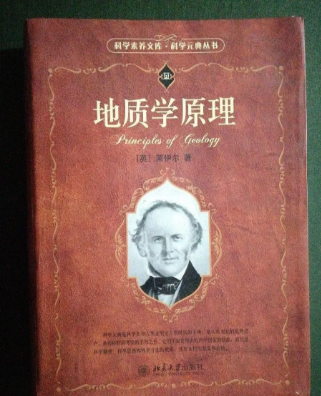
第二年夏天,当莱伊尔正致力于撰写其著作第二卷时,22岁的达尔文收到皇家海军探测船贝格尔号的邀请,成为其在环球航行期间的舰上博物学家。这给游手好闲的年轻达尔文的生活带来了激情。他的父亲曾斥责其“除了猎鸟、跑狗、捉兔外无所事事,并且将给自己和家庭带来耻辱”。
或许达尔文也正在寻找重新开始和证明自己勇气的机会。最初的反对在达尔文叔父的斡旋下转为默许,而达尔文抓住了这一机遇。为准备此次航行,达尔文开始储备更多的地质学知识。他参加了牛津大学地质学家亚当·塞奇威克(Adam Sedgwick)穿越威尔士山脉的科学考察。塞奇威克醉心于野外考察,如同时代其他人一样也是灾变论者,认为世界产生于近期相互关联的一系列灾变,并以大洪水告终。毫无疑问,达尔文与塞奇威克相处的这段时间强化了这位年轻的博物学家关于年轻地球由上帝创造的观念。
达尔文在出发之前收到了船长罗伯特·菲茨罗伊的礼物:查尔斯·莱伊尔的《地质学原理》第一卷。贝格尔号于1831 年圣诞节的第二天起锚离开英格兰德文波特港。圣诞之夜的狂欢使相当一部分船员倒下了,打乱了他们前一天的动身计划。20 天后,贝格尔号停泊在距非洲西北海岸约400 英里的圣地亚哥岛(属于佛得角群岛)。

达尔文渴望去探索并立即徒步出行。他游览了普拉雅小镇,吃新鲜橙子并品尝了他并不喜欢的香蕉。在返回的长路上,达尔文徜徉于异域风景中,生命中首次充满了兴奋之情。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里,他将花时间探索这个岛。圣地亚哥岛的风景很荒凉,但没关系。“哦,对任何一个只习惯于英国风景的人来说,”他写道,“一片完全贫瘠的新奇景象反而具有一种宏伟的气势,更多的植物可能会破坏这种气势。”他一定觉得自己像个真正的博物学家。这是一个重塑自我的机会,表明自己不是父亲眼中的懒散之人。他一定觉得自己像个成年人,第一次踏上了人生道路。
达尔文与莱伊尔在伊斯基亚岛大开眼界的经历惊人地相似,他们都观察到“在一个海崖的表面上有一个完美而水平的白色带”悬于海面上大约英尺的地方。为了看得更清楚,他还爬了上去,看到了“许多嵌在里面的贝壳,像如今存在于邻近海岸的贝壳”。贝壳层从上到下被熔岩层包围着。达尔文指出,贝壳层最上层的几英寸已经被熔岩的热量烤成坚硬的岩石。
达尔文探索圣地亚哥岛之前或期间的某个时候,就已经接纳了莱伊尔书中的观点。当他考察此处露出地表的岩层时,他看到了其运动周期和抬升的历史,看到了地球在不停地运转。他从詹姆森和塞奇威克那里学到的地质学知识无法解释这一点。海洋生物在海底的火山岩架构上繁衍生息。海平面下的贝壳被熔岩流掩埋和炙烤。随后,整个区域抬升为45英尺的海崖。达尔文认为不必用“奇迹”来描述这一地表现象。他开始以莱伊尔的观点诠释这片岩石。
达尔文认为,这些地球历史的篇章是由现存的原因和时间的缓慢作用力所写就的。面对相反的证据,达尔文能够敏捷地转换其根深蒂固的观点,这让我们看到其敏捷灵活的思维。他对圣地亚哥岛岩石激进甚至亵渎神灵般的解读,预示着其具备成为一名科学家的最大品质:愿意相信证据,无论证据可能指向何方。
1832年7月20日,贝格尔号驶离乌拉圭海岸,驶近拉普拉塔河口。就在此时,英国蒂尔盖特森林中的采石场工人点燃了装在粉砂岩峭壁上的火药。当爆炸的灰尘散去时,矿工们注意到一些奇怪的东西:一堆乱成一团的骨头嵌在岩石中。消息传到了吉迪恩·曼特尔的耳朵里。他认出这是另一只最为完整的大型蜥蜴。但这个标本显示出惊人的特征,无论是在与斑龙还是与禽龙有关的骨骼上都没有发现—它有宽大的板甲和可怕的尖刺—一种身披铠甲的巨蜥! 曼特尔将这种新生物命名为“披甲森林蜥蜴”。这是其命名的第三只不为其所知的恐龙。
1832年秋天,达尔文在乌拉圭蒙得维多收到了一个包裹,里面装着莱伊尔刚刚出版的《地质学原理》第二卷。毫无疑问,达尔文定是满怀期待地研读了一番。在达尔文穿过南美洲最南端的麦哲伦海峡,航行于巴塔哥尼亚附近之前,他实际上是在转述—甚至是“剽窃”莱伊尔的观点。达尔文在航行中的贝格尔号上思考海峡的产生,写道:“我们必须承认,年复一年,潮起潮落,只有在巨浪的作用下才能侵蚀出如此巨大的区域。”他显然是从《地质学原理》中引出这段话的:“努力去思考在不知不觉中淹没整个陆地所需要的无穷时间,人们的想象可能会枯竭到令他们难以忍受。”
达尔文现在是一个激进的均变论者,一个深时福音论信徒。在南美西海岸旅行时,他给表哥威廉·达尔文·福克斯写了封信,后者是一名牧师和业余博物学家。信中表示:“我已成为莱伊尔观点的信徒,在美洲从事地质学研究时,我甚至某些方面比他走得更远。”多年以后,莱伊尔去世时,达尔文对他进行了讴歌,并写道:“他彻底改变了地质学,因为我还记得一些前莱伊尔时代的事情。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在科学上所做的一切,几乎都归功于对他伟大著作的研究。”
达尔文自己已彻底改变了一个科学领域,为何还那么重视莱伊尔的成就? 说来简单,莱伊尔迫使思维范式发生了转变,创造了达尔文构建新科学的思维空间。
达尔文1859年的杰作《物种起源》牢牢地根植于均变论的知识体系中。达尔文对人类思想进步的开创性贡献—自然选择和普遍的共同进化—与年轻地球创造论格格不入。在一个有着6000 年历史的地球上,从一代到下一代的变化将微乎其微。因为在灾变论的世界里,进化是一种软弱的力量,无法产生巨大的变化。没有了“凿子”和“锤子”,大自然就不可能塑造生物圈。由于物种是在一次集中的创造中固定下来的,所以其后续发展是一条直线。相比之下,达尔文提出的进化需要大量的时间—地质时间。莱伊尔所提倡的均变论——“现存因素的缓慢作用”,同样是地质或生物变化的驱动力。这就是达尔文所建立的、由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所阐释的“任何人所拥有的唯一最好的想法”的基础。没有莱伊尔,达尔文就不可能成为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