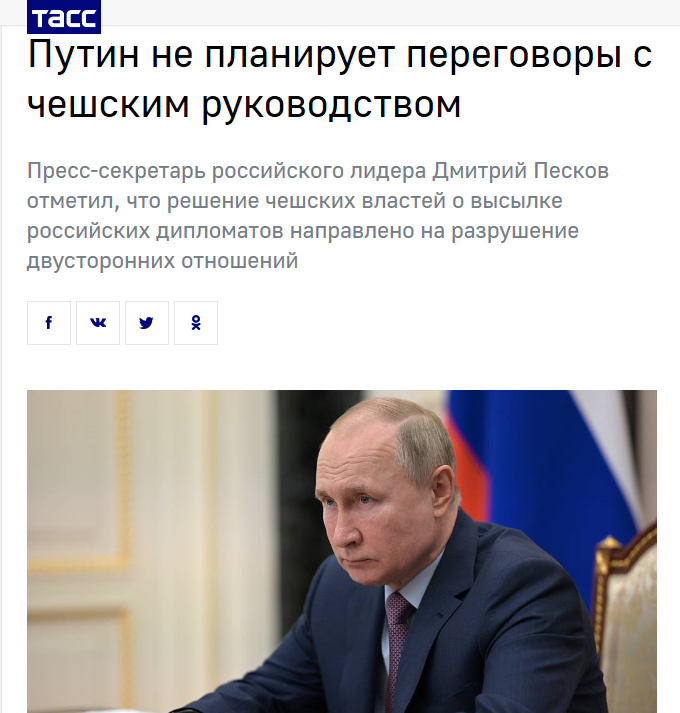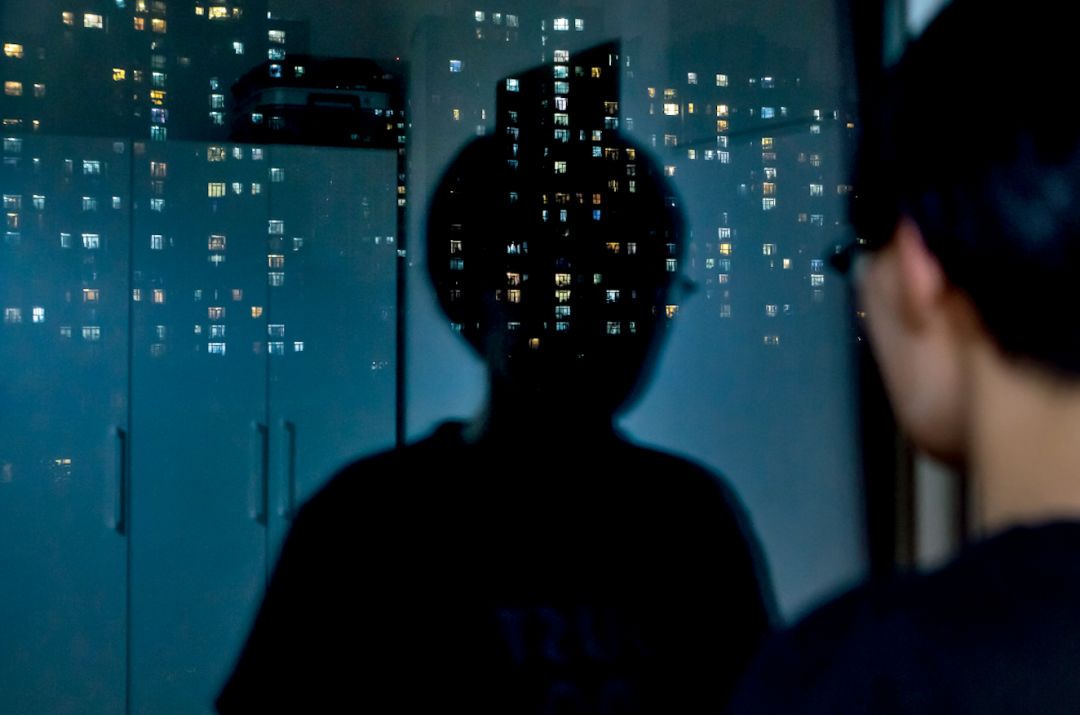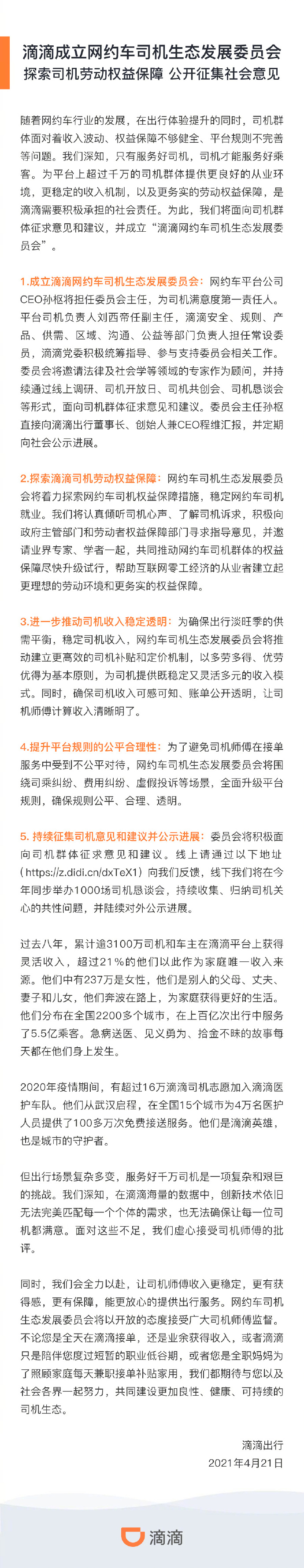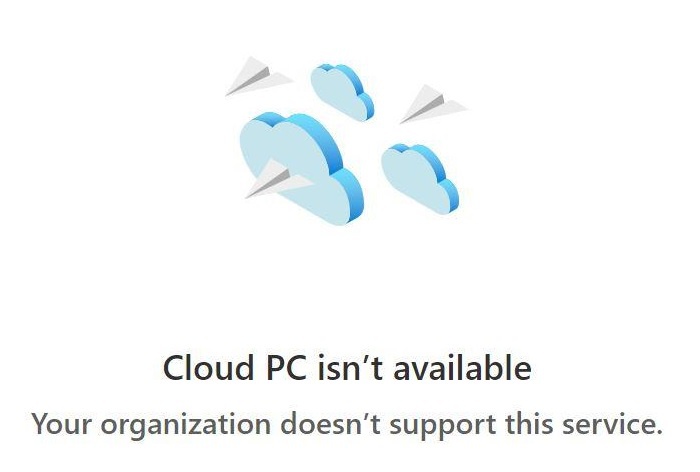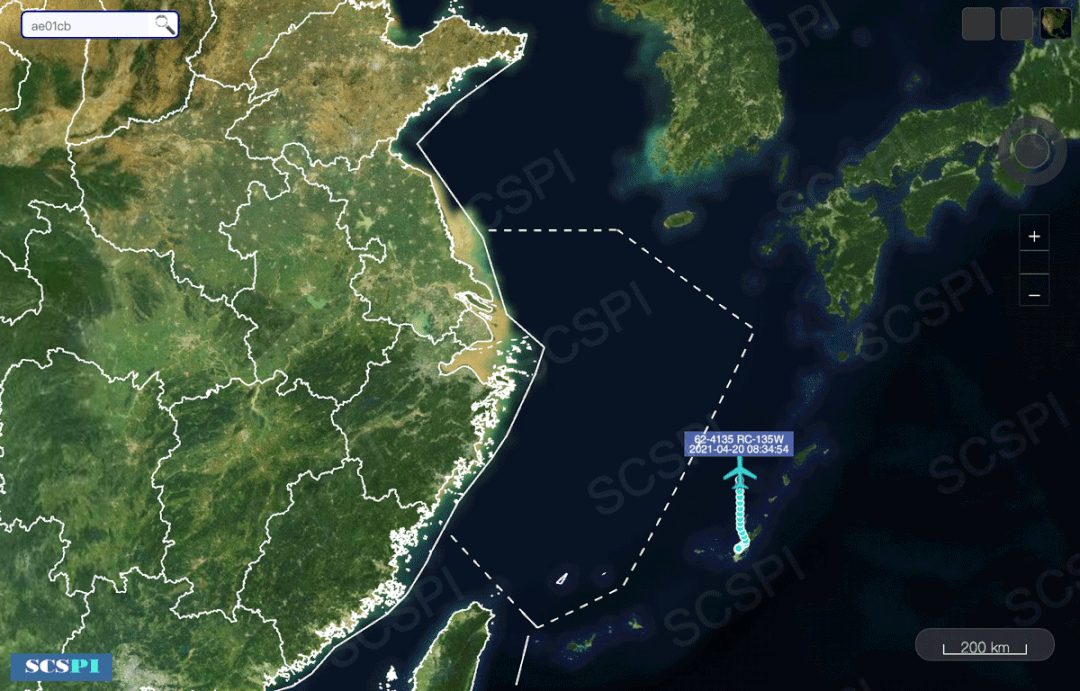原标题:核废水入海具国际通行证?从日本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历史说起
2021年4月13日早,日本内阁作出决定,要求东京电力公司在两年内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废水,一时间激起周边国家政府、民间的强烈反对。其实对于东京电力公司提出废水入海是最为“可行”的方式大概不令人惊讶,因为在2020年2月10日,日本政府经济产业省已经对此向公众进行了精致论证,早在2015年国际原子能机构(以下简称“机构”)总干事就“福岛核电站事故”进行总结报告时,也专门提及了将废水“向海洋受控排放”的可能性。因此,从很大程度上而言,若机构不为日本的此次行径背书才是有违其“国际”责任和日本长久以来向其提供福岛核电站实时情况的态度的。果不其然,在日本政府发布决定后,机构在当日也发表了以“IAEA Ready to Support Japan on Fukushima Water Disposal, Director General Grossi Says”为题的简讯。若不深究简讯全文中包含的“日本政府的决定符合全球惯例”“日本政府应以透明、公开的方式处理今天的决议”等模棱两可的字句,不少人恐会将此认为是机构给予日本方面废水入海的绝对权威的国际通行证。事实是否如此呢?以下将从日本在冷战时期同该机构的关系谈起,以供相关人士参考。
2021年4月12日,日本福岛县,航拍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水仓。
一
1949年,苏联试爆原子弹成功,打破了战后以来美国的核武器垄断。1953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开始推行为期6年的“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希望维持本国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的领导权。1957年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建立即是该计划中的重要环节:美国曾设想将机构作为其进行核原料以及和平利用核能技术输出的平台,并期待以多边外交的方式建立美国领导之下的原子能保障监督制度(safeguard),进行保障监督的目的是通过核查的方式保证核援助接受国不会把相关核材料、设施用于军事目的。1957年5月11日,《纽约时报》刊登的杜勒斯讲话中曾乐观地提到,“机构的保障监督制度将会为美国提供国际立场。我们可以期待美国体制将会为世界接受,所有接受机构援助的国家将会接受机构的核查”。但是,当时苏联、印度、法国等世界大国对让渡国家政治、经济主权持有极为谨慎的态度,而无意支持机构以上两种职能的推行。唯有日本,在世界兴起探讨“和平利用原子能”之风时,不仅同美国、英国签订双边核合作条约,同时还于机构成立次年,即1958年10月召开的理事会会议上提出了通过机构购买3吨天然铀的请求,并主动表示愿意接受机构对这些核原料使用情况的核查。毋庸讳言,这一行为的目的之一是给当时由美国主导的国际制度背书,为此后接受机构援助的国家提供行为范例。于日本本国而言,其所得即是通过介入机构事务提升战后日本的国际地位,时任机构总干事的美国人斯特林·科尔(Sterling Cole)在访问日本时曾提及,日本是经历核武器创伤的国家,并具备发展核工业的潜力,因此可以有机会在机构中获得相应的领导地位。事实证明,日本从机构建立开始就代表远东地区获得了指定理事国的地位。
针对日本提出通过机构购买天然铀的要求,苏联、印度、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印度尼西亚等国代表都提出了两点颇具说服力的反对观点:一、当前世界上铀储量充足,因而希望开发军事核项目的国家不需要通过机构提供铀,即可在机构之外获得,因此保障监督制度起不到抑制核扩散的功用,若机构采取此类严格措施,很多国家将会失去向机构提出援助的动力;二、日本将要建设的JRR-3反应堆是研究型反应堆,使用的是核原料而非可裂变核材料,因此无需进行核查。 机构总干事、英国、美国代表则从技术层面对以上观点予以驳斥,即上述反应堆并非是一种小型研究型反应堆,假设其以10兆瓦的功率运行,那么一年中可生产3千克钚,这足够在一年或两年内生产一枚原子弹。日本代表则顾左右而言其他,表示接受机构的核查是基于对机构公平、公正的信心,而不涉及对业已确立的保障监督制度基本原则的讨论。
从表面看,以上论辩运用相应科学数据,意图表明机构保障监督制度的践行可以防止核武器在日本扩散,但是若对日本当时所处国内、国际环境稍作考察便知其无法也无从进行军事核武装:首先,对处理战后日本国际事务起到重要作用的首相吉田茂在任期间即奠定了日本战后十年的外交基调是要“形成复兴重建的基础”“促进吸收外资的根本条件即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稳定”,日本在重返国际社会以后“能够站在率领亚洲的自由国家群,为世界和平和世界自由作出贡献的立场上”“重新确立大日本帝国时代的亚洲大国之地位”;其次,1955年通过的《原子能基本法》中亦规定日本“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及利用,限于和平的目的,以确保安全为宗旨,在民主管理的前提下,自主开展,并公开其成果,从而为国际合作做出贡献”;再次,1954年第五福龙丸事件后,日本国内的反核气息尚未完全消散,发展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尚有阻力,毋论进行核武装。由此观之,日本提出接受机构核查其实是对着一项虚空的制度进行的虚空行为,其实际作用已不是美、日等国宣扬的“防止核扩散”。当然,各国在当时对此也仅达成了临时性方案:日本需要向机构提供核原料使用情况的半年报告;在上述反应堆达到临界时,根据届时各国达成的协议再具体决定派遣核查员事宜。迁延数年后,1963年日本最终还是将日、美双边和平利用原子能条约中的核查义务转移至机构之下,这也是机构承接的首个保障监督条约。
二
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很大程度上是依赖美、英、加等国的帮助进行国内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建设,在国际原子能机构中也多表现为辅助美国形塑机构的众多制度,那么行至60年代,随着彼时美国国际收支状况恶化以及东南亚局势的变化,日本更多地分担起美国曾经对东南亚各国的经济援助责任,日本在机构中的行动呈现出的另一新特点是试图以东亚国家领头羊的身份向非共产主义国家进行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援助。实际上,日本对成为东亚和平利用原子能领导国的想法由来已久。在1955年美国考虑建立“亚洲中心”(Asian Center)以推行其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时,日本即意图取代菲律宾获得中心的主导权。但是,建立该中心的计划因没有得到英国、澳大利亚及其他亚洲国家的支持而归于流产。此后,日本本国于1957年建立了同位素培训学校,培养核医学、核农业方面的人才。据统计,至1962年为止,在该学校接收的1166名学生中包含112名国外学生,其中33名来自于台湾地区。基于此,日本曾尝试在1961年9月的机构理事会会议中进一步提出建立“亚洲同位素训练中心”(Radioisotope Training Centre for Asian Region)的计划,并愿意分担建立中心的费用。但是由于苏联、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这一提议最终也不了了之,其中印度的反对意见是:该中心的名称应改为“远东中心”,而不是“亚洲中心”,以示印度在亚洲国家中的地位。
为挽回颜面,日本于1963年3月举办了“亚太地区和平利用原子能大会”(Conference of Countrie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for the Promotion of Peaceful Uses of Atomic Energy)。该会规模盛大,除14个亚太国家参会外,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美国及相关国际组织都以观察员的身份加入。来自瑞典的机构理事长埃克隆德(Sigvard Eklund)亲自在会议开、闭幕式上进行了发言。针对日本代表在会上提出机构应加大对亚太地区的投入、建立机构亚太地区办公室等建议,埃克隆德亦给予了正面回应。同时期,在日本首次承办的机构有关同位素使用的会议上,埃克隆德提出“对于意欲实现工业化并满足人口增长需要的亚洲国家而言,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同位素技术)以便合理有效利用自然资源是至关重要的”,次年5月,日本同机构即达成了“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供同位素训练课程的协议”(Agreement on Providing Radioisotope Training Courses by the IAEA”)。同样也是在机构的促动下,1965年2月, 日本向泰国、巴基斯坦、菲律宾以及台湾地区提供了1600个用于研究型反应堆的辐射胶囊,机构还在当年的季报中对此进行了宣传。同年,东京还承办了第九届机构大会,这是机构首次应也是唯一一次在除总部维也纳之外的城市举办大会。但自此之后,机构主办的有关东亚地区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多是在不同国家轮流召开。如此而言,日本意图通过机构形成在亚洲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领导权的行为即使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实现,但却得到了机构的鼎力支持,其原因除却美国的助力、日本和平利用原子能技术处于亚洲国家前端外,同样重要的是,日本对机构的财政贡献仅次于美、苏、英、法、德等少数几个发达国家,并且基本不欠款(台湾地区在非法占有中国在机构中的席位期间,向机构提供的面上资金常常比日本多,但经常欠款,这导致中国在80年代加入机构时还为此事进行了协调)。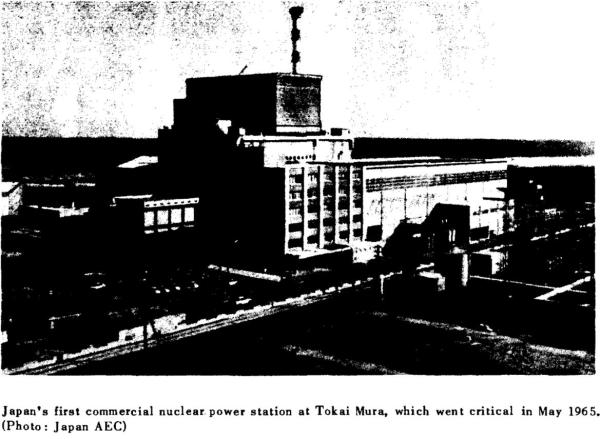
三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世界格局持续发生转变。于日本而言,自1965年首次出现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后,两国的经济争端在80年代达到顶峰;而自70年代末《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签订直到90年代中期,日本对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DA),日中也形成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中国在建设位于海盐县的秦山核电厂时也曾同日本签署了购买压力容器(pressure vessel)的条约。与此相对应,中国在1984年作为有核国家加入机构并获得远东地区指定理事国席位的过程亦没有受到来自日本的反对意见。
但是,即便在中日“蜜月期”的背景下,日本对于中国分享(尚不是超越)其在机构中的权力确实存在心理不适。这一不适感尤其反应在具体外交操作层面,以时任中国驻机构代表团一秘吴成江的外交经历为例:1986年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后,机构专门召开特别大会,讨论《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和《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事宜。大会设1位主席,7位副主席。大会主席轮到非洲地区,副主席由另外7个地区各出一人。在中国加入机构前,远东地区副主席之位始终由日本担任。中国因当时刚加入机构不久,本无意竞争职位。但考虑到当年有一个年度大会和一个特别大会,中国决定竞选一个副主席职位。但是日本一个席位都不愿让出,理由是与中国相比,日本向机构提供的会费更多。曹桂生大使向大会主席科特迪瓦通报了远东地区竞选副主席的情况,特别指出日本把会费多少作为理由,坚持霸占两个会议副主席的行径。科特迪瓦对此也颇为不满,认为按照日本方面的逻辑,他作为非洲地区的代表也不配当大会主席了。据说,他后来在77国集团内部磋商会上提及此事,引起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此外,远东地区各国对日本财大气粗的行事风格也很不满。因此,如若把此事拿到大会上表决,日本必败无疑。后来在特别大会宣布开始之际,日本大使向曹桂生大使表示日方让步,请中国出任特别大会的副主席。也正因为此,远东地区才建立起轮流制,大国小国机会均等。这是中国加入机构后对本地区做出的一项贡献。
四
时过境迁,中国及第三世界国家在机构中的地位已有较大提升,同时也在为世界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发展作出贡献。我们固然也无法用以上历史时期的事件来类比当下热议的日本福岛核电站废水入海一事。但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围绕所谓“ALPS处理水”这一概念,日本政府在4月13日的一份会议记录中提出对应要求,“明确‘处理水’和‘污染水’的不同,为此将‘废炉·污染水对策阁僚会议’的名称变更为‘废炉·污染水·处理水对策阁僚会议’。今后,‘ALPS处理水’特指经过ALPS设备净化后,氚元素含量达到规定标准之下,再行稀释后排放的水。”
(「廃炉・汚染水・処理水対策関係閣僚等会議について」首相官邸、2021年4月13日。下载地址:http://www.kantei.go.jp/jp/tyoukanpress/202104/13_a.html。)
与此相呼应,同一天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了一份关于“ALPS处理水”定义变更的文件,变更后的标准定义是“对于氚元素以外的放射性元素,在向自然排放时满足规定标准的水”。变更定义之前,“ALPS处理水”是指经过ALPS设备净化处理后存放与储水箱的水。
(「東京電力福島第一原子力発電所におけるALPS処理水の定義を変更しました」経済産業省、2021年4月13日。下载地址:https://www.meti.go.jp/press/2021/04/20210413001/20210413001.html。)
之所以进行这一定义变更,是因为实际中储水箱储存的“ALPS处理水”存在严重的不合标准问题,在日本经济产业省2020年2月10日的那份文件中有所揭示,“ALPS设备拥有对氚元素之外的62种放射性元素的达到规定浓度以下的净化能力,但是以2019年12月31日为例,储水箱中存放的‘ALPS处理水’中有70%的水除氚元素之外的放射性元素超出了自然排放时所需的标准。”而这放射性元素超标的“ALPS处理水”并不能通过简单稀释就能达到自然排放的标准,因此提出了“二次处理”的问题。
(「多核種除去設備等処理水の取扱いに関する小委員会報告書について」経済産業省、2020年2月10日、14、15頁。下载地址:https://www.meti.go.jp/earthquake/nuclear/osensuitaisaku/committtee/takakusyu/report.html。)
对于日本方面进行定义变更的行为,我们当然可以选择相信是其更新了技术处理,但我们也有理由质疑这一变更的虚空和实际可操作性。退一万步说,即使以上处理技术可行,如此大量的废水入海史无前例,又何来如美、日、机构所称的“全球标准”可以参照?从“污染水”到“处理水”的定义变更仅是日本方面的一家之言罢了。如此而言,作为具有国际公信力的和平利用核能机构应该做的似乎是促成世界各国在此事上的沟通、协调,达成令人信服的公则,而不是如历史时期呈现的那样发表具有误导公共舆论倾向的简讯。
此外,国际原子能机构是兼具核保障监督、和平利用核能标准制定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现在看来,美日至今丝毫未曾放松他们在机构中的重要作用。冷战时期,日本在机构中和西方国家相伴而行,并试图利用机构为其国内和平利用原子能发展、形成在远东地区和平利用原子能的领导权铺下道路。时至今日,我们也仍有理由质疑,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下日本有意图利用机构为其快速重启福岛地区的发展做不合理背书,并同美国联合压制复兴中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