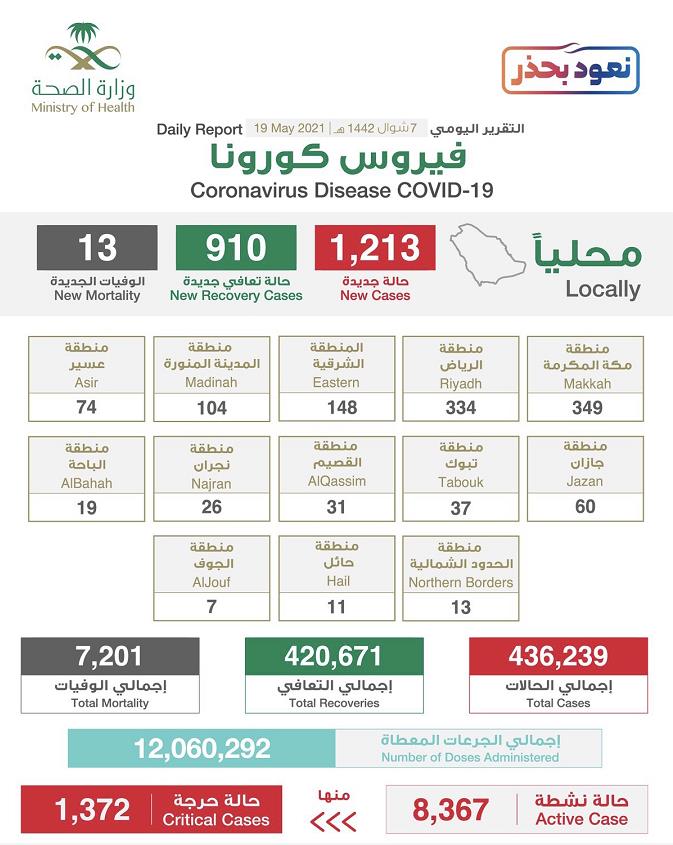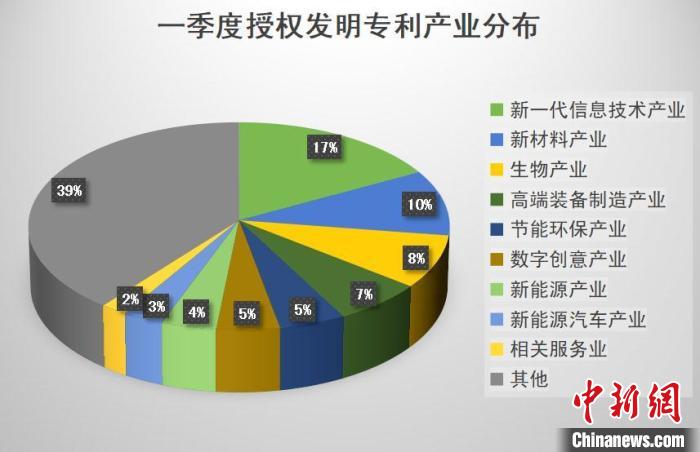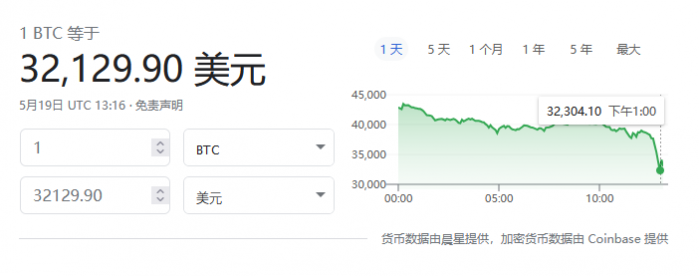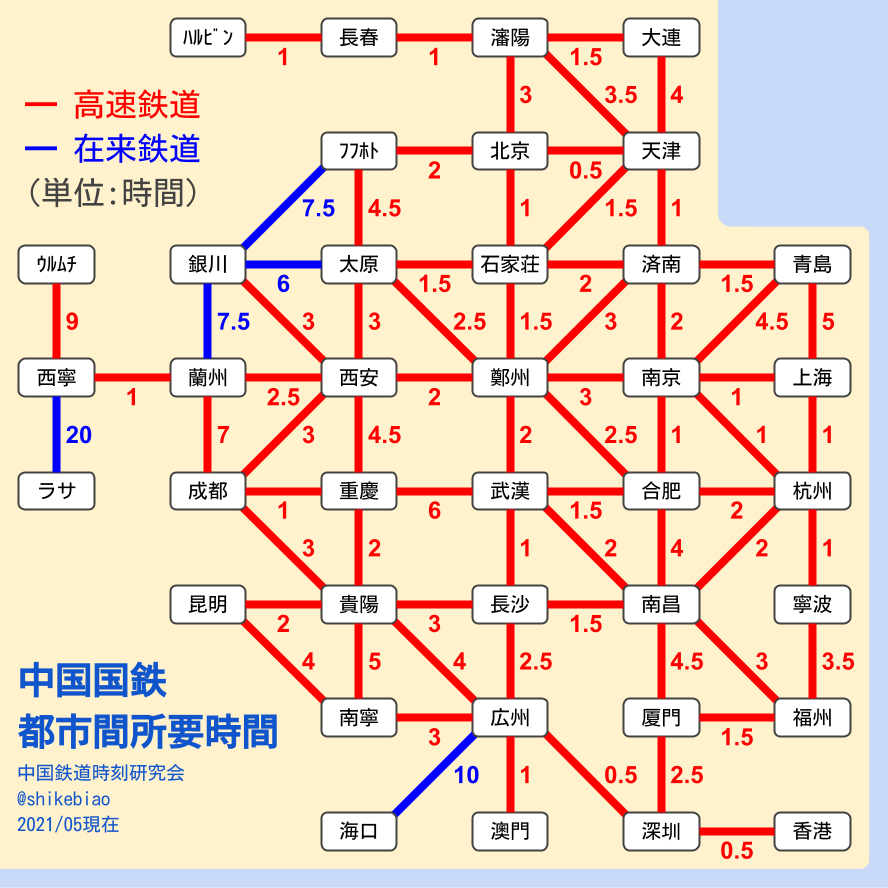原标题:专访|柏燕谊:每个焦虑的大人心中都有个不被看见的孩子
心理学家柏燕谊发现,除了那些抑郁症、强迫症、焦虑症等精神疾病患者来求助之外,更多的是家庭关系、亲子关系、职场关系中有困惑的人来咨询。人们无一例外是被自己内心中的恐惧逼进生命坠落的黑洞——焦虑、惶恐、迷茫、无助,永无止境地不知所措以及由之带来的愤怒,在内蚕食吞噬掉了我们感受幸福和快乐的巨大力量,在外则是表现出了各种拧巴和病态的关系,以心理疾病和生理疾病的形式凸显出来。
在新书上市之际,澎湃新闻记者致电柏燕谊,与她探讨了新书所涉及的种种心理学问题。对于当下社会人们普遍关心的亲子关系、婚姻关系中的种种现象和问题,例如“鸡娃式教育”、家庭暴力等等,柏燕谊也从心理学角度给出了她的阐释,并提出了专业的建议。 柏燕谊
柏燕谊心理问题需要尽早正视和解决,但人们通常很难察觉
你是怎么开始构思和写作《焦虑的大人和不被看见的孩子》这本书的?
柏燕谊:
这本书的写作大概开始于三年前。在心理咨询工作中经历了多年的积累,对于自我探索、亲密关系这些问题又有了很多新的思考,所以就想把它们整理出来,分享给更多的朋友。这是我最初的想法。当我开始写这本书时,这些想法在我内心也酝酿到了一个呼之欲出的状态。
为什么会对自我探索、亲密关系产生了很多新的思考和感触?
柏燕谊:
因为这两年我接到的关于亲子关系、婚姻关系、自我探索的咨询的比例有很大的上升。从这些案例中,我能够看到一个人内在的这样一种状态对于生活的影响是如何越来越趋于严重化的,就产生了很多感触。
在你看来,关于这类问题的咨询为什么会有明显的上升?
柏燕谊:
我觉得这跟整个社会的发展有关。过去人们对于自己内在的状态没有太多的觉察,没有发现需要去完成自己内在的探索,总觉得重要的是要多赚一些钱,上名牌学校,找一个好的工作,好像通过这些外在的物质化的努力,就能让自己的生活变好。
但其实这种外在的提升只能起到一部分的作用,还有一部分是需要我们内在有一个建构的。以前人们没有这种意识,我们的整个社会环境也没有去放大它,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没有很大的差异化,所以我觉得这给人带来的紧迫感还不是那么强烈。
但是现在,随着生活水平差异化的越来越明显,我们内在的焦虑也渐渐抑制不住了,就不能再单纯靠这些外在的物质化的东西去承受了。加上现在社会竞争激烈,会促使人们内心中想要更快地奔跑,拥有更多的东西。但奔跑是一种无休止的状态,它很容易把人推入一个又一个的焦虑之中。所以我觉得这跟整个社会的发展是有关系的。
你在书中提到,写作此书是在疫情期间,当时的社会氛围也比较紧张,人们活在一种焦虑和恐惧中。你是怎么理解这种社会氛围的?你自己又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柏燕谊:
我当时的状态还是挺平静的。在多年的心理咨询工作中,我也一直在进行自我探索和个人成长。所以当疫情到来的时候,我也会去调节心态寻找一些减压的方法。因为我本身是心理咨询师,而且参与了很多媒体的工作,所以当时参与了很多公益活动,例如公益讲课、心理援助等。在参与这些工作的时候,发现由于疫情带来的一种碾压式的焦虑,让人们内在原本就存在的焦虑状态一下子就共鸣出来了。所以当时也会更直接地看到人们的惶恐和愤怒,很多人去跟孩子较劲,跟夫妻关系较劲,这样的现象有很多。
这些更加深了我对人们内在力量的重要性的认识,正好我安排写这本书的时间与疫情重叠在一起,就也更坚定了我对这本书的写作是具有价值的一个信心。
你是如何理解《焦虑的大人和不被看见的孩子》这一书名的?
柏燕谊:
这个书名可能会让读者误会它是说亲子关系的,但其实“焦虑的大人和不被看见的孩子”,指的是当我们去面对外界,我们展现的社会角色是一个焦虑的成年人的状态;但是当夜深人静时,我们自己内心不被看见的孩子的感觉就会涌现出来。所以它指的是一个看起来很有力量的成熟的外在自我,和一个脆弱、悲伤、真实的内在自我,我们要如何去完成对这两部分的整合。这本书的核心讲的是这样的内容,之所以会涉及很多关于婚姻和亲子关系的案例,是想让读者看到我们内在的这样一种孤独脆弱的状态,如果不能自己去读懂和承担的话,就会不自觉地使用一些外在的关系去逃避自己内心的焦虑,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很多家庭矛盾的冲突。这并不是一本关于亲子教育的书。
确实如此,我刚看到这个书名时也以为它是一本关于亲子关系的书,读了以后才明白书名的真实含义。不过这本书里最吸引我的部分也是那些关于亲子关系的案例和分析。
柏燕谊:
是的,因为那些案例很直接,很赤裸裸,所以人们读了会有所触动,会有代入感。我们自己内在的焦虑,总会以一个方式呈现出来。有的人是以自己得抑郁症、焦虑症的方式,有的人其实会不自觉地把这些问题投射给孩子和爱人,通过家庭关系的破坏去呈现家庭内在的焦虑,甚至孩子就成为了某一症状的代言人。在这个时候,孩子会感觉到痛,才会去寻找原因和解决的办法。
做心理工作这么多年,我特别大的一个感触就是,比如说,三年前我给一个学校的家长开了个讲座,这些家长会跟我描述他们家庭的状态,而我通过家长的焦虑能看到一些问题的隐患。我以前特别实诚,就直接告诉家长,你这样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未来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可能性。他们肯定不爱听,因为人家孩子刚考上重点学校,会觉得危言耸听;但是三年过去之后,会发现有很多家长会带着孩子来找我做咨询,说什么时候我听过你的讲课,当时你说的是什么,然后现在我们家就出现这个问题了。有一种好像就被你这个“乌鸦嘴”给说中了的意思,但其实并不是这么一回事,而是他们的焦虑最终有可能出现的一个结果,是需要时间去沉淀酝酿的,最终转换成为一个真实的状态。凭借我自己心理工作的经验,我可以识别出某一种模式是怎样的,大概知道它的发展脉络和节奏。但对于家长来说,如果他们的孩子不辍学、不自残、不是要死要活的,如果没有真正让他们感觉到危险,没有觉得自己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他们是不会来直面这个问题的。
所以我做心理工作的时候经常有一种悲伤的感受,明明我们能够让他们只是在咳嗽的阶段,治疗一下就能好,但是非要严重到肺炎,严重到根本不好治,甚至是不能治的时候,他们才会来求助。因为心理问题大家一般都是看不到的,就不觉得那是个问题。
确实如此。大家通常只有当心理问题严重到影响正常生活的时候才会想到去看医生和咨询师。你是不是也是抱着防患于未然的心态去写了这本书,希望更多人能尽早认识到自己和身边亲密的人的心理问题?
柏燕谊:
是的,我是这样的一个想法。现在也有很多家长愿意提前去学习一些关于孩子心理健康、家庭关系或者亲子教育的知识。当他有这个学习意愿的时候,可能就误打误撞地买了我这本书了。书中的某一个案例,或是某一句话有触动到他,引发他的思考的话,他就有可能稍微调整一点点自己跟孩子或者爱人的相处模式,那就有可能会规避掉一个特别恶性的事件。我想如果这本书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作用的话,那对我来说会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因为这样可以避免有一个孩子站到楼顶上的时候,我们才去做工作,对吧?
这本书其实是写给正在经历痛苦的一些成年人看的,希望读者能够对于我自己为什么是这个样子,首先有一个认识;然后我能为我自己这个样子的改变,做什么样的努力和调整;对于我把我这个样子造成的一些破坏性的东西传递给我的爱人或者我的孩子的情况,我又能去做什么。让读者有意识成为痛苦的终结者,而不是又无限地将痛苦进行代际的传递。我对这本书有这样的一个期待。
其实很多人,如果对自己内在的问题没有进行探索和思考,可能会想我赶紧去找个对象,让我自己的内心不那么孤独或自卑,然后赶紧生个孩子,让我的孩子变得如何如何优秀,来缓解我内心的痛苦和恐惧。很多人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缓解自己内心的痛苦,来产生一种幻觉性的安慰的过程。可能父母没有得心理疾病,但是孩子就有可能得病。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读这本书去发现,我们要怎么面对和处理自己人生中的痛苦,怎么去做一些努力去改变它。
从“虎妈文化”到“鸡娃式教育”
是的,我很赞同。我觉得对孩子来说,青少年时期想要去明白这些,跟父母有很好的沟通是很难的。可能要等到年纪稍长,成年以后才会有这样一种意识。作为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我的感受是,我和我身边的同龄人普遍处理不好跟父母的关系。大家平时都在外地工作和生活,和父母的交流很少,等到逢年过节才能回家。那时的感受是很复杂的,一方面因为长期不在父母身边,是很想念他们的,见到会很高兴;一方面一回家又很容易跟父母起冲突。所以我想知道,作为青年人要如何与父母沟通,避免与他们冲突,能够与父母互相理解、达成共识。作为心理学专业人士,你有怎样的建议?
柏燕谊:
我觉得,作为青年人,如果我们不能跟自己和解,我们就谈不上跟父母和解。所谓的跟父母和解也是内在渴望期待,父母能够变成我想要的那个样子来爱我,就是和解了,对吧?如果做不到那一点的话,和解就永远不可能发生的。
所以这就是打着和解的名义,其实还是渴望着被爱护,你对以你自己希望的方式去爱护的那样的一个期待,依然是那样的一个状态。这是一种“伪和解”。而真正的跟父母的和解,其实是来自于,当一个人自己内心当中对于生活、对于生命、对于自己内心中的焦虑和恐惧有了很多觉察之后,能够接纳自己的这一部分之后,会发现自己跟父母之间的很多东西就不一样了。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就是“不养儿,不知父母恩”,这句话就听起来像道德绑架,但是我做心理咨询工作,思考了很多问题之后发现,所谓的“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就是,在我们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对于自己的无能为力,对于自己内心当中的焦虑、恐惧和不由自主的一些边界的突破。当我们自己养孩子之后,会发现原来我也不过如此,无论我多么爱孩子,我也做不到面面俱到,然后我就突然间对于自己内心当中的那种更理想化的完美期待,有了一个直面的机会。就是对于自我完美理想化的执念,有了一个放弃之后,我就完成了自我接纳,自我和解。所谓的与自己和解,就是我们终于知道,其实我们自己就是有很多的事情做不到,不论我爱或不爱,不论我愿不愿意,生活有很多的事情我是力所不能及的。这就是人的有限性。当我们对于这个问题有了一个体验性的感受时,在内心做到和自己和解,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和父母有了一个和解,这才是真正的和解。所以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一个立刻就能解决的问题,不是说跟我妈妈怎么才能三天不吵架,这就太表面化了。这其实就是刚才说的“伪和解”。我怎么能够做到一个希望的样子来让自己变得很乖巧,从而得到我想要的爱的方式,这其实是一种亲子关系中的角力。所以去做心理治疗、心理咨询,就是在体验关系的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来完成的我们内在的发现。这也是我们工作的方式。
关于亲子关系,延伸到一个家庭教育的方式就是,从过去的“虎妈文化”到现在的“鸡娃式教育”,面对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国家长往往会采取这样的教育路线。但同时青少年心理问题频发,青少年自杀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往往会引起社会普遍的关注。从心理学角度,你是怎样看待这些现象的?
柏燕谊:
我觉得从“虎妈”到“鸡娃”本身也是一个社会文明的提升的过程,虽然还远远没有到我们认为的尊重式的教育,但是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虎妈”是一种比较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简单地说其实是让孩子从内心觉得,如果我不服从,我就只有“死路”——当然这个词是在象征层面上的,孩子如果不服从,就可能失去妈妈的爱,完全是在那种简单粗暴的被恐吓、被控制、被暴力的一种状态下。而“鸡娃”指的是,我作为一个妈妈,我内心很焦虑,我有竞争的压力,于是我就让我的孩子十八般武艺样样都学得精;通过这样的一个我把“鸡血”打在孩子身上,而不是打在我自己身上的方式,让孩子呈现出那种亢奋的状态而出现好的结果。对于妈妈的控制和用“鸡血”去调动的一种“轻躁狂”的一个状态的同时,孩子也确实是有自己内在的一些技能选择收获的。
这不意味着我认同“虎妈”或者“鸡娃”的教育方式,我觉得这两种方式都是后患无穷的。但是就这个变化本身来说,我认为家长的教育方式终于能够从以前那种简单的恐吓,发展到现在能够给予一些技能型的注入,来让孩子也有自己力量的一种感受。但是这个有点,打个比方说,可能我给你吃点维生素就行了,但是我一下子给你吃了兴奋剂,用劲又过猛了。这都是有后遗症的,只不过这个变化从一个简单粗暴的家长制的一个妈妈,到现在变成了我也想带孩子去完成一些内在的提升。这种转变本身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不能指望它能立刻一步到位。我觉得之所以能发展到 “鸡娃”这一步,是因为大家在焦虑的状态下,发现以前那种简单的打骂和强制性管理不好使了,就需要“曲线救国”,给孩子“打鸡血”,让孩子自己觉得自己特棒特天才,直到有一天孩子承受不了了,要崩溃了,再往下发展就会到简单粗暴也不好使了,外在的物质化的所谓成功也不好使了,目光才会聚焦到内在的自我成长上。这两种教育方式都是后患无穷的。
总的来说这是一个进步,但是大家还是要去改进教育方式。
柏燕谊:
这不仅仅是教育方式的改进,而是整个视角的调整。以前的“虎妈”也好,还是现在“鸡娃”的妈妈也好,都是认为自己内在的焦虑是要通过塑造一个天才儿童的方式,去完成对于自己内在焦虑的安抚,我觉得这对孩子有巨大的伤害。我们的视角应该调整为:自己成为一个平和的、有力量的、温暖的妈妈。我就是孩子成长的土壤,当我这片土壤肥沃起来了之后,我这片土地上的这株玫瑰花才能真正地绽放。因为每一颗种子都有它自己的生命力,但如果我们只承认唯一的成功样态,就会扼杀种子本身的独创性。我的孩子能够成为什么样子,那是他自己的创造,对于妈妈来说,重要的是我自己这片土壤是不是足够安全,足够肥沃。如果我们把视角从整合孩子上调整到去整合自己,自己的土壤肥沃了,土壤上自然就能创造奇迹。
刚才你一直在说妈妈,我知道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妈妈”也可以换成“父母”。不过这里可以引出的一个问题就是父亲的作用。现在大家都在批评“丧偶式育儿”,呼吁社会重视父亲在亲子教育中的角色。在你介入的关于家庭关系的案例中,父亲的作用是否相比过去有所提升?
柏燕谊:
我觉得这几年真的有很大的变化。今天下午我做了一个线上的直播课程,最后20分钟是提问互动时间,以往全都是女性来问关于亲子关系的问题,如果男人要发问的话,通常会问职场关系、压力或者是管理的一些问题。但今天下午有一个爸爸就在问我,对于已经考上大学的孩子,作为一个父亲要怎样去理解和面对?这其实就是变化的体现。
现在我接受的关于亲子问题的咨询,大致是4:1的比例,就是有四个女性提问,就有一个男性提问。虽然这个比例看起来有点小,但是它也出现了,就是一个好的现象。现在已经有很多爸爸觉察到自己需要关注孩子的成长,这需要一个过程。我觉得以往父亲在家庭教育中的缺席,其实是跟我们中国文化的“男主外,女主内”是有关的,这种文化上的东西,还真不是说变就能够变得那么彻底的。
甚至就是在我们社会这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对于家庭在我们的人生中到底意味着什么,大家的认识过程也是非常漫长和缓慢的。我是上世纪70年代生人,我小的时候,父母以单位为家,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那个时候他们从未认为自己应该为家庭多做一些付出,需要陪伴孩子,那时候没有这样的文化氛围。所以那时候连妈妈都没有回归到家庭中,就更别说爸爸了。而父亲确实应该更多地投入到家庭中,因为父亲对于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边界性、力量感、原则性的培养,能起到一个不可替代的功效。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遭遇家暴的人不敢逃离,是因为恐惧被抛弃
关于家庭问题,我还很想知道,你介入了很多有关家庭关系、婚姻关系的案例,其中是否有涉及到家庭暴力的案例,对于这种情况你是如何分析理解和解决的?
柏燕谊:
有的。家暴有太多太多种,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暴力,背后有太多的可能性了。简单来说,夫妻之间的家暴,很大的一部分是因为被家暴的一方的不独立,不管是经济上还是情感上的,让受暴者不敢去逃离这样的环境,从而纵容了施暴的一方。我觉得对于施暴者来说,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内心非常脆弱的,同时又是很愚昧的。他们没有办法通过语言,通过升华的方式去表达内心的痛苦,并且能够去安慰。所谓升华的方式,就是指当自己内心很恐惧和焦虑的时候,去努力工作,或者去跳舞健身,来完成对内在消极情绪的释放、转换和安抚。他们做不到用优雅的升华的方式去处理内在的问题,就会选择简单的暴力方式。所有的施暴者都是处在特别懦弱的一个状态,他的内心需要去寻找一个更弱小的生命,去进行一个力量式的炫耀,去完成对于自己内在聚合的一种脆弱的逃离。当然我指的是常态的施暴者,而不是那种反社会人格的暴力者。
对于受暴者来说,因为不独立,所以面对一个如此无能而又暴力的对象时,受暴者依然认为这是自己生活中唯一一个可以依靠的对象。受暴者的心理是:如果离开这样的一个对象,我将进入一个更恐怖的生活状态,内心当中对于我能够拯救我自己、能够承担我自己的生活、能够去开创一个新的生活,受暴者是不自信的,甚至是完全不相信的。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受暴者宁愿待在这样的一个暴力环境当中,也不敢去打破这个不好的模式去创造新的生活。这其实跟受暴者在情感关系中的价值感是有关系的。我在做心理工作的过程中,看到有很多遭受暴力的女性其实都有很好的社会地位和工作能力,但是她们在家庭婚姻关系中却遭受暴力。这不是因为她们没有经济独立能力,而是在情感的关系上没有独立的能力。在这一类的女性心中,她认为她在亲密关系上是没有地位和尊严的,是会被抛弃的,有一种对于被抛弃的巨大的恐惧感。对于内心中没有自我或者自我不强大的人来说,最坏的关系不是暴力关系,最坏的关系是没有关系。所以她们对于没有关系的恐惧感那么强烈的时候,就不敢放弃一段不好的关系。
所以你认为从心理学层面上解决家暴问题,主要还是要受暴者自我觉醒,自我独立,是吗?
柏燕谊:
因为对于施暴者来说,我觉得他们是需要被法律干预,第二步才是去做心理干预。但是对于受暴者来说,我们至少有求生的本能。为什么我们的本能都消失了,这个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都说,这辈子谁还不会遇到个把人渣什么的,我们都有可能遭遇到,为什么遭遇之后,却没有能力去捍卫自己保护自己,我打不过我还不能跑吗?然而我都不敢跑了,这个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我们与其坐等被救,还是应该先自救,如果我们都没有一个自救的意识的话,只会不断地重复这种恶劣的状态当中。因为受暴者在亲密关系中的一个低自尊的状态,从一个施暴者手里逃走了,还是有可能会到另一个施暴者身边去。
还有一种家暴是对孩子的暴力,那就是另一个话题了。通常父母内心对自己的评价如果特别低,就会进入到一个高度焦虑的状态,会形成对于自己内在的一种厌恶和愤怒,在面对孩子的时候就会失控,会使用一种暴力的处理方式。
你前面说到,对于施暴者首先需要法律上的干预,而不是心理上的。但是目前《反家暴法》才实施五年,在具体实行中还是有很多不成熟之处的。并且其实我们平时所说的家庭暴力,也不是每一起都是情节非常严重的,有很多暴力其实是很隐蔽的,甚至都很难察觉,就更不要提进行一个法律上的制裁了。所以在心理干预上是否能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柏燕谊:
确实。但我依然不会把我的工作的救助重心放在对施暴者的心理干预上。他们内在的那种模式是向外的,他不痛,因为他拳头没落在他自个身上,而是打在别人身上,而且他对于自己的暴力是有一个合理化的过程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对他的心理干预能够起到的作用和效果并不显著。可对于受暴者来说,是真的疼,真的绝望了,已经没有人能够去拯救自己。施暴者还能通过打老婆来让他自己获得被拯救的感觉,而被打的老婆就完全处在一种没有被拯救的状态。所以针对受暴者的心理工作我觉得是更紧迫,而且也是会更有效一些的。
心理咨询的关键不在于拯救你,而是指导你完成自救
现在心理健康越发引起人们的重视。随着人们对心理疾病的了解不断加深,也有更多人能够认识到自己的病情并尝试寻求办法进行治疗,但是寻找适合自己的治疗方式的过程中依然会不断碰壁。对于病人来说,心理咨询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
柏燕谊:
实际上没有任何一种治疗的技术能够治疗所有的疾病。所以心理咨询是不是能够对心理疾病的患者起到一个疗效呢?我没有统计过,但是我认为它在一定程度上会有帮助。除了一部分心理疾病有一些遗传的因素之外,其实我们大部分内在的心理冲突是由于没有被我们觉察,也没有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智慧技巧来去缓解,所以在内心中越来越大,就形成了症状。
所以你看心理疾病本身就是因为内在的心理冲突而导致的,而心理咨询就是帮助我们去看待我们内在的心理冲突到底是什么,是如何形成的,它意味着什么,它是怎么作用在我们身上的,它对我们有什么建设性的帮助和破坏性的帮助。通过对这方面的梳理,来完成对一个人心理的治疗的过程,所以它一定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疗效的。有的人觉得心理咨询没用,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去面对自己内在的冲突,渴望有一个神奇的力量能够去拯救自己。当人们没有做好准备去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他们总是希望能有一个神迹出现,来完成对于灾难的掩盖和消除。对于这一部分人来说,心理咨询就成了他们嘴里的没用的东西。因为他们所谓的“没用”,指的是不能快速即刻地让他们再一次从他们内在的真相的这部分上逃开,不能立刻让他们被拯救,而是需要他们去完成自救。
有时也不完全是这样的情况,对于有些心理疾病患者来说,他们是遇上了不适合自己的咨询师。对于怎样挑选适合自己的心理咨询师,你有什么建议?
柏燕谊:
对的,是有这样的情况。对于咨询师,你还得谈两下才知道是哪个是真的适合自己。咨询师也是有匹配度的,因为咨询师也是人,都有自己的模式,也有自己的一些习惯,以及优势和短板。再好的咨询师,也不是所有人到他面前,都能够有治疗的效果。
第二种可能性是,确实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咨询师是在成长的初级阶段。所以碰到了这样的咨询师可能会有不太好的体验。我前面说的其实是第三种可能性,即自己还没有做好真正改变的准备的时候,说我没有遇到好的咨询师,总比说我还没有想真的改变要更容易一些。
从事心理工作多年,你觉得心理学为你带来了什么?
柏燕谊:
它让我感觉到生活很美好。生活依然一地鸡毛,但我能够从这一切里看到很多美好的东西。并且能让我在不论遇到怎样的事情和情境时,都能相对保持内在的平衡,不那么惶恐也不那么忐忑,能够很安稳地和自己在一起。以前20多岁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休息日,我根本就坐不住,得去找点事做或者约朋友,还得假模假式地看看书,要不然就会有愧疚感。但是现在我能够特别快乐、平和、从容地和自己相处,我和身边人的关系也都特别好。即使没有赚太多的钱,我也没那么焦虑。然后朋友也多起来了,工作也变得很有幸福感。
我觉得这就是心理学带给我的。如果不是因为我自己从中获益,我是不会它分享给别人的。我之所以致力于做心理咨询的科普,包括在媒体参加一些节目,是因为心理学真的让我的生活变化了,让我感觉到幸福和平静。而这些幸福平静的变化并不来自于外在的环境,而是来自于我的内心。所以我相信心理学,能够让人们走出内心的恐惧和黑暗,走到阳光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