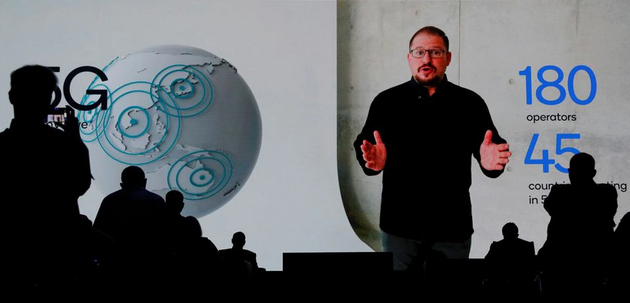原标题:爱尔兰作家萨莉·鲁尼的文学实验
 图片来源:Laura Peretti
图片来源:Laura Peretti爱尔兰青年作家萨莉·鲁尼(Sally Rooney)在她的头两部小说《聊天记录》和《正常人》中重现了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标志性风格,即压抑与疏离。“在埃布罗河谷的另一边,白色的山冈起伏连绵,”海明威曾在《白象似的群山》写下此佳句。而鲁尼也以相同的冷峻笔法,令其处女作当中的叙述者弗朗西斯在打量大学图书馆时想到,“在里面,一切都是棕色的。”孤立地看,鲁尼的这句话略显荒谬,须参照上下文来把握其意义:弗朗西斯刚收到了情人的妻子发来的电邮,在为打开它做心理建设的同时,她企图以聚焦周遭环境的方式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但未获成功。起码以我的想象而言,她的脑海里就是这些东西。面对这位对细节不大上心的作家,读者难免会迫不及待地开始“脑补”。
鲁尼也和海明威有颇多相似之处——还有雷蒙德·卡佛,她坦承自己深受海明威的极简主义影响,并对其有所革新——她笔下的对白看似漫不经心,但却具有中子星一般密度的戏剧性和情感色彩。 以下是《正常人》里的少年情侣康奈尔和玛丽安在初吻后的互动:
鲁尼对视点的把握也相当娴熟。她的控制力是如此优秀,以至于可以通过钝化康奈尔的知性并强化其感官方面的感受,来传达他与玛丽安重聚时的兴奋:“她穿着一件露背的白色连衣裙,皮肤似乎晒黑了。 她一直忙着晾衣服。 外面的空气几近凝固,洗好的衣服挂在那里,带着些湿气,一动不动。” 对于角色在思想上的局限和偏见,鲁尼始终保持尊重。弗朗西斯年纪轻轻又胸无城府,连新鲜的鳄梨都没吃过,曾幻想自己的名字被印在杂志上,“用主干加粗的衬线字体。”她以一个几乎已成通用的比喻来形容自己的第一个男性情人的躯干:“像是某座雕像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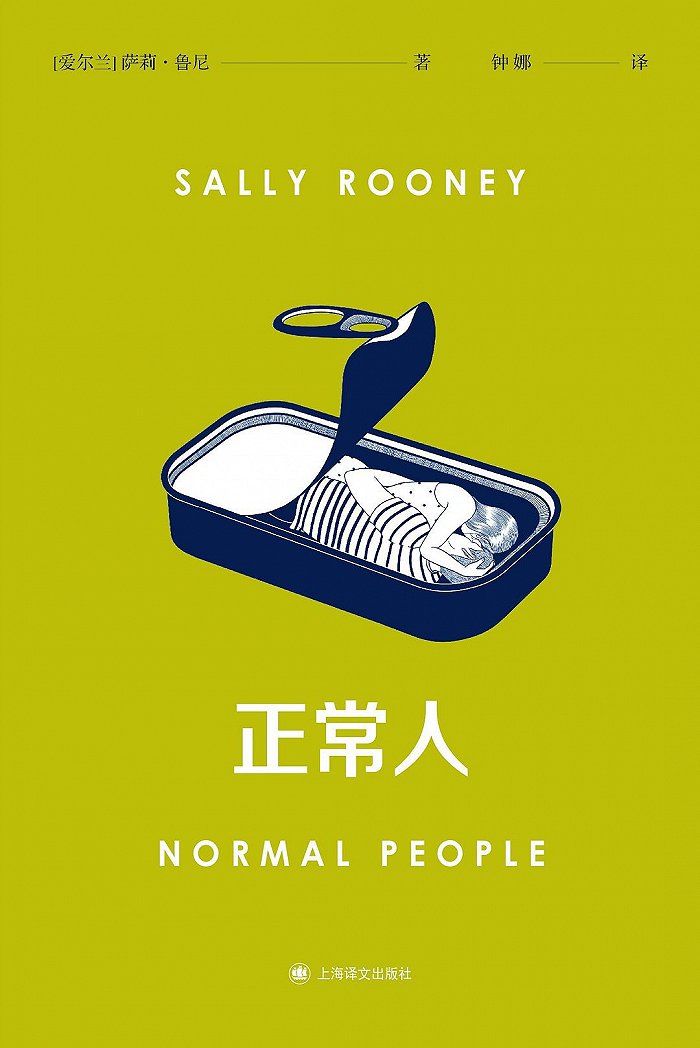
《正常人》
[爱尔兰]萨莉·鲁尼 著钟娜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群岛图书 2020-7
在鲁尼笔下,叙事的声音与各个角色的意识之形态呈现出一种严丝合缝的关系,她借此在千禧一代中赢得了“肖像画家”的美誉——而这同时也为她招来了不少政治上的批评。她的许多角色都是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左翼大学生,就像自古以来那些初出茅庐的知识人一样,充满热情但并不完全明白自己谈论的东西的究竟是什么。他们熟悉各种理论,但连家庭作业都做不好。在舞台剧《朱门巧妇》的演出上,弗朗西斯注意到了男主角服装上的洗涤说明,然后一下子就出了戏:“我得出结论,某些类型的真实具有一种不真实的效果,这令我想起理论家让·鲍德里亚,虽然我从没读过他的书,而且他的作品可能根本就没怎么关注这些问题。”有关共存于这句话之中的已知与未知,可以写一整篇论文,但它也相当巧妙地捕捉到了一个只会罗列理论家姓名而不知其实际论著(这对她而言是一种好运)的年轻人形象。事实上,弗朗西斯的洞察力还算不错了——无论最先想到这一点的是谁。
鲁尼向采访者表示,她和自己书里的某些角色一样,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而美国的批评者——许多人与她同为千禧一代,则把她拉进了至少自2016年总统大选前夕就已经肆虐于进步派政治圈子的说话态度、意识形态纯洁性与证据标准大战。玛德琳·史华慈(Madeleine Schwartz)在《纽约书评》上指责鲁尼书里的“政治大多流于姿态”,并指出她笔下的主人公远远谈不上是反叛者,而“全都是规规矩矩的好学生”。贝卡·罗斯菲尔德(Becca Rothfeld)则在《观点》杂志发文称,左派只是一些时尚的姿态,对此鲁尼并没有直接予以揭穿,这令人遗憾。在《自由》杂志的后续评论里,罗斯菲尔德走得更远,她甚至直斥鲁尼的小说是“道貌岸然型文学”:“充满了自我宣传和正确观点的表演式传播。”
我也认为鲁尼笔下角色的左翼立场是肤浅的,这些人的世界观很大程度上因小说的情节设定而未能充分展开。“整个有关‘英才统治(meritocracy)’或别的类似的东西的理念就是邪恶的,你应该能明白我的想法,”玛丽安告诉康奈尔说,后者是一个来自工人阶级单亲家庭的男孩,拜自己的固有天赋和勤奋所赐,考上了名牌大学,在那里成了一个“和富人扎堆(rich-adjacent)”的人——换句话说,就是典型的凭才能获得权位的精英。比较而言,弗朗西斯有时会被闺蜜波比说成是共产主义者,但在她生出当作家的雄心后,径自把波比的人生故事当成文学素材来加以利用,而波比直到这个揭露性的故事即将付印,才从第三方那里知道了这件事。我不认为这种不一致性会有损于小说,也许是因为我是网络上所谓的老一代,仍旧认为政治与文学各有各的使命。相当一部分年轻人的思维及说话方式的确与鲁尼的角色高度相似,而我则比较喜欢阅读那些能够从某个既有同情心又保持足够距离的视点来审视其世界的小说。
 《正常人》剧照
《正常人》剧照在鲁尼的前两部小说中,对传统关系的渴求与对激进政治的肯定至少是一样突出的,许多批评家因此认为,她就算不至于轻忽草率,起码也不够严谨。一个强壮的男人与一个顺从的女人的结合似乎颇能吸引鲁尼,恰如对上帝的信仰曾经让马修·阿诺德着迷:她无法再让自己深信不疑,但她也无法停止怀念这种结合曾赋予生命的形态与意义。在她的女主人公的生活里,怀念不时会以受虐狂的形式出现。在得知自己的已婚情人未能让她怀上孩子后,弗朗西斯把自己手肘处的皮肤都抓破了,后来还要求情人殴打自己。玛丽安曾让某一任男友打她,又让另一个情人绑住自己手腕并数落她如何一文不值,在找到一生的挚爱后,她都还在要求对方殴打自己。
在我看来,鲁尼并不需要为这些而自责,也不需要提出充分的解释,小说家的职责乃是关注与探索。如果这群与鲁尼年纪相仿的角色已经能够游刃有余地处理此类冲动,那就太不自然了。弗朗西斯也试过柔化自己的自虐冲动——试图驯服它并使之社会化——使自己服从于某种具有为自己量身打造之意味的基督教,她似乎希望以某种更广泛的交融(communion)来淡化自己在浪漫伴侣及三角恋当中滋生的负罪感。她开始阅读福音书,在教堂里静坐时,她还悟出了某种世界景象,此景象乃是她自己与其他许多人类共同缔造的。“如今在我眼里,没有任何东西是由两个人乃至于三个人构成的,”她向波比表示。在《正常人》的结尾处,玛丽安试图诉诸主动从属于康奈尔这一办法来克服自己的受虐狂倾向,后者拒绝在床上伤害她这个有意识的人,而她的理由与弗朗西斯的共同体构想相通:“没有人能够彻底独立于其他人,于是她想,何不放弃这种努力,朝另一个方向大步前进,何不干脆在各方面都依赖别人,同时也允许他们依赖你。”不幸的是,承认人类生活是一种协作,对缓和此类自我贬低的冲动并无助益。鲁尼的角色始终未能完全化解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冲突。
鲁尼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留下的一系列未曾解决的困惑:顺从的冲动,为自己量身打造的基督教,以及一种相互关怀的伦理观,这种伦理观在她的新作《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Beautiful World, Where Are You)当中再次回归。这本书的标题取自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的一首诗,该诗赞美了一段富有神话色彩的过往,那时与神圣者发生关系乃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与《聊天记录》类似,新作讲述了两对爱尔兰情侣的故事。第一对情侣是年轻的小说家爱丽丝·凯莱赫(Alice Kelleher)与仓库分拣员菲利克斯·布雷迪(Felix Brady),前者在纽约遭逢精神崩溃后迁居到了爱尔兰西部,后者则是个沉默寡言、嗜酒如命的人,他们在交友软件上相识。鲁尼把自己的职业生涯轨迹“借给”了爱丽丝:年仅29岁的爱丽丝已经名利双收,过着富裕的生活,她的两部小说大受出版业界青睐——“一开始以肯定为主,”鲁尼写道,“后来这种肯定有了谄媚意味,随之而来的就有一些负面的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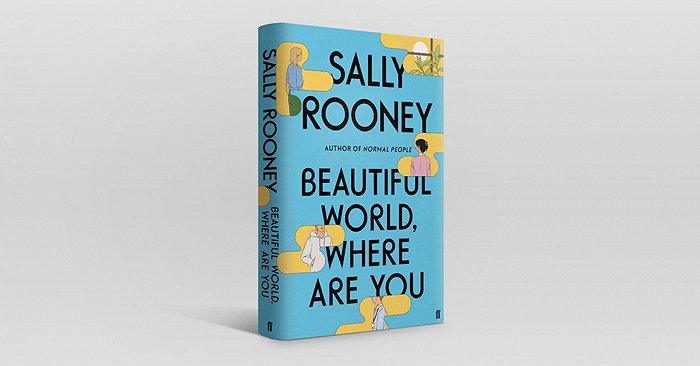
《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
这种借用给了鲁尼一个回应批评者的机会,在小说家可以是马克思主义者、而小说极少如此这一点上,她是同意批评者的。“小说依靠压制有关这个世界的真理而起作用,”爱丽丝在一封写给挚友的反思性邮件里这样谈道,她和这位朋友的交往始于大学时期,在全书的情节中皆有信件来往。小说对读者的抚慰作用在于,它令读者可以自由地关注诸如“人们究竟是要分手还是继续在一起”之类的琐碎事情。而朋友的回应是,这个问题是一般性的,不局限于小说,并指出大部分人在临终时都敏锐地意识到了时间的宝贵,更愿意谈及亲密的个人关系,而非抽象层面上的人类正义。
小说里的第二对情侣是艾琳·莱登与西蒙·科斯蒂根,前者正是与爱丽丝通信的好友,后者与艾琳是青梅竹马的关系。艾琳在一家文学杂志工作,自认为不擅社交。西蒙比艾琳大5岁,容貌极为俊美——在某个品行端正的左派政治家那里做政治顾问,也在罗马天主教会领受圣餐,曾考虑加入神职人员的行列。他的父亲曾指责他有一种弥赛亚情结(指试图通过拯救他人使自己获救,通过扮演一种救世主的角色来体会到自己的价值),小说里大概不会有人对这一论断提出异议。在西蒙与艾琳重启一段始于近十年前的浪漫关系的第二天早上,艾琳陪西蒙去做了弥撒,两人在那里手牵着手,宗教和道德方面的念想很快就融入了温和的“支配与顺从”游戏,也就是两人在床上玩的那种东西。“我觉得自己十分享受被你摆布的滋味,”她告诉他说,而他的回答是,当她顺从并任由他的手指探入她的身体时,便处于一种“恰到好处”的状态。凡俗的性爱,带着一丝香火气——这一切都很像缪丽尔·斯帕克(Muriel Spark,英国知名作家,以言简意赅著称,其笔下的“布罗迪小姐”亦有敬仰上帝同时又纵情声色的一面,故有此类比——译注)的笔法,不过口味没她那么重。
而爱丽丝和菲利克斯的头一次见面则充斥着一种恐怖的气氛——她表现出十足的尖酸刻薄与傲慢,他则一副不屑的样子,甚至有些凶暴。事实上,他先是不停地骚扰她,后来又故意放她鸽子,在酒过三巡的时候要求与她发生关系,还告诉她说没有人会关心她。鲁尼对场景的精心把控令爱丽丝保全了她的大部分尊严——但我认为其代价则是牺牲了菲利克斯作为一个角色的连贯性。读者此前已经得知,同一个男人会在床上询问女方偏好什么样的性行为表达方式。鲁尼宣称菲利克斯是双性恋,这个说法基本没有什么根据,也让他的人物形象变得更趋模糊了。在我看来,他的双性恋倾向就好比是香叶这种调味料,号称已经加进了汤里,实际上并没有入味。
鲁尼虽然希望把她对于爱的想法铺陈出来,但落实的力度还不太够。与她早期作品中的那些任性之人不同,《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当中的四人组看起来很善于制定周密的计划,甚至于有些呆板,读起来跟寓言里的人物差不多。鲁尼引入浪漫悬念的努力显得有些勉为其难。我很难说服自己相信爱丽丝和菲利克斯的结合不会是短暂而痛苦的,也不明白为什么艾琳和西蒙在第3章以后还没有正式确定恋人关系。
 萨莉·鲁尼 图片来源:Faber
萨莉·鲁尼 图片来源:Faber我推测,许多读者可能会很怀念鲁尼在头两部小说里表现出来的那种开门见山与凝练,但她的才华依旧是值得称道的。她大胆的视角转换即是一个颇有意思的闪光点。爱丽丝与艾琳的漫长邮件来往之中,穿插着一种第三人称全知者的视角,鲁尼在这部小说里首次尝试了这种视角,一位严肃的艺术家能大胆试水新工具,这令我倍感欣慰。例如,在某一章的开头部分,她在没有任何人进入的情况下描绘了一番西蒙的起居室,在这一章的结尾处,当西蒙与艾琳进入卧室并关上门以后,她又把同一间屋描述了一遍。在书中另一处,鲁尼还把菲利克斯的拣货工作与爱丽丝履行公关职责这两件事并列起来叙述,即便这两个行为之间有着一定的时空距离。我很喜欢这样的游戏。
接下来谈一谈观念本身。正如鲁尼第一部小说里有关现实主义与服装标签的即兴之论所表现的,她简单平实的文风之下潜藏着非凡的智慧。与每一个有思想的人相似,在过去几年的危机中,她迫切地感到需要创立各种新理论,借助于爱丽丝和艾琳的邮件往来,她思索着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失败、美、塑料制品、少数群体的身份认同(艾琳似乎是个尤其强调阶级的社会主义者)、艺术在特朗普时代的角色,以及某个地中海文明在青铜时代晚期的突发性衰落与崩溃。
这些电子邮件看起来不像是小说中的章节,而更像是散文的组成部分。艾琳和爱丽丝不断回返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充满爱意的、相互依赖的共同体。 为了某种更高的团结,无私似乎是必要的。艾琳对信徒在弥撒过程中真诚地将心灵交托给上帝的做法十分钦佩。 爱丽丝则引用了普鲁斯特的一句话,这句话暗示世界上存在着一种独一的智慧,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身体出发看向它,就好比观众从许多不同的座位上注视着同一个舞台一般。
但结构也是必要的。爱丽丝写道,有某种东西可以使关系“柔软得像沙子或者水”,如果没有装载它的容器的话,人们便只能“把水倒掉,放任它流走”。而这只会导致浪费,带不来乌托邦。虽然爱丽丝和鲁尼之前塑造的角色相似,对传统的婚姻并不眷恋,“但它起码构成了一套做事的办法,”她写道,这话听起来就不太像马克思主义者,而更像柏克主义者(Burkean,在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光谱上,柏克属于古典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译注)了。鲁尼暗示,友谊也许正是装载那种无形的东西所需要的无形容器。当爱丽丝和艾琳分开一阵又重聚时,鲁尼想知道的是,她们是否瞥见了“某种潜含在生活的表层之下的东西”,“那并不是非现实,而是一种隐藏起来的现实:无论何时,也无论何地,一个美丽的世界始终是存在的。”
《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略有18世纪的韵味,这体现在它的哲学式腔调上,也体现在书中的虚构人物几次三番地讨论要如何调和“浪漫主义的自由”与“爱带来的责任”之间的矛盾上。它让我想起了歌德的《亲和力》这部小说,和这本书一样,它令我产生了一种难以解释的浓厚兴趣。在新出的小说里,鲁尼并没有为她的洞见找到合适的容器,正如她笔下的角色也同样没有找到理想的社会政治结构来促成人类的联结(connectedness)。鲁尼本可以走一条更加便捷的路径,炒一炒冷饭就了事,但她似乎秉持着一种启蒙运动时期的艺术家天职——不断地去试验。
本文作者Caleb Crain是一位作家,常驻纽约。
(翻译: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