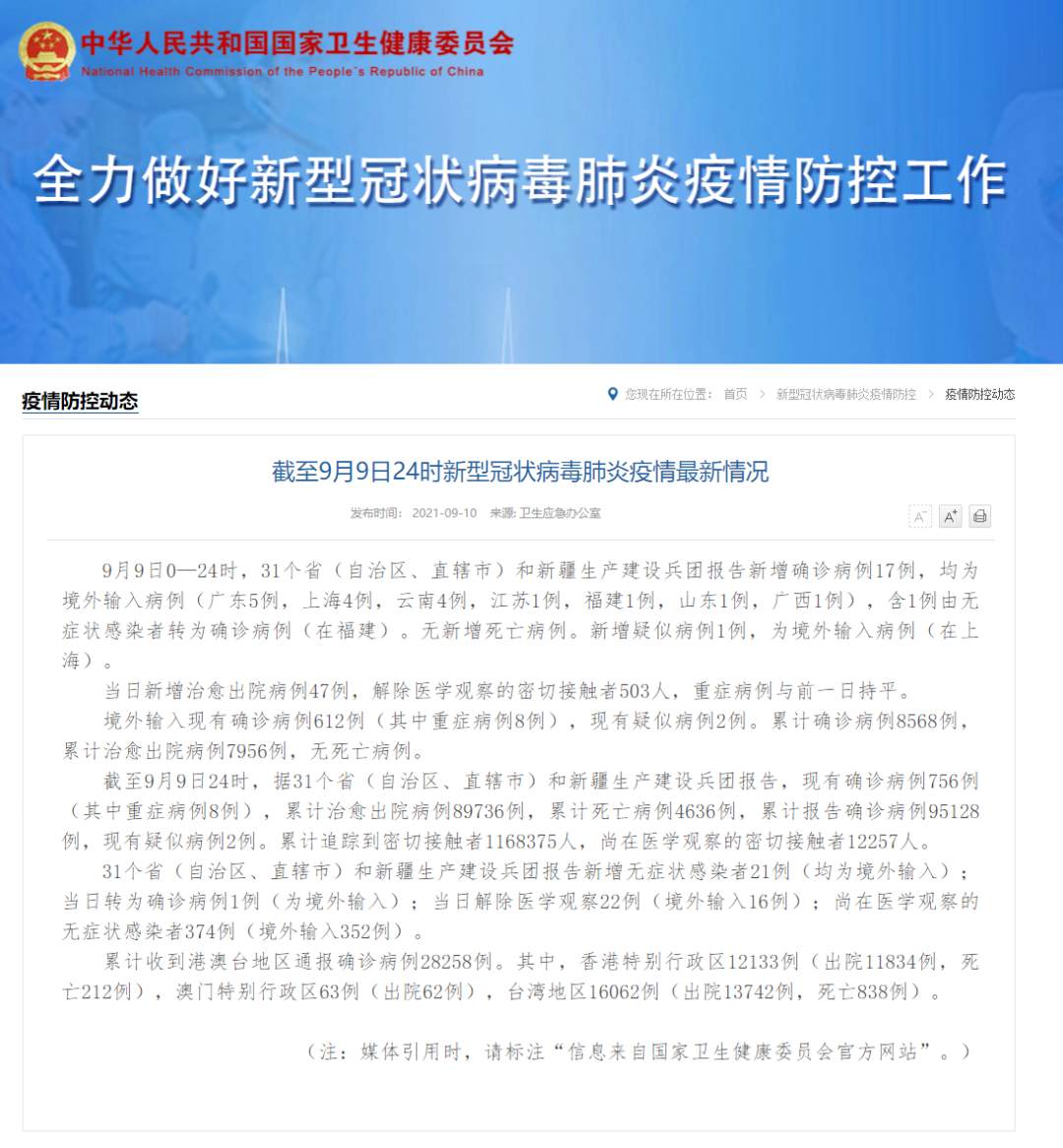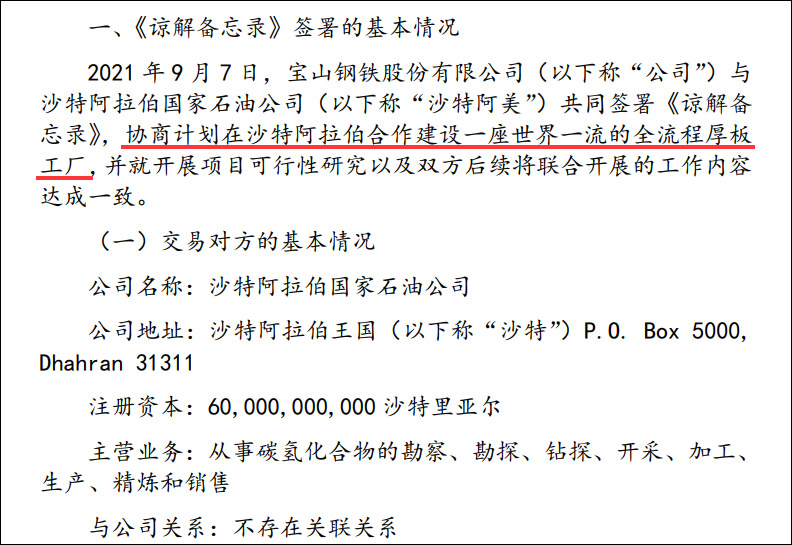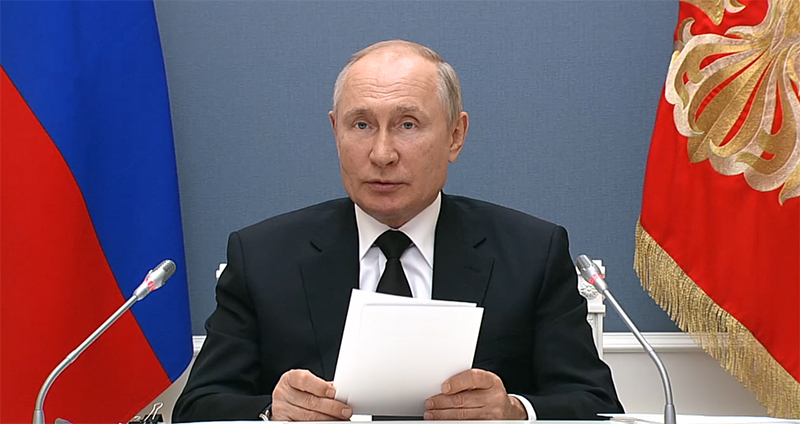单墫是我国著名数学家、数学教育家,也是1983年我国首批获得理科博士学位的18人之一。在过去几十年中,他一直专注于数学传播、普及和数学竞赛的人才选拔及相关研究。1964年他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数学系,被分配到南京成为一名中学教师。1978年,35岁的他被选拔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读研。他曾接受常庚哲、陆鸣皋等知名数学家的指导,后师从著名数学家王元。
单墫自述“对数学普及饶有兴趣。因为当了一辈子教师,而且‘好为人师’,所以写了不少普及数学文化的文章”。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接触到的多位数学大师也给他带来很大的影响。在他所著的《单墫数学与教育文选》中就谈到华罗庚、陈景润、王元、常庚哲等多位数学大师的风采,以及对后学潜移默化的影响。
华罗庚
聪明在于学习,天才由于积累
华罗庚先生非常重视培养人才与数学的普及工作。他对我国数学界影响之大,恐怕没有人能与之相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没有华罗庚就没有现代的中国数学。
1950年,华先生回国后不久即参加数学研究所的筹备。1952年出任数学所所长。他广泛搜罗人才,并亲自领导数论组与代数组的讨论班,培养研究人才。
他还在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教,亲自给大学生上基础课并撰写讲义,即后来出版的《高等数学引论》。
华先生特别热心数学的普及工作,经常给中学师生与数学爱好者作通俗讲座,并写作一些科普读物,如《从杨辉三角谈起》《从祖冲之的圆周率谈起》《从孙子的神奇妙算谈起》《数学归纳法》《统筹方法平话》《优选法平话》等。
华先生非常重视自己所做的普及工作。在日本东京大学作报告的提纲中,就将一生的工作分为“理论”与“普及”两块,相提并论。
华先生还说: “深入浅出是真功夫。”他的报告就是深入浅出的典范。1964年,我第一次听到华先生的报告。华先生特别注意听众的要求与接受能力。报告一开始就说: “今天来的人很多,我一定要把‘音’定好,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
他定的“音”果然恰到好处。那天他先举了茶杯与杯盖的例子。圆口的茶杯,杯盖也是圆,直径稍大一些。杯盖无论怎么放,也不会落到杯中。但是,如果杯口是正方形呢?即使杯盖是稍大的正方形,依然会落入杯中。这个通俗的问题立即引起了大家的兴趣。接着,他又举了当时苏联发射洲际导弹宣布的禁入区域。他说,“从这个四边形区域的四个顶点,立即可以推出发射塔是在乌拉尔山的某处。”这样的例子雅俗共赏,充分说明生活中处处有数学,生活离不开数学。
10年浩劫之后,华老决心振兴我国数学。1981年,年过七旬的华老率庞大的讲学队伍来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同行有王元、吴方、杨乐、张广厚等,又邀请复旦大学的夏道行、谷超豪、胡和生,南京大学的周伯勋、叶彦谦,还有科技大学本校的龚升、石钟慈、彭家贵等。
国内20多所大学,派近百人前来听讲。华老自己做了“矩阵几何与狭义相对论”“微积分方程的几何理论”“普及数学方法的若干个人体会”与“国民经济中所用到的数学方法”等4次报告。听众如潮水般涌向报告厅,对华老的报告热烈鼓掌欢迎,反响极为强烈。
华老还认真听取其他人的报告。有一次吴方先生的报告中用到一个三角不等式,华老立即说:“这个不等式,我来证明。”说着便起身拄着拐杖上了讲台,当场进行演算。可见华老虽已年逾古稀,思维仍然十分敏捷,而且童心未泯,很喜欢露一手给大家看看。
华老特别重视数学竞赛。早在1946年访苏期间,就专门考察了数学竞赛活动,在心中埋藏了中国倡办数学竞赛活动的种子。1956年,华先生著文欢呼“我们也要搞数学竞赛了”,并亲自倡导在北京、上海、天津与武汉四大城市举办了中学生的数学竞赛活动。
可以告慰华老的是,在华老逝世的次年,我国首次派出正式的6人代表队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IMO),并取得了三金一银一铜、总分第四的好成绩。1989年,又在IMO取得总分第一。1990年,在北京成功地主办了第31届IMO,并再次取得总分第一。
华老对年轻一代寄予厚望。他写了很多介绍学习方法的文章,把自己的心得传授给大家。他勉励青年人努力学习,反复强调“聪明在于学习,天才由于积累”。在给母校金坛中学题词时,华老语重心长地写了4个字: “后来居上。”
陈景润
把软卧票给我,我自己去换成硬卧
陈景润先生有恩于我,我的博士答辩就是陈先生主持的。那一天,报告厅挤满了人,各系的学生都来了,都想亲眼看一看这位仰慕已久的数学家。后面的人看不到,就站在折叠椅上,椅子踩坏了很多。
陈先生没有惊人的外貌,永远是那么简朴,那么平常。平顶头,戴一副极普通的眼镜,眼黑显得略大些,转动得比较少,老是呈沉思状,神游在数学王国里。
陈先生为人非常谦恭。1984年夏天,先生住在贵州民族学院。我们上山拜望,陈先生一定要亲自沏茶,我们连声说不必费事,先生坚持要沏,水瓶空了,又提 了水壶,装水,点火,忙个不停。我们告辞出来,又一定要送。因为是晚上,又是山路,大家一再请先生留步,先生才很勉强地答应了,站在月光下,目送我们离去。
我们沿着蜿蜒的山路走了一刻多钟,到了山脚,正要上公路,忽然后面跑出一个人,扑到大家身上,大笑:“我一直跟在后面,你们都没有发现。”原来竟是陈先生!
1957年,由于对塔锐问题的研究受到华罗庚先生的赞赏,陈先生被调入数学所。那时他还很年轻。从1957年到1966年的10年时间做了很多出色的工作。这么多的成果,全是在6平方米的小屋中,啃着干馒头完成的。
“文革”后,陈先生已经誉满天下。一次,我奉校方之命请先生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讲学(当时我在科大)。这时先生已搬过家,但也只有两小间,仍然单身。先生执意留我吃饭,亲手做了自诩的“盖浇饭”,就是一碗米饭一个荷包蛋加上若干片胡萝卜,大概先生平时自奉的伙食还没有这样“丰盛”。先生还一再提出“不要买软卧,硬卧、硬座都可以”,并向我要票: “把票给我,我自己去换成硬卧。”
王元
我的学生,我都要和他合作一篇文章
王元先生是我的恩师,大家都尊称他为元老。1978年4月我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读研。此前,1964年我从扬州师院数学系毕业,并在中学任教14年,扬州师院数学系的大学基础课与中学数学研究抓得极为扎实,但当时数学研究在全国高校并未形成风气。
我到中科大,跟常庚哲老师学习样条函数,又参加陆鸣皋老师主持的解析数论讨论班与冯克勤老师的代数数论讨论班。如何进行科研,实在是门外汉。
元老从北京来合肥指导,对陆鸣皋老师与我做的工作大加奖励,并在校系领导面前表扬。于是我就被定为首批博士学位的一个候选者。元老多次谈他自己学习与治学的心得,他说读中学时并不很努力,外国电影倒看了不少。考大学时未能考上最好的大学,读了英士大学。但后来院系调整,合并成立浙江大学。
元老曾说现在他不急于陷入某个问题之中,大部分时间在观察动态,看看有什么值得做的有意义的问题,有什么能够做的问题,他多次对我说太小的问题不值得做。
他还说:“我的学生,我都要和他合作一篇文章。”他给了我一个题目,但对我说:“不一定能做出来,做不出来也不要紧,慢慢想。”
但这个问题,我一直未做出来,因为觉得无从下手,想了想就放下了。1983年,我去北京参加首批博士学位的大会。想到要去见元老,觉得不好交代,便在火车上连夜想,居然想出来了,幸亏当时火车要开10个小时以上。见到元老便将这事告诉他,他也很高兴。后来又经过修改,合作完成了这篇关于哥德巴赫数的文章发表在1985年第1期《数学学报(英文版)》。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