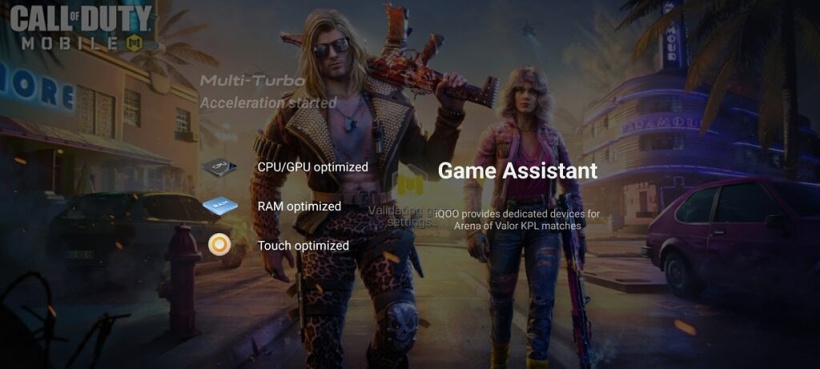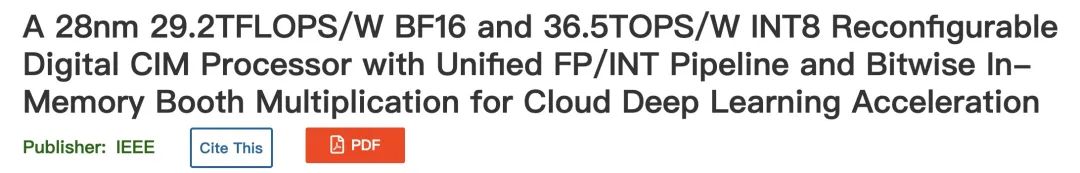相关新闻:饿了么被判赔送餐致残骑手109万 法院:双方符合雇佣关系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看似赢得了工作的自由与灵活,但只是从“生产线边”走向了“手机边”,他们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牺牲休息和安全的需要,但由此引发的职业伤害,却只能自己埋单。
文 |陈千凌编辑|朱弢
来源:财经E法
近日,“骑手因送餐致二级伤残,平台被判赔109万”的事件引发关注。外卖骑手王某在送餐过程中发生事故受伤,经鉴定为二级伤残,护理期限和误工期限都为长期,这次实际上是骑手的第二次索赔诉讼。
王某是饿了么的一名“众包”骑手。2016年8月,他在送餐途中发生事故受伤,被诊断为复合性外伤、脑挫裂伤、颅骨骨折等11处损伤,住院治疗30天。
此前,王某就已经产生的医疗费进行过一次诉讼,2017年9月青岛市崂山区法院判决由平台对王某的损失承担60%的赔偿责任,即医疗费5996.16元。后经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鉴定,王某为二级伤残,护理期限和误工期限都为长期,因此王某再次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平台赔偿他误工费、伤残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192.2万元。
在经过双方之间的拉锯战之后,最终法院判决平台赔偿王某因本次事故产生护理费、误工费、伤残赔偿金等,共计1090096元。
数千万劳动者,正在以“灵活”换“安全”
骑手王某的故事并非个例。2020年12月21日,外卖骑手韩某在配送了33单外卖后,倒在了第34单外卖配送途中,没能再站起来,当时他只有43岁,是家里的顶梁柱,家里还有两个正在上学的孩子和没有劳动能力的老人。
家属曾联系平台,希望得到平台方的理赔。但对方告诉他们,韩某伟与平台并非雇佣关系,只能给2000元的人道主义费用,其他以保险公司的理赔为主。在事件曝光引发公众关注后,迫于舆论压力平台将该骑手的保障额提升至60万元。
但是,得到如此待遇的骑手只是少数,更多的灵活从业者只能自己埋单。比如,2018年8月,一位湖南代驾司机在接单途中遭遇交通事故去世,平台此前承诺的最高120万元意外身故保险“缩水”成了1万元的“人道主义”赔偿。
这些年来中国以骑手、网约车、快递员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数量持续提升。人社部数据显示,全国灵活就业从业人员规模已经达到2亿人,约有8400万劳动者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约占全国就业人数的11%。
这些穿梭于大街小巷的灵活从业者们,看似具有工作时空不受约束的“自由”与“灵活”,但其实只是从“生产线边”走向了“手机边”。他们受制于“效率最大化”的算法系统,在“限时计价”甚至“超时白跑”的规则下,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牺牲休息和安全保障。
据2020年发布的《骑手生存与发展需求报告》显示,19.40%的全职骑手与20%的兼职骑手每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24.78%的骑手患有胃病、腰肌劳损、颈椎病等慢性疾病,37.32%的骑手表示自己每月基本不休息;88.28%的骑手因为担心订单超时,不能按时送到而选择违反交通规则。
如此高强度的劳动过程,自然引发了层出不穷的工伤事故。2017年上半年,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数据显示,上海平均每2.5天就有1名外卖骑手伤亡。同年,深圳3个月内外卖骑手伤亡12人。2018年,成都交警7个月间查处骑手违法近万次,事故196件,伤亡155人次,平均每天就有1个骑手因违法伤亡。
然而这些工伤风险高发的劳动者们,却并不能得到相应的工伤保障。这意味着一旦发生职业伤害,他们难以获得足够的救济和保障,其后果最终只能自己承担,一些低收入群体可能因职业伤害得不到有效的救济和保障而返贫。
为什么工作期间受伤害,只能自己“埋单”?
为何这么多劳动者在工作时间受到伤害,却得不到保障?
很多人都看到了平台的规避责任,但追根溯源是在于制度的短板。在缺乏法律刚性保障的情况下,具有营利属性的平台,自然不可能主动承担相应的责任及成本。
中国现行劳动法保护体系呈现“二分法”的特征,即具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才能享受工伤等社会保险待遇、经济补偿、解雇保护等系统、全面、具有强制性的种种保障。如《社会保险法》第三十三规定,“职工”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由用人单位缴纳工伤保险费,“职工”不缴纳工伤保险费。而其他关系类型的劳动者仅能遵从一般的民法规制,而民法基于合同当事人法律地位的独立平等,并不强调对劳动提供者的保障,二者之间的保障水平差距相当悬殊。
然而,很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们却很难被认定具有“劳动关系”,进而也无法主张工伤等权益保障。据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发布的《互联网平台用工劳动争议审判白皮书》显示,2015年至2018年一季度,朝阳法院判决的188件劳动关系争议案件中,确认平台与从业者存在劳动关系的仅为39件,占比不到四成。
那么为什么这些劳动者很难被认定具有“劳动关系”呢?
首先,是因为“劳动关系”的认定框架是根据标准用工形态而制定。这种“职工”式的用工形态具有固定时空、固定单位、严格规章制度约束等特征,而具有灵活性特征的新就业形态难以符合这一认定框架。
一般而言,平台并不会明确规定劳动者的出勤时间、接单数量,劳动者是自主登录平台接单,所得报酬由自主选择的接单量确定,而报酬也并非从平台处直接领取,而是从消费者支付的费用中与平台分成。
第二,平台会通过种种手段来规避用工责任。
平台一方面精心设置“免责”合同条款。如在前述王某的案件中,该骑手在平台注册时“签订”协议的第一条已经明确提出“配送平台仅代商家发送配送运单信息,为商家与配送人员提供网络信息服务”。其他常见甩锅条款还有“仅提供信息撮合服务”、“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劳动/雇佣关系”。
另一方面是将用工关系层层转包,平台不与骑手签订协议、支付报酬,而是转由配送公司、众包服务公司进行,而这些公司出于用工风险的规避需求也可能将业务转包给其他公司,这就导致劳动纠纷发生之时甚至找不到相应的用工主体。据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外卖平台由自营转为外包后,被认定为用人单位的概率从100%骤降至0.32%。
第三,劳动者自身维权能力较弱,难以有效举证。
由于新就业形态劳动的数字化,关键数据都掌握在平台手里。一旦出现纠纷,平台只需删除数据或者封禁劳动者账号即可。在“谁主张,谁举证”的模式下,劳动者实在难以拿出接受该公司劳动用工管理的实质性证据。
要实现2亿人的保障,不能仅指望平台
尊重劳动就是尊重人本身。需要认识到,劳动者是否享有相应的权益保障,应当以是否“参与劳动”,而不是以究竟属于何种身份,是否具有“劳动关系”为前提。中国灵活就业者已达2亿人,“有劳动无单位、有风险无保障”问题突出,他们的权益保障短板亟待补足。
而要实现劳动者权益的有效保障,既不能指望具有营利属性的企业自觉承担相应责任,毕竟这意味着额外的成本负担;也不能仅依靠司法的个案审判与救济,毕竟裁定标准的缺乏会导致大量的“同案不同判”;更不能寄希望于社会舆论的介入与干预,毕竟新闻报道出来的只是“冰山一角”,所以关键在于制度的破题、立法的完善。
目前国家层面围绕如何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已出台多项政策文件。如2021年7月,人社部等八部门出台《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面临的突出问题,提出要健全公平就业、劳动报酬、休息、劳动安全、社会保险制度,强化职业伤害保障,完善劳动者诉求表达机制。但是,相关政策仍存在落实难度大、平台用工关系认定规范不明确、劳动权益保障体系建设未跟上等问题。
问题的根本解决,仍然有待于从立法上明确新就业劳动者的权益。包括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身份如何认定、劳动关系如何认定、劳动权益清单如何梳理、社会保障如何安排等,都需要在劳动法体系中补充完善。
具体的制度建设上可从“抽象平等地保护”转向“具体差异化的调节”。比如,丰富劳动关系的属性分类,区分全日制就业、短期就业、季节就业、远程就业等弹性用工方式,兼职就业、派遣就业等非标准劳动,独立就业、自营就业等劳务用工,根据不同的劳动类型进行差异化的权益保障层次设计。
需要注意的是,针对实践中存在的大量用工外包现象,应该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即使平台企业与劳动者没有建立劳动关系,但只要存在用工事实,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也需要司法机关就劳动关系甄别制定更具体、明确的评判要素和标准,各级法院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机构要“穿透“劳动合同“表面”,着重对劳动关系“实质”进行考察。
当然,立法和司法调整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目前最迫切的是,应当本着急用先行的原则,加快对这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职业安全保护,迅速建设适应新就业形态的职业伤害保障机制。
由于现行工伤保险制度是为具有稳定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设计的,既没有为新就业劳动者提供参保通道,也在形式上与新就业群体有着天然的不匹配。如工伤保险的保费是由用人单位承担的,劳动者本人不缴纳,而新就业中很多劳动者的用人单位却很难判断、不固定甚至不存在雇主。再比如,工伤保险费的缴纳基数与用人单位的行业相关联,而新就业劳动者很容易从一个行业跨到另外一个行业,有时还存在跨行业劳动的情况,那么如何设置缴费条件和费用?
还有,工伤认定也是个问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往往单独工作,如何证明是因工受伤、如何申报,同时在多个平台注册从业时应当如何处理……这些难点与痛点都需要政府联动企业、工会、行业协会等多方力量进行精细化的方案设计。
总而言之,正如美国学者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所言,每个人在最广泛的自由体系内拥有平等的权利,对社会问题的考察与解决应该从最不利者的角度出发。虽然财富与收入的分配无法做到完全平等,但是须符合每个人的利益。每一个行业每一份工作,只要是辛勤劳动就值得肯定,因此需要给予灵活从业者更多的尊重、保护与关怀。
作者为互联网政策研究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