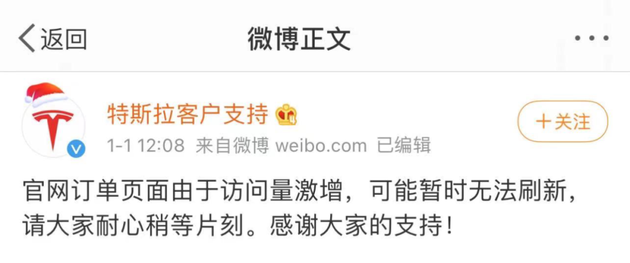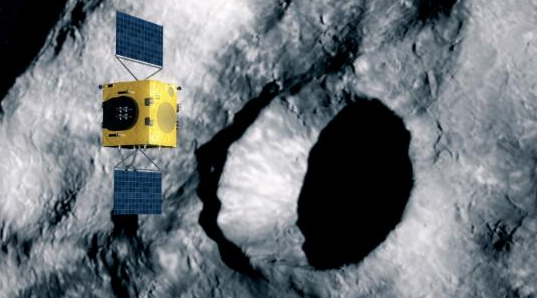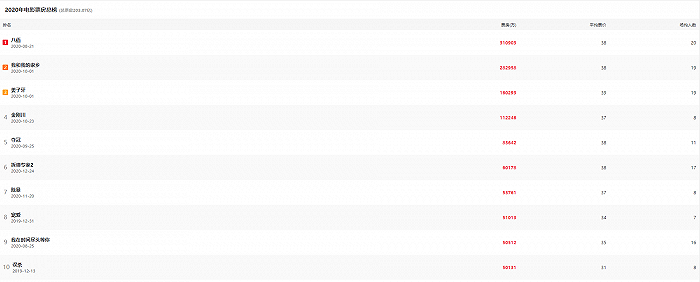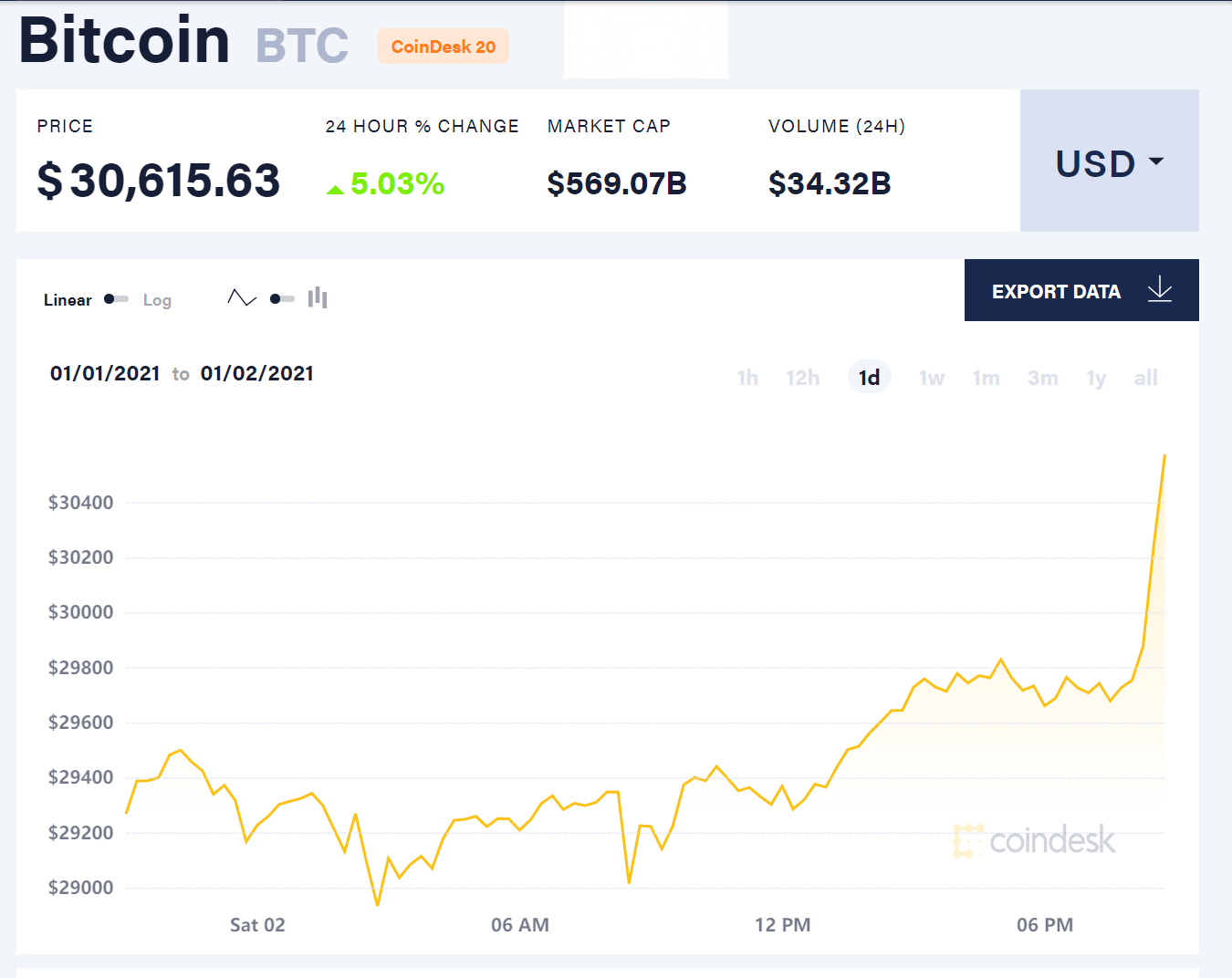原标题:判决书:一张被一审法院撤销的罚单,为何获得二审法院的支持
一审法院认定银保监局开出的罚单处罚变更随意性太强,将其处罚撤销。银保监局上诉后,二审法院又认为银保监局作出的处罚并无不妥,随之撤销一审法院的行政判决。
2020年12月29日,中国裁判文书网披露的一则二审行政判决书显示,山西银保监局因武某诉其行政处罚一案,不服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这一案诉讼源于农行下属支行发生的违法违规案件。2012年年初至2015年底,农行山西省分行营业部辖属11个支行多名员工参与推介销售未经批准代理销售的华盛金道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非法集资产品,或为该公司提供转账、结算等金融服务,收取好处费,涉及11个支行36个网点97名员工。先后共25名员工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11人被检察机关正式起诉至法院。
根据法院查明,武某于2010年5月14日至2014年8月6日担任中国农业银行太原市北城支行原行长。在上述案件中,武某原任职的农行太原市北城支行共8个网点20余人违规收取好处费。
一审法院:山西银保监局处罚变更随意性太强且程序违法,撤销其罚单
一审法院查明,2017年12月13日,山西银保监局根据信访举报,对农业银行山西省分行营业部员工涉嫌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及存在领导监督、管理等问题进行了行政处罚立案登记。
2018年5月3日,山西银保监局对武某等17人作出晋银监罚告字【2018】8号《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拟对武某处警告并罚款8万元。当月,山西银保监局对武某原任职的农行太原市北城支行开出罚单,责令该银行改正,并罚款50万元。
不过,2018年9月10日,山西银保监局再次作出晋银监罚告字【2018】11号《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拟对武某作出“取消高管任职资格2年”处罚决定。
正因如此,武某不服上述决定,向山西银保监局提出听证申请。经听证后,山西银保监局于2019年1月25日作出晋银保监罚字【2019】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认为,武某应对原任职单位多名员工参与上述案件承担直接管理责任,因而对其作出“取消高管任职资格2年”的处罚。
武某随之诉诸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武某已于2014年8月6日调离了原单位,山西银保监局对武某作出的处罚已超过两年,根据《行政处罚法》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与行政处罚”。
一审法院还认为,武某在收到第一份《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后,未提出异议,虽然山西银保监局做了补充调查,但在对武某原任职单位的处罚实施并未改变的情况下,再次作出《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处罚变更随意性太强且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同时,法院认为,山西银保监局处罚案件不规范,程序违法。
综上,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山西银保监局做出的晋银保监罚字【2019】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武某“取消高管任职资格2年”的处罚。
为何变更且加重处罚?系对涉案事件承担直接管理责任的主体认定调整
对于太原市中院的判决,山西银保监局不服并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为驳回武某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武某承担。
可以说,山西银保监局为何对拟作出的处罚进行了变更可以说是各界更为关注的。在二审中,山西省高院也认为,本案的核心问题是,山西银保监局从第一次告知武某拟作出“警告并处罚款8万元”处罚,变更为第二次告知中拟作出“取消高管任职资格2年”的加重处罚,是否有充分的事实依据。
经查明,第一次告知书和第二次告知书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在第一次告知书中,山西银保监局认定对涉案事件承担直接管理责任的主体是省分行营业部,因此拟对该部四名高管作出较重的处罚决定,对支行行长拟作出较轻的处罚决定。
但在第一次告知书送达后,农行山西省分行营业部总经理任鹏对作出“取消高管任职资格10年”提出申辩并要求举行听证,认为其在“任职中国农业银行山西省分行营业部总经理期间,健全了内部管理与控制制度,不属于直接负责的领导,不应负直接领导责任。……责任在制度的执行单位支行,……网点现场管理、风险管理及制度落实的直接领导责任在网点负责人和支行行长。”山西银保监局针对任鹏的申辩及听证申请依法举行了听证,对任鹏提供的银行内部岗位职责及管理规定等进行审查,并进行了补充调查。
山西银保监局行政处罚委员会经集体审议,认为任鹏的申辩意见成立,在调查取证过程中并未发现上级行存在统一安排部署相关违规行为的情形及证据,直接管理责任主体应该是11个基层行的时任行长。遂对省、市、基层三级行的责任重新作出认定,认定基层支行行长对涉案违法行为承担直接管理责任,省分行营业部四名领导及省分行行长承担领导责任,并据此对市行和基层支行行长拟作出的处罚种类和幅度作出调整。
上诉后,二审法院认为山西银保监局处罚决定并无不妥
在二审中,山西银保监局认为,原判认定事实错误,被诉处罚决定的处罚时效符合法律规定。原判认定“被告对原告的处罚己超过二年”,该认定错误,因为《行政处罚法》规定的时效截止点是“发现”违法行为时,而不是“立案”时。虽然行政处罚案件的立案时间是2017年12月13日,但早在2015年11月便收到陕西省信访局来访事项转送单,并于当月开始调查处理工作。
对于两份《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不存在“随意性太强”的问题,山西银保监局认为不存在这一情形。该局表示,向武某等17人送达第一份《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后,有11人向上诉人提交陈述申辩意见或听证申请及相关证据,上诉人组织开展调查核实工作。根据陈述申辩意见、听证意见及核查情况,上诉人行政处罚委员会经集体审议,认为调查取证过程中并未发现上级行存在统一安排部署相关违规行为的情形及证据,直接管理责任主体应该是12个基层行的时任行长(包括武某),因而再次作出《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送达拟被处罚人员,并依法保障被上述人武某的陈述申辩及听证权利。
山西银保监局还强调,《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并不对拟处罚人员的权利义务发生实质影响,不存在“一事二罚”情形,不存在程序违法情形。两次《告知书》送达后,山西银保监局都高度重视拟被处罚人员的陈述申辩意见,并且依法保障听证权利,不存在原审判决认为的“处罚案件不规范,程序违法”的问题。
判决书显示,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山西银保监局对武某作出的行政处罚是否超过2年处罚时效;二是山西银保监局在处罚前向武某送达两次《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程序是否合法;三是山西银保监局对武某作出“取消高管任职资格2年”的处罚决定事实依据是否充分。
山西省高院最终认定,涉案违法行为追诉时效的起算时间为2014年8月武某调离原任职银行时,“发现”时间以山西省委、省政府信访局和中国农业银行山西省分行营业部于2015年11月向中国银保监会山西监管局报送案件情况的时间为准,期间并未超过2年处罚时效,并不存在不能给予行政处罚的情形。
至于山西银保监局于2017年12月13日正式立案,客观上存在“发现”违法行为时间和立案时间间隔太长的问题。山西省高院认为,鉴于涉案违法行为在性质上属于涉众性案件,在公安机关已作为刑事案件立案侦查的前提下,为确定农行山西省分行辖区内相关基层支行工作人员参与涉案违法行为的人数及金额等基础事实,有必要待刑事案件对关键事实作出认定后,再对涉案基层支行及相关责任人员进行行政处罚立案审查。因此,山西银保监局从“发现”违法行为到两年后进入行政处罚立案审查,并不存在明显不合理或违法情形。
关于向被处罚人送达两次《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山西省高院认为,告知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听取陈述申辩或听证,本身就是案件事实调查的一个环节,是调查处理过程中的程序性行政行为。而且,经过告知和听取意见程序,为了查证当事人主张的理由和证据是否成立,就有可能再进行必要的调查核实。如果经过补充调查核实,案件事实和证据发生了变化,甚至可能影响处罚结果的,行政机关须对变更后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及拟处罚结果进行重新告知,以便当事人发表意见,保障处罚结果客观公正。因而,原判认为两次告知程序不规范的认定不准确,应予以纠正。
最终,山西省高院判决撤销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此前作出的行政判决,驳回武某要求撤销中国银保监会山西监管局作出的晋银保监罚字【2019】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100元,由武某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