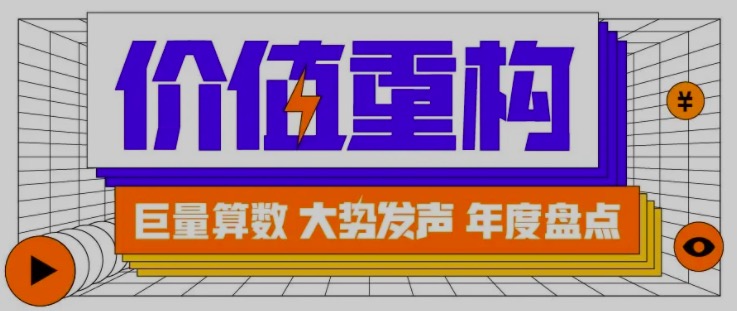原标题:生命如歌:一周城市生活
全球新冠确诊病例已超一亿人。本周我们将从疾病、残障与生死等视角与大家一同探究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所在。人总是会面临一些无法预知的福祸,而在历经了人间疾苦后,我们是否仍然能保持乐观与豁达的心态,是否依旧对生命保持着热烈与深切的渴望,就如史铁生所说,“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
在本周回顾中,我们邀请了《照护》读书会的组织者探讨临终关怀与心灵照护的理念革新与实践反思,并分享了“黑暗中对话”活动如何实现与视觉障碍者的立场互换,以及直面生死话题的死亡咖啡馆活动为何越是谈论死亡,越是让人知道如何活着。在主题推荐中,我们也整理了两份书单——如何认识“残障”、如何认识“死亡”,一份片单——摇晃的爱与幸福,以及一个由苏格兰艺术家发起的、特殊的“不再回到正常”线上艺术节。
(本期主持:刘懿琛)
近期回顾:关于你我之间差异的线上分享和线下体验
无法放弃的照护与关怀
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化为物质利益关系,当经济学话语开始愈来愈多地塑造人们思考世界的方式,当弥漫在公共空间里的犬儒主义与虚无主义让任何重要的社会行动变得愈发吃力,当新自由主义政治否定了共情、联结与关怀的价值,在这样的大时代里,我们又该如何重思照护精神与关怀精神?
1月28日,复旦大学人类学系潘天舒教授和我共同参与了由新周刊硬核读书会举办的“《照护》读书会——无法放弃的关怀”,围绕哈佛大学精神病学与人类学教授凯博文(Arthur Kleinman)的新书《照护》(The Soul of Care: The Moral Education of a Husband and a Doctor)展开了一场关于照护实践的讨论。
 凯博文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最早来到中国大陆开展研究工作的美国学者之一,他在湖南长沙开展的有关文化创伤、神经衰弱与抑郁症的研究既改变了中国大陆精神病学对于神经衰弱与抑郁症的认识,也改变了全世界对于文化与病痛关系的思考。作为精神科医生与医学人类学家,凯博文倾其一生研究并实践照护,但在妻子凯博艺(Joan Kleinman)罹患阿尔茨海默病后,作为丈夫的他却不得不重新开始学习并思考照护的意义。
凯博文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最早来到中国大陆开展研究工作的美国学者之一,他在湖南长沙开展的有关文化创伤、神经衰弱与抑郁症的研究既改变了中国大陆精神病学对于神经衰弱与抑郁症的认识,也改变了全世界对于文化与病痛关系的思考。作为精神科医生与医学人类学家,凯博文倾其一生研究并实践照护,但在妻子凯博艺(Joan Kleinman)罹患阿尔茨海默病后,作为丈夫的他却不得不重新开始学习并思考照护的意义。
《照护》分享会线上直播画面
在讲座里,潘教授首先介绍了凯博文的思想脉络,从医学的两种话语(宛如“笔直街道”的医学专业话语与宛如“弯曲小巷”的患者主观体验)到文化语境中的患者与疗愈者两种角色,从对于医学技术主义的批判到对于西方精神病学知识的重思,凯博文对于医学人类学的改造使后者跳出了民族医学及应用人类学的窠臼,以强烈的批判精神重思西方医疗实践,同时不止于理论空谈,而是进入了行动与决策领域,思考“What is to be done?”(该做什么?)的实践问题。
包括凯博文在内的欧美许多医生知识分子,对于弥漫着技术主义与官僚主义的照护实践的批判,也是吸引我进入该领域并决定译介这本书进入大陆的地方。始于我自己过去几年做医生的经验,凯博文在《照护》这本书中讲到的许多他的学生在进入医院工作后的幻灭与耗竭都给我带来了极强的代入感。全世界的医生与患者都好像在“大医疗”(Big Medicine)这只怪兽的肚子里忍耐着沮丧,但相比西方,我们对于这只怪兽的批判与突围却好像还晚了些。
潘教授与我在讲座里也都谈到了中美医学教育的不同,比如美国医学院仅有研究生教育,允许许多社科人文专业本科同学报考医学院,此外凯博文还在哈佛医学院创建了医学博士-人类学哲学博士(MD-PhD)项目。正是因为这样的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美国才出现了那么多人文素养与医疗实践兼备的医生知识分子,这些医生知识分子能够跳出狭隘的生物医学范式,以极强的人文关怀与社会责任走往医疗与健康问题的上游,以期实现更大范围内的健康公平与社会正义。
当然,讲座最后我们回到了《照护》这本书里相当重要的一条主线——阿尔茨海默病与老年照护。潘教授回忆了凯博艺罹病后的故事,他说:“(当时)我们很少有人会把姿态还那么优雅的凯博艺和失智老人联系起来,她只不过是几乎不怎么说话,但是总保持着很安静的神态。”
医学对于疾病的描述总是专业客观仿佛千篇一律,但现实中每位患者对于疾痛的经验与叙事却可能千差万别,而且总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变奏与复调。正如凯博文在这本书里说的,他照顾凯博艺的十年完全改变了他,“让他变得更有人情味了”(make him more human),让他真正懂得了照护作为人世间所有关系的本质、作为我们共同存在的基础,照护对于我们人性的引出以及对于照护者与被照护者的救赎。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从关怀自己与亲友与陌生人做起,在生活的局部重新注入“照护的灵魂”。
(文:姚灏/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住院医师、心声公益创办人)
相关活动:线上分享会|我们如何照护
 详情请关注脉络Context微信公众号
详情请关注脉络Context微信公众号 黑暗中的对话,看不见的看见
1月28日上午,黑暗中对话工作坊如期开展活动。十多位参与者在教练团队的引导下,步入一片陌生的黑暗空间,成为了暂时的失明者。“我使劲地睁大眼睛,可还是什么都看不到,于是我干脆闭上眼睛,用心聆听。”一位参加者这样分享自己的感受。 在整整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参加者们在黑暗中慢慢克服了心中的恐惧与无助,逐渐融入周围的环境中,与团队的伙伴们并肩携手,完成了一个又一个艰巨的挑战。在离开黑暗、重见光明的那一刻,参加者们发出一片呼声,这声音中充斥着复杂的意味,既有着对回到光明世界的欣喜,又有着对黑暗经历的恋恋不舍。
在整整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参加者们在黑暗中慢慢克服了心中的恐惧与无助,逐渐融入周围的环境中,与团队的伙伴们并肩携手,完成了一个又一个艰巨的挑战。在离开黑暗、重见光明的那一刻,参加者们发出一片呼声,这声音中充斥着复杂的意味,既有着对回到光明世界的欣喜,又有着对黑暗经历的恋恋不舍。接下来便是在光明中举行一个小时的交流分享。当我和助教们一手搭肩,一手拄着白手杖,出现在参加者面前时,可以想见他们彼时彼刻脸上的表情,惊讶、好奇、感慨、凝思……种种情感纷至沓来。
是的,正如此前绝大多数的客人那样,他们也将我们这些黑暗中的引导者,当成了头戴夜视仪的“蝙蝠侠”,直至见到我们这些视障者的“庐山真面目”为止。我经常自称“目中无人”,然而更多的情况是,我也正被“目中无人”着。
中国有1800多万视障者,然而能够暴露在大街小巷的却寥寥无几,能够以这样一种平等的方式与健视者面对面交流的更是凤毛麟角。有时候你很难分清因果,到底是因为视障者很少出门,大家才视之为异类,还是反过来,因为大家视我们为异类,我们才不愿出门。
曾有很多朋友告诉我,如果有选择,他们宁可选择其他残障类型,也不愿意选择失明。更有甚者,表示宁可死,也不想失明。但我总觉得,那并不是因为黑暗真有那么可怕,而是因为他们并不懂得黑暗。
幸而,在这次深入的探讨中,参加者们终于看到了看似一无可取的黑暗背后蕴藏着的东西。在黑暗中,有人感受到队友肩膀上传来信任的力量,有人懂得了沟通时换位思考的重要性,更有人体会到全神贯注的心理状态如何带领自己克服重重障碍。 大家终于达成一致:即使在黑暗中,关闭了视觉的我们,其实仍然拥有很多很多。甚至也许,在屏蔽了五感中的视觉以后,我们依然能够更加多维地看到这个世界的全貌,因为这世界,本就不是单一的画面,只有透过表象,我们才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大家终于达成一致:即使在黑暗中,关闭了视觉的我们,其实仍然拥有很多很多。甚至也许,在屏蔽了五感中的视觉以后,我们依然能够更加多维地看到这个世界的全貌,因为这世界,本就不是单一的画面,只有透过表象,我们才能看得更清楚一些。相信每一个人,都能在黑暗中,用看不见的方式看见更多的东西。也希望将来有更多人,能够看见我们,看见黑暗。(文:张平/黑暗中对话总教练)
死亡咖啡馆中的生死对谈
不知不觉,我已经在大理办了三场死亡咖啡馆活动。短短的日子里,遇见一群又一群人,聊死亡食物、死亡书籍、死亡幻想……我们不知道彼此是谁,只是因这一份好奇和恐惧来到这里,再带着些许思考离开。
死亡咖啡馆是一个没有议程、结论或导向的死亡教育小组活动。它需要至少一位活动带领人,以这个角色协助参与者互相聆听、彼此信任、共同连接死亡议题。对于带领人自身来说,带领死亡咖啡馆活动则是对自己个人成长的校验与认识自我的投入。 在大理的三场活动,每次来的都是不一样的人,有男性、女性、长辈、孩子……透过这些被死亡话题吸引而来的各种差异极大的视角,我发现这群人的认知似乎正趋于一致——我们越是谈论死亡,越是知道自己该如何活着。
在大理的三场活动,每次来的都是不一样的人,有男性、女性、长辈、孩子……透过这些被死亡话题吸引而来的各种差异极大的视角,我发现这群人的认知似乎正趋于一致——我们越是谈论死亡,越是知道自己该如何活着。人是向死而生的动物。著名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师欧文·亚隆在书里提到,我们生活中的所有痛苦,基本源自这4个方面的困扰:死亡、孤独感、自由以及生活中无法找到一个显而易见的意义。其中,死亡是反映生命整体意义的终极之镜。
揭开死亡之幕之时,我们必然要承受作为人的宿命。直视死亡如同直视灼目的骄阳,勇于面对,更像是迎接而非应战。而当我们越从理性层面意识到无法把握死亡时,越在此刻回归当下,我们关于生命的体认就越深刻、越丰富。
三场活动,25个人,我们一起谈论死亡的时光,本身就是一场对生命的欢庆。这些思考,是帮助我们对恐惧脱敏的有力工具;而对同伴的倾听、陪伴和尊重,让我们能够更加清醒地看到自己过度批判的头脑运作,也更加全然地打开感知,活在当下。
之前不止一个人问我,是什么让你一次又一次成为带领者,死亡咖啡馆活动的意义是什么?我只会一次又一次回答:在这里,我们看见的不仅是死亡。还有自己、天地和众生。(文:可贞/出家入世、出生入死的预备戏剧治疗师)
相关活动:向死而生| 2.6-2.7两日死亡咖啡馆
 详情请关注之吃诗微信公众号
详情请关注之吃诗微信公众号 本周主题推荐
生命不在于那些了无痕迹流去的岁月,死亡也并不总是只有失落的、痛苦的与伤感的。在本周的主题推荐中,我们借由书籍、影片以及线上艺术展览,试图站在一种既关切又超脱的视角上来讨论生命的价值。
(本版块撰写:刘懿琛Jady Liu陈鑫培)
书单|如何认识“残障”
唯理通讯专题系列六:残障群体
 唯理通讯推荐精选自互联网的深度文章。本期唯理通讯将视角转向残障群体,试图了解他们所处的现实困境。例如现阶段无障碍设施的建设,残障群体匮乏的教育资源与就业机会,残障人群在此次疫情中所面临的困难,以及他们被忽视的需求。
唯理通讯推荐精选自互联网的深度文章。本期唯理通讯将视角转向残障群体,试图了解他们所处的现实困境。例如现阶段无障碍设施的建设,残障群体匮乏的教育资源与就业机会,残障人群在此次疫情中所面临的困难,以及他们被忽视的需求。 阅读链接:https://www.veritaschina.org/newsletter/20200302/
《抱残守缺:21世纪残障研究读本》:全球化视野中的残障研究
 如书中所言,残障不仅是我们口中的一种隐喻,而是他们所要面临的活生生的现实。以往大多数人总是习惯性地以“健全主义”的立场去看待他们,而这本书却选择了站在文化与社会的视角,重新思考“残障”的社会性与历史性。
如书中所言,残障不仅是我们口中的一种隐喻,而是他们所要面临的活生生的现实。以往大多数人总是习惯性地以“健全主义”的立场去看待他们,而这本书却选择了站在文化与社会的视角,重新思考“残障”的社会性与历史性。 《像我们一样疯狂——美式心理疾病的全球化》
 作家伊森·沃特斯通过采访四个国家和地区心理疾病的真实案例,向我们展现了关于厌食症、创伤后应激障碍、精神分裂和抑郁症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特征。强有力地说明了美国的心理学范式是如何在其医药商业利益驱动下输出全世界,潜移默化地改变本土心理疾病的现象。
作家伊森·沃特斯通过采访四个国家和地区心理疾病的真实案例,向我们展现了关于厌食症、创伤后应激障碍、精神分裂和抑郁症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特征。强有力地说明了美国的心理学范式是如何在其医药商业利益驱动下输出全世界,潜移默化地改变本土心理疾病的现象。《残疾人剧院》:颠覆原始审美判断的表演者
 Jéréme Bel的《残疾人剧院》(Disabled Theatre)讲述了由苏黎世HORA剧院中十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的演员共同完成的舞蹈作品,引发了人们对于认知障碍患者在戏剧和舞蹈表演中,以及在社会内部所扮演角色的探讨。
Jéréme Bel的《残疾人剧院》(Disabled Theatre)讲述了由苏黎世HORA剧院中十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的演员共同完成的舞蹈作品,引发了人们对于认知障碍患者在戏剧和舞蹈表演中,以及在社会内部所扮演角色的探讨。 《有爱无陷》:身心障碍人士的爱与性
 本书描写了属于残障人群的性与爱,探索残障人士的情感故事。真正对残障者的关注并不是出于一种“猎奇”的凝视,也不是有礼貌地把目光从残障的身体上移开,而是从心灵上走进他们,理解他们真实的需求。
本书描写了属于残障人群的性与爱,探索残障人士的情感故事。真正对残障者的关注并不是出于一种“猎奇”的凝视,也不是有礼貌地把目光从残障的身体上移开,而是从心灵上走进他们,理解他们真实的需求。 书单| 如何认识“死亡”
《生老病死的生意》
 本书通过在上海等地进行的深入细致的民族志访谈,记录了中国人寿保险市场在避谈死亡的文化禁忌下的发展历程及其背后的微观政治。探讨人们对于风险社会与自身脆弱性的感知,以及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的社会文化意蕴。
本书通过在上海等地进行的深入细致的民族志访谈,记录了中国人寿保险市场在避谈死亡的文化禁忌下的发展历程及其背后的微观政治。探讨人们对于风险社会与自身脆弱性的感知,以及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的社会文化意蕴。《当呼吸化为空气》:医者眼中的生与死
 作家保罗·卡拉尼什(Paul Kalanithi)是美国著名的神经外科医生,同时也是一个四期肺癌患者,他将自己置身于医者与患者之间,在直面死亡的时分回顾自己一生的价值与意义。字里行间,读不出任何的遗憾或是绝望,反而是对生命的渴求与憧憬。
作家保罗·卡拉尼什(Paul Kalanithi)是美国著名的神经外科医生,同时也是一个四期肺癌患者,他将自己置身于医者与患者之间,在直面死亡的时分回顾自己一生的价值与意义。字里行间,读不出任何的遗憾或是绝望,反而是对生命的渴求与憧憬。 《死亡的脸》:直面死亡的恐惧
 《死亡的脸》是由外科医生舍温·努兰写作的,作为医生在面临无数的生死离别时,让他开始真挚地思考,医者除了帮助病人征服病魔,在通往人生最后的旅程中,该如何用爱与陪伴让他们有尊严地离去。
《死亡的脸》是由外科医生舍温·努兰写作的,作为医生在面临无数的生死离别时,让他开始真挚地思考,医者除了帮助病人征服病魔,在通往人生最后的旅程中,该如何用爱与陪伴让他们有尊严地离去。 《一片叶子落下来》:关于生命的童话
 这本童话,献给所有曾经历生离死别的孩子,与不知该如何解释生死的大人。
这本童话,献给所有曾经历生离死别的孩子,与不知该如何解释生死的大人。 我们在书中陪着一片叫弗雷迪的叶子经历四季,从长大到死亡的微妙情愫,轻轻地展现在简单的故事里,文字虽短,寓意隽永。
片单|摇晃的爱与幸福
《摇摇晃晃的人间》
 《摇摇晃晃的人间》记录了患有脑瘫的农村女诗人余秀华面临的现实生活,虽然有着残缺的身体,却一直对追求真爱充满渴望。该片讲述了在她成名之后,挣脱世俗束缚,告别无爱婚姻的故事。
《摇摇晃晃的人间》记录了患有脑瘫的农村女诗人余秀华面临的现实生活,虽然有着残缺的身体,却一直对追求真爱充满渴望。该片讲述了在她成名之后,挣脱世俗束缚,告别无爱婚姻的故事。《一切都会有的》
 《一切都会有的》是导演蒋能杰以心智障碍群体为对象创作的公益题材影像作品,全片时长81分钟,展现了心智障碍者真实的生活状态。蒋能杰导演已公开发布了片源,有心者可选择公益支持。
《一切都会有的》是导演蒋能杰以心智障碍群体为对象创作的公益题材影像作品,全片时长81分钟,展现了心智障碍者真实的生活状态。蒋能杰导演已公开发布了片源,有心者可选择公益支持。《小伟》
 电影《小伟》又名《慕伶,一鸣,伟明》,在虚实镜头的穿插中让我们体会到患有癌症的父亲复杂又细腻的情感。
电影《小伟》又名《慕伶,一鸣,伟明》,在虚实镜头的穿插中让我们体会到患有癌症的父亲复杂又细腻的情感。《沦落人》
 《沦落人》是关于两个沦落在香港的底层人的故事,中年男子汉昌荣在意外受伤后高度瘫痪,最终妻离子散。在他对人生几乎不抱有任何希望时遇见了Evelyn,两个陌生人从相遇到相识,开始共同寻找生活中弥足珍贵的小确幸。
《沦落人》是关于两个沦落在香港的底层人的故事,中年男子汉昌荣在意外受伤后高度瘫痪,最终妻离子散。在他对人生几乎不抱有任何希望时遇见了Evelyn,两个陌生人从相遇到相识,开始共同寻找生活中弥足珍贵的小确幸。《37秒》
 37秒是梦马出生时缺氧的时间,是导致她脑性瘫痪的原因。她不想被视作残疾人,也想拥有正常人的自由与快乐,不愿失去对生活,对美的感知力。
37秒是梦马出生时缺氧的时间,是导致她脑性瘫痪的原因。她不想被视作残疾人,也想拥有正常人的自由与快乐,不愿失去对生活,对美的感知力。《听说》
 该影片讲述了秧秧和便当店男孩黄天阔互相误会对方是听障人士,在与彼此“特别”的沟通过程中,展开的一段奇妙美好的爱情故事。
该影片讲述了秧秧和便当店男孩黄天阔互相误会对方是听障人士,在与彼此“特别”的沟通过程中,展开的一段奇妙美好的爱情故事。线上艺术节|不再回归正常
 “不再回到正常”(Not Going Back to Normal)是2020 年在苏格兰的残疾艺术家们共同提出的宣言。在线上艺术节中展出的49件艺术品回应了“不再回到正常”的理念,体现了对艺术规则的挑战,以及属于残疾艺术家们的独特想象力。
“不再回到正常”(Not Going Back to Normal)是2020 年在苏格兰的残疾艺术家们共同提出的宣言。在线上艺术节中展出的49件艺术品回应了“不再回到正常”的理念,体现了对艺术规则的挑战,以及属于残疾艺术家们的独特想象力。 艺术节网址:https://www.notgoingbacktonormal.com/
活动推荐·海报集
杭州·招募|野生青年艺术节
 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重庆·艺术项目|重庆小广告,我也爱你!
 详情请见
详情请见 广州·讨论会|“传统的频率”一键多重浓缩
 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线上展览|自拍监视-重构主体
 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线上沙龙|代孕问题面面观
 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线上读书会|当不稳定遇上无产者
 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线上读书会 | 《奥莉薇不想当公主》:你可以活成任何你自己喜欢的样子
 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如果您想联系我们,请发邮件至[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