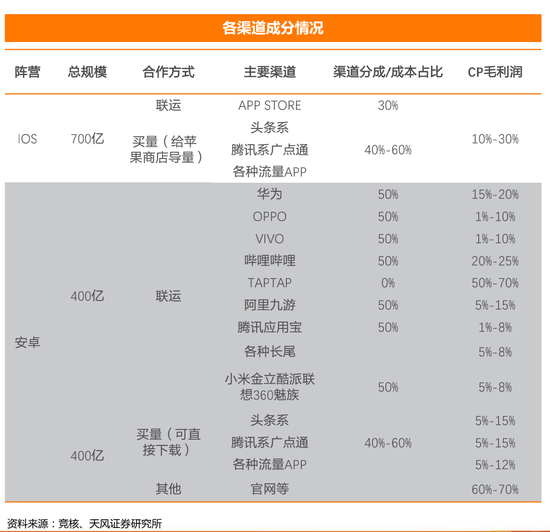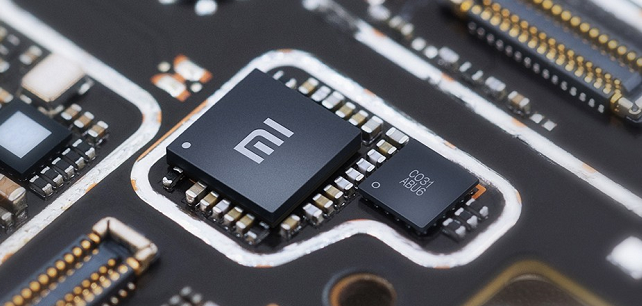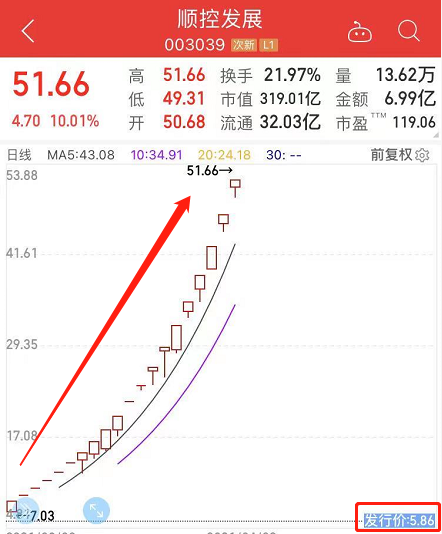原标题:深观察|“农村出身”对我意味着什么?
最近,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讲师程猛在一席上的讲演火了。“农村出身究竟意味着什么”的问题,在舆论场里久久回荡。
我的家乡位于湖北黄冈浠水县团陂镇凤形地村,村民们世代以务农为生,我的小学、初中和高中都在家乡度过,我是一个正统的农村出身的人。
我初中时候的成绩不错,现在看来是标准的学霸,记得我们黄冈搞学科竞赛,那年我念初三,英语老师带我去县城参加比赛,那是我第一次坐汽车,第一次上镇上,第一次去县城,第一次下馆子,第一次住宾馆,最后我竟然幸运地拿到了英语全市第一名,总分全市第二名。然后回来后,学校大黑板(公告栏)上写着“向姚华松同学学习”几个大字,然后听说我爷爷来学校领退休工资的时候,老师们要他请客。
进入县一中,就大变样了,那里可是高手云集,学校集聚了全县的尖子生与佼佼者,我成绩一般。成绩不好,就自卑,就更努力,但发现努力也不一定有效果,尤其身边有一些不怎么努力成绩就很好的人,我会更加自卑。这会让我产生一种宿命论——人家天生就是读书的料,人家天生就聪明。
更摧毁我的是性格方面,县城的孩子自不必说,一些和我一样也是乡下来的同学性格活泼,很快可以和其他同学打成一片,我觉得自己特别违和——想通过打乒乓球熟悉他们,他们笑话我的削球姿势丑陋无比;他们偶尔去录像厅看电影消遣周末,我没有胆量去。
大学期间,和高中有某种程度的延续,成绩没有影响我太多,核心是文化冲突——一个从山沟沟里出来的人,来到了九省通衢的江城武汉,会不由自主地不适应。身边同学们上课回答问题时的侃侃而谈,下课后相约打拖拉机的谈笑风生,某位室友可以约某漂亮女生一起上晚自习,然后离开图书馆,他可以对女生表白“我可以牵着你的手走一段路吗”,回宿舍分享这件事的时候,我内心又羡慕又嫉妒。“我是农村来的”这句话一直萦绕心头,挥之不去。
直到大三,我每周四晚上去学校的英语角,一片漆黑的树林里,聊着白天在21st century看的新闻,和女生聊天,与其说是练习英语口语,不如说是给自己壮胆——克服与异性交往的恐惧心理,提高与女性交往的能力。
钱。钱当然很重要,因为对于农村出身的孩子而言,钱一直是稀缺物,钱对我家的特殊意义在于——钱让我和我弟有了不同的命运,他成为劳动力密集型的农民工,我成为智力密集型的学术民工。1997年上半年,我当时在县一中高三复读,班上排名前十(复读班的人,录取率很高),上大学是十拿九稳,我弟当时在镇高中,十个班,他可以在年级排名前二十,我爸出身不好,地主之后,小学二年级就被迫辍学,没有手艺,靠种田想供养两个大学生,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
怎么办?弟弟选择辍学,在一次月假,别人是背书包回家,他是卷铺盖回家。这在当时的农村非常普遍,家里只能供养一个读书上大学,另外一个必须作为家里的劳动力,提早辍学干活挣钱和养家。换言之,弟弟牺牲了他的大学梦,成全了我的大学。所以,至今,我都觉得愧对他,我都尽力帮助两个侄子。
关于钱,我还清晰的记得,1994-1997年我高中的学费是每学期398块,我记得是去河里找爸爸拿学费的,他当时在河里淘铁砂。1997-2001年我大学的学费是每年1680元,作为地理教育的师范生,我们有一年十个月每个月42块的国家补助。也是凑巧,42×10×4=1680元,也就是说,国家给我们师范生免了一年的学费。
大一和大二,我每天都会记录自己每一餐的伙食费,比如早餐0.55,就是三个馒头和一碗稀饭,馒头0.15一个,稀饭0.10一碗。午餐和晚餐都是2.50,也就是2块钱的菜(一荤一素),五毛钱的饭。
那时候,我爸在武汉某砖瓦厂打工,我半个月过去一趟打个牙祭,一般是周六上午公交车近两个小时去到,周日下午回校。住的是简易工棚,晚上睡的床是用砖头搭起来的,上面放着稻草和麻垫,所谓的牙祭也就是爸爸用电饭煲弄一点排骨萝卜汤之类的,我经常半夜醒来不见他,他出工的时间不固定,时不时熬夜。我和爸爸交流不多,一直,至今都是。是不是农村出身的男孩,普遍与父亲交流不多?
此后是读研和来到广州念博士,以及后面的工作,其实农村出身的印记也一直伴随我、影响我。博士论文的选题,因为听不懂广东的白话,只能选择研究流动人口,当然与自己来到广州来到中大的自我身份认同有关——自觉一直以一个边缘者的角色而存在,现在的流行表达就是“外环路上的人”。
给自己设定交往及结婚对象的必备条件——一定得割过谷、放过牛、有相当的农村生活经验跟记忆,不然就感觉“志不同,道不合”。包括至今也是,无论老乡,还是同事,球友,徒友与朋友,都觉得与从农村出来的人处起来相对更加亲近和自然,我当然无意排斥城里人,但这个农村出身偏好的社交习惯,好像已经定型了。
现在我是大学老师了,但也不是说,每次回家都是快乐的。我记得五六年前,路过一位村干部家,他一见面就问我一月多少钱,我说几千而已,他来了一句“读书,没有啥用”,我当然非常醒目的和稀泥——是啊,不如你们当官的,做老板的。可见,赚钱多少,开什么豪车回家,城里有几套房子,是不少农村人对于“成功”的标定,什么大学教授啊,多么有名气啊,这些都是虚无缥缈的东西。
“农村出身”,于我而言是沉甸甸的回忆,有童年汗流浃背的劳作,有少年跳出农门的冲动,有青年性格违和的自卑,有中年携子回家过年的激动,我不曾介意农村的出身,更不会忘记农村的那些点滴,它注定是我一辈子的财富,我将携带这些财富走向未来的更加笃定的路。
(作者系广州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