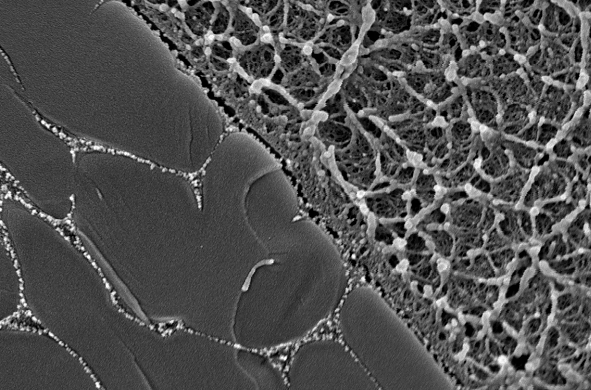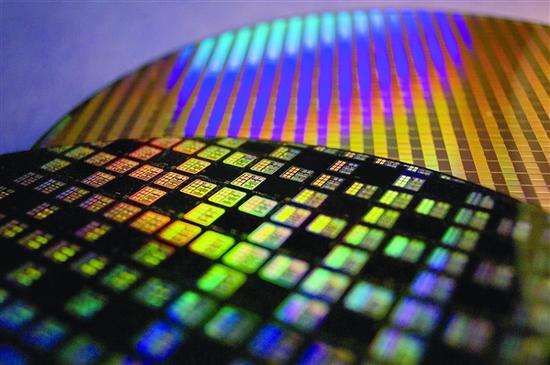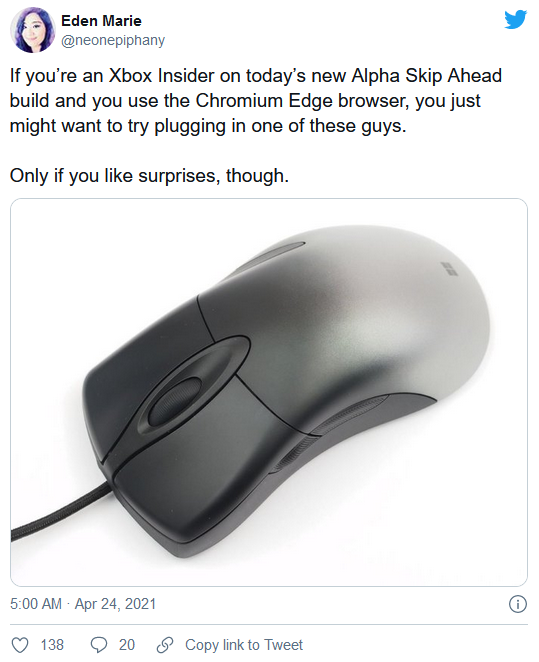原标题:斯人远去︱黎志刚:我的学术经历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历史、哲学、宗教及古典史学院(School of HPRC)教授黎志刚于2021年4月22日因病去世。黎志刚(Chi-Kong Lai),原籍中国香港,岭南大学本科(1980年),香港新亚研究所第二十六届硕士(1982年),先后师从全汉昇、刘广京等著名学者。他在企业史、商业史、海外华人史、上海史、日常生活史、航运史、中国社会经济史等领域取得重要成就。
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曾于2016年8月对黎志刚教授进行过一次“闲谈式”的采访,主要谈及他的学术经历。后来访谈未经黎志刚教授审定,也未曾刊出,不想今朝竟天人永隔。思忖再三,还是拟推出这篇访谈,在追思黎先生的同时,也希望学界同仁了解他的学术经历和研究心得。因未经审定,容有差误。
 黎志刚教授
黎志刚教授您可否谈谈自己的学术经历?
黎志刚:
我本科在香港岭南大学读中文系,后来去新亚研究所读了历史系的研究生,当时的导师是全汉昇先生。之前我想做关于郭嵩焘外交的研究,但全老师是做经济史的,他要求我做郭嵩焘的经济思想。我觉得他是对的,因为就目前来说,研究郭嵩焘在外交方面的人多,研究其经济思想的人少,而且郭的经济思想与其他人不同,确实值得研究。
硕士毕业后我本来想继续跟全老师念博士,他叫我到美国去,再做郭嵩焘,他其实是想我早一点毕业找工作。我现在的工作和同级的人相比,应该是不错了,这主要是因为全老师,他对学生的前途是很关心、很负责的。
跟着全老师读硕士的时候,他曾经对我有过考验,看看我是不是在用原始资料做研究。当我写论文的时候,他常拿原书来核对我的文章,比如涉及到清史的材料,他就会要求我马上从书架里拿出中华书局版的《清史稿》进行比对,而我每次能对到,他对我的印象就比较好。
全老师要求我到湖南省图书馆看资料,还有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见陆宝千,因为陆编过《郭嵩焘年谱》,这些对我是蛮有启发的。那年头在湖南省有很多郭嵩焘的手稿可以看到,我就跑到湖南省图书馆,当时没有介绍信,正不知所措的时候,碰到了岳麓书社的编辑杨坚,当时他们正在编辑《郭嵩焘日记》,还没有完成,所以不能给外人看。我提出想看一下,他说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能回答,我就给你看《郭嵩焘日记》。他问的问题是,你知不知道郭嵩焘的奏稿有多少卷?我说不知道有多少卷,但我知道至少有16卷,因为在他的年谱中写过既定奏稿达16卷,这个年谱是在1880年出版的,距离他1891年去世还有11年,在这段时间里他又发过几个奏稿,所以我知道他的奏稿至少有16卷。他听后就给我看了正在编辑的《郭嵩焘日记》。
我看您的资料,您有一阵子想跟余英时先生读博士?那么后来您为何选择加州戴维斯分校呢?
黎志刚:
这个是资料写错了,我并没有想过跟余先生读博士。我大概只见过余英时先生两面,没上过他的课,但是我读过他很多书。我原本打算申请何炳棣教授的博士,当时他在芝加哥大学,全老师跟我说,你在那不太好毕业,最好不要申请。我也考虑过王业键教授,不过他所在的肯特大学(Kent State University)发展空间较小。我之后又考虑过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徐中约教授、密歇根大学的费维恺教授、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刘广京教授。最后我申请到了密歇根大学和加州戴维斯分校。费维恺答应给我三年奖学金,当时他做系主任,全老师说犹太人不太可靠,还是跟中国人比较好。我后来跟费维恺还蛮熟的,因为这件事他见到我还有点生气。
刚去加州戴维斯分校的时候还遇到些困难,本来是可以给三年免学费奖学金的,但是全老师给的分数太紧了,平均下来我就差一点点,于是第一年就没有免学费奖学金。刘广京老师对我很关照,他看我没拿到奖学金,就介绍我去教人讲广东话,100美金一个月,但是也不够生活。到第二学期,刘老师有一个项目,让我做了他的助理,晚上还让我跟着他学西洋史,他是怕我主修课不合格,拿不到奖学金。我之后申请到了六年50万美金的奖金,可以不用愁学费的事,就安心做学问了。
博士毕业后,刘老师想安排我到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工作,他在台湾宣传我是他最好的学生,不过我不太希望老师帮我安排,更希望自己选择,所以没有把握这个机会。当时是施坚雅给我写的推荐信,他当时在加州大学,我上过他的课。在我博士还没毕业的时候,犹他州大学就十分希望我过去,是个一年的短期工作,给我很好的待遇,我把一个同学带过去也可以。而当时我又拿到了一个很好的奖学金,可以去日本、英国做研究。
后来有几个学校也给我职位了: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学,还有两三个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博士后。我当时本来想选香港科技大学,因为待遇比较好,但是我的家人更希望我去澳大利亚,所以我就去了新英格兰大学,这个学校的经济史比较厉害,还允许我去波士顿大学做一年博士后,为以后教日本经济史做准备。所以那个时候我常去哈佛商学院听课,跟哈佛大学的柯伟林、孔飞力都很熟,哈佛在这一年对我还是蛮不错的。
我离开波士顿的时候,行李太重了,就把我的博士论文寄出去给一些学者以减轻负担。结果运气比较好,我的博士论文《上海轮船招商局研究》获得亚历山大·格琴克郎奖(The Alexander Gerschenkron Prize),这是美国经济史协会颁给最佳非美国经济史博士论文的奖项,由一个大概四五个人组成的评选委员会完成评选,他们认为我的论文视野比较大,外国学者比较偏好这样的论文。虽然奖金只有1000美元,但在学界影响很大,我可能是到目前为止第一个拿到这个奖的中国人。
这是国家政策对公司制度的影响研究,招商局是其中一个例子。我本来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明清的官商关系》,不过后来我见到了一个学者叫韩书瑞(Susan Naquin),我作为一个年轻的研究生跟他聊天,他问我做什么题目、导师是谁,我跟他讲了,他说你这个题目不能做,也去跟刘老师说我这个题目不能做。刘老师听后就和我商量,他想让我做李鸿章这个人,他喜欢李鸿章,他认为李鸿章是完美的人。我是喜欢去找李鸿章的麻烦,我去查汇丰银行的档案,看看李鸿章有没有贪污之类的事情。后来我跟刘老师说,我不做李鸿章,我去做他的企业,就做招商局。但是招商局只是个案例,我想通过云南铜矿、山西票号,研究中国政府是怎么动员商人参加政府项目的,招商局跟他们有什么不同,同时也比较日本的一些企业和美国的铁路公司,外国人很喜欢这种研究方式。我当时读了两个博士,除了历史学还有社会科学学院的比较社会理论,我在戴维斯分校修了很多课,包括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艺术系这些课,学分够了,再交一篇论文,就可以拿两个博士。我是戴维斯分校这个项目第一个拿到双博士的。
您的硕士论文是做郭嵩焘经济思想的,这里面还是有经济史和思想史的分野,但到了戴维斯分校后就完全转向经济史了?
黎志刚:
我老师是搞经济思想的,他觉得我适合做研究,不适合教书,他可能觉得我当时英语不太好,所以不主张我教书,主张我进研究所。但是我找到的课题项目又都和经济有关系,然后他就让我做经济史方面的题目。后来我因为博士论文拿奖,有幸参与写剑桥商业史的中国部分。
您提到在波士顿做博士后之后,去了澳大利亚的新英格兰大学,在那待了几年呢?
黎志刚:
在新英格兰大学待了两年,然后我就转到昆士兰大学了。我觉得我的工作还是蛮顺利的,我曾经收到过很多工作邀请,像岭南大学的副校长找过我,还有香港的大学、澳大利亚其他的大学,伦敦大学也找过我做市场商业中心主任。因为我以前办过相关的讲座,从1996年开始,请过两百多个学者来昆士兰大学来访问。他们以为我是一个比较大的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其实不是。
我认识香港中文大学的苏基朗和梁元生先生,他们开玩笑说让我不要再做“南天王”了,说如果中大有职位出来,我可以申请一下,不过我还是没有申请。自从到了昆士兰大学后,我基本上没有申请过什么学校,除了申请香港中文大学一次。那次中大发了个聘请讲座教授的广告,我感觉我应该可以的,因为我当时刚刚升上了Reader,这个职称比中国的教授分量更重一些。这次他们没有聘请我,但是,苏基朗给我打个了电话,他说我们请了一个你很喜欢的人,你一定很高兴,就是科大卫。我认为他当然是全世界最好的。之后有人来找我,问我要不要在东亚所做一个访问教授,他们给我的待遇很好。梁元生先生当时还跟我说,如果我想在香港中文大学找工作,就跟他申请。
我2006年到香港中文大学,教一个关于中国商业的课程,只有十个人,上两个小时。讲中国的万达、海尔这些企业,也有关于中国经济转型这类的题目。我还帮梁元生教过课,时间比较短,大概只有几期吧。课余的时候主要是听科大卫老师的课,做学生时没有听过科大卫老师的课。我的老师刘荣芳,他很崇拜科老师,他是科老师的学生,他一直讲科老师很好。我比较喜欢听演讲和听课,可能和我本科不是搞历史有关。
您做经济史这一块,会和学界很多人打交道吧,比如费维恺、陈锦江等。
黎志刚:
的确是,陈锦江对我蛮好。熊月之教授到戴维斯分校访问过一年,我在那时和他建立了很深厚的交情,当时我还在读博士,大概在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年代初。有几个人对我帮助很大,在上海是熊月之,是他把我带到社科院的,他是我的推销员,但是我从来不找他,因为他太忙了。在北京是虞和平,他把我带到社科院近史所。在台湾地区是“中央研究院”的陈永发,我在台湾时还住过陈永发的家,当时全汉昇老师要求我去见陆宝千,我到了台湾想住蔡元培馆,那是比较便宜的一个宿舍,他们安排不了,所以安排我住在陈永发家,当时陈永发租梁其姿的地方住,所以我和他很熟。虽然陈永发跟我研究的领域不一样,但他写的文章会拿给我看,我告诉他不能多用带有情绪性的语言,我比较尊重他,他是个不修边幅的人,但对学术很有热情。他很希望我写一本关于晚清史方面的书,跟我说了五六年,我都没有答应,因为这本书本来应该是刘广京老师写的。我说王汎森也要写,他说王汎森不会写。其实晚清史方面我是有准备的,可以写一些,但是需要时间。
我和社科院系统比较熟,像北京、山东、上海、山西、南京、广东的社科院,都有像步平、王建朗这样比较熟识的学者。至于和大学的联系,早期是跟着中山大学的学者们像陈春声、刘志伟一起做田野,因为我比较崇拜科大卫,我觉得他是思想敏锐、不讲废话的一个学者,而且是真心在做研究。不过我不太跟他谈话,科老师时间太宝贵了,我暗地里像他学习。我在内地的大学有很多好朋友,像北大的王奇生、赵世瑜;南开的常建华、余新忠、江沛;南京大学的范金民、夏维中、陈谦平;浙江大学的陈红民;厦大的郑振满;华中师大的朱英、马敏。他们都跟我很好。
您还为李承基先生做过口述史,那是出于什么原因呢?是想把研究方向做得更广、更开阔吗?
黎志刚:
陈锦江到澳大利亚来访问,我觉得在澳大利亚没有什么材料给他看,得帮他找些新的材料,就想不如去采访一下新新百货公司老板的儿子李承基先生。我到处打听,跟李先生取得了联系。
但陈锦江在澳大利亚待的时间很短,我们只跟李先生见了一次面,我觉得访问不是很充分。之后我跟李先生通了很多次电话,我还常飞到悉尼去访问他。当时我去上海档案馆比较多,我是想做一个口述的文本,来比对我的档案研究。
我当时在澳大利亚做中山市研究比较多,想写一本关于中山的书。对李承基的研究只限于口述历史的阶段,是这本书的准备工作。后来我碰到吕芳上,吕芳上问我,你最近怎么样?我跟他说我访问了李承基先生。他说你拿来给我审查,经他审查通过就帮我出版了。李承基先生是新新百货公司创办人李敏周的儿子。我做这个书主要是探讨三个问题,一是看如何培养企业家,二是看他怎样经营这个企业,是看他退休后在侨居地的生活。
那您做田野是在什么时候呢?
黎志刚:
是1996年前后,我刚到澳大利亚教书的时期,那时我差不多每年圣诞节都到中山大学跟着他们一起做田野。其实从这个世纪开始,我就很少做田野了,最后一次是1998年。当时在做田野的过程中有几位学者特别吸引我,一个是科大卫,一个是萧凤霞,一个是滨下武志,当时陈春声、刘志伟他们都跟我同龄,都是同辈的,我们没有多少东西,主要是科老师比较厉害。直到现在我还经常关注他们的著作、读他们的书。我觉得学术是累积起来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垄断学术。我们如果有科大卫的头颅和何汉威这种对档案的认识,那就天下无敌了。
我看资料里面说您很注重去做实地考察?
黎志刚:
对,我觉得这个是受历史人类学的影响,因为从实地考察的事情,感觉很不一样。大概是在五六年前,我有半年的休假,我在营口钱包被人偷了,身上只剩下一点点钱。营口是个港口,我就把我身上几乎所有的钱都拿出来去雇了一艘船,去看以前的太古洋行、怡和洋行是怎么样的,结果跟我的空间考察不同,从中我可以看到当年招商局跟他们的竞争。再比如解放战争时的廖耀湘兵团,当初为什么要从营口出去,其实就是“关外辽东一盘棋”,这个从实地考察中可以切实感受到。我觉得实地考察是很重要的,尤其对于史学。另外,我们对史料的解读需要一种想象力,只有去过这些史料中所说的地方,才能更加清楚地理解史料。
他们考察的眷村、宗庙,是他们开展宗族研究的一种方法,但这种方法,我们也可以用来考察思想史、航运史。我现在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去看万达广场,感觉是不同的,要想看当年的唐景崧是怎么样的,我就要看看王健林、马云。我觉得历史记载的和生活中看到的还是有些出入,所以我们要做田野考察,这样可以增加我们的想象力,我觉得田野很重要。
那您最近几年主要在做什么题目呢?
黎志刚:
我做的题目都是比较长期性的。我第一个想要完成的是关于招商局的,但是压力太大了,做这方面研究的优秀学者太多,不能乱写。有一个观点,就是你写的书要跟顾炎武来比较,要看这本书对学术是否有贡献,如果乱发一些东西,对学术没有贡献,多一篇少一篇也没所谓的。所以关于招商局这本书,如果说我能够跟我的同学还有老师辈有什么不同的话,主要是我看的档案应该比他们多,我可以从档案里面发现新的问题。
此外,我一直比较关注中山人,我大概是明年有一本书出来,就是讲中山人的。应该会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三十万字的,是广东华侨丛书系列的其中之一。
另外,我找了大概有五六千种关于头发的材料,包括回忆录、档案,想写一本有关头发的中国生活史方面的书。我觉得这本书如果能写出来,在学界应该会影响蛮大的。因为头发在中国是个大问题,从晚明到现在一直关注这个问题。这需要一个比较大的视野,我想主要从经济史、社会史的角度来写。我访问过很多人,包括很多少数民族地区的人。这是我在看招商局档案受到阻碍的时候想到的一个题目,写的话要从长时段的背景的考察,结果就把我带到了社会生活史。我参与过一些关于日常生活史的国际会议,都跟头发有关系,谈过头发的文章,与会学者觉得把会议论文发出来比较简单,但是从发表的文章来看,就比较少了,不过我一直觉得这个题目很有意思。我的研究时段是从晚明到现在,我大概花两三年时间可以写完。
我和剑桥出版社有两个计划,一个就是我讲的那个头发研究,另一个就是剑桥中国经济史。出版社给我五年时间写中国企业的部分。我的中国经济史会写十九、二十世纪,是一篇介绍性的文章。目前编了三本书,一本是《经济思想、实业与近代中国》,大概包括三十个人的文章,我是跟王汎森、陈永发合作的,现在大概有十个人交稿,还有二十个人没有交稿,包括科大卫。我们主要看经济思想、实业救国是如何影响中国近代的转型的。
此外,我跟胡晓真一起做了一个计划,探讨“中国近代的道德、利益冲突和诚意”的问题,胡晓真是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的所长,她之前是研究才女的。我们的题目是《物质性、道德性与中国社会的日常》,从魏晋南北朝讲到现在,大概我们现在是十几个人,想编一本书出来,这些是目前几个有兴趣的课题。
第三本书已经编好了,是关于海外华侨的日常生活,是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跟张国雄校长以及华侨华人研究所的所长张春望一起编的。
另外我们有两篇专号出来,叫“国家航海”,戴鞍钢他们有写,我是跟朱英一起的,是关于招商局的。
我发现您还有一个兴趣,就是去哪里都要去逛书店吗?
黎志刚:
因为我们的地方比较小,没有什么中文书,我觉得学术要靠积累出来,看书还是很重要的。让学校图书馆买太麻烦了,要填好多表格,还不如自己买方便。
您觉得中国大陆的经济史与海外经济史研究有什么区别吗?
黎志刚:
我觉得像李伯重这样的中国学者的经济史做得非常不错,而且他们的视野也越来越宽大,现在出国的机会很多,找材料也方便。海外的学者受到西方的理论和比较史的影响比较大,可能会跟中国的学者看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