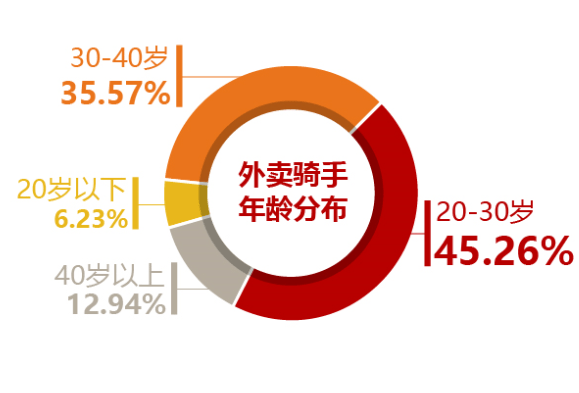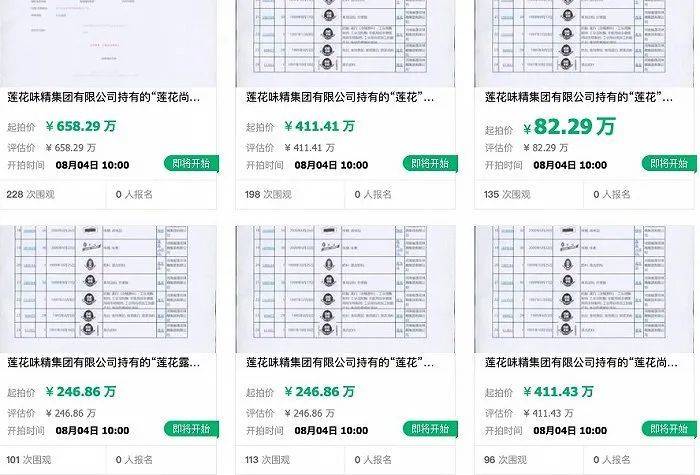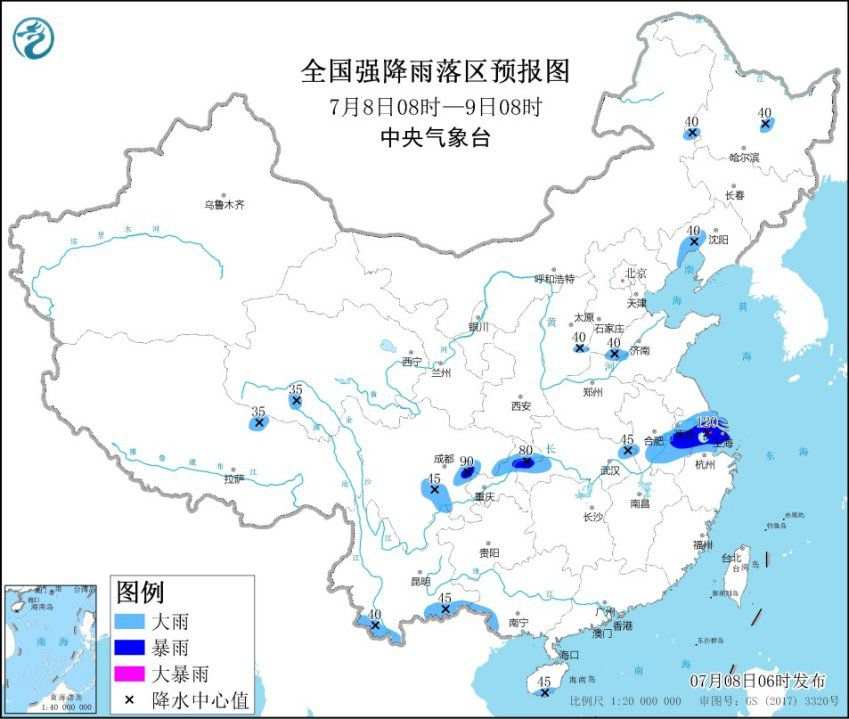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在这场文理交融的深度探讨中,理科史研究一边寻找它的根,一边寻找它的书写者。
■本报记者 胡珉琦
一个世纪前,北京大学成为了中国理科教育的开端与发祥地,此后,北大理科的发展历程便反映了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史的一个侧面。
2021年6月末,北京大学举行了“北大理科与中国现当代科技发展”学术研讨会,在这场文理交融的深度探讨中,理科史研究一边寻找它的根,一边寻找它的书写者。
北大理科史承载的是什么
2021年,在“李革赵宁理科史研究项目基金”的支持下,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正式启动了“北大理科与中国现当代科技发展历程研究”项目(以下简称北大理科史项目)。
“北京大学是我国最早设立数学、物理、化学、地质等学科的高校,北大理科巨擘云集,创新人才辈出,学术成果显著,在现代科学的引入、传播与教育等方面作出了开拓性贡献,在中国现当代科技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国科协名誉主席、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创系主任韩启德在研讨会上表示。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邓小南提到,北大理科起步于百年前的红楼,牵系着中华民族的命运,见证了科学在近代中国生成、发展的历史进程。“新中国成立以后,北大理科更是在国际科学的前沿取得了系列性的重大进展,在我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据韩启德介绍,北大理科史项目旨在通过回溯北大理科的历史足迹,探讨各学科的产生、发展、变化及其与中国现当代科技发展的关系,准确有据地把握学科发展的历史规律与趋势,加深对科学本身及其在中国本土发展规律的认识,为新时期北大以及全国理科的学科建设和科技创新提供历史启迪。
他还强调,通过这个项目的研究和传播,将使人们更加深刻体会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并推动全社会科学文化的建设。
在邓小南看来,研究理科史,不仅是关注精深的学问、关注技术的功用,更是要追踪科学思想的源流、科学风气的形成。通过梳理学科的发生、发展轨迹,思考学科研究的理论、范式,探究人物、事件之间的关联,揭示学科演变规律与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不仅为理解北京大学的历史地位增加了新的维度,也为中国近代以来社会文化变迁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域。
从这个意义来说,北大理科史项目的启动是一件大事。据悉,今后北大理科史将被作为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长期重点研究方向。项目计划在北大理科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设一个包括文献、影像和口述等多种类型的、独具特色的中国现当代科技史数据库,使其成为北大科学史学科建设和发展的特色项目之一。
如何把理科史写得像历史
写史,从来都是一个艰巨而又辛苦的系统工程。那么,如何把理科史写得像历史?
邓小南认为,“历史书写,要秉持‘实录’原则,求真知,存信史”。她表示,从操作的意义上讲,首先,“史源”渠道要开放,收集不同类型的材料,档案、实物、报章、回忆等相互补充质证,在核验的基础上,形成分类别、依时序的数据库与史料“长编”,尽可能保留各类资料——包括说法不同的资料,以便为纷繁的史实提供广博的知识背景,提供比对辨析的丰厚基础。其次,要在长编基础上,确认核心要点,形成大事记与整体纲目。
而在组织撰写的过程中,既要突出学科内在的发展逻辑,也要关注与特定时代的关联;既要聚焦理科,也要关注与其他学科及学术共同体的融通;既要突出北大人,也要关注与整体社会情势的互动。
韩启德在总结发言中也提到,科学史本身是一项求真的学问,求真就必然要有质疑、批判的精神,要以理性的思考来审视所有的一切,包括科学发展的历史。
他表示,研究学科史,一定要深入掌握材料。不能急躁,同时也不能懈怠,努力把足够的资料收集好,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科学史、理科史研究一定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精神。
“尤其还要注意不同的材料,甚至与己观点相反的材料都要尽量收集完整,然后进行比对辨析。对于这样的材料,更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研究。如果大家一时不能得到共识,要允许保持各自意见,提倡多元性。”
与此同时,要审慎、严密,不能随意下结论。韩启德解释道,世界是非常复杂的,往往理出一条线就觉得顺理成章,但实际上一个事件存在着多个甚至无数个影响因素,如果要得出结论的话,一定要非常谨慎,不能以个人所好和情感来随意剪切材料,随便得出结论。
他还强调,历史研究需要问题意识。如果单纯做一个编年史,它的意义是可以为后人做研究用。但北大理科史研究要有更大的进取心,要有研究的品位,要能够提出问题。这与搞科学研究是一样的,提出好的问题,就已经成功了一半。
“最后,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学科史研究的根在什么地方?”在韩启德看来,历史是由人创造的,历史研究的核心是人,因此,理科史研究要围绕着人来做。而人的核心是思想,所以深入的理科史研究必定是思想史,是文化史。此外,任何学科发展都是与社会紧密相关的,科学推动社会发展,而社会又决定科学发展,所以学科史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社会史。
谁来书写理科史
理科史的书写具有突出的文理交叉特性,这是一个凝聚多学科学者共同探索的复杂过程。但在实践操作中,常常是拥有理科知识背景的学者,不掌握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而史学研究者又缺乏对理科知识的足够了解。文理无法充分相融,是理科史研究面临的现实难题。
对此,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王奇生认为,理科史研究的持续发展非常需要依靠跨学科人才的培养。这个领域需要一批拥有一定理科教育背景,并对历史学感兴趣的学生,通过诸如联合培养的方式,真正进入历史学领域接受专业的学术训练,以科学史学者的思维、观念、视野来进行理科史的书写。
事实上,由单纯的科学家和科学史家来回溯同一段历史,结果往往是不同的。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吴国盛提到,长期以来,科学史界有个说法,科学家的科学史和科学史家的科学史是不一样的。
他解释说,近代科学本质上是分科的学问。主要由科学家自发从事的科学史研究一开始都是分科史,由数学家写数学史,物理学家写物理学史,化学家写化学史。
“当时的分科史或学科史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服务于该学科的需要,更多地关注科学上的问题。但后来的职业科学史家普遍认为,这种服务于学科本身需要的学科史只是一种有偏颇的‘历史’。”吴国盛表示,这种科学史往往是“辉格史”。
辉格史是一个编史学概念,即从当下的眼光和立场出发,把历史描写成朝着今日目标的进步史,把历史上的人物分成推进进步的和阻碍进步的两类,通过主要选择进步的人物和事件来编成历史,就会达成对今日目标和立场的认可和赞同。
吴国盛坦言,科学家写的科学史很容易具有辉格史倾向。他以美国生物学家和生物学史家恩斯特·迈尔为例,迈尔是20世纪公认的演化生物学的权威,他写作的《生物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奠定了他在生物学史研究领域的地位。而他在书中明确表示,自己是作为一个生物学家而从事生物学史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让读者或学生更好地理解目前的科学问题,因而,当下所面临的问题以及相应的立场和眼光,不可避免地在历史材料的选择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但在现今的科学史学科范式下,科学史家们会强调,今天的理想和目标不一定是过去的理想和目标,历史人物和事件只有放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中,着眼于当时的理想和目标,才可能得到真正的理解。”吴国盛指出,科学史研究不应该强调过去与现在的相似之处,相反,应该着重发现不同之处,发现的不同之处越多,对历史的理解就越深入,我们才有可能获得一种历史洞察力。
他告诉《中国科学报》,早在上世纪50年代国际上就已经完成了由科学家的科学史向科学史家的科学史的转折,但中国目前还处于转折期,仍然需要更多科学家参与、推动包括理科史在内的科学史研究项目,这一学科才有发展的希望。正因如此,他认为,在多位大科学家的支持下,北大理科史项目将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