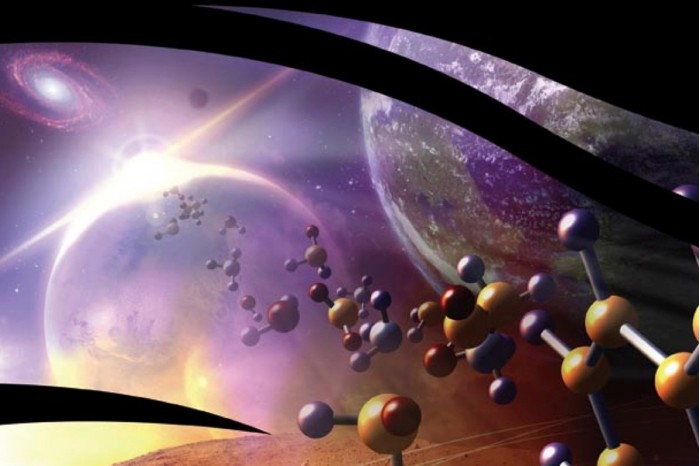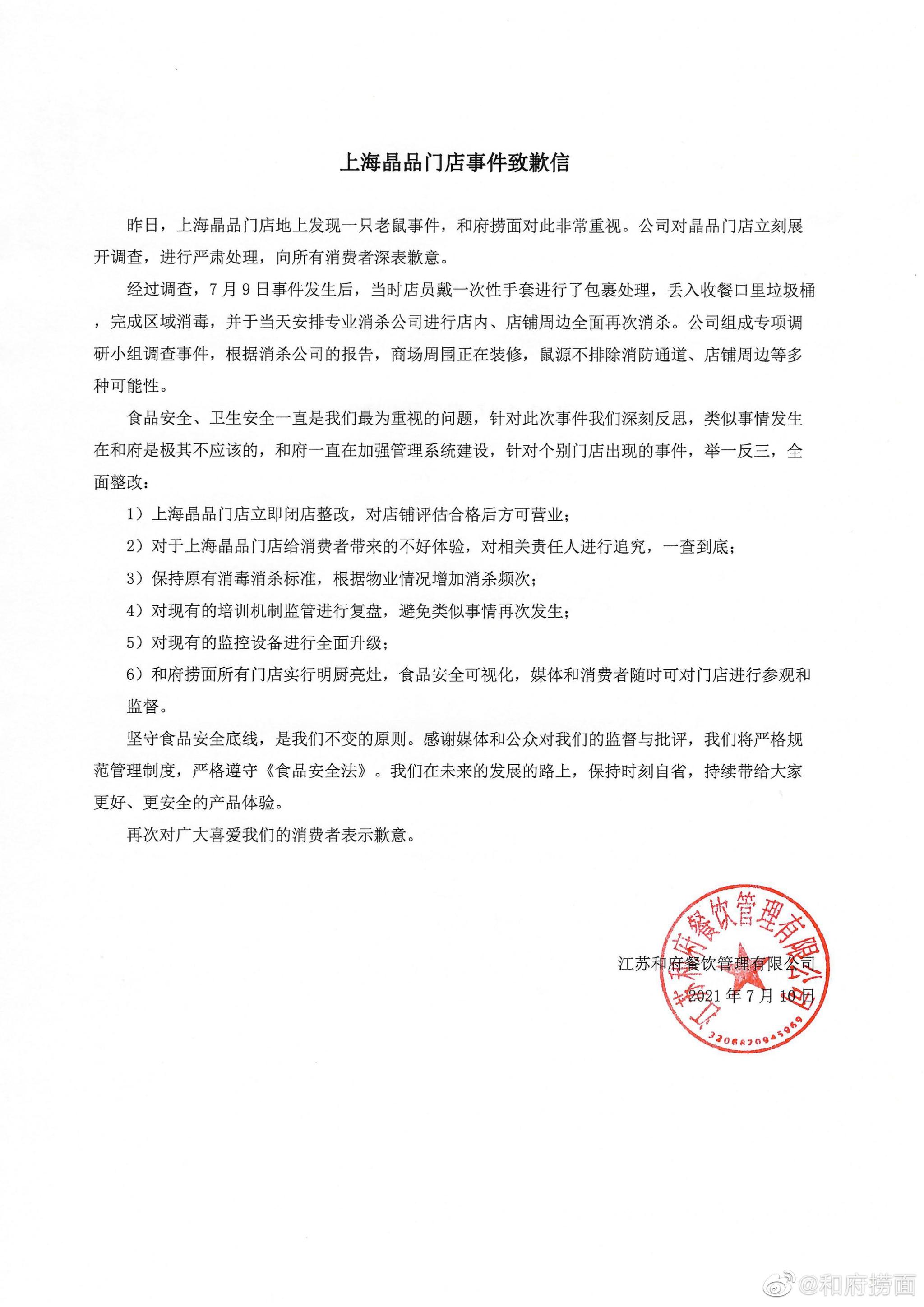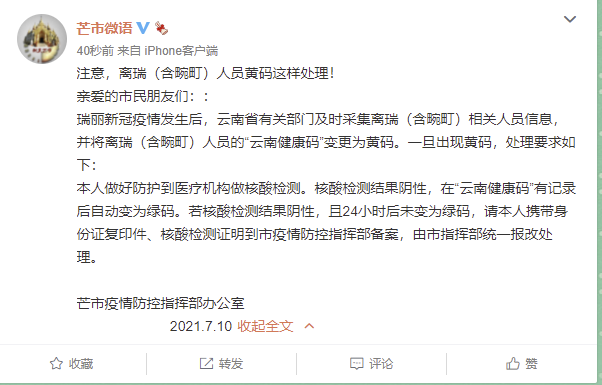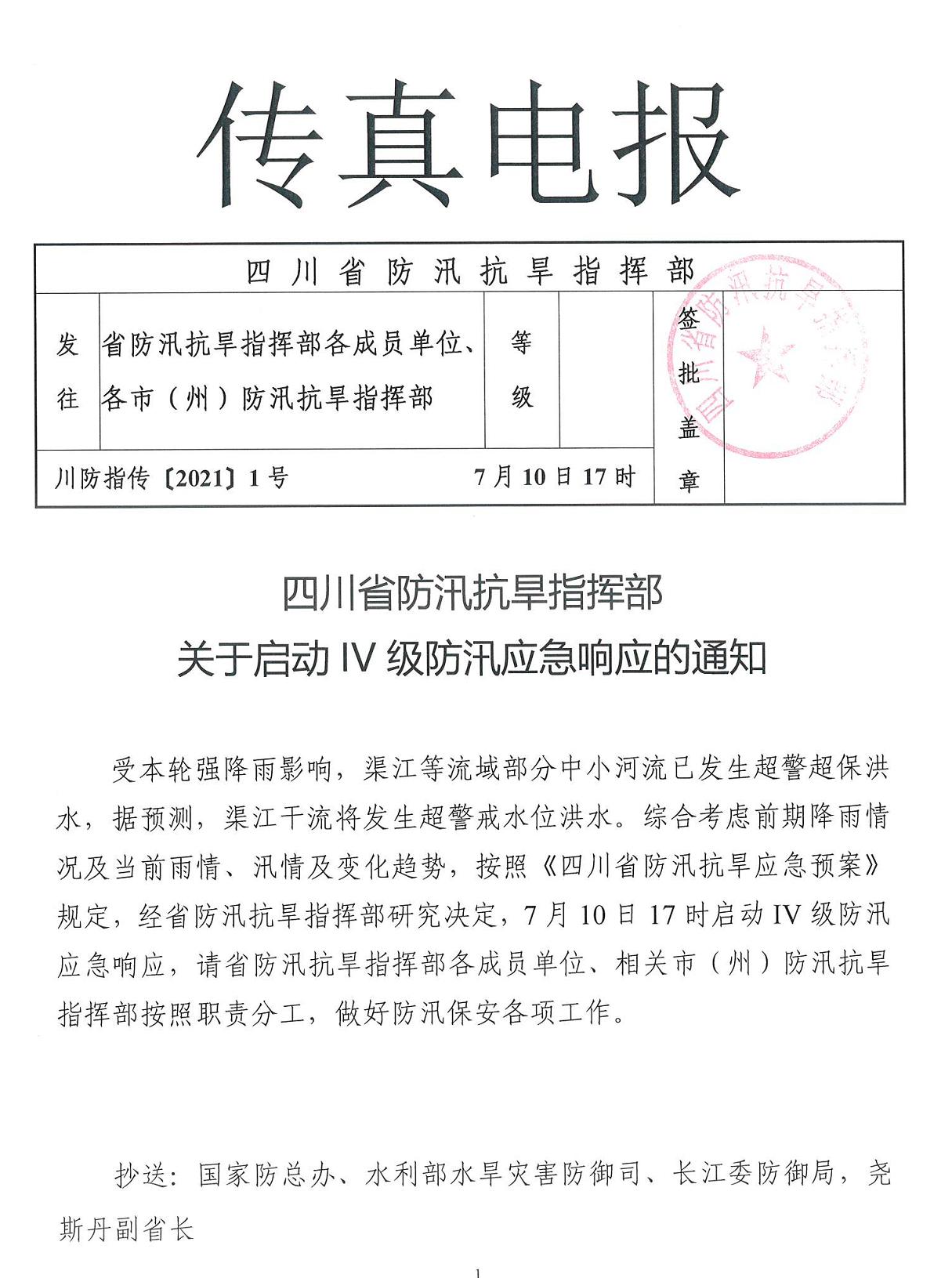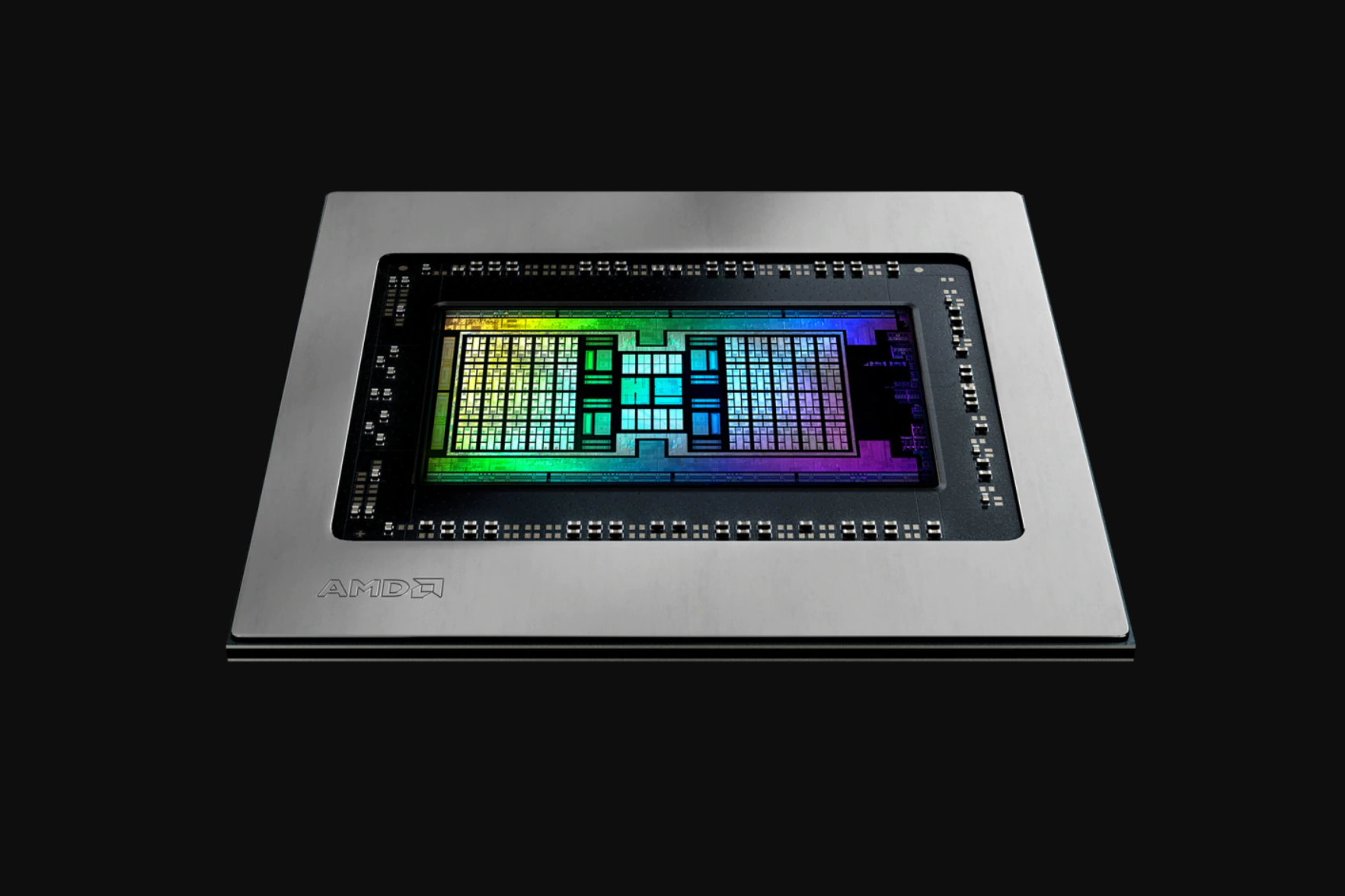原标题:《中国思维的根系》: 刨根问底,重现中国传统思维的“语法”内生逻辑
 西方思想传入中国,译著不断,可这些思想除了停留在高级知识人的头脑中,它们始终未能在普通中国人的思维深处真正扎根。为什么?在这部专著中,作者从整体的认知论域出发探寻中国思维的基本特征和呈现形,在与西方汉学的对话中,在新的视角下重新透视先人们的历史境况和思想逻辑,以此唤醒、重现中国思维的“语法”。作者认为,作为维系中国数千年悠久传统的内生文化要素,中国思维是形塑中国精神特质的重要历史能量,而中国思维的“第二域”,即中国古代思想者论证具体问题时所持有的一般性认知规则、推理形式和思维路径,是规定“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关键要素。
西方思想传入中国,译著不断,可这些思想除了停留在高级知识人的头脑中,它们始终未能在普通中国人的思维深处真正扎根。为什么?在这部专著中,作者从整体的认知论域出发探寻中国思维的基本特征和呈现形,在与西方汉学的对话中,在新的视角下重新透视先人们的历史境况和思想逻辑,以此唤醒、重现中国思维的“语法”。作者认为,作为维系中国数千年悠久传统的内生文化要素,中国思维是形塑中国精神特质的重要历史能量,而中国思维的“第二域”,即中国古代思想者论证具体问题时所持有的一般性认知规则、推理形式和思维路径,是规定“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关键要素。 萧延中,1955年生,曾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图书馆馆长,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主要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政治心理学、毛泽东政治思想等领域的研究。著有《巨人的诞生:“毛泽东现象”的意识起源》(专著)、《中华文化通志?政治学志》(合著)等;主编“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和“心理传记学译丛”;另出版编著、译著多种,发表论文多篇。
萧延中,1955年生,曾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图书馆馆长,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主要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政治心理学、毛泽东政治思想等领域的研究。著有《巨人的诞生:“毛泽东现象”的意识起源》(专著)、《中华文化通志?政治学志》(合著)等;主编“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和“心理传记学译丛”;另出版编著、译著多种,发表论文多篇。 作者在本书导论中说,思考和书写这些关于中国古代思维特质的研究笔记,其动力源头,或称“问题意识”,总的来说,来自两个不同层次的困惑。在一个比较具体的层面上,“问题”源于中国古代思想史文献的阅读经验。姑且不谈古今汉语的差别问题,就古人提出问题的角度和提出问题的方式,与今人就不尽相同。
作者在本书导论中说,思考和书写这些关于中国古代思维特质的研究笔记,其动力源头,或称“问题意识”,总的来说,来自两个不同层次的困惑。在一个比较具体的层面上,“问题”源于中国古代思想史文献的阅读经验。姑且不谈古今汉语的差别问题,就古人提出问题的角度和提出问题的方式,与今人就不尽相同。 其一,他们“为什么提这样的问题,而不是提那样的问题”就引发了笔者的强烈好奇。这里就涉及古今之人概括事物的基本方式的不同。在古人的脑际中,整体宇宙是合为一体的,“天”与“人”,动物与植物,就本质的意义上讲就是一个东西。在这样的预设下,“天视民听”“罪遭天谴”就成为一种很自然的状况。而在经过启蒙洗礼之后的今天,“人”变成了大写,被视为世间万物的中心,宇宙则成为被人类所驭使去创造消费价值的“物质”,“天”与“人”成为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属类,如果再在其中寻求直接的相关性,就属于“思维混乱”之类的妄念。
其一,他们“为什么提这样的问题,而不是提那样的问题”就引发了笔者的强烈好奇。这里就涉及古今之人概括事物的基本方式的不同。在古人的脑际中,整体宇宙是合为一体的,“天”与“人”,动物与植物,就本质的意义上讲就是一个东西。在这样的预设下,“天视民听”“罪遭天谴”就成为一种很自然的状况。而在经过启蒙洗礼之后的今天,“人”变成了大写,被视为世间万物的中心,宇宙则成为被人类所驭使去创造消费价值的“物质”,“天”与“人”成为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属类,如果再在其中寻求直接的相关性,就属于“思维混乱”之类的妄念。其二,古人“为什么这样地提问题,而不是那样地提问题”,这里的意思是,同样的问题,可以以这样的方式提出,也可以以那样的方式提出。例如,同样是涉及身体健康的问题,人们既可以从生理和心理各系统的角度予以解释,也可以从阴阳协调、内外平衡的角度给予关照。前者依据的是形式逻辑推理,而后者则更多地依据隐喻式类比的演化联想。起码在政治思想的范围内,中国古人反反复复地在论述君、臣、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就管理和控制技术的角度讲,已相当发达。但至迟到黄宗羲,论述上述议题时仍然没有超出“权力均衡”的框架,所谓批判专制君权的意识,并未超出改朝换代式的“革命”范畴。
那么,究竟是什么约束和规定了他们的“问题”性质?数千年来这些问题被反反复复以同样的方式提出,这本身就暗示着在其背后可能存在着某种力量“使之然也”。这种超越制度,或者参与制度建构的因素究竟是什么? 作者认为根源在于中国思维的方式。中国思维是维系中国数千年悠久传统的内生文化要素,是形塑中国精神特质的重要历史能量,它以“默会知识”的形态渗透进中国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至于达到“日用而不知”的社会无意识程度。它不仅是“智性的”,而且是“心性的”;不仅是“思想”,而且是“情态”。
作者认为根源在于中国思维的方式。中国思维是维系中国数千年悠久传统的内生文化要素,是形塑中国精神特质的重要历史能量,它以“默会知识”的形态渗透进中国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至于达到“日用而不知”的社会无意识程度。它不仅是“智性的”,而且是“心性的”;不仅是“思想”,而且是“情态”。尽管中国传统思维与现代科学理性分属不同的知识类型,但面对复杂丰富的现象世界,二者并非必然构成非此即彼的简单对立。超越以“前现代”标签作为衡量中国思维知识性质的线性准则,剖析和理解其中自洽的内在理路,是寻求和挖掘二者借鉴互渗之可能性的路径之一。
作者在书中说,中国思维有“共时性”特点。在方法论上,“共时性”描述既不是以发现“规律”和证明真理而抽象历史的所谓“宏大叙事”,也不是以抓到关键“钥匙”而一劳永逸地实现解释意图的本质主义,它仅仅是面临整体性议题时的一个有用的观察视角,一种便捷的透视工具,一项分析过往的认知取向。 国际知名哲学家郝大维、汉学家安乐哲在《孔子哲学思微》一书中指出:中国文明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一直有一套不同于西方的预存观念(presupposition)在起作用。由于在翻译中未能发现和承认这种差异,致使我们对中国的世界观有种似曾相识的错觉。本书的研究正是着眼于中国思维的“第二域”,即中国古代思想者论证具体问题时所持有的一般性认知规则、推理形式和思维路径,探寻规定“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关键要素。作者的研究横跨了历史学、哲学、心理学、文字学、宗教和政治学等多个领域。
国际知名哲学家郝大维、汉学家安乐哲在《孔子哲学思微》一书中指出:中国文明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一直有一套不同于西方的预存观念(presupposition)在起作用。由于在翻译中未能发现和承认这种差异,致使我们对中国的世界观有种似曾相识的错觉。本书的研究正是着眼于中国思维的“第二域”,即中国古代思想者论证具体问题时所持有的一般性认知规则、推理形式和思维路径,探寻规定“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关键要素。作者的研究横跨了历史学、哲学、心理学、文字学、宗教和政治学等多个领域。本文原载于百道网,作者宗和
图片授权:pexel
本书被评为“2020年人文社科中文原创好书” “2020年度人文社科好书”和“2020年度教师喜爱的100本书”,入选百道口碑好书。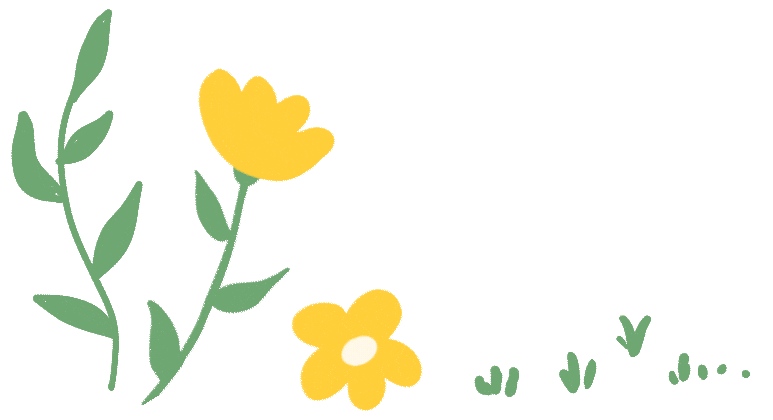
原标题:《《中国思维的根系》: 刨根问底,重现中国传统思维的“语法”内生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