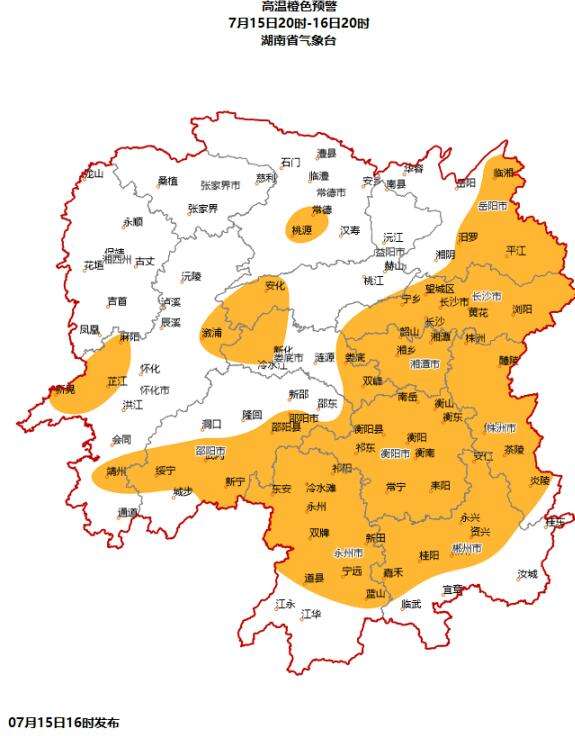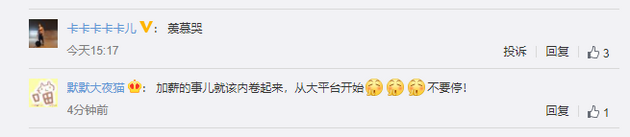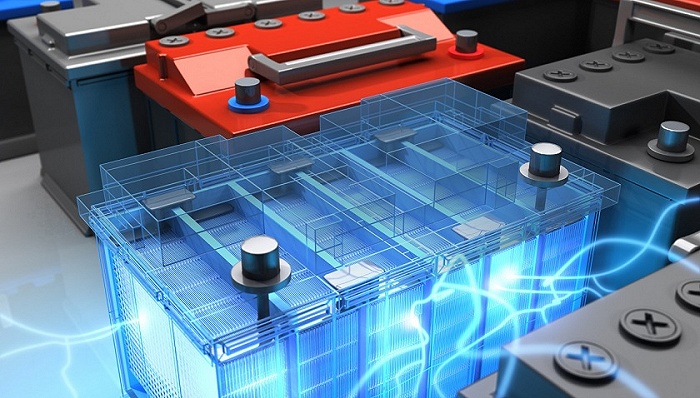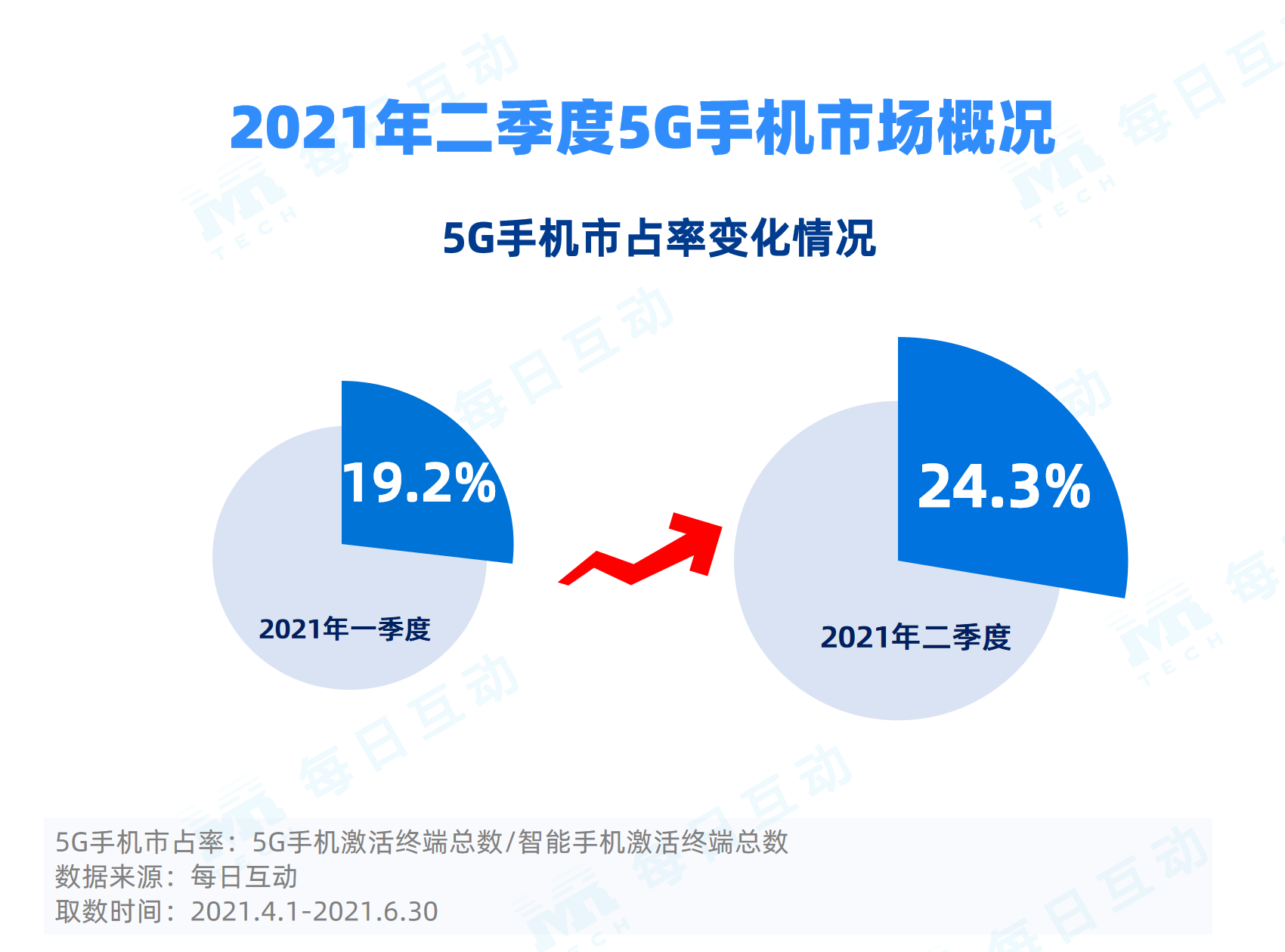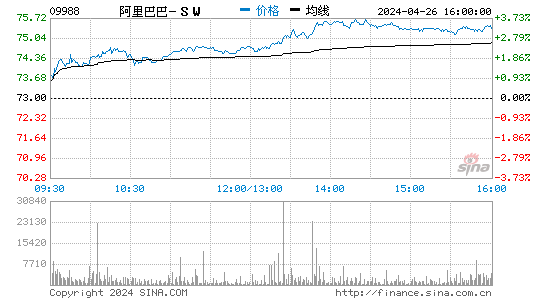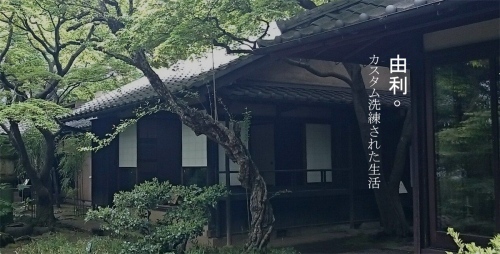原标题:人生呢,不必总执着“做自己”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作者:陆飞,编辑:苏小七,监制:猫爷,题图来自:《大豆田永久子和三名前夫》
前段时间,擅长描绘人性的“金牌编剧”坂元裕二新作,日剧《大豆田永久子和三名前夫》(目前豆瓣评分8.8分)完结了。
大豆田在整理旧物时,发现过世的母亲竟然有一封写给陌生人的情书,言辞惊人,说自己愿意舍弃一切,只要能和对方在一起,这份情书最终没有寄出去。
看完信后,她开始怀疑母亲生活的其实并不幸福,看似豁达背后,是母亲不敢做真实的自己,被家人所拖累吗?
最后,母亲的情人真桑用一番话解开了大豆田的心结:“她是真心爱着家庭,同时真心向往着自由,一个人心中有着极端矛盾的两种想法,两种想法都是真实的,无论哪一个都是真正的她自己。”
虽然电视剧迎来了结局,但困扰我们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做自己”真的就是所有问题的答案吗?
作为当下最流行的口号,品牌广告、媒体故事、同事好友,到处都在对你说“勇敢做自己吧”,仿佛“做自己”是最高级的活法,一切苦恼都将不攻自破。
可是“做自己”的内涵如此的暧昧不清,这些进一步的追问也没有解释: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怎么办?为了做自己可以伤害别人吗?做不到时,又怎么办?完全相反的两个想法,都是平等的真实的自己,这可能吗?又要选哪个呢?
一、也许我们可以欺骗世界,但还是要面对自己的内心
每当说到“做自己”时,免不了让人想要反过来追问:“为什么现在的做法,不是在做自己?”
为真心热爱的事业奋斗是做自己,为了自己的物质需求而接受并不喜欢的工作,就不是做自己吗?很有主见、特立独行的人,是做自己的人,被认为是唯唯诺诺、没有什么特别想法的“普通人”,不可以就做这样的自己吗?
如此说来,“做自己”这句话其实有两种暗含的意味,第一层,是推崇真实;第二层,是变得更好。而当现在的语境中说出这句话时,往往主要指的还是后者的意思。
前一阵,蒋方舟在微博上发了一段话:社交媒体上传播着同样的情绪,“逃避是有效的,废柴是快乐的,成功是不属于我的,自私是正常的,没关系,我们都一样。”
于是我们很容易沉浸在一种自我宽慰之中:“真实的自我就是最好的。因为已经做了自己,所以不必做更好的自己。”
“更好的自己”是一个容易让人误解的表述,在这里蒋方舟做了一个明确的限定,她描述的那些没有做更好自己的人,是已经做了真实自己的人。
可是一定有人会追问,真实还可以分好坏的吗,今天晴天,明天下雨,这种好,那种坏,是由什么判定的?说到底,为什么非要成为更好的自己?
这不仅是质疑,也是困惑,是每一个“逃避的、废柴的、自私的”但真实的人都问过自己的问题:这就是我吗?我要成为的,就是这样的人吗?
显然,如果“好”比“真实”重要,“做自己”的整个大厦就坍塌了;但要是失去“好”的层面,它也终究会被死气沉沉的一片灰暗所吞噬。
只有一个办法能破解僵局,就是把“真实”和“更好”两个维度重新统一起来。
 图 |《大豆田永久子和三名前夫》
图 |《大豆田永久子和三名前夫》所谓“做自己”,简单说来,就是听从自己的内心。那要是一个人已经听从了自己的心,是不是就结束了呢?其实没有,ta还要问问自己,听从的是哪个部分。
我们把心抽丝剥茧,问问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却猛然发现,根本不存在一个完全一致的自己。既想要安稳清闲地当个公务员,又想要热火朝天地创业致富,想要月亮也想要六便士,每个想法都是真的,而什么是更“好”的想法?就是更真的想法。
换句话说,就是“以自身为目的”的那些想法。
是想要独身,但不想被人指摘,也害怕没人养老的生活,所以选择孩子吗;还是虽然人人都讲独身更快乐,但由衷喜欢孩子,还想多要几个?
哪个是以自身为目的的更真的想法,旁人全然没有评断的权力,完全是每个人内心的法庭:没有人可以打开你的心,探视清楚每一个抉择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你甚至可以狡辩,可以骗自己,没有人会知道,你是自己唯一的法官。
而这是多么大的负担,近乎英雄主义的要求。一个人骗得过世界,对自己却无处可逃,那双审视的眼睛始终观照着,随时准备宣判自己。
或许有的时候,我们想要暂时闭一下眼,在欲求、恐惧、逃避、软弱的自己中歇一歇,就让我们去吧。
二、做更好的自己,是否是另一种规训?
既然,“更好的自己”是完全主观的事,下一个迷惑便随之而来:做更好的自己,是每个人自己的责任吗?是不是除了怪罪“要用一生来治愈的童年”,每个人都没有做不到更好自己的借口?
如果我们一边呼吁人们“做更好的自己”,一边把所有责任都推给每个个体,那就跟说“独立女性都应该有自己的房子和工作”,“每个人都应该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在北京没有年薪300万不足以拥有自己的人生”一样,是一种伪善,是抛弃了绝大多数人的新自由主义式的口号。
 图 |《大豆田永久子和三名前夫》
图 |《大豆田永久子和三名前夫》前段时间有一部女性题材的纪录片,其中一集讲到一位全职妈妈,她天天在家,逐渐焦虑失眠,不快乐到让孩子都忍不住劝她,“去追求你喜欢的事情吧,活出自我”。
听上去非常善解人意,跟我们平日说的、听到的开解也十分相似。可是,没有人去探究,她为什么渐渐失去了自我,追求喜欢的事和她所承担的母职之间,是不是存在矛盾,让她没办法同时做到两件事。
娜拉应该出走,可出走以后呢?
如果不能提供支持,仅仅谈“做更好的自己”,反而会成为新的暴力。我们可以简单指出人们忘却自我,而不去看到ta背后的压力,我们鄙视别人的软弱,而不管ta现实的需求。
为什么你不做自己呢,明明你可以做到的啊?尽管60分就能活下去,为什么你不想要90分呢?
可是单独凭ta自己,真的做不到90分啊。叫醒了铁屋子里的人,让ta瞥见了自己的不幸而不伸以援手,已经足够心碎;还指责ta不努力去往外面的世界,就称得上严酷了。
于是,人们为自己感到羞愧,或怨恨他人,或质疑自己,一个美好的宣言,最终的结果是造成更大的分裂。
近几年的社交媒体上越来越流行“真小人”,人们追捧这种人,因为觉得比起说风凉话的伪君子,真小人很真实,代表了无能向上的某部分自己。有意思的是,为什么人们下意识地在真小人和伪君子之间选择,完全忽略了真君子?
因为真君子,事实上就是更好的自己,舆论对真君子的质疑,对应的现实是人们无力向好。
一方面,每个人必须以个体之躯与大环境的困难斗争,只有变好的义务,却很难有求助的权利;另一方面,举目望去,“好”的模版非常单调,如果一个人心中的好不属于其中,ta就只能在自己和社会之间二选一,选择哪一个,都有随之而来的痛苦。
这也是为什么,一种非典型的“好”开始被我们所关注,比如《螺丝不肯拧紧》的陆庆松,比如《平原上的娜拉》中的刘小样。
打开豆瓣,三不五时地就会看见一些都市传说,某人的90后同事突然出家了,才发现寺庙里原来有好多清北毕业的;某人的女性朋友在大城市打拼到中高层,有一天突然辞职卖房回家种地去了,一天天都过得很开心。
近年流行的许多影视作品,也有许多“都市边缘人”,本来被主流价值观认为是不值一提的人,被描绘为像“烟囱里排出去的烟灰一样毫无意义、毫无价值”的人,却仍然能够坚持演奏,自得其乐地聚在一起生活。
当我们看见他们,心中的某个部分就能喘一口气,哦,原来这样也可以生活,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许我还是能做到的。
做更好自己的渴望,或许一直蛰伏着,它也许会永远蛰伏下去,除非得到一些耐心、一些帮助,或是有时候,能够遇到一些同类。
三、不存在“我就是这样的人”
关于“做自己”,最复杂也最多争议的一个问题,是关于真实,也可以说,是关于塑造。
回到文章开头提到的日剧《大豆田永久子和三名前夫》,大豆田的妈妈既想要抛夫弃子追求自由,又想要留在家庭之中,让大家都开心。她的爱人说,这都是真实的她,怎么选都是她自己。
这是真的吗?
不妨换成这些更熟悉的网络争议:一个女生喜欢穿JK制服,同时又想要摆脱被凝视被物化的身份,这两种愿望是同等的吗?她觉得穿JK的自己很可爱,可是为什么JK会让人显得可爱?为什么她希望自己是可爱的?
一个化妆的女生怎么才能确定,到底自己想要化妆是为了取悦自己,还是取悦别人?
大豆田的妈妈,她想要留在家人身边,想要让他们开心,这份心情完全可能是真诚的。可如果仅仅考量到这里,对于增添她的幸福似乎毫无帮助。
我们要问的是,她的这个愿望,有多少是因为这样的想法,从小到大可以得到身边人和社会的鼓励赞同,而相反的想法会被打压?
会不会是她的某种渴望能让家人开心,相反的想法却会造成冲突,而她的性格特质不喜欢冲突或者喜欢让别人开心?这种力求和谐和自我奉献的特质,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做自己”从来不只是自己的事,我们无法完全脱离环境去讨论“自己”。困难在于,有一些环境,本身很可能正是这个人需要摆脱或克服的,但由于长期去适应环境,我们已经分不清楚哪一些个性和愿望是自己的,哪一些是为了保护自己而采取的伪装。
 图 |《大豆田永久子和三名前夫》
图 |《大豆田永久子和三名前夫》之前网络上掀起一阵关于全职主妇究竟是否可取的讨论,不同立场的两方吵到不可开交乃至互相鄙视,支持的人觉得,这是她自己真心向往的生活方式,没有人有权阻碍她的自由;反对的人则认为,不平等的社会环境下没法谈个人意愿是否真实,何况这么做还会压缩女性的公共空间。
这样的争论或许很难达成共识,因为双方完全在不同的层次上论证。
谁对谁错?不妨参考福柯的意见,为了解释“自我”的问题,他区分了“解放”和“自由实践”两件事。在很多人看来,解放即自由,把人从压抑他的社会环境中解放出来,他就是自由的了。
但是福柯说,这种观念是有风险的,“认为存在着一种人类的本性或基础,作为某些历史、经济以及社会过程的结果,并且它一直受到压迫机制的掩盖、疏远或约束。依据这种假定,人们所要做的,就是打破这种压迫局面,从而就会获得自我和谐,重新发现自己的本质或者重新与自己建立充分而积极的关系。”
但是并没有这样一种本性,也从来不存在“我就是这样的人”,甚至不存在“是人就一定会需要这个”。
在压迫之下,无法界定女性的选择是否完全是自由的,但即使解放了,每个人仍然需要运用自由,来探索自己的意愿,也许她会发现,自己才是真心想穿高跟鞋、化妆、当全职主妇。
认为她们不会有这样的愿望,和从前认为她们只有这样的愿望一样,是我们过于根深蒂固的本质主义。
再比如很常见的“人是理性的动物”“虎毒不食子”,它暗示了这样一种观念——我们可以找到人之为人的那个单一“本质”,和人作为种群成员的固有特征,好像所有存在过的人类,都有同一个本质,那就是都天生适合当家长。
这种想法,在人性越来越复杂和多样的现代社会,无疑已经不再合适。
回想一下,当下的这许多话语,让我们无意识地对于世界和人怀着怎样的一种印象?是不是认为人不过是受自然或历史法则支配的动物,淹没在生产和消费的集体生活中,每个个体可有可无?
这种以“我们”代替“我”,以普遍性代替个别性的心理,早已深入生活日常。
反过来看,这也是“做自己”最革命的一面:如果每个人都去“做自己”,世界就有了许许多多的人,而不只是一种人的复制。
这像是一种魔法,让被合并同类项后的“十颗水果”,还原成了三串杨梅、五片西瓜、两只椰子。在这个更多风味的世界里,大豆田妈妈或许可以重新理解,什么是真实的自己。
四、把自我作为道德
关于“做自己”的所有困惑,都无可避免地指向一点:“做自己”和满足他人,以及适应社会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既然如此,“做自己”是不是自溺自私的不道德行为?
答案是恰恰相反。
晚年的一次采访中,福柯被问到了这个问题:当自我关注与关注他人相分离时,它是不是有变成绝对之物的危险?自我关注的这种“绝对化”,难道不会成为向他人行使权力(从控制他人的层面而言)的方式吗?
他的回答是:“不会,只有当人们不关注自我,并且成为自己欲望的奴隶之后,控制他人和向他人行使专横权力的危险才会出现……那个观念很晚才出现,即当自爱变得可疑,并且最终被认为是各种道德过错的来源之一时,它才会出现。”
自爱何时变成了一件道德上可疑的事?关注他人和自我奉献,为什么就成了比关注自我更好的品质?
说到底,为什么“做自己”会在这个时代成为一种流行话语?正是人们的自我觉醒了,发觉在主流话语和现实标准中的“好”不仅越来越难以完成,而且本身并没有十足的说服力。
我们为什么要做那些事?为什么我的人生是另一项事业的手段,而不是自己的目的?
不去考虑这些事情的人反而是不道德的,这听起来有点违背常理,但其实很简单。一个人完全按照“现实”的逻辑去行动,无疑最容易获得现实的好处。假如只想要这种好处,人们根本不需要做自己,只需要去理解现实,依据现实改变自己的想法和行为就可以。
这样的人听起来很罕见吗?绝非如此,回想一下大名鼎鼎的“平庸之恶”这个概念。
阿伦特旁听了对纳粹战犯艾希曼的审判,她试图说明,一个普通人是如何犯下巨大的罪行,并且完全不感到自己有罪。在这样的背景下,阿伦特认为,一个没有自我的人,一个不考虑如何与自我相处的人,反而什么都可能做得出来。
艾希曼的恶行是罕见的,但若是换一个时代,他不过就是一个擅长接受现实、服从指挥的“普通人”。
而和艾希曼相反,“做自己”的人,需要在现实之外,另外建立一套内心标准。
毫无疑问,有了两套标准,就会出现不一致的时候。不一致有时候是痛苦的,在一些极端的情形下,你甚至能听到自己的灵魂与现实格格不入,被搅动被磨损的声音。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聪明点,放弃“无用”的内心标准?
因为我们是人,而非机器。多出来的这套标准,增添了心灵和世界的深度,也是正义的真正保障。面对现实中失意痛苦的人,人心中的那套标准可以告诉ta,这不是你的错。
五、尾声
对于一个人应该如何度过一生,历史上有过数种答案。在宗教时代,人要做神的子民,该做什么自有教义裁决;在启蒙时代,人应该听从于理性的要求,做进步者。
所有这些答案,都有着明确的好坏标准,当人彷徨迷惑时,像奥古斯丁说的那样,“他不能做他意愿的善”时,总有一个外部的力量来引导或者裁决他。
而“做自己”,是这几个答案都陆续破裂,失去了可信度之后,被提出来的新答案。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具备公共的标准,因而在过程中,会明显地感觉到“我与别人”以及“我与自己”之间的拉扯。但参差多态乃幸福本源,这一份拉扯感,正是我们为彼此的自由与幸福作出的努力。
做自己是一项浩大的重新制定标准的运动,运动或许成功,或许失败,但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没有定论的未来。
对于参与其中的人,召唤我们的并非未来的胜利,而是每一个塑造自己的瞬间,是过程中无数的选择、遭遇、新的渴求、欣喜、伤痛,这些点亮生命的时刻超越了任何一种结局,让人最终可以坦然地说:我曾活过啊。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作者:陆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