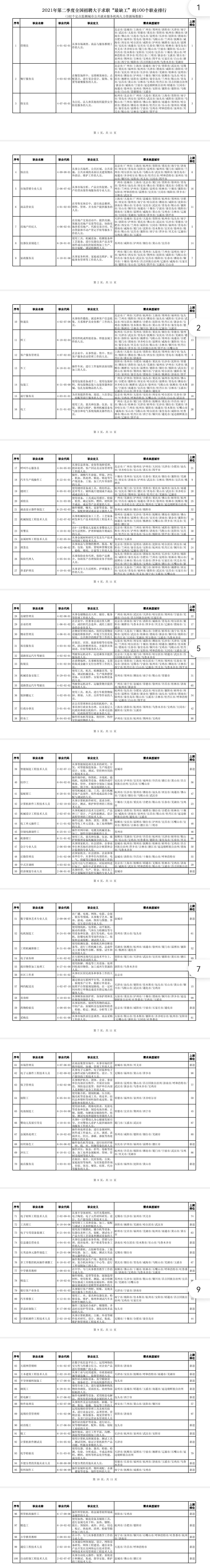原标题:15年前,她成为第一位自费前往国际空间站的女性旅客
2006年8月22日,一通来自太空探险(Space Anventrues)公司的电话拨进了加加林航天员培训中心。
这座别名“星城”(Star City)的培训基地,位于莫斯科以东约20千米的密林深处。20世纪60年代始建后,不断扩大规模,形成树木掩映中被水泥墙隔绝的一座独立小城。
从这里,100多名航天员走向星空深处。它也见证第一位自费前往国际空间站的女性旅客走向太空。
接到太空探险(Space Adventrues)的电话时,这位伊朗裔美国女商人阿努什·安萨里(Anousheh Ansari)刚刚结束一天的训练,回到自己在加加林航天员培训中心的房间休息。
她参与了太空探险公司的私人太空旅行项目,作为日本商人榎本大辅的候补成员,在加加林航天员培训中心接受培训。
按照原定计划,安萨里将于2007年进入太空。
但电话那头的工作人员告知安萨里,她已成为执行9月份的联盟号TMA-9任务的正式船员,将随联盟号-FG飞船一同飞往国际空间站(ISS)。
“我不敢相信,以为他们在开玩笑。”安萨里后来这样对记者回忆自己的反应。当她确认电话所说的内容属实,安萨里完全被震惊和兴奋感击中了:“如果不是因为周围有人感到尴尬,我会尖叫起来。”
她提前拿到了童年梦想的通行证。
 伊朗裔美国女商人阿努什·安萨里,第一位自费前往国际空间站的女性旅客。
伊朗裔美国女商人阿努什·安萨里,第一位自费前往国际空间站的女性旅客。太空少女
安萨里的童年在德黑兰度过。
在沙漠绿洲中的那些夜晚,幼年的安萨里躺在外阳台的床铺上,眼睛盯着德黑兰夜空中闪烁的星星,想象太空中可能存在的另一位女孩。
“那时候空气还没有那么脏,夜空中可以看到很多星星。”她在自己的博客上以第三人称视角回顾那段岁月,“……她躺在床上,深深地看着宇宙神秘的黑暗,心想,外面有什么?有没有人也在她的床上醒着,在夜空中凝视着她?她会找到她……看到她……她会飞出去,漂浮在美妙无边的自由空间中吗?”
安萨里一步步走向肯定答案。1979年,伊朗爆发革命,16岁的安萨里随父母在1984年移民美国。在这里,安萨里在乔治·梅森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分别攻读了电气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的学士和硕士学位,并遇见了她的丈夫哈米德·安萨里(Hamid Ansari)。两人一同创办了电讯科技公司(Telecom Technologies Inc.),公司的科技专利为他们赢得了巨额财富。
她从未忘记太空梦想。2001年,电讯科技公司被圣思网络(Sonus Networks)以1080 万股股票换股交易方式收购。安萨里成为圣思的副总裁兼新智能 IP 部门总经理。她借此回到喜爱的太空领域继续探索,去澳大利亚斯威本科技大学攻读天文学学位,期间,她遇见了彼得·迪亚曼迪斯(Peter Diamandis)。
安萨里少女时代的夏夜绮思,在这次会面商谈中变为可实现的蓝图。迪亚曼迪斯是XPrize基金会的创始人,他告诉安萨里,他打算启动第一次商业太空旅行,安萨里决定参与这个计划。2006年,她在基金会的协助下,通过太空探险公司与俄罗斯太空项目的人员交接,进入加加林航天员培训中心接受培训。
 安萨里在太空飞船内
安萨里在太空飞船内通往拜科努尔之路
“我的丈夫有时会开玩笑说:‘你知道,我认为你不是来自这个星球。你可能来自另一个星球,你只是想回家。’”安萨里曾笑着告诉采访她的记者。
为了这次“回家”,安萨里在“星城”里接受了长时间的训练准备。每天的训练时间从早上8点开始,到晚上 7 点结束。训练内容包括了解仪器、飞船、国际空间站的相关知识,也包括生存训练、零重力训练和离心力飞行等身体适应训练。
安萨里对生存训练尤其印象深刻:“我们必须自己穿好装备,进入太空舱,他们会将舱体扔进水中,模拟紧急着陆。”安萨里和其他宇航员乘坐一艘载有太空舱的小船前往黑海,俄罗斯联盟号的太空舱没有水中迫降的特殊设计,因此舱体会在一定时间后沉入水中。安萨里和宇航员不得不脱掉装备,穿上救生衣,在太空舱沉没之前离开。“这非常困难,”她说,“我一生中从未做过这种事。”
训练将她送往哈萨克斯坦的拜科努尔火箭发射基地。2006年9月2日,安萨里同远征14号机组的两位宇航员迈克尔·E·洛佩斯-阿莱格里亚(Michael E. Lopez-Alegria)和米哈伊尔·秋林(Mikhail Tyurin)被一同转移至哈萨克斯坦的拜科努尔发射中心隔离,为国际空间站之旅做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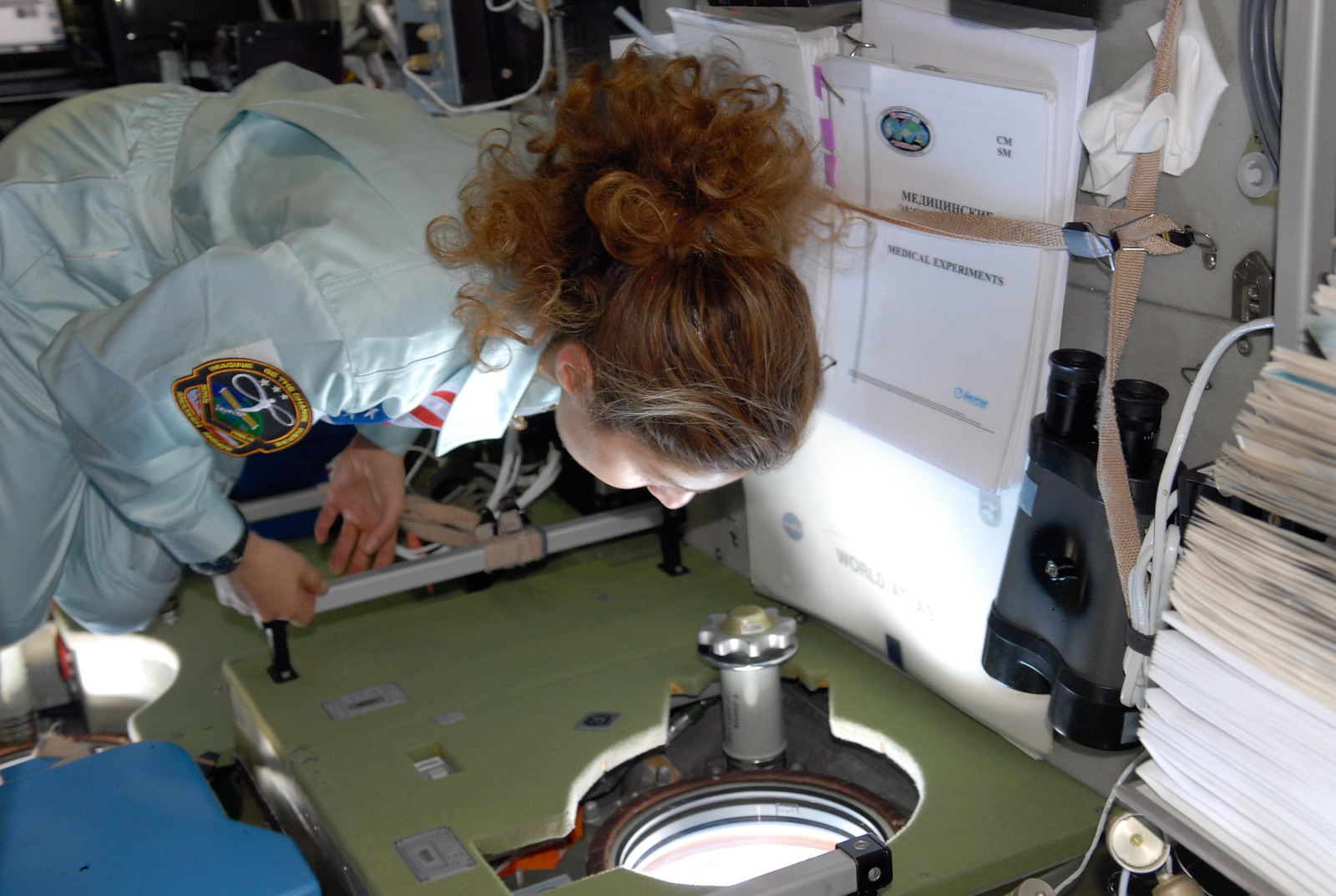 安萨里在太空飞船内
安萨里在太空飞船内9月17日,宇宙飞船起飞的前夜,安萨里向全球的网友们公布她的情况:“这一天终于到来……离我(去)的航班还有几个小时,我还是很难相信我在这里,还是一脸懵。”
这是拜科努尔时间晚上7点。再过6个小时,工作人员将带她前往火箭发射台,45年前,太空第一人尤里·加加林 (Yuri Gagarin)从这里乘火箭进入太空。这里也是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女性瓦伦蒂娜·捷列什科娃 (Valentina Tereshkova) 的宇宙飞船于1963年发射升空的地方。
安萨里为期11天的太空之旅,从拜科努尔的火箭发射台开始。她将在国际空间站停留9天。
离开地球前的最后一天,她从博客写作中休息下来,与留在地球的家人们告别:“他们都在这里……当我们在玻璃墙后面看到彼此时,眼泪就开始滚落下来。”这是个忐忑的时刻,当安萨里看到丈夫哈米德的眼睛,她感受到了他的“爱意、钦佩,夹杂着焦虑。”几个小时后,她将离开她生活了40年的星球,远离她的家人。在接下来的几天,她和他们之间的距离将达到最大。
9月18日,在40岁生日后的第4天,安萨里启程“回家”。
旅途
在发射台上,安萨里吃了一颗晕车药。
联盟号抵达空间站的行程需要48个小时。在它进入轨道、追逐空间站时,它将一直绕轴旋转,仿佛“世界一直围绕着我们旋转”。米什建议她将睡袋挂在居住隔间的天花板上,把头放在舱口中央,这样,她们会靠近质心,不会感觉到旋转效果。
这让安萨里想到蝙蝠倒挂于洞穴:“好吧,我们在我们的小洞穴里,漂浮在地球上,前往国际空间站。”
但当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她却发现自己困在这个洞穴中。“我非常兴奋,迅速从包里溜出来,飞到下降模块,然后翻转过来,直接飞回居住舱。我一停下来就意识到我所做的不是一个好主意!我感觉内脏在我的肚子里跳着恰恰……我停下来,尽量减少我的动作。从那时起,我基本上变成了木乃伊。”
即使很小的慢动作也让安萨里感到非常恶心,太空症状困扰着她。失重带来了两方面影响:脊椎因为失重而伸展,让安萨里感到腰痛,而血液失去重力的帮助,也很难流到下肢,聚积在头部。
“感觉就像长时间做倒立,”安萨里在博客里向地球上的网友们介绍,“您的脸会变得浮肿和发红,而且头痛。”
安萨里不得不求助于飞行外科医生的晕车注射液,她在睡袋中度过了这两天。“我对自己真的很失望……在这里我以为我总是应该在太空中,现在我终于到了,我病得连窗外都看不到......”她回顾当时的心情,“我一直告诉自己,‘停止这种废话,你比这强,这(些想法)只存在于你脑子里,你可以阻止它……’”
在船体对接时,安萨里完全清醒过来,看着联盟号越来越靠近空间站。她是如此兴奋,以至于“联盟号每靠近太空舱一英寸,我就感觉自己的状况更好一分。”她这样写道,“时间过得真的很慢,但终于到了他们准备打开舱门的时刻。”
 安萨里说太空的味道“闻起来像烧焦的杏仁饼干。”
安萨里说太空的味道“闻起来像烧焦的杏仁饼干。”当他们拉开联盟号一侧的舱门时,安萨里闻到了太空的味道。
“闻起来像烧焦的杏仁饼干。”她说。
“回家”
国际空间站里,宇航员们已经为对接做好了准备,他们从另一边打开舱门,拥抱联盟号的成员,欢迎他们到国际空间站。安萨里到达了目的地,她终于“回家”了。她将在这里停留9天,用于参与实验和博客写作,向地球上的网民们报告她的空间站生活。
安萨里与宇航员们相处愉快,甚至学会了俄语。在她的记录中,空间站有大约 1500 平方英尺(“大约相当于一个普通三居室房子的大小”),里面装满了成吨的设备:“我们六个人无处可去,但我们仍然相处得很愉快……”
但她要学习的不只是语言。太空的生活有许多需要适应的地方。在失重的环境中,物品需要魔术贴才能固定下来。“你只需要记住,如果你放下一件东西,它不会停留在同一个地方”。在安萨里的记述中,空间站里有着一袋袋不同形状和颜色的魔术贴条,用在各种东西上。
同样在空间中漂浮的还有宇航员。安萨里必须练习在失重的空间行走浮动。“我是个菜鸟,”她写道,“我飞来飞去,撞到墙和东西上。最初几天,我会用力推墙,结果因为飞得太快无法停下来,“砰”地撞到另一面墙,然后弹回到我开始的地方……”但很快,她的‘飞行’技术受到了宇航员称赞。
在这里,一天大约从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凌晨4:00 开始,到晚上7:30熄灯结束。白天,宇航员们需要进行自己的实验任务。安萨里也会参加其中的几项。她参与了四项实验研究,其中包括研究贫血背后的机制、肌肉的变化如何影响腰痛、空间辐射对国际空间站机组人员和在空间站上安家的不同种类微生物造成的影响。
“每个人都忙于执行由莫斯科和休斯顿的任务控制中心分配给每个机组人员的特定任务。”安萨里说,“时间表将根据需要上传到站点,并附有具体的活动说明。”
但在晚上,宇航员们可以放松一下,聊天,给家人打个私人电话,或者只是静静欣赏窗外的美景。


安萨里在博客中记录最多的还是她看到的地球,她详细记录了她眺望窗外时看到的地球模样。在太空站不同的窗口视角中,安萨里最喜欢的是她睡觉的小船舱与对接舱的侧窗。“你可以看到地球在宇宙黑暗背景下的完整曲率。”她写道,她总是喜欢先看看“整体”而不是“部分”。
任何边界都已经消亡,“您无法分辨一个国家的终点和另一个国家的起点”,唯一清晰可见的边界是海洋和陆地的边界。在白天,海洋的蓝色随着深度和太阳表面反射的方式变幻出数百种蓝色色调,大部分没有植被的陆地也清晰可见。地球的大部分地区通常被白云覆盖,这一开始让安萨里感到沮丧,但她很快被云变幻莫测的形状和排列迷住了:“有时它们看起来像一张厚厚的白色蓬松毯子,有时像散落一地的小棉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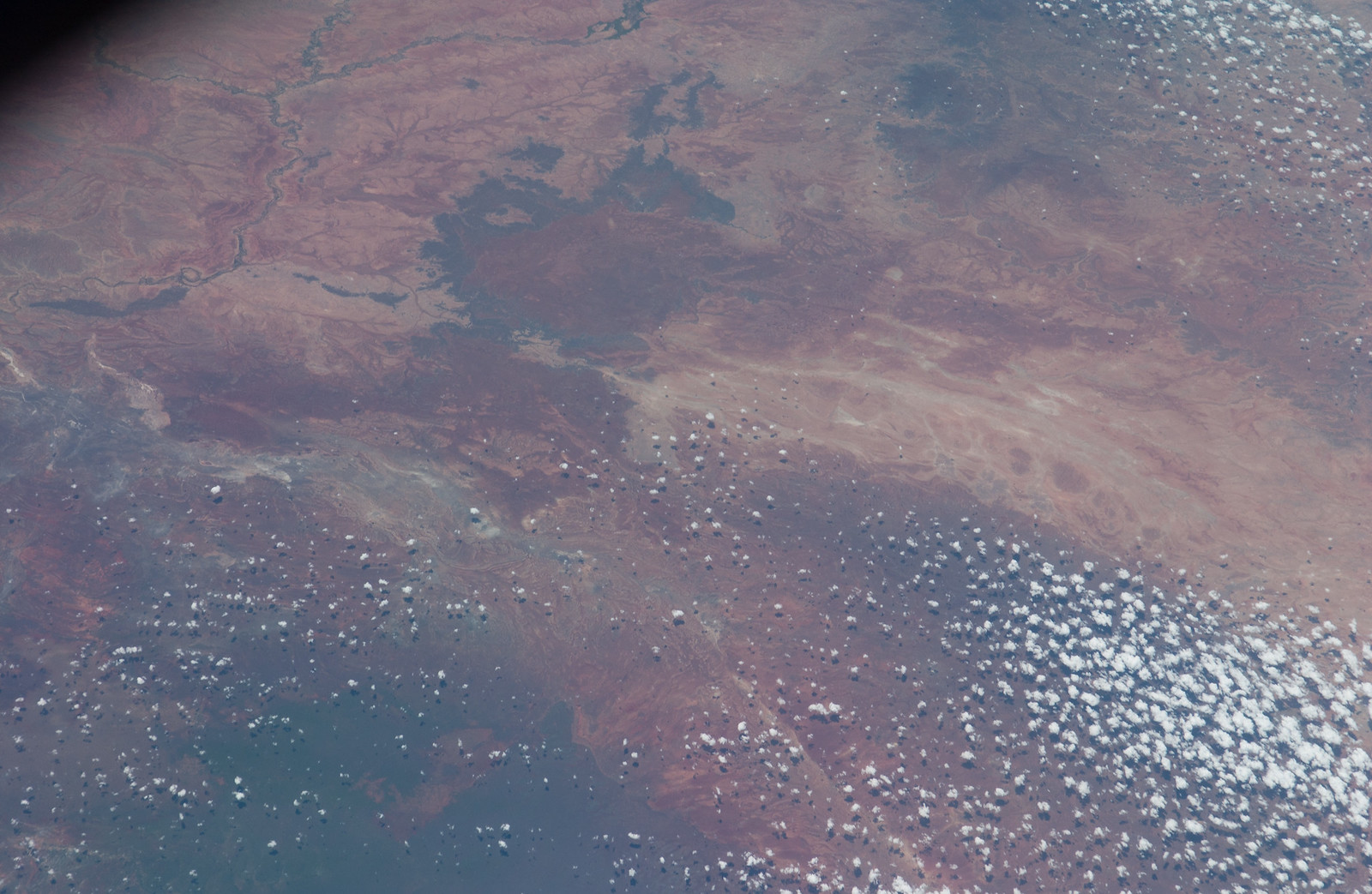

黄昏惊人而夺目。随着太阳落入地球背面,天空开始变暗,变幻出橙色与最漂亮的蓝色混合的惊人色调,然后夜幕降临。
空间站的夜晚与地球上的夜晚大相径庭。空间站每90分钟绕一个完整的轨道运行,外面很黑,但太阳在每个轨道上升起和落下,他们可以在一天中观看32次美丽的日出和日落。
大多数晚上,安萨里都能看到下面的雷暴。从空间站的角度看来,这“像一场壮观的灯光秀”,这些闪光随机出现在不同的位置,有时安萨里正在听约翰·帕赫贝尔的“佳能”,雷暴看起来有人在用音乐编排闪电。
但她最喜欢的景色是夜晚的宇宙景色。“星星简直难以置信……看起来有人在黑色天鹅绒毯子上撒了钻石粉。银河很容易看到,就像悬挂在整个地球上的彩虹……我的眼睛无法离开它。我把头靠在窗户上,一直呆在那里,直到冰冷的窗玻璃让我头疼……然后我稍微把头向后挪开一些,再继续凝视。”
在国际空间站的窗口里,“任世事更迭”(Watch the world go by)是就是它的字面意思。由于空间站的转速比地球快20倍,尽管二者朝同一个方向旋转,从空间站的角度看,地球也仿佛在慢慢地向相反的方向旋转一样。
安萨里写博客说,这是她生命中最平静的时刻。她很难睡太久,一直强迫自己睁开眼睛,只为全神贯注地凝视这种美丽的图景,哪怕只为了“再多一秒钟”。

回归地球
2006年9月29日UTC时间 01:13 ,联盟号TMA-8在哈萨克斯坦草原(阿尔卡雷克以北 90 公里)安全着陆。安萨里与远征13号机组成员,美国宇航员杰弗里威·廉姆斯和俄罗斯宇航员帕维尔·维诺格拉多夫一同返回。一位身份不明的官员递给了她红玫瑰,她的丈夫哈米德给了她一个吻。救援人员乘直升机将他们转移到科斯塔奈(Kustanai)参加欢迎仪式。
安萨里生命中这一章的结尾以沉重而虚弱的体感告终。失重环境会对人体机能产生影响,肌肉缺乏重力锻炼,以至于在突然面对地球上的重力拉扯时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安萨里很高兴能回来见到她的家人,但重力环境让她感到沉重。
她感到自己的心留在了空间站上:“我一直试图再次闭上眼睛,假装我回到了那里,那里是安全的,那里是自由的……”
安萨里的太空旅程全程以日记的方式发布在她的博客网站上,她本人也以第一位自费前往国际空间站的女性和伊朗人的形象被公众记住。
不同于前三位太空旅行的男性富豪,安萨里将商业私人探索太空视作一项事业发展:“不仅是为了让我的梦想成真,而且让数百万人的梦想成真。”在起飞前,她决定投资XPrize基金会,设立一个奖项来鼓励新生的太空探索产业。这个奖项后来被命名为“安萨里X大奖”,用以奖励第一个能用自制的飞行器将3名乘客送到100公里外的太空,安全将其接返地球,并能够在两周内使用同一架飞行器重复上述载人飞行的公司或组织。
 与亚特兰大航天飞机擦身而过
与亚特兰大航天飞机擦身而过安萨里在博客里坦言,她不喜欢被理想化为“偶像”,但她确实希望成为一个榜样。在接受Space.com的采访时,她曾说自己太空旅行的意义是“希望激励每个人——尤其是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女性和年轻女孩,以及没有为女性提供与男性相同机会的中东国家——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去追求梦想。”
“有时这对他们来说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我相信,如果他们把梦想牢记在心,培育它,寻找机会,抓住这些机会,他们就能实现他们的梦想。回顾我的生活,我希望我能给他们一个正面的例子,展示这是如何发生的。”
她认为太空旅行能加深对地球上人们彼此之间连结意义的理解:“从太空上看地球,你看不到任何边界、不同种族之间的差异或任何类似的东西,你看到的只是一个星球”,而这个家园如此珍贵,“你看着地球上的避风港,然后转过身来,看着宇宙的黑暗,发现你周围没有很多宜居的行星或卫星。你会觉得你需要珍惜这份珍贵的礼物”。

离开太空家园返回地球的时间里,安萨里从没有忘记这趟旅行。如今,在她的空闲时间里,她总是通过“X- Prize”基金会四处活动,推进她的太空教育活动。
15年过去了,一次葡萄牙的媒体记者在全球探险家首脑峰会上见到了这位54岁的女性工程师,她看起来仍然精神饱满。
记者询问安萨里,是否想要再一次踏上太空之旅?安萨里的回答和十五年前返回地球时给记者的回复一样:如果有机会返回太空,她会在“一眨眼”间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