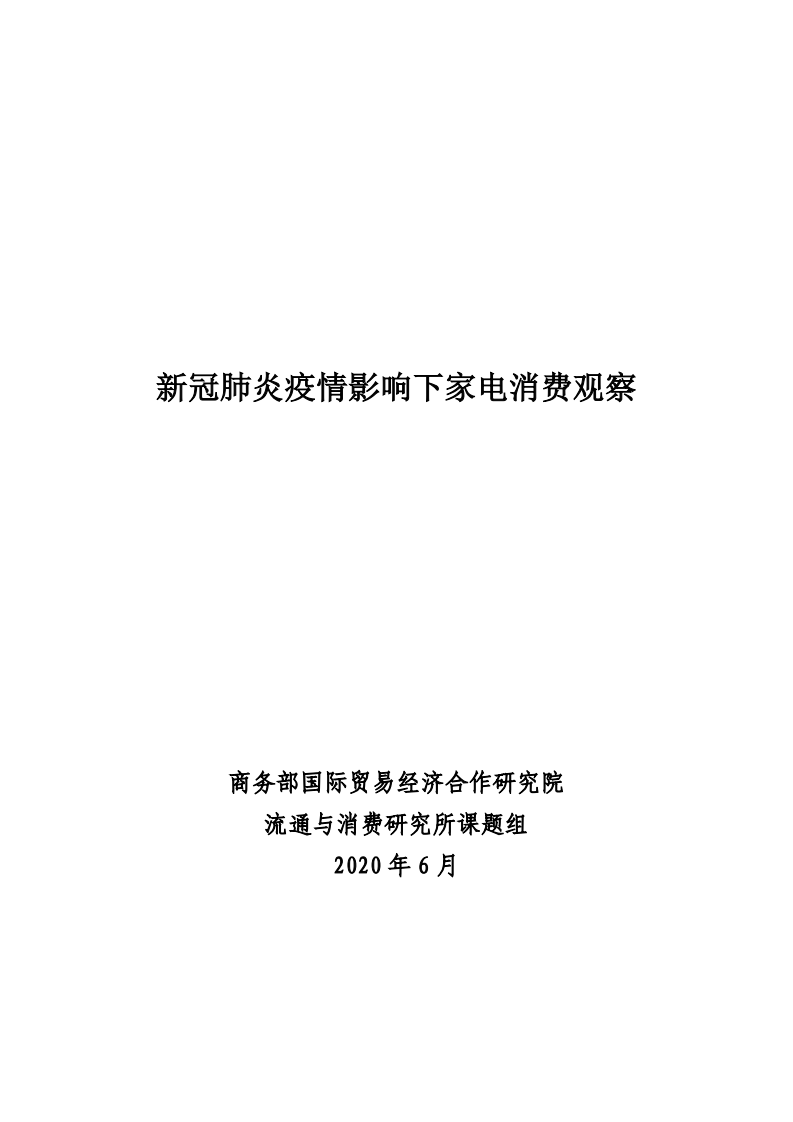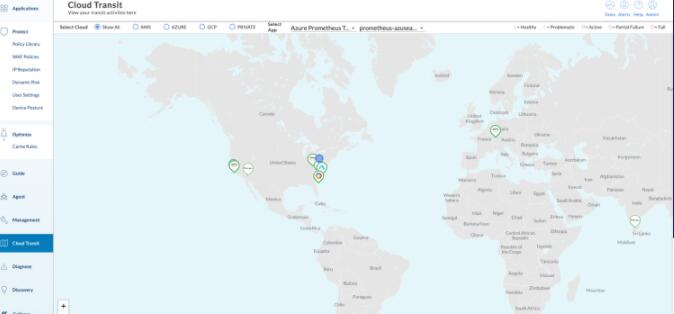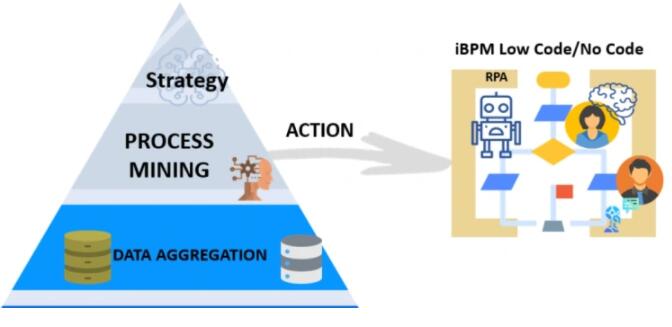原标题:回归乡村能拯救单调的城市生活吗?从法国“重返大地”运动谈起

19世纪英国作家哈代的笔下,乡村少年裘德爬上路旁的谷仓久久眺望不远处的基督寺镇,直至小镇最高建筑的塔尖一点点消失在暮色之中。彼时,城市不断向外延展,工业化为其提供扩张动力,进化论调为其提供精神支持,无数裘德这样的年轻人或积极拥抱或被迫卷入到了城市生活。
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认为,“人们对居住形式倾注了强烈的情感,并将这些情感概括化……将乡村和城市作为两种基本的生活方式,并加以对立起来的观念,其源头可追溯至古典时期。”因此,当城市被赋予一个价值,乡村却总是被贴上一个相反的标签:城市是现代的、便捷的、开放的,乡村就是落后的、不便的、保守的;而当城市的弊病日益凸显,乡村便新增了某些乌托邦与古典田园式的想象。
在这种思维下,厌倦了城市生活的人们自然而然地会选择回到乡村,并且这种想法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股思潮。日前,“中法环境月”以“重返大地——逆城市化潮流在法国与中国”为主题,邀请了策展人欧宁、历史地理学者丁雁南、“大地艺术节”中国项目策划人孙倩和法国历史学家凯瑟琳·乎维耶在沪展开对谈。对谈回顾了法国过去50年间“重返乡村”运动的历史,也描绘了新近十年出现在中国的中产阶级返回乡村的现象。二者关照,不仅能为我们提供一个窥见当代社会的切口,更重要的是提供一种当代生活方式的构想和图景。
 “重返大地——逆城市化潮流在法国与中国”活动现场(主办方供图)
“重返大地——逆城市化潮流在法国与中国”活动现场(主办方供图)从反叛主流文化到反全球化:法国重返乡村50年
乎维耶在回到阿尔代什省的祖父母家度假过程中遇到了她后续研究中被称作“新农村人”的群体:他们大多受过高等教育,在城市有着优渥的工作和居住环境,却要离开城市回到乡村过田园生活。在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这种现象源于一场人群由城市向乡村的迁移活动,它起源于美国,传播到欧洲,并影响了世界,被称为“重返大地运动”(Back-to-the-land movement)。
法国的“重返大地”运动迄今已有50余年的历史,在不同时期社会背景的影响下呈现出不同的思想逻辑和发展形态。在历史上,法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因此城市化也是距今不远时期发生的事情,许多涌入城市的年轻人也如乎维耶本人一样其父辈或者祖父辈仍旧是农民,在其成长的过程中仍与乡村有紧密的联系。最先开始离开城市回到乡村的人抗拒城市文化,他们希望回到自然,在踱步和冥想中寻找自身意义。这些先驱虽然往往是个案和象征性的,但很快受到了关注。
1960年代末,一些由嬉皮士和边缘人组成的群体出现在乡村,他们希望通过自给自足的方式生活,这群人也成为首批重返乡村的实践者。除去对工业文化所塑造的单调城市生活的拒绝,他们还受到了反对核武器和环保主义这些在60年代盛行的思潮的影响,另外还有些人则是出于对60年代青年运动的失望。尽管在最初的一段时间他们与当地人有诸多矛盾,不过在融入后他们还是深刻地改变了乡村。最为显著的是,在他们的鼓励下,离乡前往城市求学工作的部分年轻人重新定居在乡村,也形成了1975年之后十年的第二波返乡浪潮。
 法国普罗旺斯的乡村(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法国普罗旺斯的乡村(图片来源:视觉中国)第二波返回乡村的人身处法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期,却因希望过一种与自然更亲近的生活而重返乡村,社会学家将其称为“乌托邦的移位”,这种移位也承载着新的生活意义。这一时期,法国出现了第一位参与总统选举的环保主义者勒内·杜蒙(René Dumont),政治性的环保主义也是当时返回乡村浪潮的影响因素之一。
随着乡村生活环境的改善,1985年后乡村迎来了一批与之前动机大不相同的新居民——他们认可城市的生活方式,在返回乡村后仍然从事城市的工作;他们渴望改善生活环境,却对乡村文化缺乏意识形态上的亲近感。在他们之后,1995年-2005年间,乡村又迎来了新的定居者,这群人是城市中的弱势群体,回到乡村是出于降低生活成本的目的。前两波已经在乡村定居并融入的新农村人积极为他们提供帮助,通过协会等形式教会他们农业生产或是手工艺技能。
2005年至今,被乎维耶称为“第五波浪潮”的群体特点则更加复杂化。一方面他们有更加明显的政治倾向,身携极端的环保主义者和反全球化者的标签,他们回到乡村居住在简陋的居所中,希望能够进行自给自足的生活;另一方面,他们是“认知无产者”,他们接受了高等教育,自诩为“新农民”,希望创造并实践一种新的价值观。
回顾法国“重返大地”运动50年的历史,有两个特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返回乡村动机的复杂,一部分人想要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而返回乡村,比如第三波浪潮中对居住环境挑剔的城市居民或第四波浪潮中希望降低生活成本而返回乡村的城市弱势群体;另一部分人返回乡村则是出于对生活方式的追求和实践,这部分人往往有更多想法,比如第一波浪潮中反叛主流文化的环保主义者、反殖民主义者、反全球化者以及2005年之后出现的“认知无产者”,他们将乡村生活方式看作对自身价值观的探索和实践。无论出于何种动机,我们总能看见社会变迁在这之中的深刻影响。
二是不同群体间关系的复杂性。不同时期的“新农村人”之间、新农村人与当地人之间都有着复杂的关系,前两批首先融入的新农村人建立协会帮助之后返回乡村的人,通过政治参与到当地的建设;第三批回到乡村改善生活的富裕城市居民不可避免地推动了乡村建设,不同思想的青年群体也在自身实践中影响着乡村文化。
中国当代的“重返大地”与“归隐山林”传统有所不同
欧宁将视线拉回到中国,他认为中国“重返大地”的潮流发生在最近十年,一些城市中产开始有了一种离开城市回到农村的倾向。他表示要区分“重返大地”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回归山水或回归土地的士绅实践,二者联系其实是非常弱的。首先,“重返大地”中的环保思想是一种类似于佛教“众生平等”的观念,而非儒家所描绘的从属关系。“众生平等”是一种非人类中心的生物生态主义,包含了生物多样性等现代思想。再者,在中国文化的传统语境中,土地是满足人类欲望的工具,人们从事农耕、在土地上定居、收获粮食和向中央政府交税都仰赖土地。同时,土地代表着儒家构建的社会系统,古代任官退休后告老还乡是回到出生成长的土地上,也是回到在土地上所形成的伦理结构中。因此,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出现类似“重返大地”的活动。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欧宁认为,城市对于中国也是一个新生事物,传统中国并没有城市概念,直至民国时期才出现现代意义的城市。欧宁将中国的城市化分为五个阶段:在建国伊始,国家迫切想要工业化,依赖于用农业产品去换取前苏联的资源,这一时期城市化发展得十分缓慢。1964年中苏关系恶化后,大量军工企业内迁,西南内陆涌现出许多城市,该时期被称为“三线建设”,即由军事推动城市化进程。1980年代,特区开发使中国城市化的速度大大加快。1990年代“南巡讲话”后,南方涌现了许多房地产企业进一步推动了城市化建设。新世纪开始十年的几个大型活动(比如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让北京和上海成为超大城市。2010年至今,高铁和高速路网的建设提高了偏僻地区的能见度,让许多中产阶级有了前往乡村度假的条件,为中国版本的“重返大地”打下基础。
在欧宁看来,中国新近发生的“重返大地”运动与国外有非常大的不同,国外“重返大地”运动的发生往往是由于社会危机的出现,人们自发地去寻找城市生活的替代方案,其背后有环保、平等等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中国城市中产则是由于想获得更宜居的环境,同时路网的建设和互联网的普及让他们前往乡村生活成为可能。丁雁南借一封近3000年前来自巴比伦的信指出,既能享受城市便利又能远离世俗喧嚣的居所是从古到今的人都梦寐以求的,因此不难理解逆城市化的发生。他认为当这种现象出现时不要先入为主地进行道德判断——无论是消费主义抑或是精英主义——这些价值判断无助于进一步理解这个复杂的现象。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孙倩则从自己策划“大地艺术节”中国项目的经验出发讲述了她对“重返大地”的观察和感受。本来默默无闻并无特点的寒溪村因“大地艺术节”获得了极大的曝光,吸引了广泛的社会关注。艺术节本身也反向促进了乡村建设,完善了村庄治理,引进外来资源,构建起了乡村产业和文化品牌。孙倩说,她在艺术节的策划工作中始终坚持三点,一是坚持当地村民为主角,尊重当地文化,通过艺术节放大本地价值,而非引进外来文化;再者力求简单叙事,学术性的表达会加剧城乡对立,拒绝“空降的俯视的填塞式的艺术内容”;以及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方向。孙倩认为,艺术进入乡村不仅仅是艺术圈的事情,也是一种社会活动,一种“重返大地”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