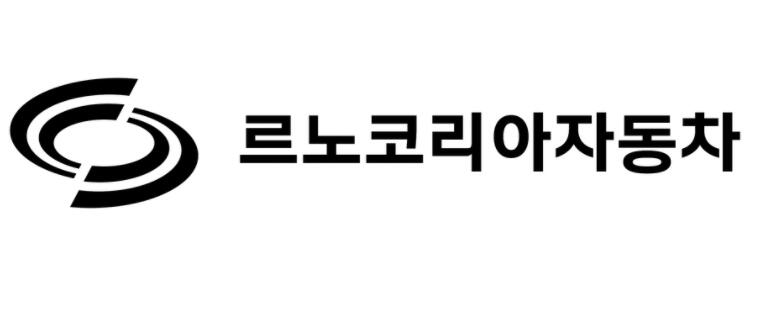3月13日,在英超第28轮一场关键比赛里,曼联主场3比2战胜热刺。这场比赛中已经37岁的C罗完成帽子戏法,表现神勇无比。
赛后在夸赞C罗的诸多评论里,我们注意到这么一条:C罗早在2020年10月就感染了新冠。那是最早也是最强力的一批病毒,并且当时还没有疫苗。但如今在C罗身上好像完全看不到新冠后遗症的影响。
当然有人会说,运动员的体质和普通人怎么能相提并论?用他们举例属于以偏概全。那么问题来了,当我们在讨论新冠后遗症有多可怕的时候,是不是也会用另一方面的极端例子来以偏概全呢?
最近,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在国内肆虐,多地出现了大量新冠患者以及无症状感染者。在讨论疫情的视频和文章下面,评论留言中讨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后遗症。因为这一轮病毒呈现出致病性弱、感染力强的特点,所以大家对他的恐惧更多集中在感染后长期带来的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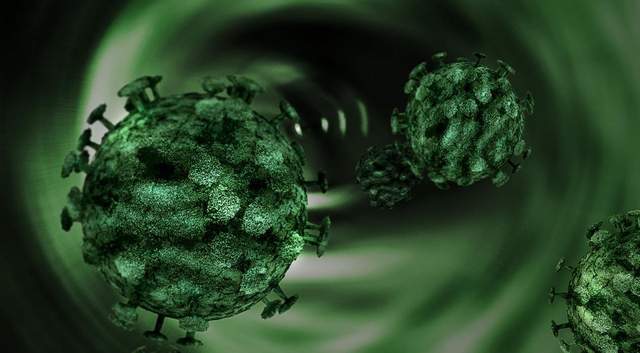
然而随便网上一搜就会知道,媒体上的新冠后遗症非常恐怖。其中既包括大家能够预想到的呼吸系统疾病后遗症,也包括一些听上去很吓人的“意外后果”。这些信息反复发酵,极大强化了人们对疫情的恐惧心理。
但这些关于后遗症的信息,真的那么准确无误吗?
提前说明,本文并不希望对疫情防控提出任何建议,只是希望大家更加理性看待疫情。我们绝不能轻视疫情,也不必对其进行妖魔化处理。
阴云密布:目前有哪些已知新冠后遗症?
稍微整理一下网络上大家对新冠后遗症的担忧,就会发现更多惧怕的不是那些相对普遍的呼吸疾病后遗症,而是一些似乎来自权威机构的,足够令人意外的东西。
比如说,3月7日《自然》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英国一个研究小组通过对罹患过新冠的人群进行跟踪大脑扫描,发现新冠对人脑有一定程度的影响。通过对比发现,新冠病毒可能导致大脑灰质减少和不同程度的脑组织受损。一些新冠患者会出现包括注意力、专注力、信息处理速度下降和记忆力受损等情况。
紧接着,“《自然》杂志证实新冠会导致脑萎缩”的消息在全球不胫而走。尤其是在防控程度非常高的中国,更加深了大家对新冠后遗症的抵触心理。毕竟恐惧往往来自于未知。
除了脑萎缩之外,新冠另一个可能后遗症也让人忧虑。1月13日,《纽约邮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讲述了一名30多岁的美国男子在感染新冠后出现了男性生殖器缩短,并且出现功能障碍的情况。这篇文章还表示,一项来自英国的研究表明,有5%的成年男性在感染新冠病毒后出现了男性器官缩小,还有15%的人出现了功能障碍。

比起这些新冠上下攻击的新闻,更多研究证实了新冠会出现冠状病毒感染后的大部分后遗症。比如2021年《自然医学》发表了一项研究,研究小组通过追踪康复后的新冠患者,发现在治愈新冠后2-6个月内可能出现一系列后遗症。即使是非重症患者也会有后遗症表现。
这些早期新冠后遗症中,最常见的是疲劳或肌肉无力,占到了63%;睡眠困难占到26%;23%的人有焦虑与抑郁情况;也有很多人出现胸部影像异常和肺功能损伤的情况。
整体而言,目前我们在媒体上能看到的新冠后遗症,包括嗅觉和味觉失灵、乏力、失眠、关节肌肉痛等典型症状,也有脑萎缩等“意外”情况。
这些症状的存在,让无症状与轻症比率更高,治愈效果越来越好的新冠听上去依旧恐怖。新冠后遗症可谓是“阴云密布”。
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所有这些研究基本在最后都要强调一点:目前对新冠后遗症并没有系统性、获得广泛共识的研究——而这也是媒体和网友往往会忽略的一点。
疑点是什么?
事实上,目前所有对新冠后遗症的研究,都是一些小样本、高效率的追踪观察,并不具备双盲对比和规模化分析的意义。
这并不是因为科学工作者不努力,而是新冠发展太快,留给研究的时间太少。世卫组织给出的官方后遗症定义是:持续两个月以上、无法用罹患其他疾病来解释的症状。而确定一项疾病的后遗症,一般都需要两到三年的系统化研究时间,并且这还是在疾病病毒性与临床表现相对稳定的情况下。
然而新冠的特点是发展极快,病毒飞速变异。而全球各地卫生防控水平、疫苗接种普及率也区别巨大,难以进行统一的研究和衡量。就像在疫苗研究初期,科学家无法断定疫苗的有效期限,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观察。如今也没有时间来证实新冠的不同毒株到底有什么后遗症,这些后遗症是否可逆转,是否能将长期存在,后遗症与疫苗和药物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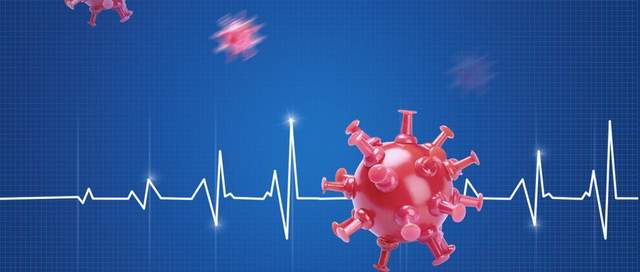
这种时候,将一些小样本、小规模的研究,甚至某位患者的自我表述作为讨论后遗症的依据,就难免陷入与“C罗能帽子戏法所以没有后遗症”类似的误区。
比如说,《自然》杂志发表的关于新冠可能造成脑萎缩的研究,其实早在2021年就预发表出来了。这说明这项研究针对的是最早一批新冠患者和最早的病毒株。由于接受观察者年龄在50-80岁,年龄普遍偏大,并且都没有接种过疫苗,所以这项研究的结果是否能在今天成为参考其实还有待商榷。
而且媒体宣传这项研究的时候也往往可以忽略参照系。这项研究表明新冠可能在一年时间里导致2%的大脑萎缩,听上去非常吓人。但这个年龄段其实即使身体健康,每年也会脑萎缩0.3%左右。而且嗜酒、外伤、慢性病、中风等疾病导致的脑萎缩率远比2%大。这样一对比,似乎就显得没那么夸张了?

另外一种关于新冠后遗症研究可能存在的疑点是回忆偏差。2021年3月,《男科学杂志》就发表了一项来自罗马第二大学的研究,团队对100名患过与未患新冠的男性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患新冠者男性功能障碍机率更大。但这项研究是通过网络问卷的方式进行的。于是就有人提出质疑,男性在患过某种疾病后,总会认为自己的某些器官比以前缩小了,并且功能有损。这是某种社会心理现象,或许不足以表明新冠的影响。
当我们根据患者自我表述来判断后遗症普遍性的时候,经常会有这个问题:这些表述中存在幸存者偏差。因为只有那些后遗症特别严重的患者会出来诉说。不严重的,早就正常生活,正常踢足球的并不会反复讲述自己得过新冠这件事,最终导致大众对后遗症的整体性性欠缺了解。
总之,新冠后遗症的系统性研究还有待深入,需要更长时间去解析。我们既不能因此轻敌,放松防护,也不必因此妖魔化这个本就难缠的对手。
警惕反安慰剂效应
1961年,美国医生沃尔特·肯尼迪发明了“反安慰剂效应”一词。随后数十年,这一效应在诸多医学实验中得到了验证。很多人都知道安慰剂效应,即给患者某种暗示,然后告知其有效,往往会真的有效。但安慰剂效应还有个邪恶双胞胎,即告知一个人某东西有害,结果导致其在恐惧与忧虑中受伤。
由于反安慰剂效应的深入研究,比如它的致死性、致病性,都突破了医学伦理。所以人类对反安慰剂的了解还远远不足。一些研究表明,反安慰剂效应可能会驱动大脑前额叶的变化,但更多人认为这是一种心理状态导致生理变化的典型案例。
上世纪70年代,美国有一个著名的肝癌误诊案。一名叫萨姆·舒曼的病人被判定了肝癌,几个月之后他就发病去世。但在解剖时却发现,他的肿瘤很小,根本没有扩散。这个人除了死亡之外,身体基本一切健康。
这种反安慰剂效应造成伤害的例子,在传染病中更为常见,被称之为“群体癔症”。这就是为什么在大规模传染病的防治中,一定要结合心理治疗与心理干预。因为传染病扩散的过程里,很多人可能只是轻症甚至并未感染,但都会因为反安慰剂效应的存在陷入疑病、焦虑、过度紧张等问题,甚至比真正的患者表现更加明显。

传染病的心理因素很难从病理因素中剔除出来,很多新冠患者报告了焦虑、抑郁的后遗症。很难说这到底是新冠后遗症,还是周遭的歧视与敌意,自身对身体的担忧,最终产生了反安慰剂效应发作。
过度渲染、夸大,甚至妖魔化新冠后遗症。尤其是斩钉截铁提出新冠后遗症会影响生育,影响智商,轻症也会有后遗症等等,其实是并无根据的论断,本质是对患过新冠人群的不公与歧视。这会扩大他们的心理障碍,使他们遭受非常不公平的对待。比如百度就有“男朋友得过新冠要分手吗”这样的推荐搜索。
这种情绪进一步蔓延,就有可能加大对密接者、可能感染者、无症状感染者的非必要排斥,甚至引发社会恐慌,继而导致对防疫政策科学性的干扰。
在全球性疫情面前,心理因素绝不是空穴来风,也绝不能有“宁可信其有,宁杀错无放过”的妖魔化思维。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反射到他人身上;我们的每一次非必要恐惧,都会在网络中被放大。
对付新冠和新冠后遗症,或许就像张文宏医生说的那样:消除恐惧是战胜它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