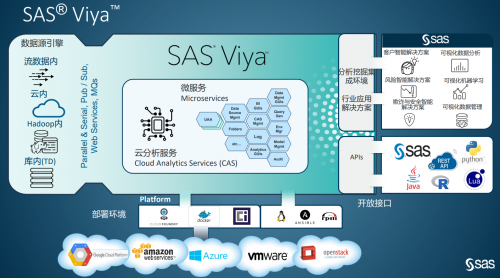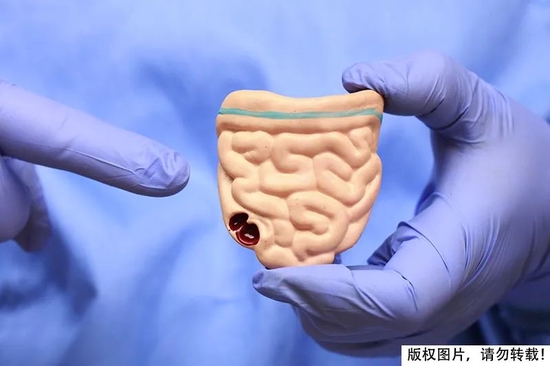■自然
李万华
早晨散步时遇见一棵树。树长在低矮山坡上,山坡中间是高速公路,绿色护栏一直向前,坡下一条普通马路,旁道树零落如散兵游勇。几个月不见雨雪,天干物燥,坡上灌木蒙一层黄色浮尘,枯草纠结成毡片,用来绿化的一排云杉依旧冬天色调,灰绿,没有生气。那棵树不大,树干直,苍老的黑,树冠蓬开来,枝上挂一些不稠密却也不稀疏的叶子。那是去年的树叶,已经干枯,蛾黄。远远看去,像开了一树蛾黄色花朵。风不大,轻轻拂过,树叶摇曳,发出似有似无的声音。一只喜鹊站在树枝上,不出声。
从远处看,那棵树更像从一幅画上剪下来,插到山崖上,它的气质风姿与环境不相符。周围有些乱,是时日错乱,春天来了尚不知的情形。有人夜晚过来,在山坡下给祖先烧纸,祭品散放在发黑的灰烬上,似乎也没乌鸦来吃。又有人将黄色和白色的哈达系在云杉树上,是苍黄里的一抹明亮。前几天,在离山坡不远的地方,我看见山桃开花,细碎的粉和寡淡的白。连翘也在开,没有叶子的黄色小花显得孤单。香荚蒾想必馥郁得能迷倒一头大象,可是大象在更远的地方。更远的地方,应该青山横亘,白云出岫,杜鹃花塞满山谷。然而眼前这山坡,却还沉浸在冬天的梦境里,仿佛醒来还需要一番大力气。
我试图走近些,以看清那是一株什么树,喜鹊不喜欢被打扰,拍一下翅膀飞去。
马路上走来一人一狗。男子戴米色宽沿帽,一件宽大的土黄色外套没系纽扣,里面毛衣绞着过时的花纹,裤子肥肥大大,双手塞满了东西:一长条透明塑料,一头捏在手里,一头拖在地面,一节木棍做成的手杖,一个大的编织袋鼓鼓囊囊。京巴狗摇动身子,慢悠悠的跟着走。流浪汉带着流浪狗,鲍勃和它的猫那样,我这样想,对那流浪汉多了一丝敬畏。然而当我走得更近,擦肩而过时,他们似乎又不是流浪汉和流浪狗了。那男子虽然衣着邋遢,颜色变旧,却是干净的,黑红的脸颊也干净,京巴狗显然没挨过饿,微胖,毛色有光泽。
一时阳光照耀,云在天空碎成鳞片,周围再无人影,路上也无车辆经过。
忽然想,如果用摄像机将此时情景拍下来,是可以剪辑到塔可夫斯基的电影里去的,像《牺牲》的开头那样。亚历山大和他的儿子在海边种一棵树,树小,没有叶子,更像一棵枯死的树。他们背后,云水苍茫,海鸥“啊-啊”地叫,不见身影。海边滩涂上,一所孤零零没有任何依傍的房子似乎已被遗弃。一条铺有碎石的小路弯弯曲曲伸向远处,路边草地上,流光滑过草茎,野草并不丰茂。亚历山大一边栽树,一边给他刚刚做完手术的孩子讲故事:
很久以前,有一个老僧侣,住在东正教的修道院里,他叫帕姆维,他在山上种了一棵像这棵树一样干瘦的小树。他对他的门徒,一个叫约翰·克洛的僧侣说:“记得给这棵树浇水,让它尽快长大。”于是,每天黎明时分,约翰就带着满满一桶水上路,他要爬上山顶才能给那棵干枯的树浇水,浇完水回去时,已是晚上。每天如此,从不间断。三年过去,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当约翰爬上山顶,他看到他的树开满了鲜花。
孩子不说话,亚历山大自言自语:不要去管别人说的那些方法啊,系统的培育啊,诸如此类的东西,要知道,有些时候,我经常想,要是每天,准确的说是同样的时候,人们做同样的事情,就像一种确定的、系统的仪式,每天都在那个时候,世界可能就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