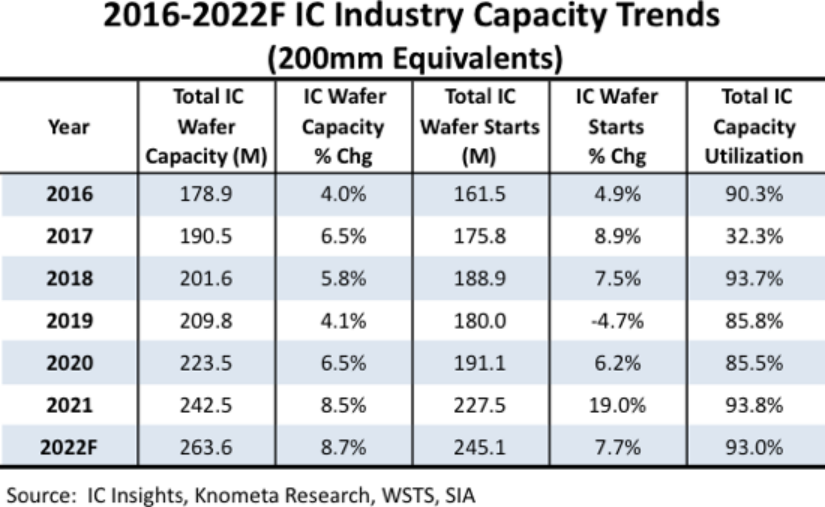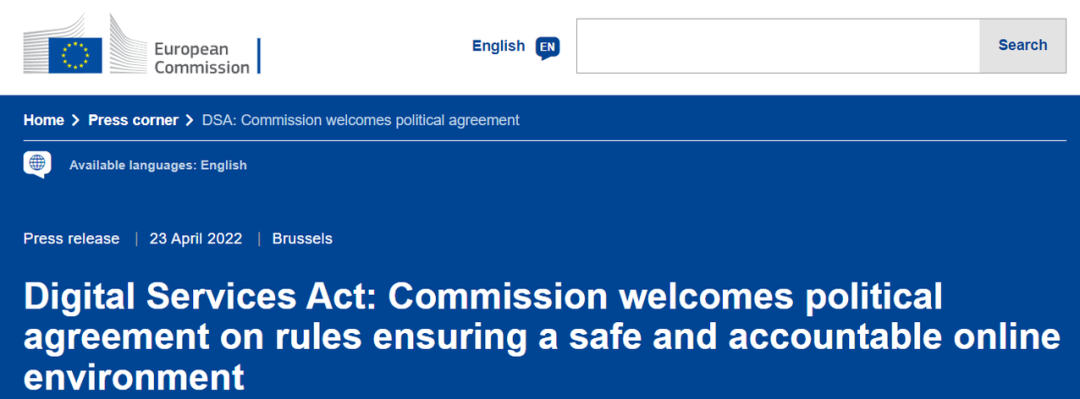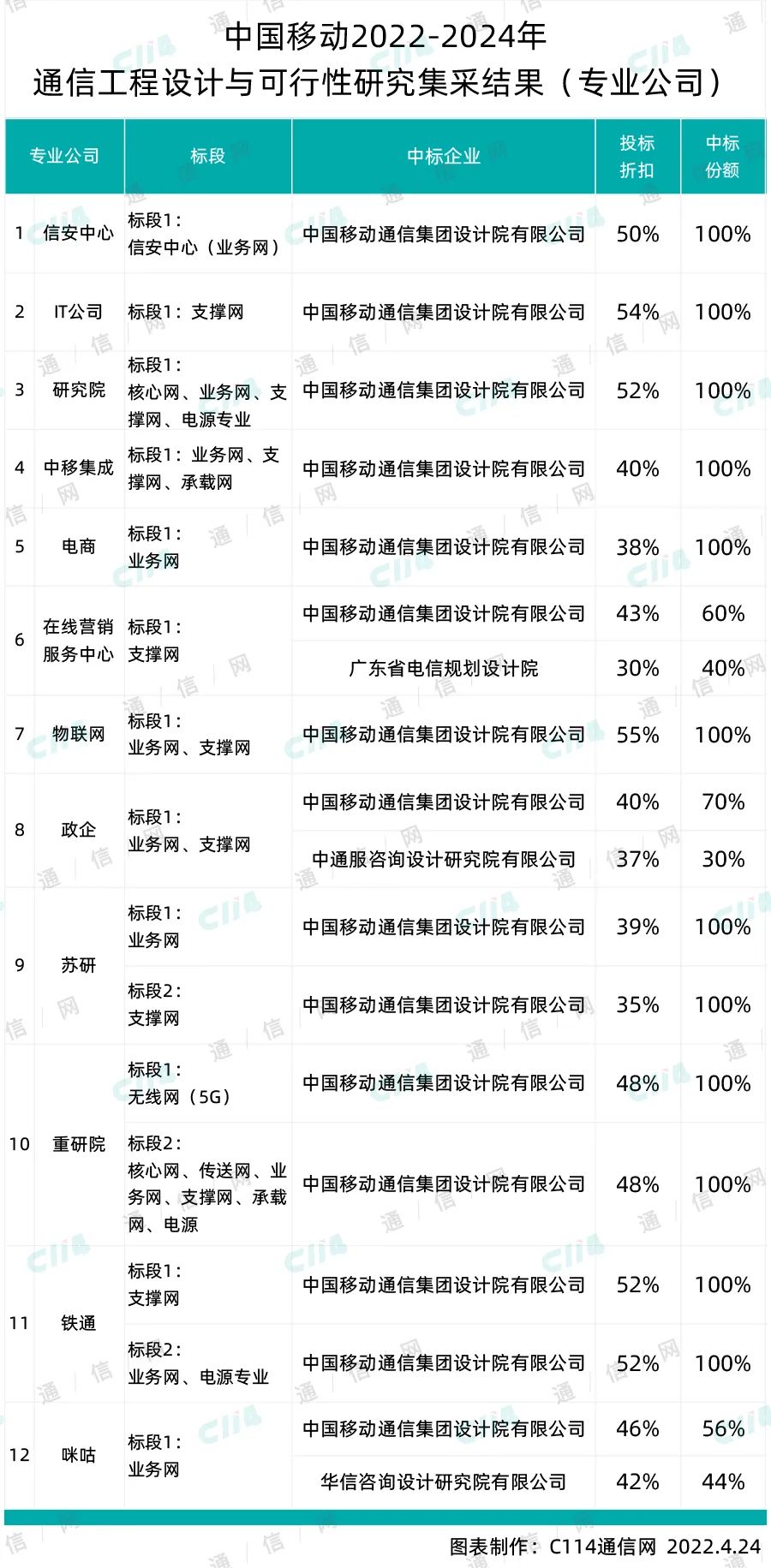蒿子粑属老家桐城的特色小吃,坊间有“不是所有的蒿子粑,都叫桐城蒿子粑!”的说法,可见家乡人对它的喜爱,从品相到口味,要求都极高。街头巷尾,一年四季,都能看到流动的摊点冒着热气和香味在售卖蒿子粑。当然,最好吃爽口的,还得用应季新鲜上市的蒿子做。它不仅是一种地方美食,而且还承载着丰厚的地域文化内涵。远在异乡打拼的桐城人,满心欢喜地收到家里寄来的蒿子粑,常常会吃出一脸幸福的泪花。
早春时节,春风浩荡,鸟语花香。池塘边,柳条划破一冬的枯寂。地里的野草根茎耐不住寂寞,把蛰伏一冬的嫩绿从潮湿的土壤里使劲地往外拱。田野里,不少植物在泛青,蒿子便是其中之一。
暖阳下,蒿子发青后,逢着雨水便蓬勃生长。旷野里、石桥边、土坡上都有蒿子的身影,有时聚在一起,有时又零星地散开,仿佛在试探着贪食客的耐心。蒿子喜欢生长在碧绿的草丛里,秆子和叶茎呈淡淡的赭青色,叶片背面白细的绒毛,摸起来特别柔软,形状与野艾叶有些相似。
听母亲说,蒿子分柴蒿、香蒿两种。柴蒿个子高,生长快,多呈青白色;香蒿,个子矮,色泽深一点,多趴向地面,与泥土亲密接触。细细闻,有股淡淡的清香;尝起来,舌尖微微发涩,但一经烟熏火燎便香气弥散。采蒿子多是妇女和孩子们的活,男人们须在田间地头劳作。一竹篮蒿子采下来,指甲缝里黑乎乎的,手上也沾着浓绿的汁液,要好几天才褪得掉。
母亲先是拣尽掺在其间的杂草,剔除我误采的不知名儿的野菜,再是掐去老梗,拿到水塘边一根根洗净。母亲撅着身子,半蹲在麻石条上反复搓揉,几番过后,碎渣便随浓稠的汁水一起流进塘里,引得鱼儿争相啄食。待青色蒿汁褪去大半,蒿子的香味更纯正了。母亲将蒿子揉成球状,够做二三回的,多出的蒿子摆在日头下晒干,储存起来,宝贝儿似的,待蒿子罢市后,再做给我们解馋。
挑上一块年前腌制的腊肉,肥瘦相间的那种,切成豆粒般大小,先是放在锅里爆炒,待七分熟,满屋氤氲肉香时,加入开水煮沸。再放入淘洗干净的蒿子,加磨制好的米粉,均匀搅拌。和稀了,母亲便加一二勺米粉;和硬了,便再添一点水。母亲不紧不慢地抓起一块粉团,双手压平,做成圆形的小粑,平摊在砧板上。待油锅冒烟,倒入自家产的菜籽油,挨个儿放蒿子粑,以免黏在一起,用稻草炆火慢烧。
蒿子粑贴在锅边,“滋滋”地冒着热气,待一面金黄起壳,再翻边。母亲沾几滴水,盖上锅,等到蒿子香味穿过锅盖,满屋子乱窜时,便可出锅。
我常围拢在锅台边,像只小馋猫,只待蒿子粑出锅,便抓上一只,烫得我直跺脚摆手。母亲呵呵地笑着:“瞧你吃的!”她便拿出筷子戳一个递给我,一般要吃三五个,直到打饱嗝才罢休。蒿子粑要趁热吃,冷了,就变得僵硬,嚼不出蒿子的香了。奶奶最喜欢母亲做的蒿子粑,豁了牙的嘴慢慢地嚼着,直说香!
乡村里,每到三月,家家户户蒿子飘香。其实,早在二月中下旬,乡亲们就在找寻蒿子的踪迹。气温回暖,草木葱茏,田野里土生土长的野菜,在那个贫瘠的年代抚慰了多少乡民的辘辘饥肠!
吴中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