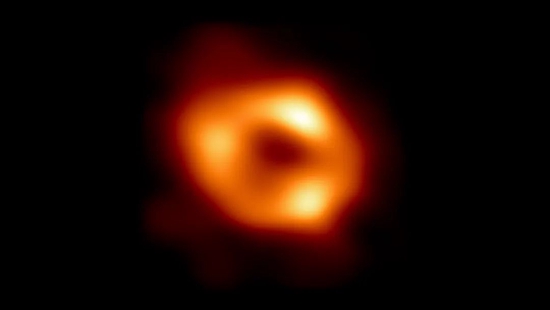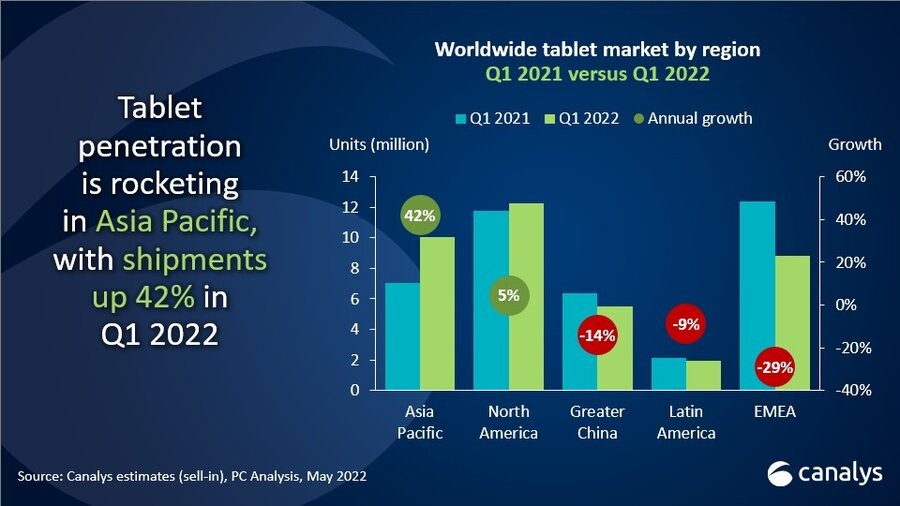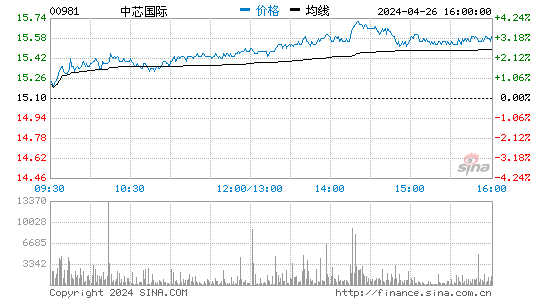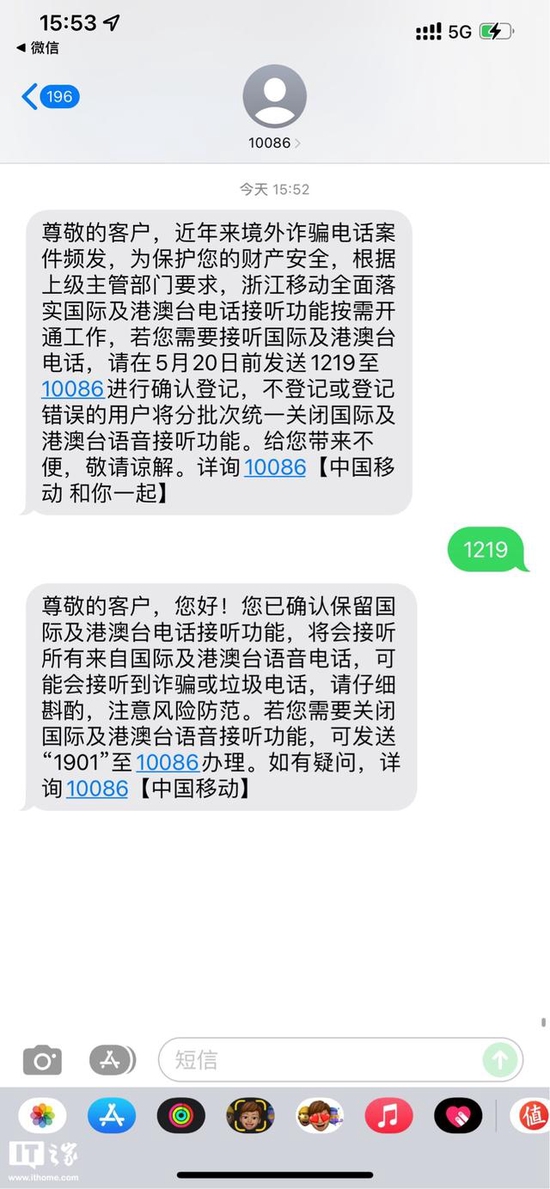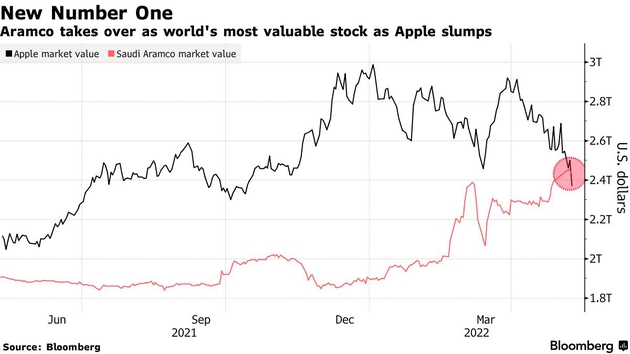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本报记者 张文静
科学家要破解宇宙运行、物种演化等深邃奥秘,但作为“职场人”,他们免不了要考虑那些关乎职业发展的问题。比如,科学家一般会在什么年龄达到最佳工作状态?科学创新的生命周期是多久?科学家职业生涯中出现突破性进展的迹象是否存在?什么样的合作会带来成功?年轻科研人员如何将成功的概率最大化?
一些科学学研究者正致力于解答这些问题。这个新兴的研究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用量化方式认识科学的演化路径,探讨科研活动涉及的种种因素与其产出之间的关系。
他们的研究会给科学家的职业发展带来启示,从这个角度上说,这些研究或许可以称为科研人员的“成功学”。
你的“奇迹年”什么时候到来?
1905年被称为爱因斯坦的“奇迹年”。就在这一年,爱因斯坦接连发表了数篇彻底改变物理学的论文。他解释了布朗运动,印证了原子和分子的存在;他发现了光电效应,向量子力学迈出了关键一步,并因此在1921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创立了广义相对论,完全改变了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认知。在这一年的年末,他写下了世界上最著名的公式:E=mc2。
虽然爱因斯坦的高度是常人难以企及的,但他这种研究成果集中爆发的“连胜”现象却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爱因斯坦的连胜仅仅是一种巧合吗?在更多科学家的职业生涯中,重磅的研究成果也会倾向于在某段时间内接连到来吗?如果有这种连胜期存在,会发生在什么时期呢?
在不久前出版的《给科学家的科学思维》一书中,美国西北大学科学学与创新中心主任王大顺和美国东北大学教授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共同探讨了这一问题。这些探讨基于王大顺等人2018年发表在《自然》上的一项研究。
在研究连胜现象之前,王大顺就对一万多名科学家的职业生涯做过研究分析。他发现,研究人员发表最有影响力的论文的时间完全是随机的,其出现在研究生涯早期、中期或晚期的概率是一样的。
而在2018年的研究中,王大顺等人不仅关注科学家的最佳作品,而且关注他的次佳、第三佳作品,考察这些作品出现的时机是否具有统计学上的有效规律。
他们使用谷歌学术搜索和Web of Science平台获得了超过两万名科学家的研究论文数据,这些数据包括每篇论文在发表十年之内的引用情况。他们还将研究范围扩展到学术界以外,考察了艺术家和电影导演的作品情况。
研究人员首先计算了个体的三个最佳作品产生的时间间隔,然后进行模拟。他们随机打乱了三个最佳作品在个体职业生涯中出现的顺序,并再次计算了它们之间的时间间隔。
他们发现,与随机数据相比,现实数据中一个人的两个巅峰作品有更大概率在相近时间内出现。也就是说,无论是科学家、艺术家还是电影导演,职业生涯中的连胜期都是存在的。
通过进一步深入研究,研究人员发现大多数人至少会经历一次连胜期,他们连胜期的长度随职业的不同而不同,比如艺术家大多持续5.7年、电影导演持续5.2年,而科学家会持续3.7年。
虽然连胜期出现的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在王大顺看来,这项研究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比如在鉴别或培养有潜力的科学家时,可以将连胜这一概念纳入考量因素,否则可能会错失机遇。
在这方面,耶鲁大学有过一次教训。化学家约翰·芬恩在67岁时发表了研究成果,证实了一个新的电喷雾离子源。这是一个重大突破,至少他自己认为是。但耶鲁大学仍然让他退休,将他请出了校园。
此后,约翰·芬恩不太情愿地在弗吉尼亚联邦大学重新安顿下来,该校为他提供了实验室继续从事研究。自此,他的连胜期开启了。1984至1989年,约翰·芬恩的研究论文一篇接一篇发表,最终创立了电喷雾离子化的质谱分析法,使大分子和蛋白质的测量更快、更准确,促进了癌症诊断和治疗上的许多创新,这使他获得了2002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多样化的科研团队,影响力更大?
除了个人科研产出之外,如何组建一支优秀的科研团队也是很多科学家最关心的话题。科学家是拉上彼此熟悉的、有“共同语言”的人一起工作好,还是选择多样性更强的合作伙伴好呢?一些研究给出了数据。
近年来,不少研究都对科研团队多样性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探讨,这些多样性因素包括国籍、种族、所在院校或机构、性别、学术年龄和专业背景,等等。毫无例外,这些研究都显示,科研团队的多样性有助于提升团队效率,无论是在产出量上还是在产出更具影响力的论文上。
有研究分析了1985—2008年由美国作者撰写的250多万篇研究论文涉及的种族多样性情况。研究人员发现,由来自4或5个不同种族的作者撰写的论文,比全部来自相同种族的作者所撰写的论文,获得的引用量平均要高5%~10%。
针对国籍或机构多样性的研究也呈现出相似的结果。有研究人员对1996—2012年8个学科的所有论文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由来自不同国家的科研人员撰写的论文,更有可能被高影响力期刊发表,而且往往会获得更多的引用。
有趣的是,在针对多样性的研究中,团队的种族多样性因素对论文影响力的提升作用似乎最显著。
2018年发表在《自然—通讯》上的一项研究,分析了由600万名科学家撰写的900多万篇论文,探究科研影响力与种族、学科、性别、隶属关系、学术年龄等五种多样性因素之间的关系。
研究人员将这五种多样性指标与团队成果的五年总引用量进行比较,发现种族多样性与影响力的相关程度比任何其他指标都更强。即使他们控制了论文发表年份、作者人数、研究领域、论文发表前作者的影响力以及大学排名等因素后,团队的种族多样性仍提升了10.63%的团队影响力。
对此有一种解释认为,能与更多样化的同事合作的科研人员,科研也会做得更好。也就是说,论文影响力的提升可能是由于团队成员思想开放、善于合作导致的,而并非由于种族多样性本身。
为了验证这个观点,研究人员设计了一种“个体多样性”指标,通过采集某位作者所有的早期共同作者情况,测量其种族多样性的程度。然后,再将它与“团队多样性”进行比较,即某篇论文共同作者中的种族多样性程度。结果表明,虽然团队多样性和个体多样性都具有很高的价值,但前者对科研影响有更大的促进作用。
不过,王大顺在《给科学家的科学思维》一书中也提醒,这些研究依据的都是论文发表数据,因此这些发现可能仅限于那些足以成功发表论文的团队。也就是说,当团队真正形成并有了论文产出之后,多样性才能与更高的影响力联系在一起。
科学家陷入盲人摸象的困局?
在论及上述科学学研究的价值时,《给科学家的科学思维》译者、西南大学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教授贾韬表示,一位成功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实践中,通过观察自己以及身边的科研活动,对各种规律进行符合逻辑的归纳总结,也很有可能形成系统化的科学认知,这些认知将进一步为他的成功助力。然而,个人对科学的观察往往局限于“身边”。
当涉及跨学科、跨国家的复杂问题时,缺少大规模数据的量化分析,而仅仅依赖身边的经验,也许会让科学家陷入盲人摸象的困局中。
贾韬举例说,国内科研人员很可能会基于直观感受,认为医学、生物、农业和化学这样的学科是“劳动密集型”的,六七个人共同完成一项工作、合作发表一篇论文是学科的常态,因此人力投入是发展这些学科的必要条件。
这种直观感受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在我国这些研究领域中,2017年作者人数少于5人的论文占比在25%以下。然而在全球其他国家,这一比例为50%甚至更高。也就是说,这些领域中,规模较小的研究队伍创造了一半的科研产出,而这才是这些学科在全球发展的常态。
“脱离大数据的系统性分析,仅仅依赖自身的感知,我们很可能会走向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的学科发展道路。”贾韬表示。2019年,《自然》发表了一项对科研团队的研究,发现小团队比大团队更能做出颠覆式的创新成果。“考虑到小型研究队伍在颠覆性创新上的特有能力,这样的选择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系列其他问题。”
同时,在贾韬看来,目前一些科学学研究,比如关于团队多样性的研究,所基于的数据主要是英语国家的论文产出,相关的结论是否适用于我国,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我们在一些初期工作中,已经发现了我国高被引论文的国际影响力呈现出与其他国家不同的规律,但是这些观察结果到底是对应着不同的机制,比如高被引论文在我国不能准确地反映其科学影响力,还是对应着相同机制下的不同参数,比如我国的论文发表增速全球最高,还需要大量的后续研究分析。”贾韬说。
无论如何,在贾韬看来,当我国逐步从科技的追赶者变为全球的创新中心,科学的结构性变革必然会到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科学学的研究变得极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