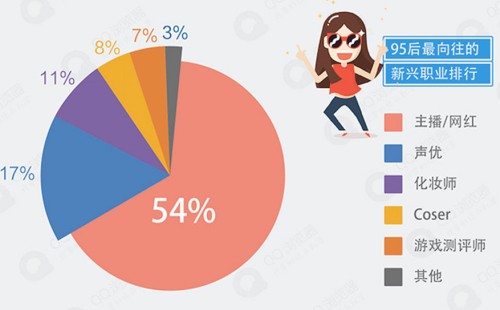■自然 米肖
周日开车离开市区,往南一直走,终于见到一个绿树掩映的村庄。
村子前后,一望无际白亮亮的池塘,每个塘口都不大,一亩见方。有的养鱼,有的种莲藕。塘埂上连绵的菜地,小白菜秧、空心菜、韭菜、紫茄……马铃薯开着青紫的花。天气太热,蜜蜂和蝴蝶都藏起来了。黄瓜藤在架子上,黄花早已枯萎,依旧坠在松青色瓜蒂上,所有的叶藤上布满刺,毛茸茸的。早黄豆差不多要拔光了,迟黄豆苗正一刻不停长着,一茬接一茬,生生不息。除了菜地,塘埂上还有平房,青灰色鱼鳞瓦———这年头,鱼鳞瓦就像一种稀有品质,真少见。
正碰见一个塘口拉网收鱼。男男女女穿着一种改良过的连体皮衣,小腿部位接的是胶靴。渔网慢慢收拢,白鲢翻着筋斗。最后,捉的是汪丫鱼。鱼贩子早已一旁等候。一篮舀下去,足足五六斤,汪丫鱼大小不一,其间混杂着螺蛳、河蚌。原以为小孩会雀跃欢呼,不料反应平静,可能天气闷热之故,太阳晒得无处躲藏。三十年前,我们碰上干塘,过节一样快乐,等大人们把鱼全部取上来,小孩子才可以下去摸河蚌螺蛳,也能收获一点漏网的小鱼小虾。三十年前的人,仿佛没有现代人聪明,只知道往塘里投点廉价的白鲢苗,鱼饲料尚未诞生,一年下来,白鲢何其瘦,最多七八两左右一条。唯一的好处是,吃野食的鱼生长缓慢,口感好。
村子周围的水田,全被储满深水养鱼养藕,随便走到哪里,都是扑面而来的水的气息,特有的,熟悉已久的,非常好闻的水腥气。这种水腥气,在一个人的生命里消失了三十年,不能忘记。
站在藕荡下风口,被荷叶的香气环绕。这种味道特别微妙,似乎可以解暑,清凉油一般直往鼻腔肺腑里钻———清新植物的气息。蓼在塘埂默默开花,略显单薄,适合远观,有虚无缥缈的美,仿佛得不到的遥远,分明近在眼前。
村旁旱地,不是荒芜着,便是租出去了———有的盖了蔬菜大棚,有的种植蓝莓。蓝莓小屋门口躺着一只被打死的野鸡。据说这一带尚有野鸭出没。举目四顾,蓝天下一马平川的田畴远畈,天际线边笼罩着白茫茫的雾霭。入梅了,空气的湿度明显浓了———置身旷野,即便有风,也呼吸不畅,偶有胸闷之感。
我们在大棚里亲手摘了五六只紫茄,四五条一尺见长的油丝瓜,自然成熟的西红柿,一把豇豆……孩子站在大棚门口小脸晒得虾红,嚷着回家———难道,作为神明一样的稚子,不曾感受到一丁点田园野趣?
到底是两代人了。从哪里来的,到哪里去。倘若一个人梦里都是乡野的气息,那也只能说明他的婴儿期、少年期在乡间度过罢了。如今,村庄在一年快似一年的消逝着,城镇化的路是一定要走的。村里年轻人,谁不曾有过对于“城市文明”的向往?
一位妇女顶着烈日在地里锄草,被磨得光亮的锄头柄,握在她双手间,一下一下运动着,脚下是嫩生生的黄豆苗,头上麦秸编的草帽,身体在青蓝色的衫子里瘦得出奇。一大片黄豆地,就她独一人,蛮辛苦的。
因为辛苦,也产生不了多少经济收益,理所当然,许多村里人弃田,来到城市工厂流水线上。像我这样的久居城市的人,又厌倦了所谓的“城市文明”,一心惦念着乡野的好,比如整一块菜园,自种自食。
回家将豇豆烧了,嗯,是小时候的味道;丝瓜做了一盆汤,滋味无限。现在市场上售卖的长丝瓜总顶着健硕黄花,几日不衰。据说激素所致,一直不敢吃。黄瓜也是,总坠着日不落的超大黄花,一看就不正常。
生在当下,我们一生要吃进多少激素才算完?
从乡下大棚摘回的几样菜,珍稀似的,舍不得吃,存在冰箱,一天烧一点。西红柿切开,有籽,自然熟透,表明没有涂催红素。
是不是中国人口太多,而且都特能吃,造成供不应求的局面———不仅猪牛羊马、鸡鸭鹅鱼要缩短养殖期,连蔬菜瓜果都逃不过这种即成式的命运?然后,催生素和激素就被绝顶的中国人发明出来。
在中国,人活两难———乡下人向往都市人的轻逸,都市人羡慕乡下人果腹的有机绿色。实则,两头人皆活得难,两头人都不知道往哪儿奔。中国底层百姓的生活现状一直如此,无非如此。
而少数人如我,聊以在平凡的日子,毒瘾发作一般,间或往乡下跑一趟,侥幸带点有机蔬菜回来,点缀一下被激素包围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