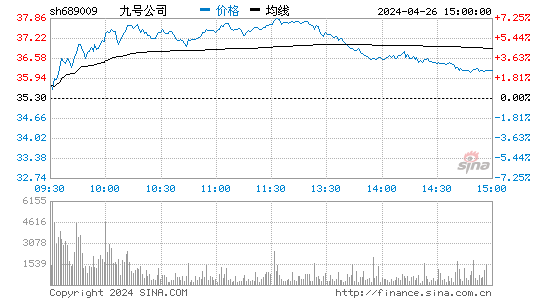我叫泽仁多吉,是川藏线上的一名邮车驾驶员,也是一名押运员。这种驾押合一的模式,在川藏线上是家常便饭。我总是这样一个人开着车来回跑。茫茫的青藏高原之上,白云朵朵的蓝天之下,几百公里范围内通常只有我和我的影子。当然,偶尔也会有狼。
那个时候,我们甘孜全州共有邮车27辆、驾驶员27名,押运员却只有8名,平均每天在途邮车是18辆,因此大部分邮车只能实行驾押合一。也就是说,许多时候,我除了要开车,还要当押运员。你一定觉得不可思议吧?但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这么过来的。
我负责押运的邮件和机要文件,大部分发往西藏昌都。在那个年代,地球上所有发往西藏昌都的邮件,都要经过成都、雅安、康定、甘孜、德格五地中转。从成都到昌都,海拔从500米升到5000米,要途经二郎山、折多山、橡皮山、罗锅梁子、雀儿山等许多令过往司机胆寒的地方。
现在,许多事情我都记不清了,但我仍然记得一个数字——5050。准确地说,是5050米。岂止是记得,应该说从来不曾忘记。这是一个海拔高度,但它不是一座山的海拔,而是一段公路的海拔。这段公路就是雀儿山山顶的那段路。
雀儿山藏名叫措拉,意思是大鸟的羽翼。“爬上雀儿山,鞭子打着天。”每一名路过的驾驶员大概都熟悉这句谚语。那时候,我每个月都要翻越雀儿山不止十遍。
每次出行前,妻子洛绒卓玛都会为我准备几沓龙达。龙达是我们藏传佛教祭祀神灵的纸制品,上面印有六字真言,顺风撒放,可以保佑我们平安吉祥。
每当抵达雀儿山垭口时,我就会将这些龙达高高地撒向天空,并高喊着祭神的祷语:“哈索,哈索!”做完了这些,我才感觉我可以平安翻越雀儿山了,尽管我对这里再熟悉不过,但为了在家中等我的洛绒卓玛,我总是这样一遍一遍虔诚地祈祷着。
除了险峻的公路,雀儿山另一个响亮的名号是漫山遍野的格桑梅朵。格桑梅朵,就是格桑花。生长在5000米高海拔地区的格桑花,其实是青藏高原上最普通的一种花。它在雪域高原简直太普通了,一到花季满山都是。但雀儿山的格桑梅朵却不普通。在我们藏区有一个美丽的传说,无论是谁,只要找到八朵花瓣的格桑花就找到了幸福。我就是在雀儿山找到了八瓣的格桑梅朵,并用它将美丽的洛绒卓玛变成了我的妻子。
我太喜欢这片美丽的格桑梅朵了,每次行经这里总是难免一番流连,一定要找到一朵八瓣的格桑梅朵才肯罢休。我将它带给洛绒卓玛,她总是将它们种在阳台上,我们的阳台简直要成为一片格桑梅朵的花海了。
常年穿行在川藏线上,危险还是时时会来。前面已经说过,我们有时会遇见狼——巨型高原狼。有时是孤狼,有时是群狼。
有一回,我在川藏线上开着车犯起困来,索性停下来休息一会儿,不知不觉等我醒来时已是傍晚。我准备下车解个手,刚把车门打开,就骤然发现有一头狼在邮车下面。我吓一大跳!连忙关上车门,隔着车窗仔细看,才发现不是一头狼,是整整五头巨型高原狼在围着邮车打转!这五头目光如炬的高原狼在邮车周围来来回回地走动,整整半个小时,没有要离开的意思。所幸刚才我没有下车,要不然早已成了狼群的腹中餐。我在驾驶室里惊魂未定地待着,后怕不已。我知道,这个时候一定要镇定,千万不能慌张。我盼着有过路的车辆解救自己,可是川藏线上来往的车辆实在太少了,何况现在已经是傍晚,车辆几乎不可能出现。我只能盼着奇迹发生。奇迹真的发生了!一辆军车迎面开了过来,我得救了!狼群看见军车轰隆隆地开过来,很快就都散了。从这回以后,我就再也没开车打过盹了。
有人可能会觉得,群狼比孤狼可怕,其实孤狼才更可怕。众所周知,狼是群居动物,很少单独活动。如果你碰见的是一头孤狼,那说明这头狼饿极了,才会冒险离开狼群单独出来觅食。在川藏线上总有这种情况发生,一头饿极的高原狼虎视眈眈地盯着你,企图将你变作它美味的食物。我就碰到过几回,不过我实在洪福齐天,每一回都死里逃生。我简直就像有九条命的猫。
比高原狼更可怕的,是劫匪。
那个日子我一生都不会忘记。那是个冬天,我们的邮车行至雀儿山时,公路上突然出现乱石码起的路障,邮车还没停稳,枪声就响了。
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四名劫匪埋伏在山坡上,用改装的半自动步枪疯狂地向我们的邮车开火。我的左眼被击中了。好在这回车上有一名押运员次仁(那几年我们州局好不容易增加了押运员编制),我俩在一起有个照应,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劫匪抢走次仁身上的几百块钱就逃走了,目标似乎不是车上的邮件尤其是机要邮件。但也不能大意,我捂着汩汩流血的左眼眶让次仁赶快去报警,我在车上守着邮件。等救护车来时,我早已经晕过去了,眼眶里流出的血凝结成了冰块,但我对此浑然不觉。
昏迷整整十天后,我醒了,我问身边的人,机要文件还在吗?身边的人告诉我,都在。这我就放心了,只要机要文件安全,我受点伤就无所谓了。
我们所有邮车押运员和驾驶员都知道,在每一车邮件中都有一个特别的邮袋,袋子上有两根红色的竖条,里面装的是机要邮件。大件不离人,小件不离身,这是对机要邮件的管理规定——那是比自己生命还要珍贵的东西。
我再一次捡回一条命,但我的左眼眶变得像藏区公路一样空荡荡了。更加残酷的是,我的右眼球下也有弹片,因紧邻大脑无法手术,视神经不断萎缩,我右眼的视力也慢慢消失了,我成了废人一个。
怎么说呢?我现在连牙膏都不会挤了,要么挤在手上,要么掉在地上。可我曾是一名优秀的神枪手啊!我可以毫不谦虚地说,退伍成为邮车驾驶员之前,我是我们连队最优秀的狙击手,几百米的目标从来不会浪费第二颗子弹,射击项目大比武年年我都是第一名。但是现在,一支小小的牙膏我都不能准确地把它挤到牙刷上。我还有什么用呢?我将牙膏狠狠地摔在地上。
洛绒卓玛听到动静,轻轻地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她什么也没说,我知道她在流泪。
第二天,我在卧室里闻到了熟悉的格桑花香。我摸索着,摸到了一盆盛放的格桑梅朵。我用手指数了数花瓣,是八瓣。
我感觉我空荡荡的眼眶里有泪水涌出来。我哭了,像高原呜咽的北风一样失声痛哭。
我报名参加了盲人按摩培训班,在成都开了一家小小的按摩店,店的名字叫格桑梅朵。
我跟洛绒卓玛说,等我攒够了钱,我们就再去一趟雀儿山,去漫山遍野的花海中寻找八瓣的格桑梅朵,只要我们仔细找,就一定能找到。也许还会遇见高原狼,但我已不再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