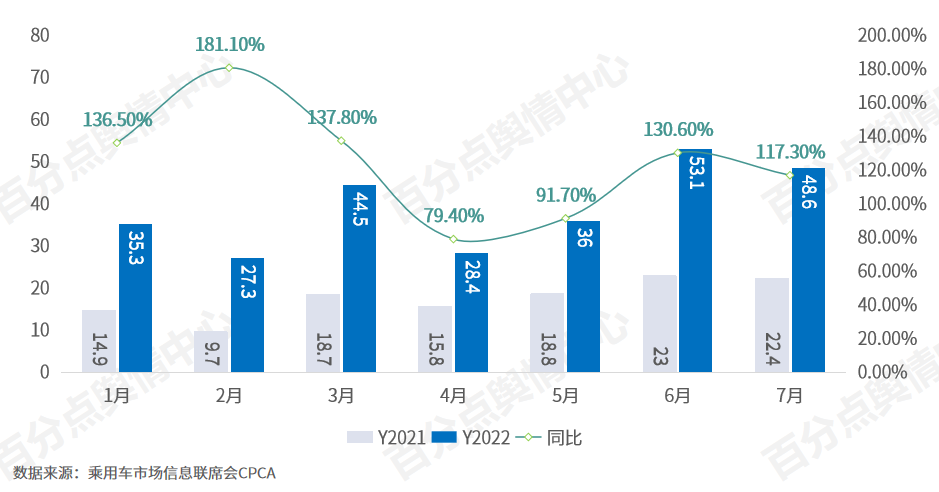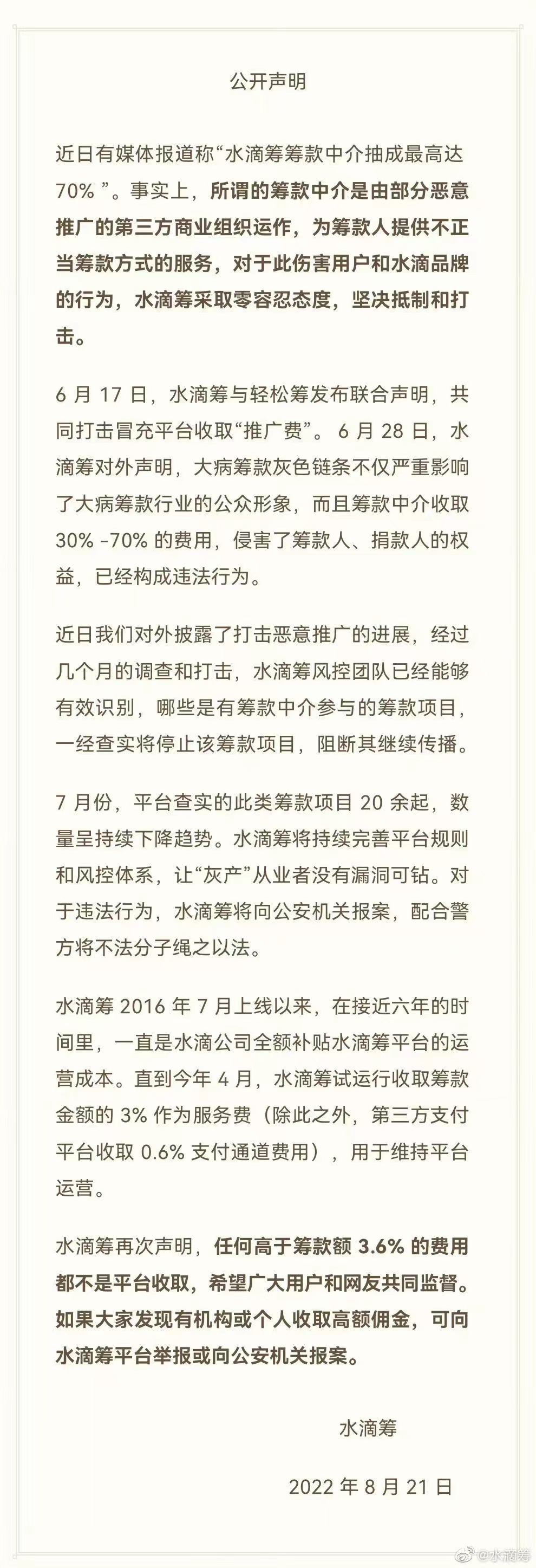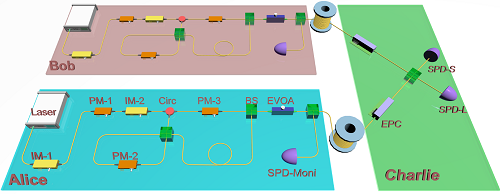■私读 《降魔变》 ◎马鸣谦/著 中信出版社
·赵柏田

马鸣谦在苏州生活和写作。鸣谦让我钦佩的地方在于,他可以同时做着几件事,且每一件都做得非常出色。
鸣谦是小说家、译者、行走者,还是一个很有造诣的佛学文化研究者。他早年的两部长篇小说《隐僧》和《无门诀》,都是以佛教文化为背景的。他译诗,译的是英语世界里素称难译的奥登,后来还译了松尾芭蕉。他的这些小说和翻译,在中国文学和出版界树立起了良好的口碑。他的写作面貌有着同时代人所稀缺的丰富性。他是一个文化建构者,也是写作行里的一个苦行僧。几年前他跟我说,与君同行有一人。这也是我想跟他说的。
鸣谦的《降魔变》,是一个取材于晚唐西域一段真实历史的长篇小说。安史之乱后,陇右为吐蕃所据,沙州大族张议潮兴归义军,归唐后,使得这一边陲之地重睹汉官威仪。小说写的就是沙州归义军政权的更迭。
这是一个南方作家的“西部世界”,是鸣谦的西部想象。为了写出这部小说,马鸣谦没去过一次敦煌,因为他不想扼杀了他的想象。现在,他强劲的想象终于结出了事实之果。第二代归义军使主张淮深一家的“灭门案”,是这个小说的核心事件,以猎鹰人程子迁和少年曹仁贵的视角,串连起整个故事,四个章节层层推进,展示了一个晚唐的敦煌世界。
我初看惊讶的是这个小说的开始为什么是一图一表。一幅陇右道地图,一张敦煌大族世系表,已经在告诉我们,阅读这本小说,要做好同时进入两个世界的准备,那就是历史世界和文学世界。读鸣谦的小说,须预先做一些功课,我专门去读了荣新江先生的《归义军史研究》,还有敦煌藏经洞关于沙州归义军的一些文献,大多简略零散。历史滋养了这个小说,小说在多大程度上还原了这段史实?这是我的第一重好奇。但我更感好奇的是,从史实到小说的这个艺术性的转化,鸣谦是如何完成卡尔维诺说的那种“轻逸一跃”的。
这是小说家马鸣谦的一张“秘图”。他后来的“诗人三部曲”,其实也是遵循着这张秘图的草稿。
继续说《降魔变》。在当下的历史小说中,它称得上是一部巨著。不仅仅是它的体量,还有它的完成度。我最看重的是这个小说的现代性。历史小说写出现代意味,或许正是鸣谦一直致力的。小说前引《哈姆雷特》里的一句话,已在暗示他要写的是人性中的魔性和救赎的主题。中国的历史小说,从说部走出,演义和戏说是拿手手段,稀缺的正是那一点现代意识与现代精神。鸣谦的笔法是有承接的,他回到了鲁迅《故事新编》和施蛰存《将军的头》的传统。
我们讲中国叙事文学的滥觞和日后的发达,可以从宋元杂剧、金元院本、诸宫调、早期话本小说、晚唐五代变文和曲子词一路演变下来。鸣谦的小说语言,细细读去,如抽丝剥茧,竟有着说书人的几分余韵。他总是把新与旧结合得很好,把传统与现代平衡得一点不生硬。他对唐朝猎鹰、赛球、佛事、绘画的描写,构成了全书坚实的物质基础。其实,小说的这一物质性基础是我久徊不去的,可惜此道久疏,现在的许多小说都是不着地的。
像马鸣谦这样不依附于某种文学秩序的小说家,照几年前的流行说法,或许是被叫作“野生作家”的。这倒让我看出了鸣谦生活其中的城市的一些倔强来。长着扑克牌脸的“文学秩序”可以不接纳《降魔变》,但阻止不了这种“野生”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