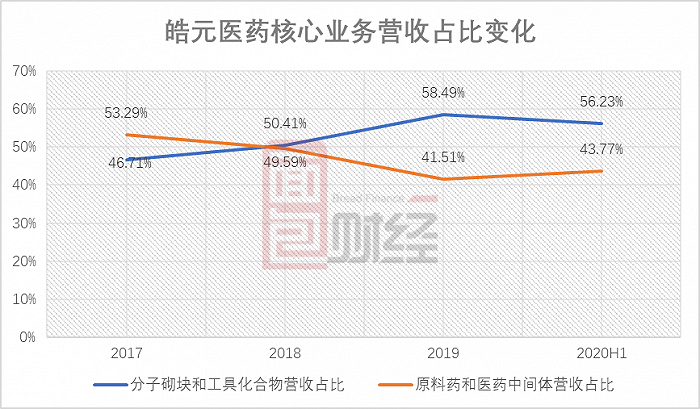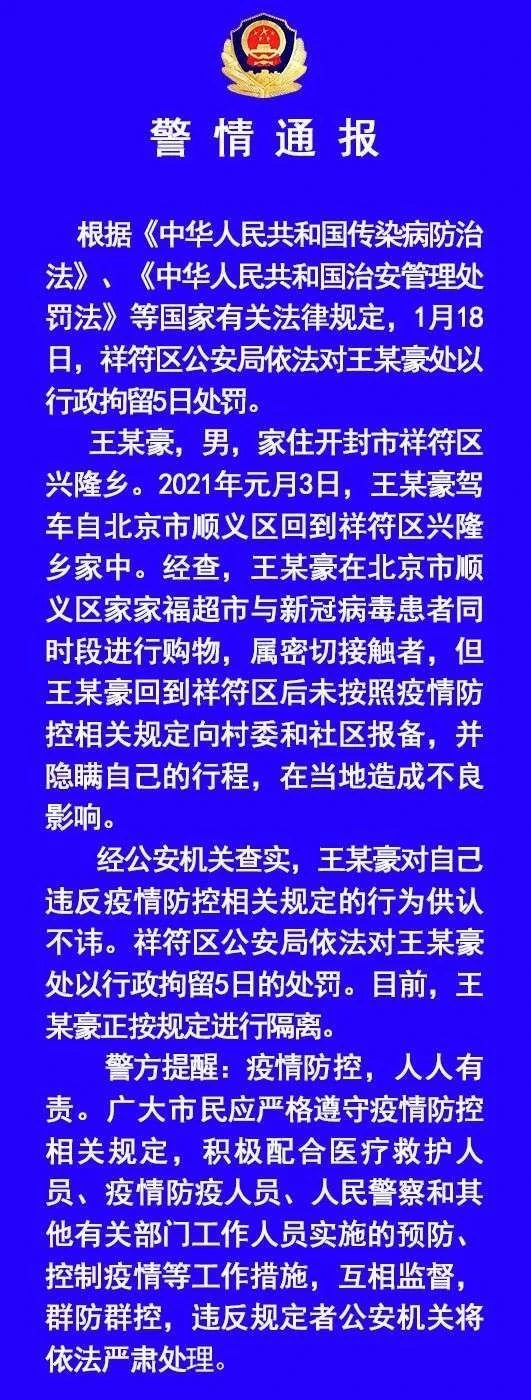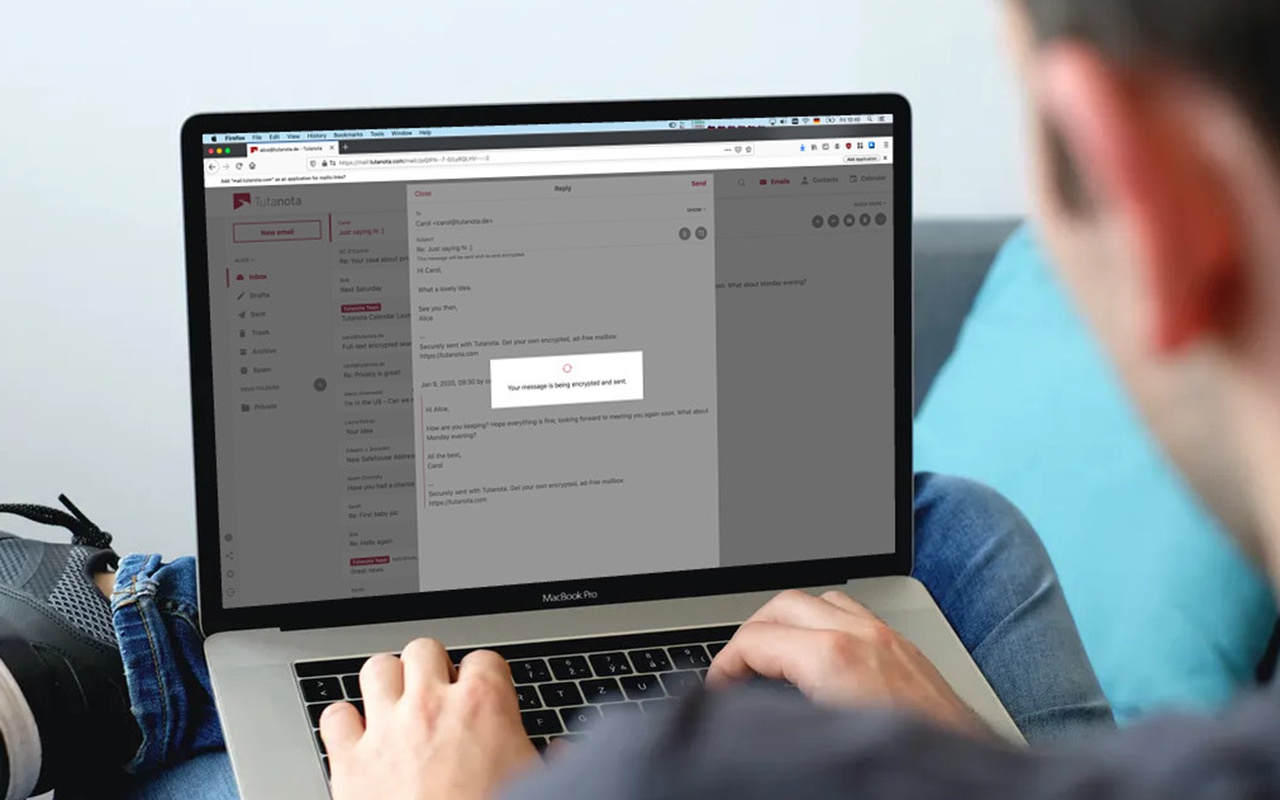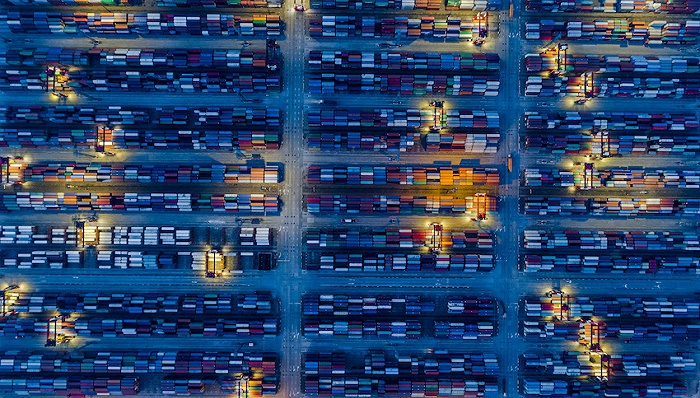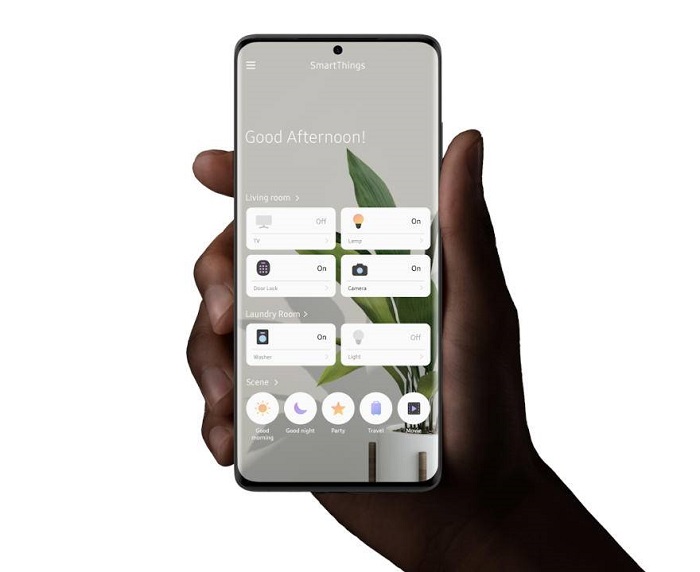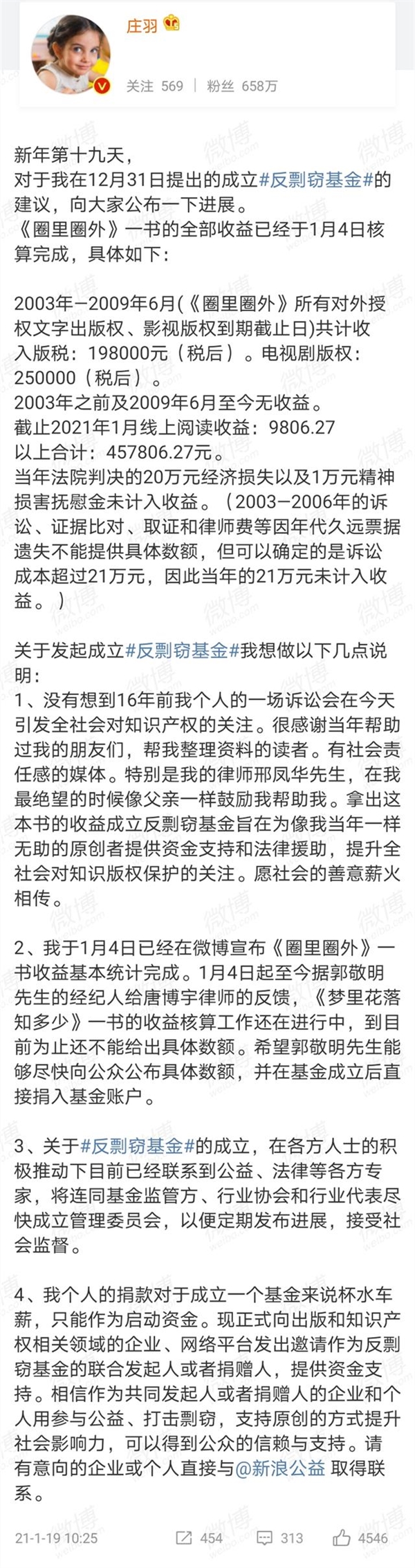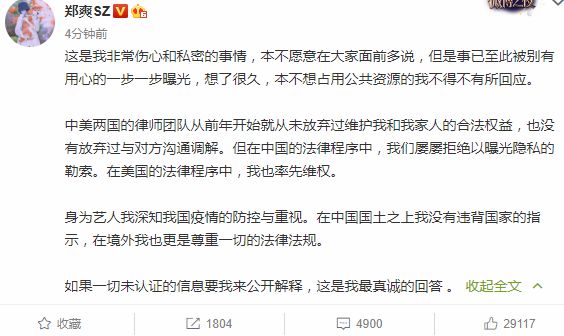图片来源: Taylor Young on Unsplash
图片来源: Taylor Young on Unsplash来源 WIRED
作者 Grace Huckins
翻译 李姗珊
编辑 魏潇
在 2009 年,一个匿名网友发表了一篇题为《去你的、去你们的论文》(Fuck You and Fuck Your Fucking Thesis)的文章。在文章中,作者表达了对成为学术研究对象的抗拒——她是位跨性别女性。“你觉得通过你的研究能为我和其他跨性别女性的生活做出多大的改变?你觉得靠研究我们对于月经的需求就能改善情况吗?”她在文章中问道。理论上,这些质问是向那些做课题的研究生发出的。“你的研究能够改变我的人生吗?能改变任何一个人的人生吗?”
十年过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的法律系学生 Florence Ashley 仍在思考这些问题。她在一篇研究中引用了上述文章,并在 2020 年11 月发表到了《生物伦理学》(Bioethics)期刊上。在这篇论文中,Ashley 讨论了研究倦怠(research fatigue)的概念,在接受 WIRED 采访时,Ashley 将其形容为一种研究对象产生的职业倦怠。“首先,这是因为你配合参与了过多的研究,” Ashley 表示。“还有一个原因是你的参与没有带来任何有价值的回报。这是一种消极的心理和情绪状态。”
作为跨性别群体中的一员,Ashley 也曾经历过研究倦怠。尽管她知道,研究者的身份给了他们一定程度的优越性及对实验程序的共情,但她时不时还是会发现自己不愿参与看起来很有趣的研究。“我的经历是,看到设计非常酷的研究时,我的内心会充满这种焦虑情绪:‘我应该参与这项研究。’但同时,我又对它产生了深深的倦怠,” Ashley 这样表示。一些同样感受到这种倦怠的同伴,即便参与了研究也往往半途而废,尤其是在研究使用了不合时宜的表述、不敬语言或没能很好地反映群体需求的情况下。
研究倦怠并不仅仅是一个伦理问题——它还可能影响研究本身。疲倦的被试无法为未来的研究形成助力。如果少数群体对参加研究感到倦怠,他们将在学术研究中被进一步边缘化。“这将对未来研究造成阻碍,并且是对某些特定人群的未来研究造成阻碍,从长期来看,这最终会导致一种不平等。” Ashley 说道。
 图片来源:Andrew James on Unsplash
图片来源:Andrew James on UnsplashAshley 强调,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主要来自几十年来一些学者对原住民社区的研究,这些原住民已经被过度研究了,而且一部分学者在做研究时并不在意原住民群体的感受。Ashley说:“有这么一个笑话,每一个原住民家庭中一般都有一个父亲,一个母亲和一个人类学家。”
Marianna Couchie 是加拿大安大略省尼皮辛保护区原住民(Nipissing First Nation)的前族长。她曾见证了针对自己族人的过度研究。当尼皮辛人在留守地开始新一轮的捕鱼计划时,捕鱼团队的领导者告诉 Couchie,他被各种采访请求弄得不厌其烦,这些采访抓着同样的问题问了又问。跟捕鱼团队的领导者一样,Couchie 也同样对情况感到失望。她浪费了无数的时间回答重复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他们的群体没有任何价值。“他们很愿意分享自己的故事,” Couchie 代表尼尼皮辛族所有原住民这样说。但持续的问话——研究者毫不思考这些问话将对群体产生什么益处——浪费了原住民的时间和精力。而由于原住民对于研究没有话语权,他们无法将研究转向能回应他们需求的方向。
Cindy Peltier 是尼皮辛大学(Nipissing University)的副教授及原住民教育主席,她将这种研究方式称作“直升机研究(helicopter research)”。“这些研究者闯进我们的社区,带走他们想要的信息,并发表他们自己想要发表的结论,从不向社区寻求任何咨询,”她表示,“人们觉得本地居民仿佛就是被捕的观众。”(这种情况到今天还是非常严重:近来,美国的一些部落民族不愿参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领导的 DNA 采集项目,因为他们害怕自己的基因数据将被控制。)
研究对于被试来说是无意义的,还可能导致倦怠——尤其在研究数量众多,潜在被试数量又极少的情况下。这种现象带来的结果是,少数群体社区变得极其脆弱。这种情况不仅仅对于跨性别者以及原住民被试成立,还对乡村居民、罕见病患者、移民以及其他对反复被研究感到倦怠的人成立。人们已经不想再为高高在上的研究当小白鼠了。“研究倦怠主要发生在公共兴趣的范围超出了本地人群的回应能力的情况下。” 加拿大蒙大拿州立大学(Montana State University)的地质学副教授 Julia Haggerty 说到。她的研究方向为乡村能源开发造成的影响。
然而,我们确实还有很多了解边缘群体的理由。医学研究者希望研制出针对罕见病的治疗手段;社会学家以及人类学家希望他们的工作能够帮助大众了解极少受到关注或常常遭受不公正对待的群体。但最后一个目标往往是不切实际的。“对于边缘化群体,公共兴趣集中在政策实施上,因此,研究人员们坐着飞机找到这些群体,认为自己一定能解决问题,可之后什么都没有发生。”英国谢菲尔德大学(University of Sheffield)的社会学教授 Tom Clark 在一篇关于研究倦怠影响力的早期论文中写道。“真正让研究在政策制定上发挥作用是非常困难的。”大量研究被放在架子上积灰,对外面的世界无法造成任何的影响——这种情况被 Clark 称为“社会的研究饱和(the research saturation of society)。”
Clark 等人认为,为了避免研究倦怠,研究者一定要考虑研究对象的需求以及渴望。其中的一种解决方法是参与式行动研究(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这种方法中,当地成员将接受训练,作为研究者(而不是被试),参与到研究中来。Peltier 相信,要想真正的造福社区,这种合作不能仅仅收集、分析数据或者帮助社群进行成果展示。“任何参与性研究,都需要在研究开始构思的时候就加入对于社区权益的讨论,”她说道。
 图片来源:Andrew James on Unsplash
图片来源:Andrew James on Unsplash当 Peltier 的学生与原住民社区进行合作时,她不仅鼓励学生们组建学术委员会,还需要成立一组由当地社区成员组建的委员会。这些社区成员能从研究初始就引导研究方向。她表示,通过招募社区成员,这种方法进展顺利。“原住民应该得到的不止是决策桌上的一席之地,” Peltier 表示。她不仅与尼皮辛族建立了联系,还和他们的聚集地——维克维孔原住民保护区(Wiikwemkoong Unceded Territory)建立了联系。“我认为他们需要参与到研究决策中来,他们需要决定研究的方式以及目标。”
但这种程度的参与并不好实现。“与本地社区建立的协定不需要都看起来一模一样,” Haggerty 说到,“研究者不需要许下无法达成的诺言。我们只希望他们至少能往前多走一步,为当地社区做一些思考。”
Clark 相信,参与式行动研究可能会太过耗时,对于研究时间和预算都很紧张的众多研究者来说更是如此。在无法做到和当地社群协同研究的情况下,他认为,研究者们至少应该通过诚实的态度缓解研究倦怠。只向研究对象呈现最佳情况下的结果,即(许诺)研究能够帮助他们建立关乎日常生活的政策性保护是有害的。“我认为你应当向他们呈现最现实的结果,” Clark 表示,“如果真能帮助研究对象,那最好不过。但很可能这种最好的结果不会发生。”
另外一种让原住民对研究掌握更高控制权的方式是,研究者需要向当地自己的伦理审查委员会征求批准。加拿大休伦湖上马尼图林岛(Manitoulin Island)的原住民就是这么做的:任何针对当地尼皮辛族原住民进行的研究必须需要得到马尼图林阿尼什纳比研究审查委员会( Manitoulin Anishinaabek Research Review Committee)的批准。
为了解决重复研究对于自己族人的影响,尼皮辛族前族长 Couchie 也想到了类似的解决方案。通过与加拿大尼皮辛大学学者的合作,她建立了针对原住民群体研究的管理方案。“参加研究对于原住民而言有什么好处呢?” Couchie 说到,“研究者需要证明,他们的研究将为当地社群做出贡献。”
但对于诸如跨性别群体等不同群体而言,无论是建立群体内部的伦理委员会还是与某所特定大学进行合作看起来都不太可行。但 Ashley 在发表于《生物伦理学》的那篇研究中表示,每所大学以及独立研究机构的伦理委员会都可以行动起来,主动避免实验引起研究倦怠。几乎所有以人类为对象的研究都需获得机构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因此,Ashley 认为委员会可以有效激励研究者,避免研究倦怠的出现。
机构伦理委员会与社区伦理审查委员会相距甚远。Ashley 讲这个组织形容为“时而吹毛求疵,时而过于宽松”,对于研究者来说,这是一个决定自己的课题申请能否通过的匿名群体。无论如何,通过拒绝可能导致研究倦怠的——比如重复过多或没有考虑到社区需求的研究申请,该机构有可能改善学术现状。“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科学界文化的改变,” Ashley 表示。“研究机构的伦理委员会可能在这场文化转向中发挥作用。”
不过,Ashley补充到 :“即便这样也是不够的。我们真正需要的还是让科学家们意识到这些问题。”
参考链接:
https://www.wired.com/story/for-marginalized-groups-being-studied-can-be-a-burd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