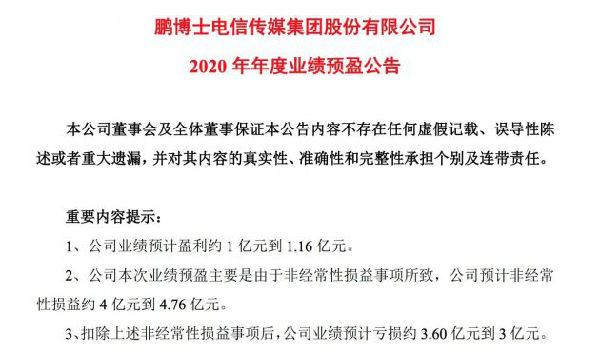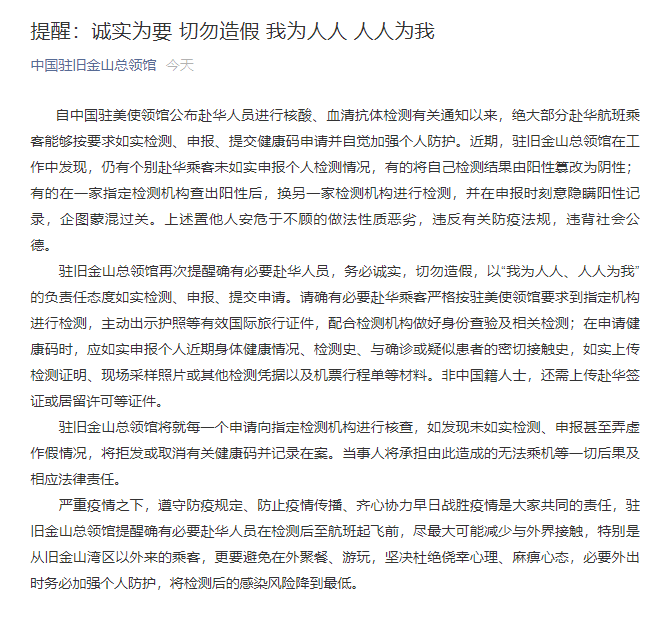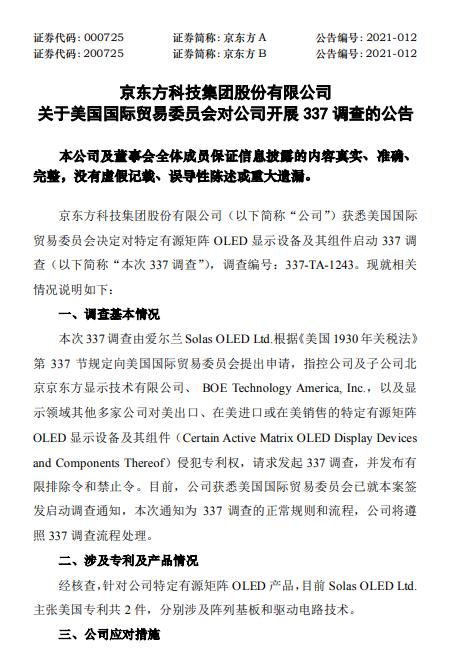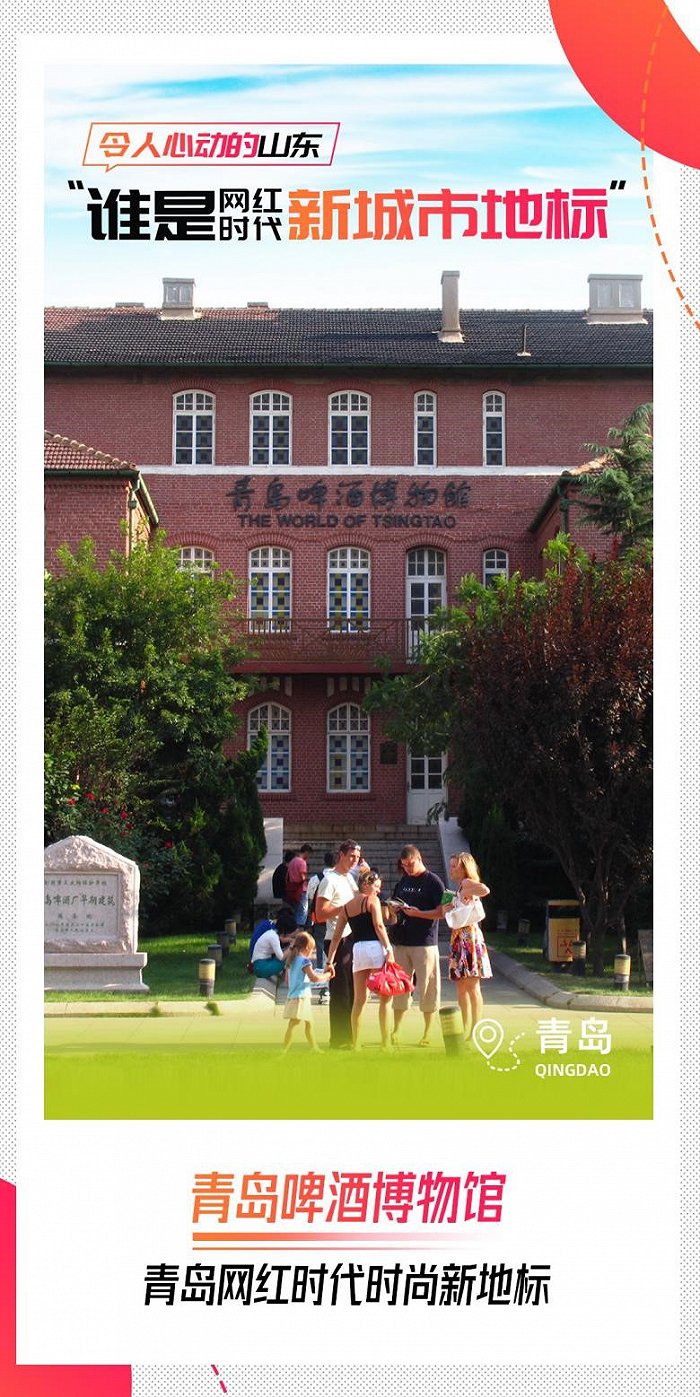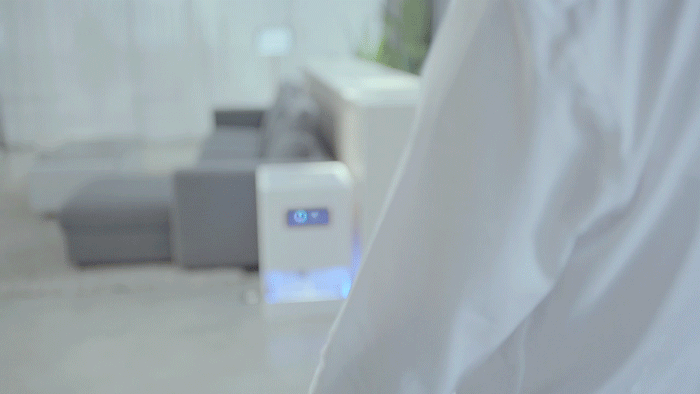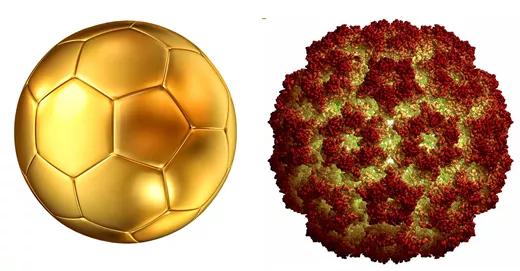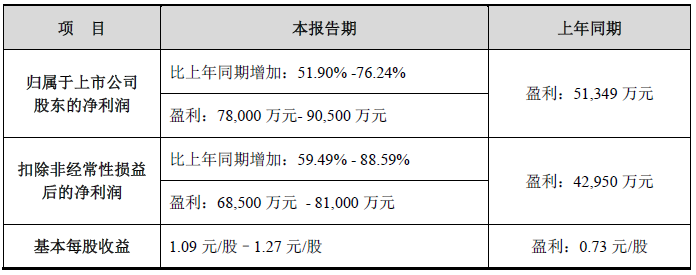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天文学家、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王绶琯,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1月2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王绶琯,1923年1月生于福建福州,1943年毕业于马尾海军学校,1945年赴英国留学,1950年改攻天文,入伦敦大学天文台进行研究工作。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20世纪90年代,王绶琯与苏定强等共创“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望远镜(LAMOST)”方案。国际编号3171号的小行星,被命名为“王绶琯星”,标志着他在天文领域的杰出贡献。而他不仅致力于科研,还非常重视人才培养,1999年他倡议并联合60位科学家创立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被会员们称为“科学启明星”。他曾说:“科学普及了,才能让更多孩子受益。我们尽力根植一片深厚的土壤,让科学之树枝繁叶茂。”(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李苑)
王绶琯院士:人重才品节 学贵安钻迷
本报记者 麻晓东
《科学时报》(2011-09-08)
在视野所不及的地方
焕出明光
有风雨漫天
忘去了海的颠簸
在夜郎古国结识诗词
1936年,13岁的王绶琯考取了福建马尾海军学校。一年后,抗战爆发,海军学校被迫西迁,最后落脚在贵州桐梓。王绶琯回忆说,当时学校在那里租了一个大户人家的大院——金家楼作为流亡校址。西迁时老师们都没有携带眷属,师生在课余、饭后相处的时间很多。有几位老师是诗词爱好者,使爱好文学的同学得到了引导、启蒙。老师们随身携带的各种诗词选集也在学生中传抄。在桐梓学习生活的几年间,王绶琯经常和李作健、陈克等几位同学习作唱和,那也成为了他在流亡期间一段难忘的回忆。王绶琯笑着告诉记者,至今他还和李作健保持诗词往来,而两人现在都已是90岁上下了。
1945年~ 1952年,在英国留学期间,王绶琯随身带了两本手抄的诗词,还夹了一本在桐梓时同学借的南宋词(同学上前线了),这本书一直被保存到“文革”后。当记者问到在英国期间是否也写诗的问题时,王绶琯想了想说:“想家时就写。”那时他开始脱离了“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心态,对名著佳作逐渐能够品味。那几年他还热衷于探索新诗,也尝试创作,但自觉总是离不开旧体诗的窠臼。
1989年,王绶琯应老一辈数学家孙克定之召共同创建了中关村诗社并任社长数年,诗社的社友们也多是科学家,他们提出“以诗明志,以诗寄情,以诗匡世”,并刊有《社友诗抄》多部。2006年,他在友人的建议下出版了《塔里窥天——王绶琯院士诗文自选集》,在该书的前言中,他写道:“这些乌合的‘故我’聚到一起后,我不无惊奇地发现原来自己始终没有走出过‘象牙塔’(拜科普之赐,是‘塔’的范围始终在扩大),也始终是在‘以管窥天’(只不过有时候用的是观测天文现象的‘管’,另一些时候则是地道的‘管窥蠡测’)。据此现状,这个集子就取名为《塔里窥天》。”
人生多面体中两个最光彩的面
作为我国著名天文学家,王绶琯开创了中国的射电天文学观测研究领域并予以推进,他也是中国现代天体物理学的早期创建者之一。上世纪90年代,他又和苏定强等共创了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望远镜(LAMOST)方案。1993年,为表彰他对天文事业的贡献,中国紫金山天文台将3171小行星命名为“王绶琯星”。
在科学研究和诗词创作的方法上,王绶琯则认为有很多共通之处。王绶琯说,在做科研时,他每天早上到单位的第一件事,通常都是去图书馆查阅一遍最新的科技文献,感觉有价值的就会记下来。作诗也是一样,当读到别人的好诗或在生活中对自然、人生有所感悟和触动时,也会“储存”起来,当一闪念的警句产生时,就将其条理化、入律、成诗。
王绶琯认为,喜欢某种东西就要自我实现,争取达到最高境界,这也是人生的一大乐趣。学科学,学写诗都是一样的。《论语》的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王先生说,“这句话我们这一代人三四岁时就在念。不断深入就不断会有新的感悟”。他80岁时写了一首“老书新读”,中间两联是:“无弦纸上寻真趣,空谷音中辨故交,句外神情鱼饮水,行间天籁凤还巢。”表达了他的这种体验。
王绶琯在他的《临江仙·书怀》一词中曾写道:“浮沉科海勉相随,人重才品节,学贵安钻迷。”这也是他自身的一种写照吧。
二零零四年中秋
人生几度共中秋 等待戈多白了头
桂魂香溅吴刚斧 凤管音系萧史楼
西江月
眼倦登场作秀 心系闭户雕虫
南顾常怀泰果 西行稍近莎翁
王绶琯细说——做人与治学
本报记者 陈盈
《科学时报》(2004-4-22)
王绶琯:我写的是“人重才品节,学贵安钻迷”。是一首词里边的两句。其实这算不上什么格言,如果一定要让我说,只能算做是一种自勉吧。
记者:“才、品、节”与“安、钻、迷”有什么关系?
记者:《中国院士治学格言手迹》中的格言是您一生做人、治学的凝炼?
王绶琯:我写的是“人重才品节,学贵安钻迷”。是一首词里边的两句。其实这算不上什么格言,如果一定要让我说,只能算做是一种自勉吧。
“安、钻、迷”是张劲夫同志在主持中科院工作时提倡的。当时我们都觉得提得非常好。做科学工作,“安”是一种心态,就是要安心,这对那个年代的人来说,一般是能做到的。那时候人的热情高,工作服从国家需要,即使专业不特别对口,也都能够安下心。“钻”就是钻研,要找准方向钻进去,要刻苦;但光能吃苦还是不一定能有所作为,于是,还应当“迷”。“迷”就是喜欢、痴迷。古人说做学问:“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成了“乐之者”就会迷进去。入迷的科学家不舍昼夜地搞科研,在旁人看来很苦很累。我想他自己肯定不会觉得苦(他是“乐之者”呀)。累则是难免的,但不觉得苦就也会情愿地累。这“安、钻、迷”三个字也是真正做科学的人的愿望,领导来提倡还又多了一层意思:支持你去“安”、去“钻”、去“迷”当时是50年代,已经过了快半个世纪了印象还是挺深刻的。
记者:“才、品、节”与“安、钻、迷”有什么关系?
王绶琯:还有“才”跟禀赋有关,但是对于一个科学家,是“安、钻、迷”使得他的“才”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掘、增长和调动。“才”的发挥是有目的、有方向的,这就回到了“安、钻、迷”的“安”,按前面的说法,是“服从国家需要”,也就是“安”于国家发展科学的需要(今日的“国家需要”,从某些极其紧急的实际任务,到极其宽泛的首创探讨,已经有了很大的个人禀赋发展的空间)。这是方向、是目的。对个人来说,是志向。而科学家的“品”说的是这个“志于科学”的志向能经得起挫折、抗得住干扰。按高标准的要求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这是格言,出自《孟子》,是我们民族素来尊崇的传统品德。有才无品,朝三暮四,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素来是不可取的。还有“节”,指的是“气节”,是“立志”的坚定程度的考验,说大了可以要求到“舍身取义”这样的自我牺牲。《孟子》那个格言中的第三句话:“威武不能屈”说的就是“节”。科学生活中不会老有这么惨烈的牺牲。但是我们中华民族是经历了许多奇艰巨险过来的。所谓“时穷见节义”。“节”是素养,我自己这一代人就经历过国难深重的年月,历史记载里的“节”表达了我们民族的正气,科学史也焕发青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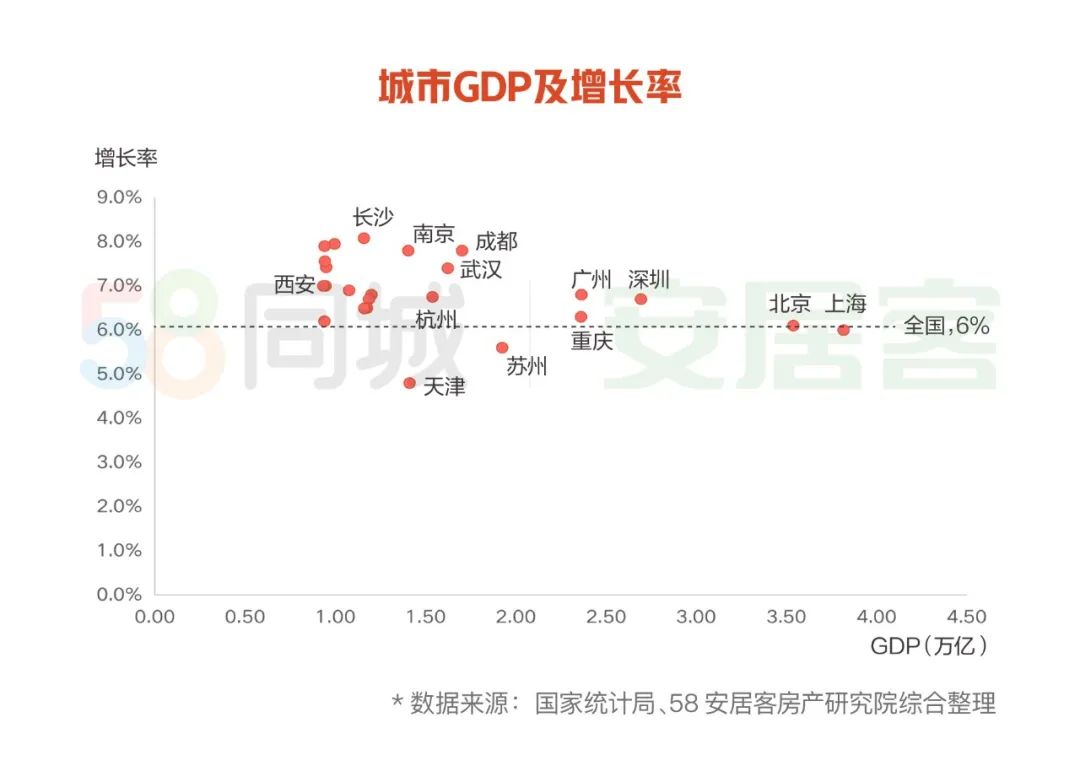



![[图]在解开袋熊立方体粪便之谜后 科学家近日成功实验复现](https://n.sinaimg.cn/spider2021129/449/w700h549/20210129/e65e-kiksqxf6343572.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