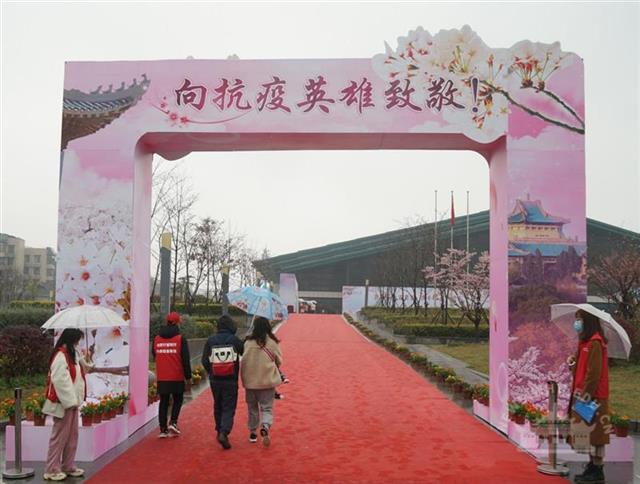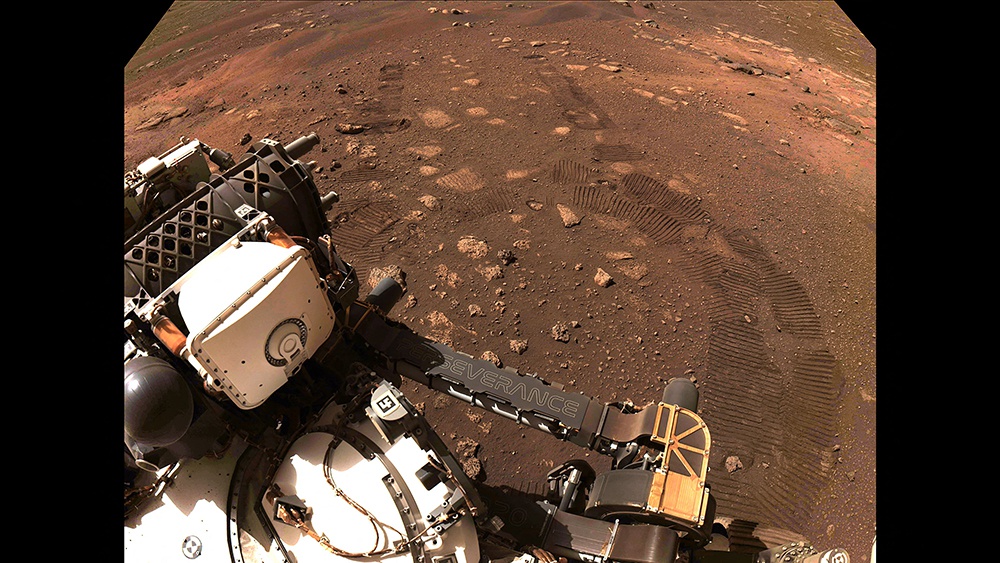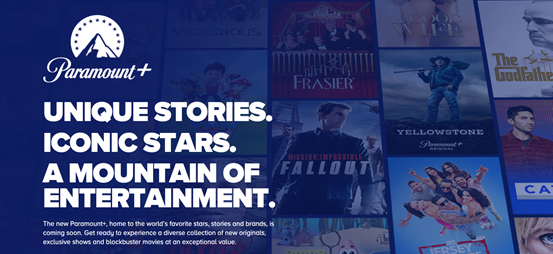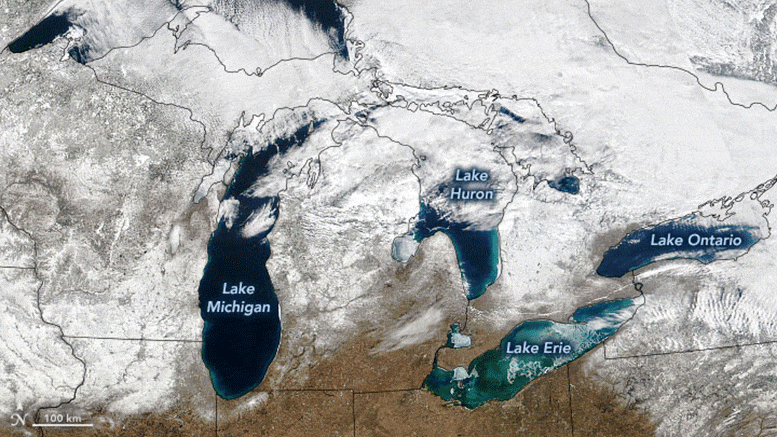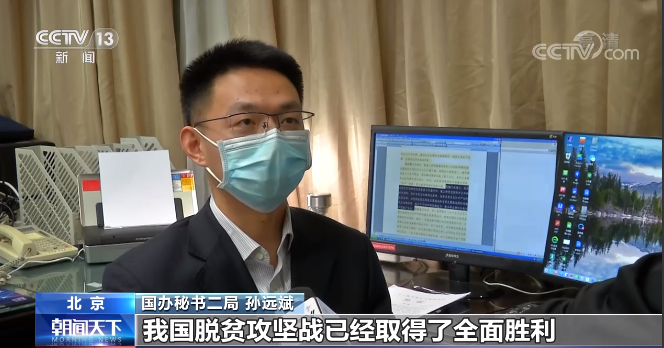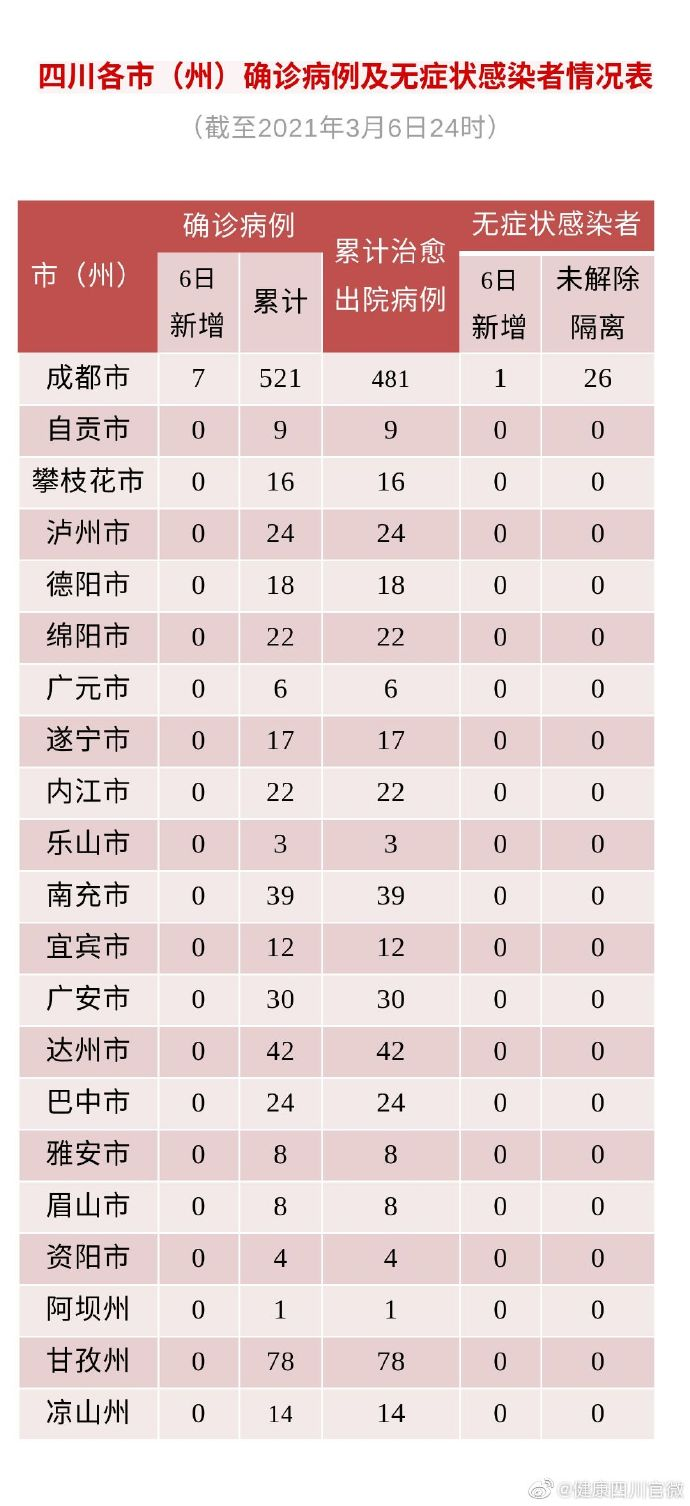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钱玉娟 刘雨琪
你有Clubhouse账号吗?
向经济观察报记者抛出这一问题后,还没等作答,PM3000主理人陈砾雷便“凡尔赛式”地说到,“我在Club-house上和4999人一起听了马斯克说话。”
在2021年早春火爆起来的“舶来品”Clubhouse,不但吸引了聚焦产品案例分析的陈砾雷,当他将自己对这一产品的体验分享到朋友圈时,发现包括微信、微博等在内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几乎被“求邀请”、“来互关”等关于Club-house的消息刷屏了。
远望资本创始合伙人程浩也从另一层面感受到了,Clubhouse基于实时音频技术带来声音社交,这一现象级的火爆。不断有创业者来咨询他,“能不能在中国也复制出一个类似的产品?”
热潮再起
Clubhouse诞生于海外疫情正肆虐的2020年4月,而声音社交并非其首创。即使在海外,与其同处一个赛道中的还有Tiya、Chalk、Rodeo等应用。
更为实际的是,在声音社交领域,有不少产品madeinChina,像Tiya就是由“中国在线音频第一股”荔枝专门打造的一款出海社交产品。
当然,并非只有荔枝最先发现了声音社交的机遇点。据悉,Tiya做了两年,最终于2020年10月在美国上线。早在Tiya出海前,国内不少移动社交领域中的玩家,围绕音频技术展开产品创新,像音遇、Soul等以声音社交为主题的应用,甚至成为2019年社交应用市场的黑马。
除了上述将声音作为社交要素,“完全奔着社交目的”的App外,专注对网络用户行为进行研究的华中科技大学传播学系硕士生导师李雪莲还提及了像播客这种,大家相对熟悉的模式产品,“这种社交性相对要弱一些,媒体性更强。”
正在湖北一高校就读的女大学生小谢,在去年疫情期间接触到了播客,“大一时因为孤独,总喜欢用喜马拉雅等来听有声书、段子和评书。”起初只是为了让自己的身边有个声音陪伴,小谢的目的简单直接。
但渐渐的,小谢发觉自己喜欢上了用播客听一些学术性较强的节目。“这些节目中的学者们会分析与讲述,比我自行阅读论文要更方便。”在她看来,学术研究本质上就是一个交流与讨论的过程,尽管她还没有用播客进行社交,但“它(播客)确实构成了我现实社交缺乏时的一个补充。”
有别于小谢,25岁的长沙姑娘陈小姐向记者讲述起了她在猫耳App上的“声音恋人”体验。
“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我经常会在平台上听着温柔男声说晚安,仿佛自己就有男朋友。”她心里清楚,这是一种虚拟的社交方式,但通过声音社交进一步充实了她对爱情的想象。
记者对话的几位声音社交产品用户,在采访中都不约而同的认为,声音不只是传达出内容,效果往往比文字、视频更有温度。
“电脑屏幕已经够冷了,总要找个方式取暖吧?”在互联网大厂美团工作的孙先生,是一名典型的程序员,过去两年间,他习惯了在通勤时间听播客。
孙先生说,不看视频既是为了让眼睛休息,还有另一层原因,“听播客更能把我带入虚构的情境中。”在他看来,利用镜头语言拍摄出来的视频往往让人觉得是一个刻意制造的产品,而单纯的声音让人对场景的想象是,“主持人和嘉宾正在圆桌旁进行交流,而你就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他们的讨论。”
产品有别
从Clubhouse这个产品诞生后,荔枝创始人兼CEO赖奕龙也一直在用,但更多是“在研究”。
在他的理解中,这个产品“就像是一个在咖啡馆聊天的方式,非常亲近地引入了语音房。”即使在中国已有的元素里面,Clubhouse跟人的行为、社会的行为结合的都非常深。
谈及中国大部分产品,赖奕龙并不避讳谈及其中的表演性质、娱乐性质。“Clubhouse它不是一种表演。”他对这一产品在信息传递的及时性、互动性及内容性、社交性等方面的创新予以赞赏。
尽管每次登陆Clubhouse都要打开VPN,陈砾雷觉得这一步繁琐没什么太大影响,毕竟能第一时间follow全球商业“大佬”马斯克,还能查看不少“高阶”活跃用户的动态、观点言论等。最吸引他的是,即使身在不同国度、空间,“不需加好友”,就能通过平台进入“高阶”用户所在的主题房间,自由听取对谈,甚至有机会“举手”发言进行交流。
“社交是具有阶层性的,真正有效的社交只存在同一个阶层内。”陈砾雷以Soul这一声音社交产品为例说到,“Soul不能上传自己的照片,就算是视频聊天都会默认戴头套。”他认为这种通过群聊派对,聚焦初入社会的年轻人,带来的“无关乎收入、地位的社交方式”,正呼应了“Soul”的名字,让普通年轻人有机会向别人展示自己的灵魂,给了这个群体一个平等的社交机会。
虽然Clubhouse也致力于建立熟人网络,比如邀请制、希望每个人都用真名,但它并非放低社交门槛。另外,对于精英阶层间展开的“在线沙龙”,用户依然可以通过搜索房间标题找到并进去听讲或交流。这一点又让Clubhouse具备了一定的媒体属性。
国内虽然有非常多依托声音来进行社交的平台,但李雪莲觉得大小不一而足,多是聊天室的形式,“实质上都是一个点对点的互动模式”。
而Clubhouse能够做成这种实时社交的开放性的超大平台,她认为,“这应该是每一个媒介研究者都会关注的话题”。
公开属性,且最多能够同时允许5000人在线,Clubhouse极大地扩展了社交互动的空间。实际上,李雪莲的关注点,正是目前不少跟风Clubhouse推出声音社交产品的平台要突破的方向。
映客直播推出的语音社交App“对话吧”,产品从研发到测试上线仅历经6天时间,除夕当天上线后也同样采取了邀约制。
在“对话吧”上线9天后,映客董事长奉佑生在线上“组局”,其中包括朱啸虎、周亚辉、包凡这样的创投圈大佬在内,进行了一场名为“在中国能做成一个Clubhouse吗?”的对谈沙龙。
但是不足一天时间,“对话吧”临时从应用商店下架,彼时官方对外表示,由于在线人数近万人,为保障后续产品体验,后台需进行技术升级和相应的形态调整。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赖奕龙细看Clubhouse的产品逻辑和底层想法“非常奇妙、精妙。”特别是在产品想象力方面,他认为中国多数声音社交产品是“大家一起围观,然后有一个表演,没有想到把生活中社交的自然形态搬到一个产品上来。”
若从娱乐化互动的层面来分析,赖奕龙认为中国的产品处于领先。毕竟Clubhouse里面的功能相较简单,而中国语聊类产品中的玩法非常丰富,又融入了很多互动方式。这也是他提及中国产品较之Clubhouse最大的差别。
等风的人
谈及声音社交产品的共通之处,赖奕龙说,都是“相信语音社交是下一代的社交”。但他以荔枝旗下的Tiya为例讲到,团队基于一些轻松娱乐“玩”的场景来开发,最不同的地方是“我们走向大众化、娱乐化,他们(Clubhouse)走向传播类、内容类。”
在他看来,不同路线切入的受众群体自然不同。Clubhouse更聚焦精英人群,而像Tiya这样的App则面向大众人群多一些。
映客旗下的“对话吧”正“镜鉴式”模仿Clubhouse。不论在内测邀请初期以高阶、优质的行业大V居多,开设活动也多是知识分享类。
在程浩看来,荔枝通过Tiya出海,扎根海外做声音社交“会有些机会”,但目光转移至国内,声音社交这个模式,“与映客也没什么关系”,他甚至在采访中建议,“像创业公司以及只有一定体量的公司就别参与了”。
抛开投行身份,程浩作为迅雷创始人,也算是一位在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浪潮里久经考验的创业老兵。“声音社交是个热点,但坦率讲,跟创业公司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他建议,创业公司一定要找大公司看不上或没看懂的东西做,那才有希望。
程浩回忆起当初创立迅雷时,虽然没花过什么市场费用,“只要产品做得好,下载快,我们根本不愁获客”,他形容彼时的用户能像滚雪球一样的增长。
而今移动互联网时代,产品迭代之快,市场环境也大不一样了,“流量红利都没了。”在程浩看来,创新一款声音社交产品,获客是一个大门槛。
实际上,对于一切纯App领域的创业想法,程浩都不鼓励,“你已经没有韬光养晦的时间了。”他会如此直截了当地劝诫创业者们,建议他们换个赛道。
程浩认为,创业公司“没法防御巨头的流量碾压”,就算花大价钱买流量,对比互联网巨头拥有的流量矩阵优势,“根本没戏”。
诚然,Clubhouse带动了声音社交风口再起,但基于国情及相应的一些审查制度,程浩也无法确定中国版Club-house能否做成,但他揣测,最终能把这一模式跑通的,或是腾讯、字节跳动等既有运营经验又有流量的巨头。
上述程浩提及的两大厂是否早已筹谋其中,不得而知。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微信创始人张小龙也“身”入Clubhouse,更有人偶遇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在Clubhouse中讨论起了技术发展。
在声音社交再次涌动起热浪的当下,以社交为根基的巨头腾讯会作何创新?陈砾雷在此期间看到不少文章就微信与Clubhouse进行分析,他仅基于社交的底层逻辑看,Clubhouse在维持同阶层社交关系的同时,还打通了非熟人之间的社交通道,但“这个通道,是微信不具备的”。
采访中,陈砾雷将熟人关系链比喻为微信的“命根子”,在他看来,微信是否值得“破圈”去做中国版的Club-house,这个答案或许只有马化腾或张小龙可以给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