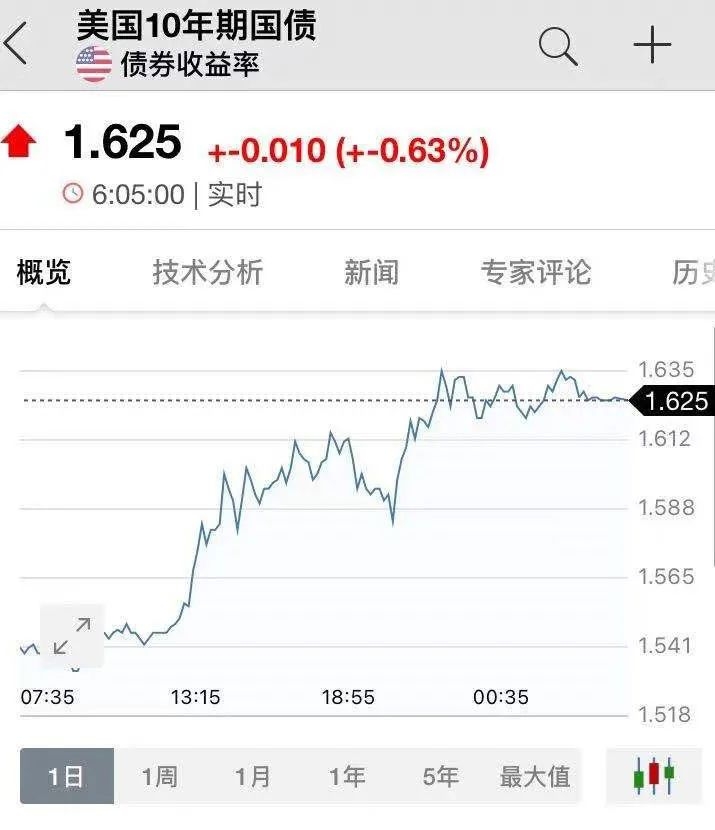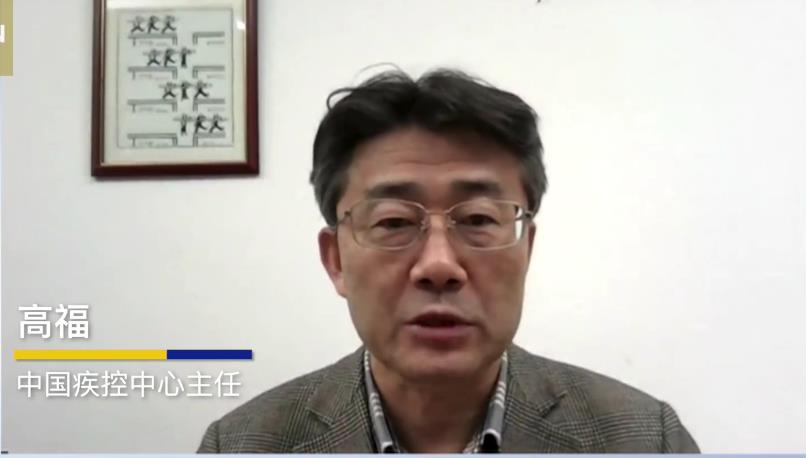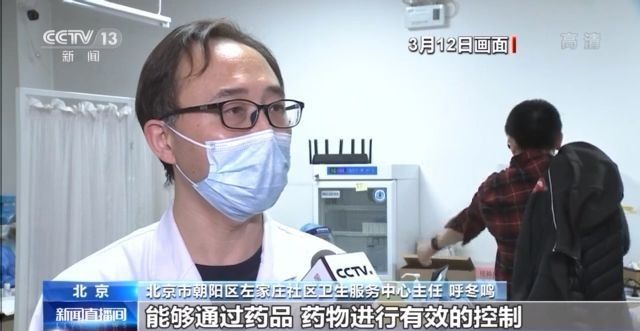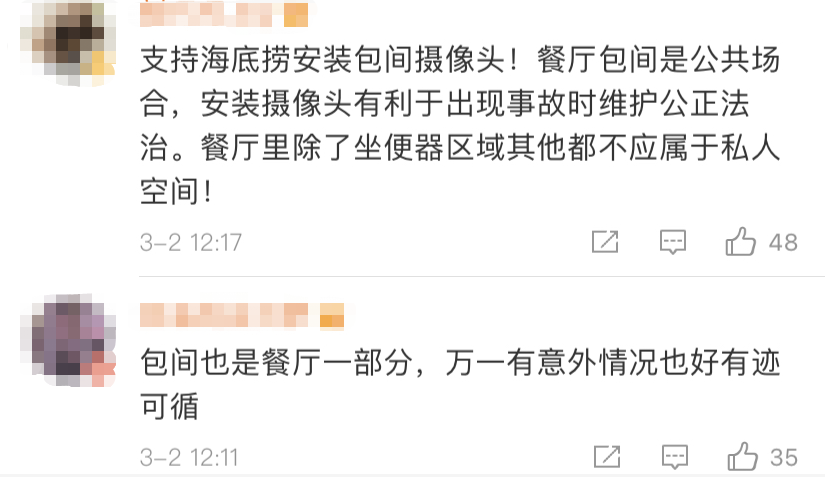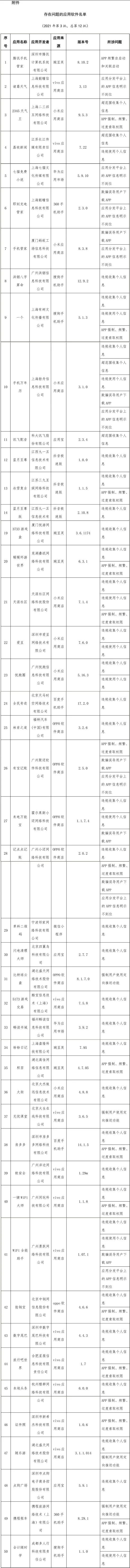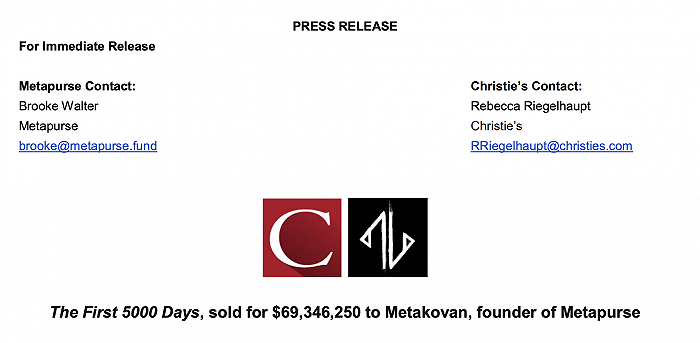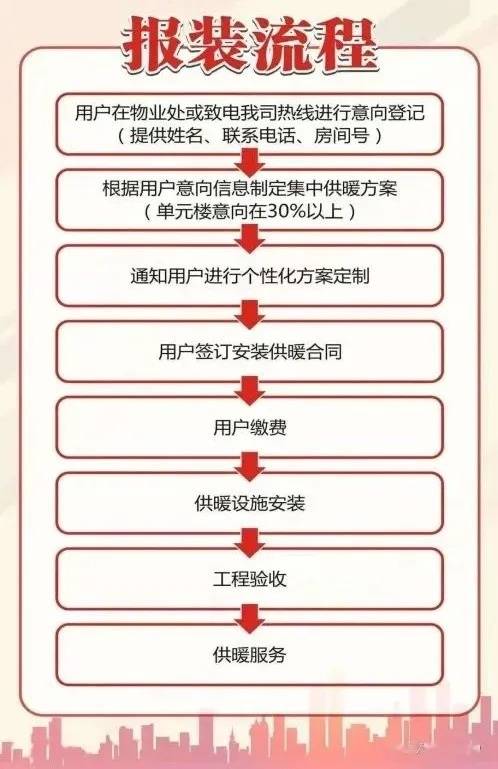原标题:病人庞麦郎
原创 范志辉 音乐先声 收录于话题#音乐人8个
作者 | Echo 编辑 | 范志辉
当庞麦郎这个名字再次闯入视野,我们首先想起的一定是那双已经被遗忘许久的“滑板鞋”。经纪人白晓在视频中宣布庞麦郎已经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时,他提到,“那双滑板鞋,我也是很久之后才明白它的意义”。
至于那双滑板鞋究竟代表什么,他没有给出具体的阐述。拥有无法被定义的一类象征,是所有作品得以广泛传播的共性,唯此,它的意义才是可以流通的。我们可以说滑板鞋是一个漫无目的的梦,也可以说它是那天上照耀着满地便士的月光,它同时也可以是滑板商家用于推广产品的一个最好用的梗。 如今看来,这首歌所处的分裂语境,以及庞麦郎从一夜爆红到《惊惶庞麦郎》之后的备受攻讦,无一不预示着他的病理状态——精神分裂症。
如今看来,这首歌所处的分裂语境,以及庞麦郎从一夜爆红到《惊惶庞麦郎》之后的备受攻讦,无一不预示着他的病理状态——精神分裂症。庞麦郎和他的“滑板鞋”
回溯庞麦郎的走红,关于那首有着诸多传奇色彩的《我的滑板鞋》究竟是华语乐坛史的一个Bug还是奇异的灵光一现的争论仍在继续。
从专业主义、传统审美以及工业标准来看,这首歌的词和曲都不符合基本的规范。可是,神曲之“神”,往往不在于音乐特点本身,而在于引发大众狂热参与的“神传播”。
何以引发最广泛的传播?猎奇只是其一,共鸣才是核心。 从歌曲本身呈现的意象来看,“梦想”是一个崇高的词,“滑板鞋”这种批量生产的东西,则是工业化中非常廉价的一个词。但是,当滑板鞋所能够赋予人的滑行姿态与粗糙的现实对人的摩擦形成对比,我们可以瞬间明了梦想着拥有一双滑板鞋的意味。
从歌曲本身呈现的意象来看,“梦想”是一个崇高的词,“滑板鞋”这种批量生产的东西,则是工业化中非常廉价的一个词。但是,当滑板鞋所能够赋予人的滑行姿态与粗糙的现实对人的摩擦形成对比,我们可以瞬间明了梦想着拥有一双滑板鞋的意味。当我们刨开一切可能的解读空间,回归到他的真实创作动机来看,作者最初就只是为了表达当拥有了小时候梦想已久的一双滑板鞋的愉悦心情。但在歌曲传播过程中,这种发自本心的愉悦却沦为一种笑料用于娱乐大众,源于他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在现代化的大城市里不过是多数人唾手可得的事物。
这种错位,是社会性的,也是时代性的。 当一个人最梦想的东西——滑板鞋,这里展现出的是乡土与城镇的碰撞。联系庞麦郎出生农村却梦想着成为国际化巨星的心态,以及从一夜爆红到精神病院的悲剧性际遇,这种碰撞具有明显的时代意识形态烙印。在这种巨大的错位之间,庞麦郎试图以一套属于自己的语言体系构建他自己的王国。他把陕西称为“孟加拉斯图”,把汉中称为“加什比克”,全国有200多个城市被这样的庞氏英文命名。他觉得这样更加国际化。
当一个人最梦想的东西——滑板鞋,这里展现出的是乡土与城镇的碰撞。联系庞麦郎出生农村却梦想着成为国际化巨星的心态,以及从一夜爆红到精神病院的悲剧性际遇,这种碰撞具有明显的时代意识形态烙印。在这种巨大的错位之间,庞麦郎试图以一套属于自己的语言体系构建他自己的王国。他把陕西称为“孟加拉斯图”,把汉中称为“加什比克”,全国有200多个城市被这样的庞氏英文命名。他觉得这样更加国际化。 或许正因如此,贾樟柯才会评价这首歌让他为之哭泣,他总是为底层社会中无法化解的结构性孤独而哭泣,为那些被巨大的历史跃进拖着走的时代而哭泣。总之,我们很难将这首歌的质量与其热度之间的矛盾简单地归结为偶然。
或许正因如此,贾樟柯才会评价这首歌让他为之哭泣,他总是为底层社会中无法化解的结构性孤独而哭泣,为那些被巨大的历史跃进拖着走的时代而哭泣。总之,我们很难将这首歌的质量与其热度之间的矛盾简单地归结为偶然。从庞麦郎身上重新认识疯狂
当庞麦郎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这个消息在被扩散开来,人们开始纷纷猜测他走向疯狂的原因,对此普遍存在两种论调,一类认为这源于艺术家心智与现实格格不入的永恒冲突,一类认为这是一夜爆红后无法承受的巨大心理落差。而庞麦郎的个人形象也在这两种论调中游移在艺术家与庸人之间。
庞麦郎走向疯狂的原因自然是多重且无法确知的,明晰的只有人们是如何看待他身上的疯癫的,这也是更值得讨论的。 不久前,一条2012年排查疑似精神病患者的旧闻被重提。其中,“无故不上学、不上班、不出家门、不和任何人接触”、“对人过分冷淡,寡言少语、动作慢、什么事情都不做,甚至整天躺在床上”、“过分话多(说个不停)、活动多,到处乱跑,乱管闲事等”等11个问题成为衡量疑似精神病患者的线索。
不久前,一条2012年排查疑似精神病患者的旧闻被重提。其中,“无故不上学、不上班、不出家门、不和任何人接触”、“对人过分冷淡,寡言少语、动作慢、什么事情都不做,甚至整天躺在床上”、“过分话多(说个不停)、活动多,到处乱跑,乱管闲事等”等11个问题成为衡量疑似精神病患者的线索。由此联想到今日庞麦郎被强制入院,我们会发现,在理性主导的现代社会,我们关心的不再是“疯癫是什么”,而是如何矫正非正常行为。然而,何为正常?
我们的常识大都由“排斥”的方式建立起来,因为只有在表达互斥的语法中我们才能通过厘清事物之间的区别而快速认识它们。反之,一旦我们发现它们总是有所勾连、交叠覆盖,我们便很难对一个甚至是最基础的事物做出判断。错误往往发生于,我们这种构建常识的方法被用于对他者的认识上,便造成我们对人性的忽略。 而庞麦郎入院事件在舆论场中引发的巨大骚动,虽然其中不乏并不礼貌的指指点点,但总算是将大众的目光同时聚集于精神病这一症状与个体的人性之上。由此,我们得以从庞麦郎身上重新认识疯狂。
而庞麦郎入院事件在舆论场中引发的巨大骚动,虽然其中不乏并不礼貌的指指点点,但总算是将大众的目光同时聚集于精神病这一症状与个体的人性之上。由此,我们得以从庞麦郎身上重新认识疯狂。福柯的《疯癫与文明》如此总结疯癫的历史进程:在文艺复兴时期,疯癫是神秘的启示;在古典时期,是罪恶;在近现代,是病情。而在对庞麦郎入院的讨论中,他的疯癫涵盖了以上所有特点。
凭借《我的滑板鞋》这一略显疯癫的作品走红,他的天才无疑与神秘的启示有了联系。当被经纪人告知他患有精神病多年,大多数人都认为这并不让人意外,因为他的举动一直就不太“正常”。 那么,以上这些关于疯癫的认识,是疯人应得的吗?对此,福柯认为,疯癫的历史只是一场理性的独白,疯癫自身却是沉默的。因为疯癫被拒斥在理性话语之外,失去了发言的地位。就如被强制入院的庞麦郎,早已失去了与喧哗舆论对话的机会。
那么,以上这些关于疯癫的认识,是疯人应得的吗?对此,福柯认为,疯癫的历史只是一场理性的独白,疯癫自身却是沉默的。因为疯癫被拒斥在理性话语之外,失去了发言的地位。就如被强制入院的庞麦郎,早已失去了与喧哗舆论对话的机会。排版 | 安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