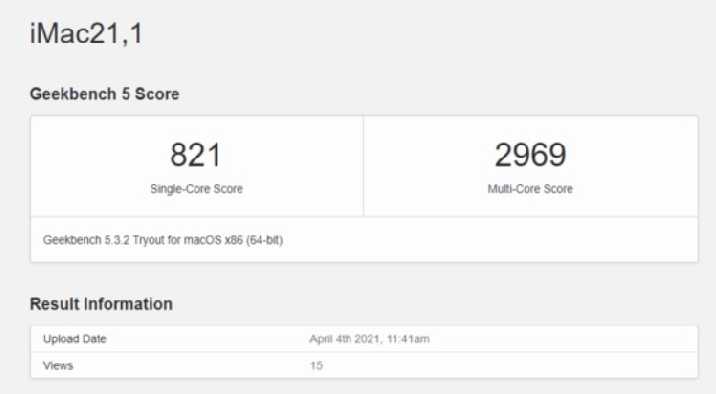来源:第一财经

本文字数:2584,阅读时长大约4分钟
导读:在《男孩》中文版的前言与后记中,都一再强调南非独特的历史地理背景对库切及其“男孩”所造成的巨大心理影响。这过于简单化,太历史决定论,也太地理决定论了。
作者 | 割麦子
库切的小说《男孩》,副标题,是Scenes from Provincial Life,“外省生活场景”。相应地,《青春》则是“外省生活场景之二”。这里,Scenes应该是某种有布景的场所,而Provincial则不仅是地理上的“外省”,还是这种“场所”的“心理特性”:粗野、偏狭、受贬斥、受诅咒,一句话,一个低等野蛮的“异域”。
《青春》里的事件实际上发生在伦敦,但它依然是“外省生活场景之二”,不仅仅因为它是《男孩》的续篇,更重要的,这种“外省性”是“他”——也就是库切自己“随身携带”的。这个“场所”不仅是地理性的,更是心理性的,如果我们记得对弗洛伊德来说,潜意识恰恰就是一种“场所”,一种被意识的“首都”挤到边缘的广阔然而粗野的受诅咒的“外省”。
对这位出生于南非而长期生活于英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来说,这两种意义上的场所,即地理的和心理的,是重叠的,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相互激发,彻底难解难分。它既是相对伦敦来说的南非,相对南非开普敦来说的伍斯特,相对开普敦富人区及其贵族学校来说的普拉姆斯戴德及其圣约瑟夫天主教学校,又是相对英国移民来说的“阿非利堪人”(荷兰移民后裔),相对基督徒来说的冒充的天主教徒,相对笼罩性的母爱来说自觉只是某种“被爱物”的儿子,相对人人手执教鞭的老师来说“必然要受罚”的学生,相对农场的主人们来说的过客——而且是过客中的“儿子”,相对生活“正常”的一家子人来说摔断了腿最终死在养老院里的“安妮阿姨”以及她终身为其父守护着的那堆角落里永远卖不出去的“著作”,甚至是相对正式的校际板球比赛来说自家院子里的模拟击球和接球训练(“他”对这种另类的简陋的“自我比赛”的热情有时候超过了“正式比赛”,就像有时候他会觉得自己热爱伍斯特超过开普敦,热爱南非超过英国,尽管在大部分时候,当他身处那些“外省”性的“场所”,即坐标上负的一面,他无疑渴望的是那些“正面”的东西)。
并不是说,处在“外省”的位置就是引起创伤的原因,“中心”也逃不脱,比如说,中心的中心,伦敦或者巴黎,也会有图森式的中产阶级“创伤”——库切也曾借伊丽莎白·科斯特洛之口说:“中产阶级安全的想象是危险的。”创伤不是来自一极的低贱,而是来自两极的对举。创伤总是相对的。当你选择了,尤其是被迫选择了,那些失去的,从指缝间滑走的,就成为创伤。因此创伤是普遍的,是无处不在的。什么都可以成为创伤,你的获得,很可能成为他的创伤,而甚至他的失去,也有可能成为你的创伤。让我们来看库切的实例。
“学校里男孩总是要受罚的。几乎天天如此。男孩们被喝令弯下腰去,手要碰到自己的脚指头,然后还要挨教鞭。”通常,我们会认为一个孩子受到体罚,无疑是他的一种童年“创伤”。但问题远不是这么简单。库切告诉我们——实际上这是每一个孩子真正深刻的体验——如果你身处一个普遍体罚的大环境里面,那么无论是不是被“扁”,对孩子来说,都是一种“创伤”经历。如果被扁了,“光是想想这个念头就叫他羞愧难当……他知道皮肉之苦不是自己最要命的心结。如果别的男孩受得了,他也能受得了……他怕的是羞耻,这可是最令他胆怯的,要是轮到他被叫出来,他会紧紧攀住课桌不放。这会招来极大的羞辱:这会使他崩溃,也会招致其他男孩来跟他挑衅。如果有朝一日轮到他被拎出来暴扁,受了奇耻大辱的他就再也不会回到学校里了;最后走投无路就只能自杀”。因此他在班里从不出声,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家庭作业完成得很好,课堂提问总能给出正确答案,怕的就是出错。“但事情怪就怪在这儿,只有挨上一顿暴扁才能打破他一直担心被打的恐惧。他很明白这一点……如果真是如愿以偿地被痛扁一顿,从另一方面来说,他就有可能变成一个正常的男孩,就能轻松地加入关于教师和教鞭的讨论了,交流各自遭受的不同等级的痛感程度。可是,他自己却没法越过这道坎。”
当众遭受体罚是一种侮辱,是对他的一种否定,因此是“创伤”;但如果大家都受罚了,唯独他没有,那么他就成为一个“异类”,成为一个大环境中的“外省”,从而无法获得足够的认同感。“他从来没有挨过揍,对此深感羞耻。他没法轻松地触及教鞭什么,不像这些男人(他父亲及其兄弟们)对这事儿几乎就是心领神会。”这种游离和不被承认,也是一种“创伤”,甚至对于“成长”来说,是更致命的“创伤”。
另一个例子。“他知道母亲是爱他的,但问题就在这儿——她置于他那种爱,实在不对头,却总是逼上来。她一切的爱都包含着十足的戒意,好像随时准备扑过来,保护他,把他从危难中拯救出来。”当“母爱”一再被浅薄地加以歌颂的时候,它的泛滥在社会学意义上可能对孩子造成的伤害,特别是以它的名义而行的某种吞噬性的占有欲,却总是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法国大革命振奋了日后亿万人心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前两个已经经受了各种甚至是极为激烈的批判,唯独“博爱”,却似乎成为了一种默认的碰不得的意识形态,从最激进到最反动,不管对自由或平等持何种绝然对立的态度,对于博爱,却众口一词,争相引之为最后的护身符。可是稍微理性地思考一下,套用“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的句式,我们又何尝不可以说:“爱,多少占有假汝之名”?库切的另一部小说《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给我以最深刻印象的,正是他对于这种司空见惯极为“日常”的“自私的博爱”所做的鞭辟入里的揭示。
在《男孩》中文版编辑和译者所写的前言与后记中,都一再强调南非独特的历史地理背景对库切及其“男孩”所造成的巨大心理影响。作为问题的一个方面,这并没有错,但却过于简单化,太历史决定论,也太地理决定论了。事实上一种历史地理的社会现实,并不是直接投影到一个人的心理上,一一对应,仿佛石头和它的影子。心理的动因会为自己“创造”出相应的地理实在,粉饰它、丑化它、建构它、改造它。因此你很难说清楚一种歧视性区分的根源,到底是地理因素还是心理因素。实际上这两个因素是互为因果的,不需要去强行找出那个唯一的“第一因”。“创伤”既来自于“场所”,又需要“场所”来搬演,但“场所”本身却伴着“创伤”戏剧千差万别的上演方式,而一次又一次地再生和重构。

《男孩》
J.M.库切 著 文敏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