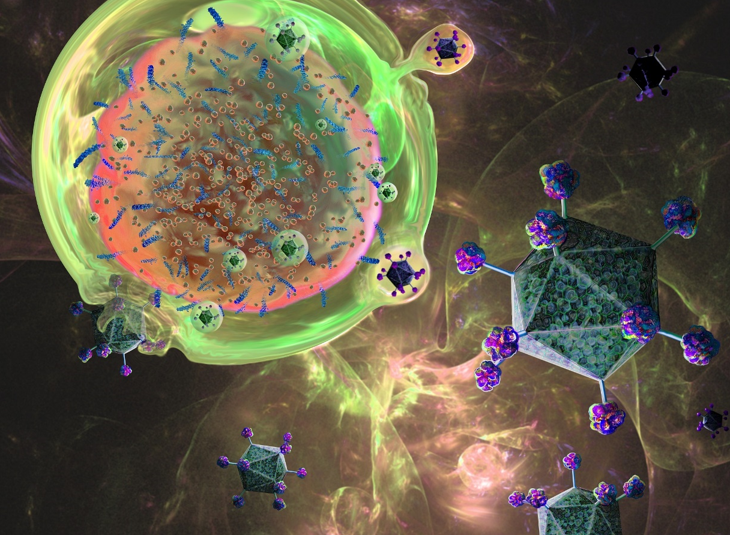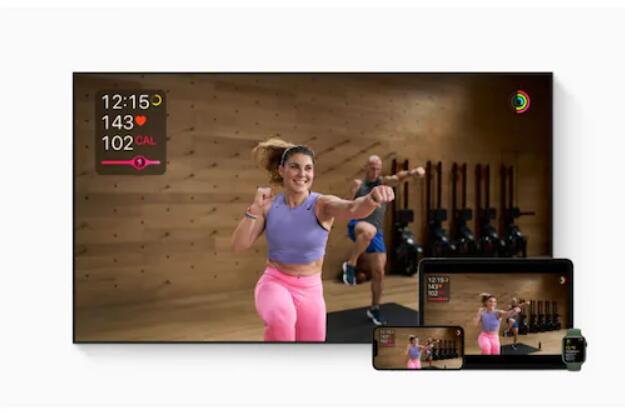原标题:当“取消”走向“审判”:小说写到种族主义,萨莉·鲁尼便是种族主义者?
 萨莉·鲁尼最近推出的新书成为了第一世界评论家们的关注焦点 图片来源:Linda Brownlee/The Guardian
萨莉·鲁尼最近推出的新书成为了第一世界评论家们的关注焦点 图片来源:Linda Brownlee/The Guardian社交媒体并不会凭空创造出告密者和说谎者。抱有恶意的人总是会捏造出各种诋毁之语,而听话只听表面的人则总是会把委婉混同于罪过。当刻意的无知与汹涌的恶意得到的是奖赏而非鄙夷,互联网的作用也不过就是极度强化这些历史上早已有之的阴暗时刻。
在乐观主义占主导的时期,人们很容易对毁谤他人者表示同情。在《正常人》里,萨莉·鲁尼(Sally Rooney)笔下的女主人公有这样的思考,“残酷所伤害的并不只是受害者,加害者本人也无法幸免,并且后者所受的伤害很可能更深重、更持久。”受害者也许可以走出来,加害者则必须与“自己是个恶棍”这一认识共度一生。
鲁尼的《正常人》出版于2018年,这一年乃是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从偶尔可见的小插曲迈向暴烈的审判运动的转折点。就算加害者较其目标“所受的伤害更深重也更持久”,这种痛苦也丝毫未能减缓真假参半之消息的传播,以及显而易见之谬误的扩散。
鲁尼提供了一个恶意如何把自己打扮成美德的绝佳案例。由于最近出了新书《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Beautiful World, Where Are You),她成为了第一世界里评论家们的关注焦点。在竞争如此激烈的环境里,要做些什么才能先声夺人地吸引眼球呢?今天就有了一个现成的答案:把你的目标打成种族主义者。即便这一指控很快就被证明是子虚乌有的,其引发的恐惧程度在如今“进步主义”的西方,也足以让某些编辑和读者找到各种逼迫人噤声的借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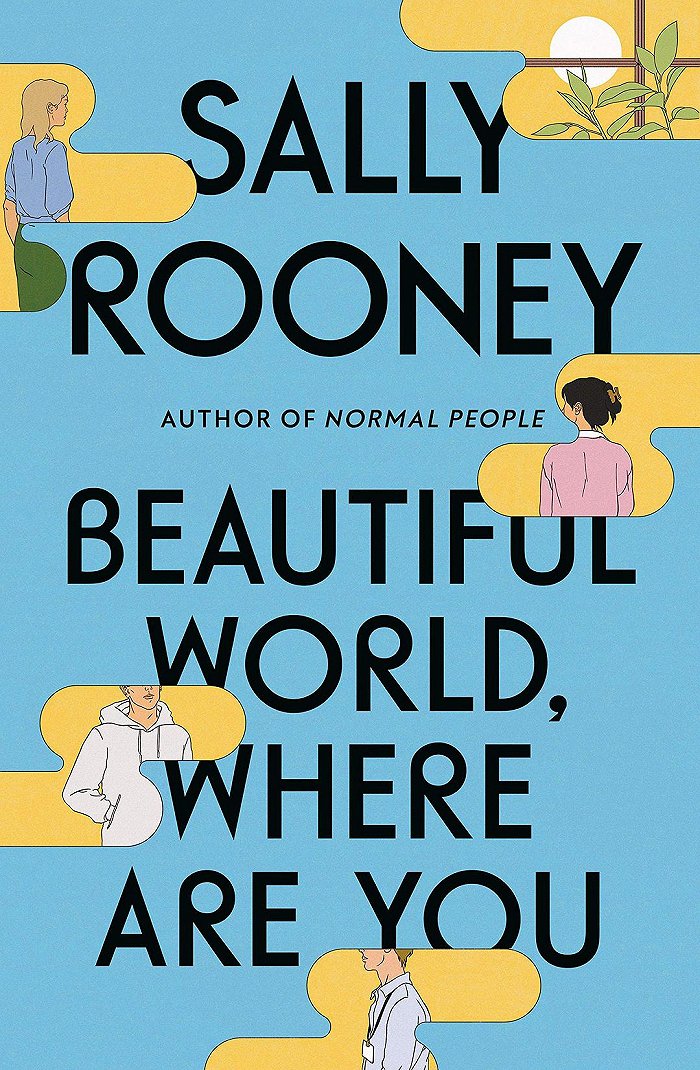
《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
《悉尼先驱晨报》的伦理卫道士们声称“不愿误导”以及“对借助于无情的虐待来获取满足的做法不感兴趣”,对鲁尼发起了长篇大论的批判。其评论员杰西·杜(Jessie Tu)竭力吹嘘自己是多么地勇敢,因为她敢于否认鲁尼是一位有趣的作家这一共识,接着又声称,“《正常人》应该被称作《白人》,因为在鲁尼的世界里,像我这样的人根本就不存在。书中提到的亚洲人都是游客,只说他们把意大利各大博物馆门口的道路堵得水泄不通。‘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在威尼斯这么折腾——那里全是看到什么东西都一阵猛拍的亚洲人,’一名男性角色如此抱怨道。”
这篇批判文章上线时,我正好在读那本书,然后发现了其中的反亚裔心态。这些话来自书中的一个不甚讨人喜欢的男人杰米。他在鲁尼笔下的形象是个游手好闲、行为放荡的富家公子哥。一名评论家能犯下的最低级、最愚蠢的错误,莫过于对作家及其笔下的角色不加区分。在书中,杰米当即就受到了批评。一名一同用餐的男子对他说:“你这个天杀的总归会和亚洲人打交道……刚才你针对亚洲人说的那些话有种族主义性质。”
此处最为明显的恶意,体现在作家就是她笔下的角色这一看似可靠的假设上,也表现在忽略文本中的间接证据上。种族主义指控一旦成立,那这本书的主旨就可以被说成是“两个白皮肤的、身体健全的、相貌出众的异性恋者在思考成为一个白皮肤的、身体健全的异性恋者是多么地艰难”(但这种说法和种族主义指控皆站不住脚)。
有时,当我试图谈论一些进步派的“猎巫者”时,我会得到这样的回应,那就是我应该把自己的精力放到谴责那些掌握实权的右派诽谤者上面。我的确有这样做,也承认这种说法在英格兰的确成立,有威权主义倾向的保守派享有比进步派对手更大的权力,并利用它来清算BBC以及政府机构里的不同意见,但尼古拉·斯特金治下的苏格兰则根本没有这回事。
不过这严格来说不算斥责。你应当能同时反对左派和右派当中最恶劣的那一部分。主张由于你在道德上和鲍里斯·约翰逊可以等量齐观,你便可以基于自己选择性的道德观而得到辩护,这种说法根本算不上有效的论证。
在任何情况下,实施伤害的权能都是相对的,取决于你所处的位置。就自由派文化人圈子而言,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公开受到进步派羞辱的恐惧都要远大于对国家惩治的恐惧。如果羞辱是正当的,那也就罢了,但如果批错人了又当如何?
这些问题在今天几乎不可能有答案。人力资源部门和警方永远也不会让希望明辨举报之真伪的研究者查看他们的档案。不过,20世纪的一些独裁国家已公开的档案却足以证明放任无视真假的批斗之风盛行将会导致何等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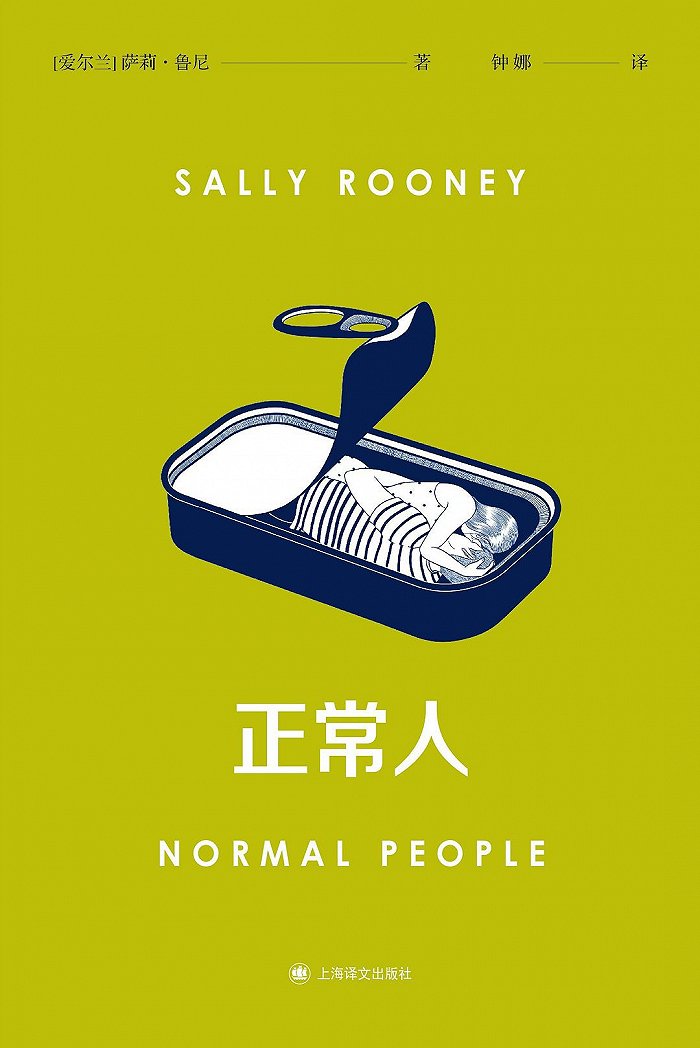
《正常人》
[爱尔兰]萨莉·鲁尼 著 钟娜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群岛图书 2020-7
据一些研究纳粹德国秘密警察档案的历史学家估计,在向秘密警察毁谤告密的案件中,有40%的动机为个人恶意:妻子想要休掉她的丈夫以便和情人在一起(亦有相反的情况),而一些员工也把办公室政治玩到了极致。今天你依旧能听闻其微弱的回响。在竞争白热化的出版业市场里,公众的政治愤怒可能让一些人找到借口,因为单纯的文学上的妒忌心,便利用它来逼迫对手出局。美国曾有一个大快人心的案例,某作家曾以挪用男同性恋题材的指控来打击同行,但后来他也因为将塞尔维亚人对巴尔干穆斯林实施大屠杀的题材用作某个甜蜜爱情故事的背景而落到了同样的下场。
在英国,许多作家已经留意到了文学组织的沉默,这些组织大多受一些低级的文化官僚管辖。它们的初衷原本是为了保护作家,使之免于恐惧并不受金主宰制,但在JK·罗琳面临一波又一波的死亡及强奸猥亵时却无动于衷,没有提出任何谴责。
一项来自东德的研究同样富有警示意义,它涵盖了1945年希特勒覆灭至1989年柏林墙倒塌这44年的时间。历史学家赫德维希·李希特(Hedwig Richter)曾记录下,东德人如何在无人授意且自己也没有告密的法律责任的情况下主动向上级举报他人。指控使他们有了一种希望,认为国家会因此而善待他们,而他们也可以“在今后避开一些潜在的问题和误会”。这种取悦他人的倾向戏剧化色彩较少,却构成了左派(以及右派)打压异端的持久危险。人们因恐惧而被迫和他们保持一致,担心稍有不服就会被打成异端分子。其结果便是这样的文化氛围:表面上自信满满,实质上毫无建树且唯唯诺诺。这种情况对你来说并不鲜见。它就发生在你身边。
(作者Nick Cohen系《观察家报》专栏作家)
(翻译: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