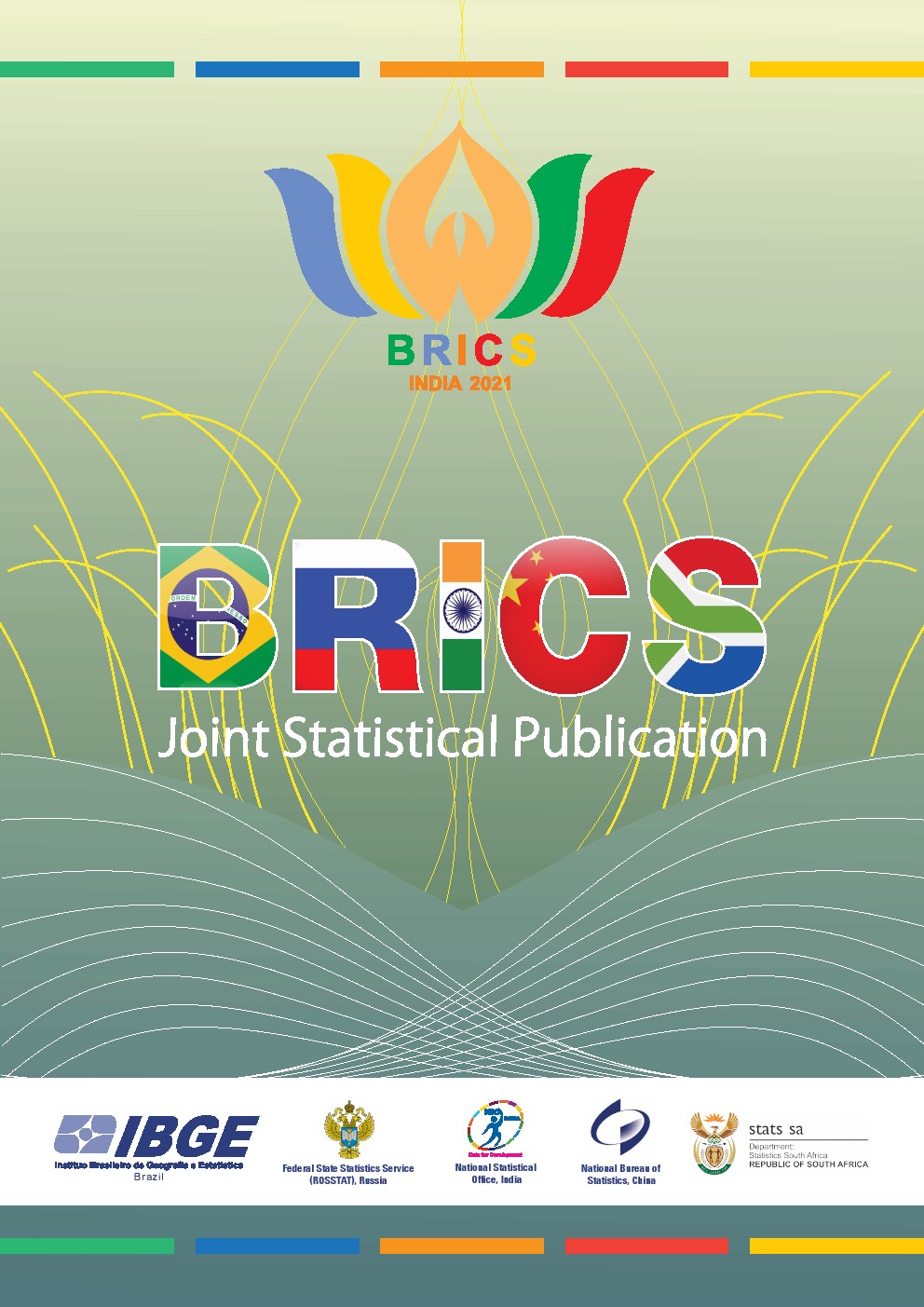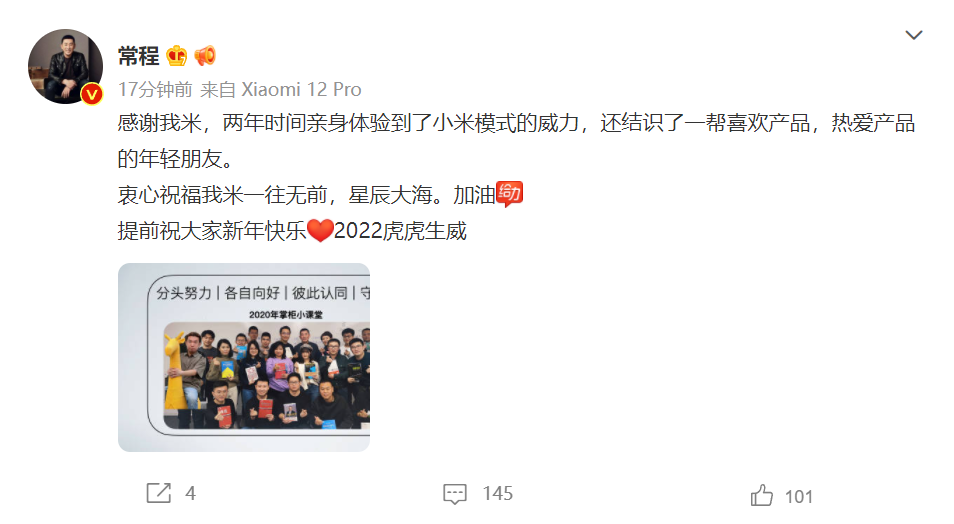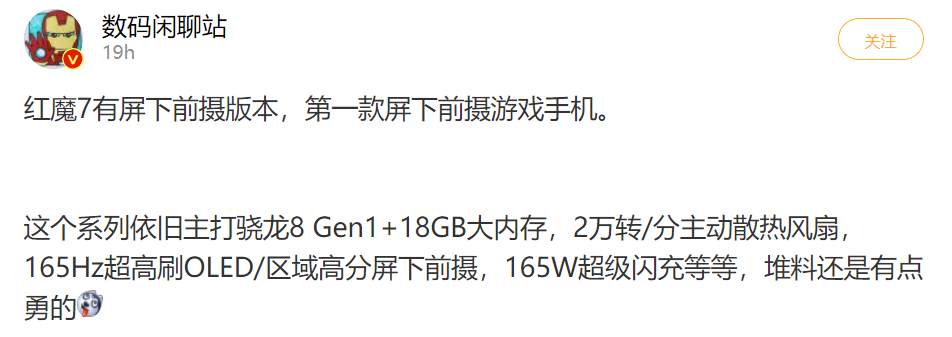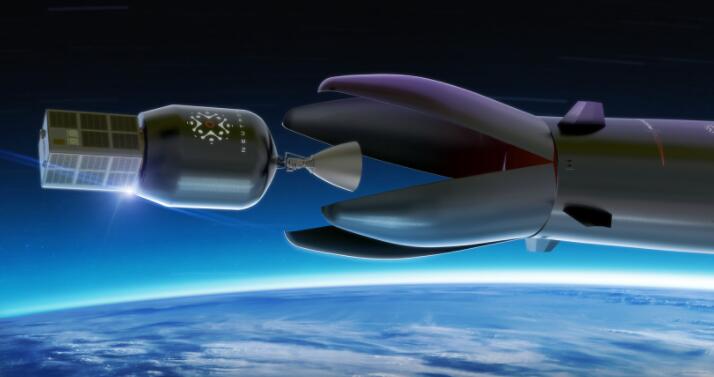作者:弗兰克·维尔切克(Frank Wilczek)
出品:新浪科技《科学大家》 鹦鹉螺

本文节选自《万物原理》(Fundamentals:Ten Keys to Reality)选段,作者弗兰克·维尔切克是美国理论物理学家,现任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教授。2004年因在夸克之间强相互作用理论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与戴维·格罗斯和戴维·波利策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在粒子物理学和凝聚体物理学都有所建树。
检验一流智力的标准是头脑中能同时持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却能并行不悖。
——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
显然,这种互补性推翻了学术的本体论。真理是什么?我们之所以要提出彼拉多的问题,并不是出于怀疑和反科学的意义,而是出于信心,我们相信对这种新情况更进一步的研究将会让我们对物质和精神世界有更深的理解。
——阿诺德·索末菲
互补性这一概念最基本的形式是: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思考同一个事物的时候,似乎会发现它同时具有不同的性质,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性质。互补性是一种对待经验和问题的态度,我觉得这种态度让我大开眼界、受益良多。它真的改变了我的思考方式,并且让我变得更加强大:想象力更加开放,也更加兼收并蓄。现在,我想依据我的理解,和你们一起探索由互补性向外发散的见解。
这个世界既简单又复杂,既逻辑森严又怪诞不经,既秩序井然又混乱不堪。如我们所见,对基本原理的理解并不能解决这些二元性,反而还会突出并深化它们的影响。如果不把互补性牢记在心,你就无法完整地描述物理现实。
人类同样也被二元性裹挟。我们既渺小又庞大,既转瞬即逝又长盛不衰,既知识渊博又懵懂无知。如果不把互补性牢记在心,你就无法完整地描述人类的状况。
科学中的互补性
丹麦伟大的量子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率先阐明了互补性的强大力量。如果直观地看待历史,我们会说玻尔从他对量子物理的研究中掌握了互补性的概念。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玻尔的这种思维方式其实早在他对量子物理领域做出卓越贡献之前就已经形成了,甚至有可能他正是凭借这一认识才得以在量子物理领域做出这样的贡献。在这里,一些为玻尔写传记的作家看到了丹麦哲学家、神秘主义者瑟伦·克尔凯郭尔对玻尔的影响。
从1900年左右人们初次发现量子行为的迹象开始,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现代量子理论出现为止,这期间出现的一些不同的实验观测数据之间存在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科学家也为此进行过一段激烈的争论。在这一时期,玻尔堪称构建模型的大师,这些模型能解释一些观测结果,同时也能够战略性地忽略其他的观测结果。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是这样评论他的工作的:
这种不稳固且矛盾的基础足以让玻尔这样直觉敏锐、思维敏捷的人把握住原子的主要规律……及其在化学上的重要性,在我看来就像一个奇迹——哪怕是现在看来也同样如此。这是思想领域中最高形式的音乐神韵。
玻尔通过这一时期的钻研,将互补性发展为一种强大的洞见,这一洞见从科学发展到哲学,最终成为全人类知识宝库中的共同财富。
量子力学中的互补性
在量子力学中,波函数是对一个物体(无论是电子还是大象)最基本的描述。一个物体的波函数可以被看作一种原材料,
我们可以把它加工成对物体行为的预测。对于不同的问题,我们需要用不同的方式处理波函数。如果我们想要预测物体的位置, 那就必须用这种方式对它的波函数进行处理;如果想要预测物体的运动速度,那就必须用另一种不同的方式来处理波函数。
这两种处理波函数的方式大体上可以类比成两种用于分析音乐的方法:通过和声以及通过旋律。和声是针对某个局部的分析,这种方法监视的对象是事件中的某一时刻,而不是空间中的某个点;旋律则是一种更为全局性的分析。和声可以类比于位置,而旋律则可以类比于速度。
我们无法同时处理这两个信息,因为它们会互相干扰。如果你想要获得有关位置的信息,那么就必须以一种损坏速度信息的方式处理波函数,反之亦然。
波函数是为了定量描述微观粒子的状态而引入的,用Ψ表示。波函数在通常情况下是空间和时间的复函数,即Ψ=Ψ(x,y,z,t)。将爱因斯坦的“鬼场”和光子存在的概率之间的关系加以推广,玻恩假定Ψ*Ψ就是粒子的概率密度,即在时刻t,在点(x,y,z)附近单位体积内发现粒子的概率。波函数Ψ的绝对值的平方因此就称为概率幅。
虽然数学上精确的细节可能会相当复杂,但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处理方式背后都有着坚实的数学基础。我们目前认为,量子理论中的互补性不只是一个空洞的判断,而是一个数学上的事实。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用数学概念讨论量子互补性,也就是波函数及其处理。我们可以通过实验更加直接地考虑同样的状况,以获得不同的视角。在这一前提之下,我们不需要考虑如何处理粒子的波函数来做出预测,而是要考虑如何通过粒子的相互作用来测量它的特性。
微积分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思想成就之一,也是数学领域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分支。除此之外,我们更应该关注的事实是:如果没有微积分,人类就没有现代科技。
在量子理论的数学框架之下,位置和速度的互补性可以被看作一个定理。但是量子理论中的数学有诸多怪异之处,它只能试图描述大自然,却不能揭示真理。事实上,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许多量子理论的先驱,都对其成熟的数学形式持怀疑态度。
与量子理论无法同时预测位置和速度相对应的是,我们永远不可能在实验中同时测量这两个性质。如果想要同时测量位置和速度,我们就得跳出量子力学的框架及其处理波函数的方法, 构建一个新的数学理论。
年轻的维尔纳·海森堡在奠定现代量子理论的基础之后不久,就意识到,量子理论的数学推导会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即位置和速度无法同时被测量。他将这种认识总结为“不确定性原理”。由他的不确定性原理产生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这条原理是否正确地描述了物质世界的具体事实(即我们可以观察到的事物)。海森堡一直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在他之后,爱因斯坦和玻尔也参与了进来。
在物理行为的层面上,这种冲突(或者说这种互补性)反映了两个关键事实。第一,若要测量某个物体的性质,那你必须和它发生相互作用。换句话说,我们的测量并不是捕捉“现实”,而是对其进行采样。

正如玻尔所说:
在量子理论中……目前为止,在逻辑上理解迄今为止未受质疑的基本规律……要求,物体的行为以及物体与测量仪器的相互作用这两者之间不能存在任何明显的分割。
第二,精确的测量需要强大的相互作用,这也巩固了之前提到的第一个关键事实。
考虑到上述内容,海森堡思考了许多不同的用于测量基本粒子位置和速度的方法。他发现,每一种情况都符合他的不确定性原理。这一分析让他建立了信心,他认定量子理论中奇怪的数学特性刚好反映了物理世界中一些奇怪的事实。
我们在前文提到的两个原则(观测是积极的过程,以及观测具备侵入性)是海森堡分析的基础。如果抛弃这些原则,我们就不能用量子理论的数学运算来描述物理现实了。然而,它们却破坏了我们在儿童时期建立起的世界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我们观察到的外部世界在“那里”,它和我们自己之间有着严格的分割。在吸取海森堡和玻尔的经验之后,我们开始意识到,其实如此严格的分割是不存在的。我们通过观察世界也参与了对世界的创造。
海森堡在哥本哈根的玻尔研究所从事不确定性原理的相关研究。这一领域的两位先驱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并且形成了某种科学上的父子关系。玻尔早期有关互补性的思想一开始是作为对海森堡研究工作的诠释而出现的。

爱因斯坦不认可玻尔和海森堡的发现,他对互补性感到不满。他认为,两种有效却不相容的观点无法同时存在。他希望能找到一个将所有可能性都包含在内的更为全面的理解。他尤其希望能够找到同时测量粒子的位置和速度的方法,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并尝试设计能同时揭示一个粒子的位置和速度(或是动量a)的实验。爱因斯坦的思想实验非常巧妙,他所考虑的比海森堡要复杂得多。
在著名的玻尔–爱因斯坦论战中,正如玻尔在《就原子物理学中的认识论问题和爱因斯坦进行的商榷》一文中所描述的那样,爱因斯坦用一系列思想实验向玻尔发起了挑战。这些实验挑战了量子力学的互补性,特别是能量和时间的互补性。在应对这些挑战的过程中,玻尔每次都发现了爱因斯坦的分析中存在细微的缺陷,并且成功捍卫了量子理论的物理自洽性。
他们的论战以及后来其他的论战阐明了量子理论的本质, 但迄今为止,对量子理论正确性的质疑从未取得成功。与此同时,我们运用量子理论设计了许多堪称奇迹的东西,从激光到智能手机,再到全球定位系统。其实之前我们还拿不准这些基于量a在前面有关不确定性原理的讨论中,我提到的一直是位置和速度的关系。实际上在物理学的文献中,更常见的说法是动量而非速度,这从技术的角度来看会更加方便。之后我会继续使用速度这个说法,因为大多数人对速度的概念更加熟悉。
子理论的设计能不能取得成功,但它们的辉煌无须多言。如果说“杀不死你的会让你变得更强大”,那么量子理论及其暗含的互补性现在确实非常强大。
(这对我们在本节的开头提到的大象意味着什么呢?虽然从理论上讲,量子不确定性确实存在,但是我们在对大象的测量中其实完全可以忽略它。在实际应用中,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同时测量大象的位置和动量。它们的不确定性与它们本身的数值相比根本微不足道。但是对于原子中的电子来说,情况就不同了。)
不同层面的描述
运用不同层面的描述是互补性的另一个来源。当用于描述系统的一种模型过于复杂而无法使用时,我们有时候可以根据其他概念找出一个互补的模型来解答重大的问题。
我会用一个简单而具体的例子来阐述基本思路,这个例子意义重大,并且实用性极强。用于填充热气球的气体是由大量原子构成的。如果我们想通过对原子应用力学定律来预测气体的行为,就会面临两个很大的问题:
•即使我们能够满足于以经典力学为基础(作为近似值)来进行运算,我们也需要知道每个原子在某一初始时刻的位置和速度,这样才能获取方程在运算过程中所需的数据。收集并存储这么多数据是完全不切实际的,而量子力学只会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糟糕。
•即使我们能够以某种方式获取这些数据并存储它们,跟踪粒子的运动所需要的计算也更加繁杂到不切实际。
只需要引入密度、压强和温度这些不同的概念,我们就能得到一些简单的定律,用于描述空气的大尺度行为。热气球驾驶员在驾驶的过程中需要用到的并不是针对原子的描述,而是我们现在引入的这些概念。从理论上讲,针对原子的描述包含的信息更多,但是如果你的目标是驾驶热气球的话,那么其实这些信息中的大多数都是没用的(更糟糕的是,它会形成干扰)。
例如,我们现在考虑某个特定原子的位置和速度。由于它在不断地运动,并且还会与其他原子相撞,因此这些性质会随时间迅速地发生变化。原子精确的初始状态对其实际的运动轨迹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其他原子的行为也同样对它的运动轨迹有所影响。因此, 与某一特定粒子的位置和速度相关的信息非常难以计算,并且时时刻刻都在改变。简单讲,它既不简单,也不稳定。密度、压强和温度等概念在这些方面则更为有效。找到并量化这些简单而稳定的性质是一项重大的科学成就,我们可以用它们来解答重大的问题。大多数科学学科都是在寻找简单而稳定的性质,它们可以解答一些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我们有时会将其称为涌现性质。
找到有用的涌现性质并学会巧妙地运用它们,可以让我们取得很大的成就。在整个自然科学领域不同学科的历史中诞生了许多重要的涌现性质,如熵、化学键、刚度等,我们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许多有用的模型。
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自然科学学科之外,比如我们希望能更加有效地理解人类的行为以及股票市场,等等。对这些学科 “原子”层面的描述同样很复杂,若是要跟踪单个神经元或是单个投资者的行为,那将会复杂到令人绝望,更不用说跟踪组成它们的夸克、胶子、电子和光子的行为了。
如果你的目标是与他人和睦相处,或是通过投资股票获利,这些方法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所以我们要转向别的概念来回答这些大尺度的问题,这些概念你可以在心理学和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找到。我们可以在书中查阅到针对人和市场的模型,它们与微观的“原子”模型是互补的。在心理学和经济学领域,我们还没有找到多少像物理学家的气体模型那样可靠的模型。对涌现性质的寻找,以及对建立在涌a原文为emergent,指包含大量简单成分的系统中由各组分间的互动自发出现复杂现象的过程,又译“层展”“演生”等。——编者注
现性质基础上的实用模型的研究仍在继续。
用最基本的构成要素完成对整个世界的描述会给人带来极大的满足感。人们很容易认为这才是最理想化的描述,而其他高层次的描述仅仅是近似的,是由于我们对系统的理解过于薄弱而不得不做出的妥协。这种态度把“完美”放在了“优秀”的对立面,它看起来很深刻,但实际上非常肤浅。
为了解答那些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我们时常需要转变焦点。发现(或是发明)新的概念以及找到运用它们的新方法,是兼具开放性和创造性的举措。在设计有用的算法时,计算机科学家和软件工程师都很清楚,关注知识的表达方式是非常重要的。良好的表达可以区分可用的知识以及“理论上”存在但并不真正可用的知识,因为定位和处理后者需要耗费的时间太久,并且会带来很多麻烦。二者之间的区别就像是真正拥有金条和知道海洋中理论上溶解了大量金原子之间的区别一样。
因此,如果我们能完全理解基本定律,那么我们得到的既不是“万物理论”,也不是“科学的终结”a。我们仍然需要现实的互补性描述。现在还有很多重大的问题没有得到解答,也有很多伟大的科学研究有待完成。
这是永无止境的。
在科学之外:人类知识宝库中的互补性

艺术领域的例子
我的音乐家朋友明娜·珀莱宁(Minna Pöllänen)提出了她的领域中一个美妙的互补性的例子,我在前文中曾经简要地提到过这个例子。在复调音乐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会同时出现——每个声部都有一个旋律,而它们合奏时则形成了和声。我们既可以关注旋律,也可以关注和声。其中任意一种与音乐互动的方式都是很有意义的。你的注意力可以在二者之间切换,但你无法同时关注这两个部分。
毕加索和其他立体派艺术家创造的视觉艺术,以图像的形式捕捉了互补性。通过从多个角度描绘同一幅画中的某个场景,他们可以更加自由地表现他们重视的内容。小孩子在绘画时也会这么做。这些作品中奇特的夸张和并置强调了可能被视为互相矛盾的不同视角,这在物质世界中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种坦率的互补性在小孩子的绘画中显得很可爱,而大师则可以通过这一点向我们展示何为天才。
人类的模型——自由和决定论
我们也会构建人类心理的模型,并以此解答相关的问题。
例如,如果我们想预测一个人在社会环境中的行为,那么我们可能会考虑他的性格、情绪状态、生活经历、母文化,等等。简而言之,我们给他的思想和动机构建了模型。这个模型的核心概念是意志,也就是关于选择的想法。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想预测如果这个人在核爆中心会发生什么的话,那么采用基于物理学的另一类模型将会更为合适。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的思考和意志完全没有意义。
基于思想和心理学的模型以及基于物质和物理学的模型都是有效的,可以分别用于解决不同的问题。但是这两种模型都不完整,也无法完全互相替代。人类确实会经过思考做出选择,而人类的身体则服从物质的规则,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体会到的事实,它们都千真万确地存在。我们要贯彻互补性的思路,接受这两种模型同时存在的事实。我们要认识到,它们谁也不能证明另一类模型是假的,因为事实无法证明其他事实是假的。它们只是反映了对待现实世界的不同方式。
人类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吗,还是说人类只是数学物理学的提线木偶?这是个很糟糕的问题,就像是在问音乐到底是和声还是旋律一样。
自由意志是法律和道德中的基本概念,而物理学在没有它的情况下同样取得了成功。如果从法律中移去自由意志,或是在物理学中注入自由意志,都会将这些学科搅得乱七八糟,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自由意志和物理决定论是现实中具备互补性的两个方面:互补性、思维的拓展以及对不同观点的容纳。
我要用更简单的语言重申互补性的几个要点:
•你需要解答的问题决定了你要用到的概念。
•从不同的角度,甚至是不相容的角度对同一事物进行分析,可以为我们带来有用的见解。
因此,互补性实际上是一份邀约,邀请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从互补性的角度来看,那些不熟悉的问题、事实和态度给了我们尝试新观点的机会,并从它们所揭示之事中学习。这可以促进我们拓展思维。
既然如此,那我们为何不把互补性也运用到艺术和科学之间的冲突、哲学和科学之间的冲突、两种不同的宗教之间的冲突以及宗教和科学之间的冲突中去呢?
从不同的角度看世界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
就我自己而言,小时候接触天主教的经历启发了我开始思考宇宙的奥秘,寻找隐藏在事物表象之下的意义。事实证明,即使在抛弃了宗教严格的教条之后,这种求知的态度仍然保佑着我继续探索未知。现在,我还会经常回顾柏拉图、圣奥古斯丁、大卫·休谟的言论,或是伽利略、牛顿、达尔文、麦克斯韦那些 “过时的”原始科学著作,我以这种方式与那些伟大的思想对话, 并且尝试着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思考。
当然,尝试理解不同的思维方式并不意味着你一定要认同它们,更不是说要接受它们作为自己的思维方式。在互补性的思想下,我们要保持超然的心态。那些独断专行地主张自己有权规定唯一“正确”的观点是什么的意识形态或是宗教,与互补性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
但就算如此,科学仍具有特殊的地位。它在许多方面的应用取得了非凡的成功,无论是作为理解的主体还是作为分析物理现实的方法,科学都赢得了显赫的名声。狭隘地给自己下定义的科学家无法开拓自己的思维,而回避科学的人也只会让自己的思维更加贫乏。
有关互补性的未来展望
准确性和可理解性
超级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正在蓬勃发展,这会改变我们将要提出的问题,以及我们能够找到的答案的类型。
玻尔自己半开玩笑地提到了清晰的表达和真理之间的互补性。这有点儿过头了,因为像基本的算术这样的东西就是既清晰又真实的。
但是,一些成功的模型需要的计算超出了常人所能及的范围,而它们会导致类似玻尔所说的这种互补性产生,这是相当严重的。现在在国际象棋和围棋这两种曾经被视为人类智力巅峰的竞赛中,最棒的棋手是计算机。
我们有大量关于国际象棋和围棋的文献资料,伟大的人类棋手在这些文献中解释了他们用于组织相关知识的概念。但是作为这些领域现在的王者,计算机并不使用这些概念。人类的概念适用于在运用图像以及进行并行处理等方面拥有超强能力的大脑,不过人类大脑记忆力相对较弱,并且运行速度较慢。
计算机可以开发出完全不同的概念,当然它们也可以发现对人类而言有效的概念。它们只需要自己和自己下很多很多盘棋并观察哪一种方法有效即可,换句话说,它们遵循从实践中学习的科学方法。在量子色动力学,也就是我们的强相互作用理论中,科学家发明了一些概念来填补描述夸克、胶子的基本方程同最终出现在大自然中的那些更复杂的物体之间的差距。这些概念帮助我们人类的大脑理解了这些问题。然而,其实目前为止最有效的策略是用最少的指令将运算的工作交给超级计算机。
上述示例的特点就是清晰的表达(以及真理性),但是其中举例说明的基本现象很可能是普遍存在的,即思维机器能够发现并使用那些对于没有得到辅助的人脑而言不切实际的模型。
简而言之:人类可理解性和准确的理解是互补的。
谦逊与自尊
我认为,谦逊和自尊之间的互补性是我们基本原理中的核心理念。无论目标如何变化,它都是不变的主题。我们在浩瀚的太空中显得微不足道,但是我们的体内有大量的神经元,而构成神经元的原子当然就更多了。宇宙历史的跨度远远超过人类的一生,但这不妨碍我们有时间进行大量的思考。宇宙的能量超出了人类能够掌控的范围,但是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去改造周围的环境,并积极地参与到其他人的生活中。世界很复杂,它神秘莫测、难以捉摸,但是我们已经对它了解了很多,并且还在学习更多。谦逊是必要的,但是自尊同样也是必要的。
自主、通用的人工智能(AI)可能还需要好几十年才能达到人类的水平。我们发展人工智能的决心不可动摇、进展不可阻挡,除非发生灾难性的战争、气候变化或是瘟疫,否则我们可能只需要一两个世纪就能达成目标。考虑到工程设备在思维速度、感知能力以及体力等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智能水平的顶点将会从没有得到机器帮助的智人过渡到电子人和超级智能身上。
基因工程也有可能产生超能力生物。它们会比现在的人类更聪明、更强壮,当然我也希望并期待它们能更有同情心。
实际上,对善于思考的人类而言,意识到这些即将实现的可能性会让我们更加谦逊,不过我们也不能丢了自尊。在天才科幻小说家奥拉夫·斯塔普尔顿于1935 年发表的小说《古怪的约翰》(Odd John)中有一段动人的描述,小说的主人公(他是一个因基因突变而获得超人智力的人)与他的朋友,同时也是一位传记作者(朋友是一个普通人)交谈时,深情地把智人描述为“灵魂的始祖鸟”。


始祖鸟是一种高贵的生物,并且我认为它也是一种快乐的生物。飞行是一种令人兴奋的体验,它当然也可能有糟糕之处, 但是我们人类从远古时代直至今天都不曾拥有这项能力。始祖鸟的荣耀不曾褪色,甚至还因为其后裔的光彩得到了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