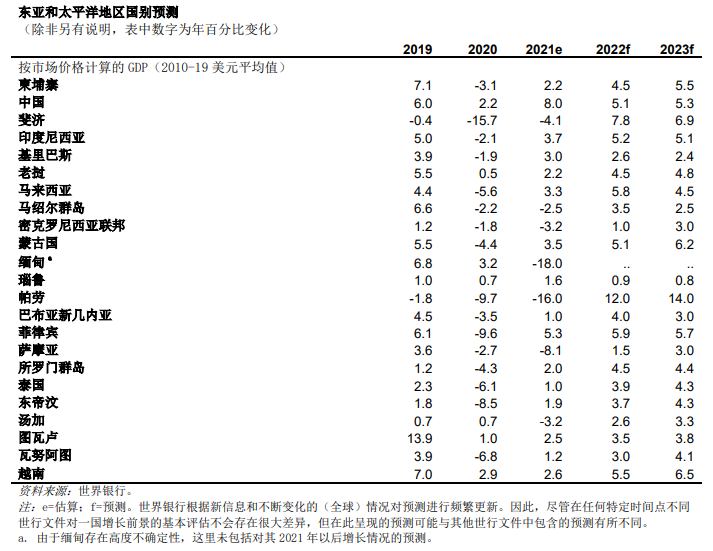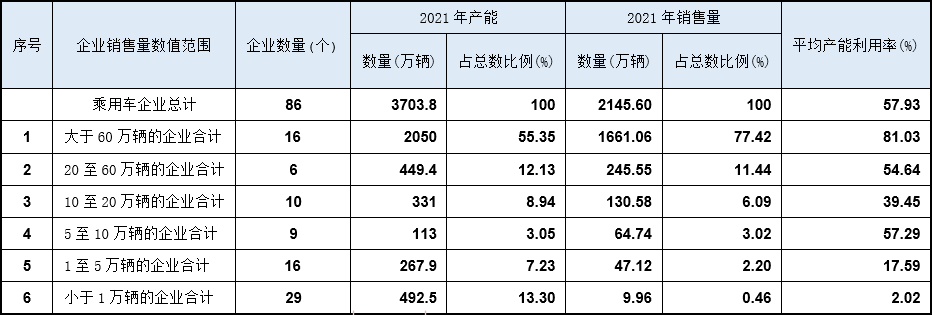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一个31岁的年轻人,在2021年6月被骗到柬埔寨,被要求参与电信诈骗工作,因为拒绝,他被多次送去卖血,沦为“血奴”。我们进入到一个与他有着相似经历的受害者群,他们揣着各异的想法而来,从未想过自己会因此闯入到世界黑暗的一角,被再三转卖,强制参与电信诈骗或者网络博彩,成为人口贩卖产业链上的一环。我们对这些信源的可靠性进行了多方交叉验证。以下是他们的口述。
口述/方钟平 小泽 崔风
实习记者/石震方 张潇珂
编辑/王珊
方钟平
我是2021年8月份来到柬埔寨这边的。我是一个灯光师,来柬埔寨是一个朋友叫我过来帮忙,我就过来了。在柬埔寨这边,基本上拍摄的时候,灯光都用的不多,然后灯光的配置也比较简单,没有国内的那种条件。所以我就负责副机位,相当于是一个外聘人员。
我的命运发生变化是在剧组工作完成解散后。当时,喊我过来的那个朋友去泰国了。他叫我一起去,我就买了11月17号的机票,准备飞去泰国找他。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之后,我突然发现自己护照逾期了一个月。朋友就给我推荐了一个叫小叶的人,说自己的护照都是找的这个人。我把护照还有900美金给了小叶,一个星期之后我问他护照办得怎么样了,我的飞机没几天就要飞了,我很着急,那两天就一直追着他要我的护照。他说叫我多等两天,大概是第九天的时候,也就是11月14号的凌晨,他联系我说等一下把护照给我送过来。
大概是凌晨1点多的时候,他联系我,叫我下楼去拿。到了酒店下面之后,他说没看到我在哪里,就叫我找一辆黑色的车,我就走到车旁边去了。从车上就下来三个人,一个宪兵,有一个保镖,还有一个人,三个人就把我强行拽上车了。宪兵手里是有枪的,我也不敢乱动。这台车开了一夜从金边开到了西哈努克港(以下简称“西港”)的一个园区里,路上他们没收了我的手机,并说小叶把我卖给他们了,卖了1.8万美金,让我现在老老实实跟着他们去上班。
 西哈努克港的渔船(图/视觉中国)
西哈努克港的渔船(图/视觉中国)到园区时,是早上六七点钟的样子,太阳刚刚升起。当时我想得比较简单,我就和他说,那你看能不能我把这个钱给你,你放我走,我给你2万美金,把你们花的钱还给你们,你们放我走。他们就和我说,走是不可能走了,不可能放我走的,因为出去之后肯定会报警,会对园区不利。
我后来才知道这种绑架和贩卖在当地挺常见的,因为疫情国内的人很难再进到柬埔寨来了,他们招不到员工,就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补充员工。他们有一群专业的绑匪,把人绑过去之后,把你身上所有的财物拿干净,然后再让家里打赎金,赎金打过来之后也不会放了你,会再把你卖到园区去。
 《大佬》剧照
《大佬》剧照我很快就知道了这是一个诈骗公司。工作是在一个类似国内那种办公室的地方,好几排的电脑,然后人挨着人,房间里面有很多监控,门口站着带着枪的宪兵和保镖在站岗。我在第一个园区的时候,基本上一个房间里有一百来号人,房间里倒是有空调。他们的诈骗方式一般被称之为“杀猪盘”,具体的流程是这样操作的:
首先三个人分成一个小组,每个小组有一个小组长,几个小组组成一个大组,有一个大组长。小组三个人的分工是不一样的。小组第一个人被称之为“接粉的”,他们每天会往国内发短信,一般内容就是免费领取电饭锅或者是电烤箱之类的,短信下面有条链接,点链接进去就会加上他们的微信。“接粉”就是每天接待这些刚加上微信的人,然后那些微信都是他们每天去找“号商”租的。
 《你觉得我是谁》剧照
《你觉得我是谁》剧照加上他们的微信之后,“接粉的”会把受害者拉进一个微信群里面,群里面会有一些诈骗公司自己的托,他们就在里面闲聊,让那些受害者相信这个活动是真实的,“接粉的”也会在群里面发红包,争取这些人的信任。等差不多初步获取信任之后,“接粉的”就会让受害者去下载一个APP,诈骗公司的APP,这个流程他们称之为转三方,就是转到第三方平台,因为在微信群里面聊天容易被封号。
然后就到了后续人的工作。总之每个人做的每一步都是为了套取这个人的信息,并骗取更多的钱财。他们将这些任务分解,每完成一个步骤就会给入圈的人几块钱,就这么叠加起来,但是任务继续往下去,这些入圈的人也得往里面充钱。越来越多,每一步都是有套路的。我刚去的时候,就待在其他人后面,看看他们怎么上班的,怎么操作的。他们当时说如果我不想工作的话就把我再卖到别的公司去。当时我想着说,谁知道卖的下一家是什么情况,而且这个卖一次赔付的钱会往上累加,钱越来越多,就不好赔付了。我就跟他讲,那我老老实实在这里上班,你们别把我再卖了。看了一个星期之后,就把我分到一个小组里开始工作了。
那种工作环境是非常压抑的, 每天国内的时间早上8点50上班,晚上11点下班,完不成业绩加班一个或两个小时。有的时候大家骗到了人,骗到了十万、二十万那种,会突然站起来大喊一声,然后其他人就会给他鼓掌。那种场景真的是很魔幻。
特别是,在办公室的房间里有两个巨大的音响,类似夜店的那种,放出来的声音震耳欲聋,震得胸腔都在共鸣,你猜音响是用来干什么的?是用来播放那些受害者哭喊的声音,播放受害者哀求他们把钱还回来的声音。没有人理会,许多人在一边哈哈大笑,你那个时候会觉得身边的人都不是正常人。
 图|视觉中国
图|视觉中国我在第一个园区待了20多天,被打了许多次。第一次就是刚到没多久的一个晚上,我躺在宿舍的床上,有一个很壮的保镖来我床边,拍拍我,示意我跟他走,他把我带到一个房间里,然后对方就跟我说,你不要这个态度,你给我好好上班,之后就把我打了一顿。
第二次被打是我被卖进去半个月之后,因为那个园区还比较大,里面也有店铺什么的,我当时已经没有手机,没办法与外面联系,我有一次偷偷买了个手机和电话卡,和我一个朋友取得了联系,告诉他我被绑架了。但这件事被绑匪知道了,他们威胁了我的朋友,打了我一顿。第三次也是类似的事情。
在这里工作的人并不都是被绑架或者被骗去的,我听大组长们聊天的时候说到过,很多人是从国内自己偷渡到柬埔寨的,来做这些诈骗的工作,所以在这里根本不能相信身边的任何人,你的一举一动,身边的人都会和管理的人讲,时时刻刻都有人在盯着。那种环境很容易让人崩溃。
在我被救出来之前,公司正准备将我再次卖出去。在他们找的第一个下家那里,我说我是被绑架的,说完之后那边公司就没要我,因为这种绑架的他们应该是觉得可能会比较麻烦。
当天晚上就再找了一家,公司警告我不要说我是被绑架的,就说自己是自愿过来上班的,是因为跟里面的组长有点矛盾所以要离开。被卖那天,我就看到新园区有围栏,围栏上面有电网,下面还有个水沟,就类似护城河那种的,那个时候真是想跑也跑不了。当天晚上我是被关在烂尾楼的三层,里面有很多房间,我被关的房间隔壁还关着别人,我还能听到他们拿电棍电人的声音,那个人叫得很惨。那天,也有一个保安拿着电棍守在我的房间旁边,当时我就比较绝望了。
我们当时的宿舍十二个人一个房间,上下铺,类似大学宿舍那种。有个人和我一个宿舍,他在里面好像是做技术型的,做后台那些,那个时候我问过他,自己把赔付的钱给了能不能出去,他说不可能的。他跟我说,出去是不可能出去了,他当时被打得已经有点残疾了,他说,在这里的话,有口气活着就不错了。
 《极恶非道》剧照
《极恶非道》剧照那时每天我都会想很多东西,每次都会吓得自己一身冷汗,想着自己可能是出不去了,担心自己会一直被困在这里,更会担心自己随时都有可能消失不见了,因为之前看到过很多媒体的报道,哪里又出现一具尸体的新闻。我很长一段时间睡眠都有问题,就门外有一点动静都会惊醒的那种,每天担惊受怕的。
因为我之前说我是正常过来上班的,园区的这群人就对我没有了那么大的戒心,就给了我一个私人用的手机,平常可以跟他们公司的人联系。我就用这块手机自己联系国内的朋友,通过各种软件联系朋友,给他发定位和一些园区的照片,我的朋友就找到了中柬义工队。义工队的陈队长帮我的朋友找了翻译,陪他去西港警察局报警,朋友拿着我的护照,还有他的护照。后来我就被警察从园区带出来了。
小泽
我叫小泽,今年16岁,贵州人。我是去年辍学的。我不上学的原因很简单,其中一个是因为我父母经常吵架,有点矛盾就吵,总是闹离婚。我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妹妹今年15岁,弟弟13岁。一直以来,我妈总觉得我和弟弟妹妹小,也就忍着不跟我爸爸离婚。我爸是个脾气暴躁的人,我很小的时候他就会对我妈拳打脚踢,我上高中之前他也会打我,所以我很怕我父亲,平时遇到什么困难和问题,也不会怎么主动和他交流,都是我妈和我交流。可是,我妈一直在外面打工,一年只能见上一两次。
另一个原因是我在学校总是遭人欺负,我小时候经常转学,那时父母工作不稳定,他们每换一个地方打工,我和妹妹就得跟着他们一起转学,转学的次数已经多的让我也记不清楚了,小学四年级我才回到老家读书。从小学三年级开始一直到初一,都会有人欺负我,一般都是两三个男生那样的小团体,因为我平时比较腼腆,话不是很多,看起来比较老实。那时候我的胆子又比较小,怕他们报复我,我也不敢向别人寻求帮助。
 《无人知晓》剧照
《无人知晓》剧照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三年级时,有个比我高一个年纪的同学,他抢我钱,我当时没有给他,他就叫上他们班的两位同学,每天放学堵我、打我,我看见他都是绕着走。有时候我还会被他们打伤,回到家里,家里人又会认为我和别人打架斗殴。
这些事情让我很不开心,我想离开学校。中考之后,我进入了职校,读了半年之后,我开始考虑退学,想要逃离学校这个环境,这个事情,我跟父母讲过,他们坚决不允许,因为这件事他们骂了我很久,但是我还是自己做了决定。
离开学校之后,也找过一些工作,在酒吧里面当过服务员,做了一个多月,全勤1400块钱,一个月后我就离开了。之后,大概2021年3月的时候,我之前的一个同学问我要不要上班,说地点在广西,我跟他关系并不是很好,但他接连给我打了一个星期电话,我就答应了。他说做销售,工资一个月8000块钱,当时因为没有工作,在家帮别人照看店铺,我对这个工作心动了。我家在农村,父母在外打工,我们也跟着四处漂泊,家里从小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好,8000块钱对我和家里都是蛮大的补贴。我没有告诉父母,就自己坐车到了广西南宁,到了之后我才跟他们说的。
到南宁是3月底的事,这期间我一直和那个同学在联系,他帮我找了住的地方。过了几天之后,他告诉我有辆车停在酒店门口,等着要带我去公司面试。我从酒店出来以后看到一辆黑色的商务车。司机戴着口罩,我看不清楚脸。我上去发现连司机有三个男人。年龄看着在35岁以上。一开始车子走得好好的,没什么。但是透过窗外的高速两边的风景,我感觉越走越偏僻,我当时有点慌,就问了一下,什么时候到?他们给我的说法是接到公司面试,然后就没再多说,我也不敢询问。他们在路上就把我的手机没收了,之后就被控制了。
 《极恶非道》剧照
《极恶非道》剧照随后,不知道走了多少天,这期间换了好几次车,有一些比较高的山梗和小河流,这些车过不去的地方,都需要我们自己下来走。然后我才知道自己到了柬埔寨。虽然我知道事情不对了,但也没能力逃走,我被一路带到了西港的一个园区里面做诈骗,我不想做诈骗,我也不会做。他们就每天都打我,还不给我饭吃,饿了我也只能硬扛着,最久的一次我被饿了整整五天。他们打我用的是电棍,我身上经常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有时候我被打得会滚进桌子底下。在园区里面,我也不敢生病,有了情况只能硬扛过去,就算你生病了,他们也不会给你治。
我很想回家。但是公司主管告诉我,要么上班要么死,还说只有我家里面拿20万的赔付才给我走。我不敢告诉我家里人,因为怕被园区发现。家里母亲自己在外打工,还要供弟弟妹妹们上学。有好几次我都想自杀了,但是又不敢。有几次我想逃跑,可门口的保安都拿着枪。我知道我们所在的园区之前有人逃跑,被抓回来以后头都被打破了口子。我身边的人有的成功跑掉了,没有跑掉的被抓回来了。知道抓回来并不是因为我见过他们,而是主管会给我们放他们挨打的视频。这之后,没有人再见过他们。
 电影《监狱风云》剧照
电影《监狱风云》剧照我被卖到了好几家公司,在各个园区里面待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我是年前被解救出来的。我真的没想过会被同学卖到这边。有很多人说,你不去柬埔寨就没事了吗?但是到广西的时候我已经被控制住了,一切已经超出了我可以主导的范围。我希望能早点回家,也希望家里面不要再有人被骗到这边了。我真的很害怕自己悄无声息地死了。我有听到园区里的人说有专门养人卖血的,我不知道这些人如果按照对方的要求给了钱,是不是能让他们走。我周边其他被骗到这里的人说,就算给了诈骗这些人赔付以后还是会卖到别的园区里面去。
 《放逐》剧照
《放逐》剧照我现在还在柬埔寨,也是在等待回国的机票回家。我们被解救的这一波人现在住在义工队安排的酒店里,两三个人一个房间,现在能活着非常幸运。我白天会打扫一下房间,帮忙做一下饭,我不喜欢到处乱跑,因为比较缺乏安全感,我感觉金边和西港这两个城市都很黑暗,走在路上都充满了恐惧,总感觉有双眼睛在暗处盯着着你,随时对你下手的那种感觉。
崔风
我今年24岁,来自安徽亳州,目前已经被解救。2021年初我还在轮胎厂工作,我是听之前在工厂的朋友说在柬埔寨工资很高、能赚大钱,也看到了他朋友圈所晒的生活十分滋润,我便心动了。我告诉父母之后他们也十分支持。于是2021年4月,我就坐上了前往柬埔寨的飞机。
飞机落地的第一天,我找到之前在工厂的朋友,也是他介绍我走进所谓的团队。我却发现他们的工作竟然是赌博。因为我以往听别人说做赌博生意的老板一般心狠手辣,也出于对赌博的恐惧,我果断拒绝了这份工作,选择了另一份可靠的工作。

《赌圣》剧照
因为疫情的缘故,大概在2021年10月份,我服务的老板需要飞往菲律宾,只留下我一人在柬埔寨。在柬埔寨待了几个月,我从身边人的讨论和网上新闻中知道柬埔寨发生了许多起诈骗、绑架等恶性事件,连中国警方都惊动了,他们也已经派卧底进入柬埔寨了。我听了有些害怕,便也有了回家的念头。在查阅航班的时候,我发现从柬埔寨飞往中国的机票价格已经从原来的两三千涨到一万六了。虽然我这几个月的工资是可以支付“天价”机票,但当时的我仍然有侥幸心理,总想着“机票过几天就会降价”。而且,我觉得自己来柬埔寨赚大钱的目标还没有实现,一直犹豫着没有回去。
谁想到,疫情愈演愈烈,机票的价格不断飞升,我再也支付不起机票钱了。在等待的过程中,我的存款也已经花光了。在走投无路下,有人鼓励我说可以去“盘口”碰碰运气。这是当地的黑话,泛指诈骗窝点。他讲反正在境外,没有人了解你,做了也没有什么责任。因为我当时已经穷困到连一顿饭都吃不起了,于是我动摇了,并劝说自己先将就干着,把机票钱挣到了就回国。
我最开始做的是彩票类的网络诈骗,主要是假扮富二代和拟造彩票课程骗取客户的信任,然后再让他们进行汇款。我也根本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所以从事这份工作的四个月中并没有什么业绩可言。在四个月后的某一天,我们四五个工作人员,加上这个团队的领导,一共大概一共七八个人再次移动到西港的另一个园区。我虽然不知道具体原因,但猜想可能是因为我们业务不佳,所以换到另一个园区做不同的工作了。在到了那个园区之后,我以前的领导却直接失踪了,换了一个面目和善的老板管理我们。
 图|视觉中国
图|视觉中国一个月后,我们再次因为项目的更换进行转移。因为疫情,我们离开中国城之后并没有直接去往下一个做项目的地方,而是来到了一个被称为隔离点的酒店。老板声称要隔离一段时间才能继续工作,他把我们的手机全都收上去进行了刷机。之后带领团队的人又换了一个陌生的面孔。这个类似的情况我前不久也经历过,所以感到一丝不妙:这一定是把我们卖给另一个盘口了,要不然为什么要刷机又换新老板呢?于是乘其不备,我直接从这个酒店逃跑了。当时的酒店还是没有保安或者看护的,故逃离颇为容易。
我逃到了一个本地人开的酒店暂时落下脚来,也开始思索之后的日子到底怎么办。就这样我在这个小宾馆里一待就是两个月。眼看生活费又要告急的时候,我在一个叫飞机的本地的社交软件上联系上了一个老乡。这个老乡告诉我他在一个也是在干彩票项目的团队在工作,他说我也可以过去试试。老乡劝我这个工作来钱快,也比较轻松,所以我还是想信了他,并跟他说我挣到钱就走,不会长期待在这里。他同意了。
那天我记得很清楚,是2021年6月1日。因为之前介绍人跟我说当天入职的话就能拿到全勤奖。那个盘口距离湄公河很近,大概是在越南和柬埔寨的交界处。具体的位置我也不清楚,只记得车行驶的道路坑坑洼洼,极为难走。路旁偶尔还有几栋荒凉的烂尾楼。我是下午五点左右进入这个地方的,第一天就发现这不是老乡口中的彩票业务,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诈骗团伙。第二天上午十点,我便提出离开的请求。没想到昨日和善的老乡却换了一副面孔,他告诉我不在这里待半年就别想出去,要出去就要拿一万美金的赎金。
我“入职”之前,刚听工友说就在前几天有一个试图逃跑的人被保安用电棍殴打,最后被手枪在腿上打了一枪。因此我不敢和介绍人顶撞,便就在这个团队待下了。每天的例行工作都是煎熬。每天十一点准时上班,深夜十一点准时下班。我和工友们住在普通的宿舍里,在任何地方都有安保二十四小时看管我们,以防我们逃跑。我听同伴们提到在这个楼的八层可能是个刑房,专门把人绑架到那里进行毒打和电击。团队里除了我以外还有三十几名中国的受害人,他们有通过偷渡来到这里的。经历过这一系列的事情之后我再也不能相信这些看似无害的人,所以我和他们交谈甚少,生怕哪一天说话一不小心就招来殴打和电击。
日日重复的枯燥工作,没有可以交流的对象,看守日日夜夜的看管,再加上初来时候因为想离开从而拼命反抗,然后被一顿毒打……我很痛苦,我几乎不说话,直到现在我还庆幸当时自己不说话,也许说了就没有运气活到现在。在这期间我还是没有放弃离开的念头。
在进入这个团队第五个月的时候,我实在在这个地方待得发疯,我就从三层的窗户跳了下去。跳楼之后左腿摔骨折了,没逃掉。大家都在想方设法逃跑。有的在去医院就医的时候逃跑,有的在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逃跑等。我摔骨折后被送到了医院,为了防止我逃跑,他们安排了四个保安全职在医院看守我。他们把我的私人手机、身份证、护照等一切电子产品以及关键证件都没收了。我在医院一共住了十天,花费的金额大概是四千五百美金。团队的老板垫付了这个费用,他说我的赔偿金加这医药费少说也得两万美金,所以腿好了之后还需要正常上班。我很绝望。
我能逃跑源于有个工友离开前没有带自己的手机。我当时马上意识到机会来了,所以就把自己的电话卡插到了这个工作机上开始求救。我联系上了我的父母,在告知他们情况之后,我妈妈便着急得要报警。但我冷静思考了一下,觉得中国的警察很难管理在中国境外的罪行。于是我研究了一下国外用的社交软件,然后注册了Facebook,看能不能在上面碰碰运气。幸运的是,我真的找到了一个之前被困在诈骗集团的同胞。他找人求助将我救了出来。
 2019年8月28日,柬埔寨金边,民警每两人押着一名犯罪嫌疑人,登上飞机。(图/视觉中国)
2019年8月28日,柬埔寨金边,民警每两人押着一名犯罪嫌疑人,登上飞机。(图/视觉中国)回望整个过程,我觉得我之所以能够逃出来,是因为我一直都没有放弃逃跑的想法。跟我一起的受害者他们很害怕,尤其是在我跳楼逃跑之后都远远地离开我,生怕我的事情连累了他们。我想,他们一定也知道“半年之后就放你们走”这样的话是从头到尾的谎言。从被解救到现在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一直觉得很恍惚,感觉在这盘口工作的半年时间像无边无际的噩梦一样吞噬着我。日前我因为信任了太多不该相信的人才让自己陷入诈骗团伙的圈套里。我现在讲自己的经历,是希望让更多的人意识到这个问题严重性,不再受骗。
(方钟平、小泽、崔风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