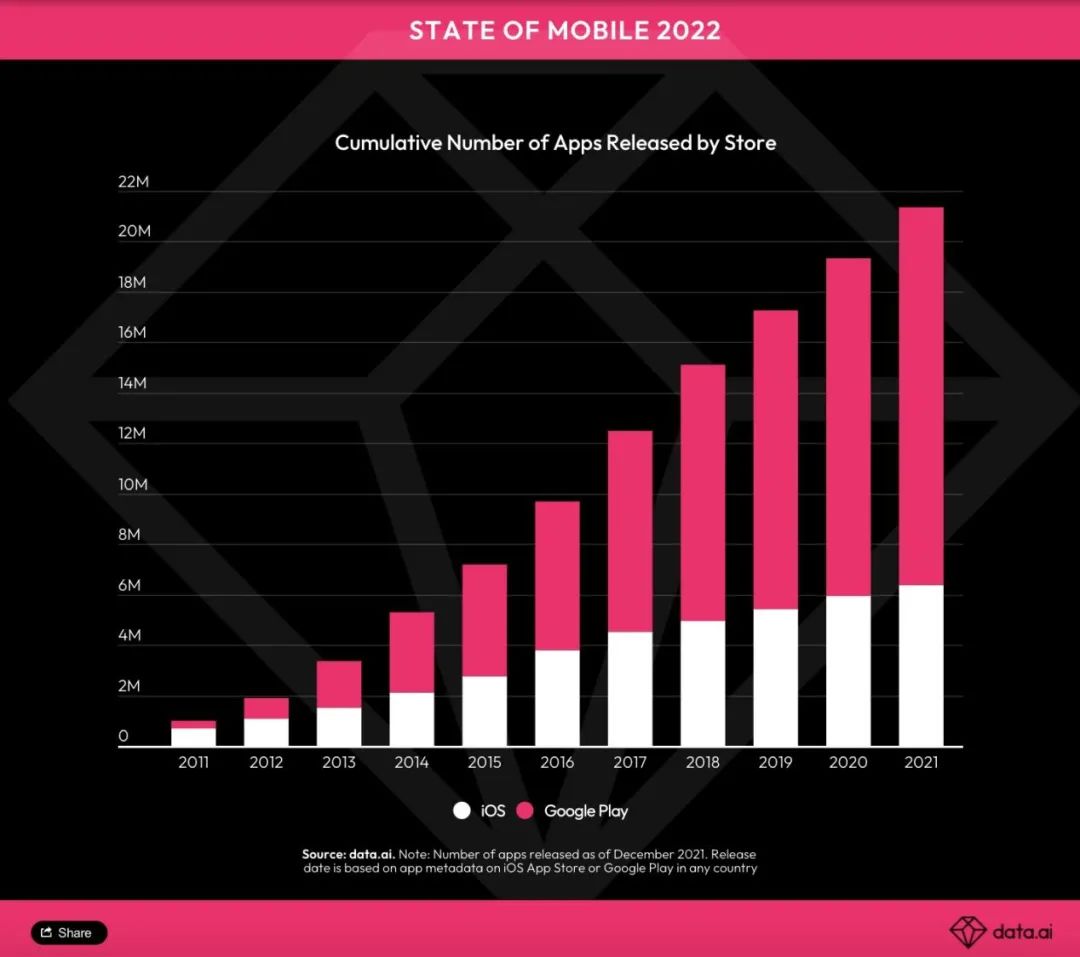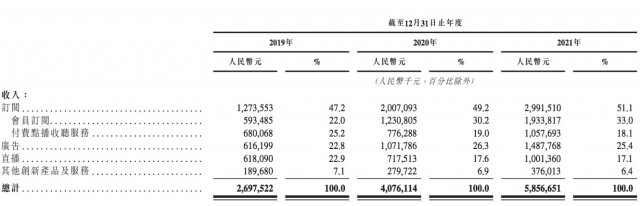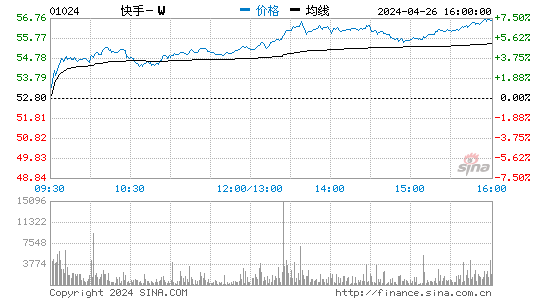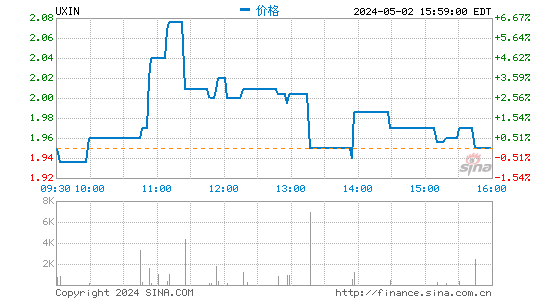作者 | 田瑞颖
西湖大学近日再迎全球顶尖学者加盟——德国工程院首位华人教授院士、著名生物工程学家曾安平。此前,他是汉堡工业大学终身教授、生物过程与生物系统工程研究所所长。
加入西湖大学后,曾安平将打造一个全新的校级合成生物学与生物智造中心,并担任该中心创始主任,未来的研究将与“双碳”密切相关。
曾安平在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坦言,在58岁时回国是人生的一次重要“变道”。他还笑称,此次回国还“砸”了太太的“饭碗”。
从跨专业读博,擅自更换导师布置的课题,不顾导师担忧开辟新方向,再到36年后归国重来,曾安平在一次次“变道”和“颠覆”中,践行着对兴趣的“自由”追求。
“从头越”
《中国科学报》:自1986年前往德国攻读博士学位以来,你在德国有36年的事业和生活。58岁决定回国,对你意味着什么?
曾安平:
这像我在回国路上心里反复回荡的这句“从头越”。
回国对我的生活和事业都有很大影响,包括家庭。我太太原来和我在同一个研究所,她当年毕业于北大化学系并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后来一直在我的研究所负责分析实验室。我一回国,相当于原来的研究所就“关门了”,把我太太的“饭碗”都给“砸”了。
在德国,辞去大学终身教授和公务员身份是一件很稀少且常人难以理解的事情。除了高度的学术和教学自由,德国教授还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以及很好的医保和养老待遇。
其实,我太太不仅丢了“饭碗”,还丢了“教授太太”可以终身享受的最佳医保及退休金待遇。因为她也是学术出身,还是比较理解和支持我的梦想。
《中国科学报》:2020年,你在德国主持的项目刚获得超过1000万欧元的科研经费,随后又获评德国工程院院士。是什么原因让你决定回国?
曾安平:
可以说是机缘巧合吧。我这几年一直在琢磨二氧化碳捕捉和大规模生物制造的问题,也有一些合成生物学方面大的想法。
虽然主持的德国研究基金会重点专项很大,也与“碳中和”和合成生物学相关,但还是要分心去组织协调,不能完全投入科研,我对在德国从事研究的慢节奏也有点失去了耐心。而中国的快速高效,令我兴奋。
尤其在中国各方面对“碳中和”及合成生物学这一新兴学科的高度重视的背景下,如果能把合成生物学的基础研究和工程应用很好的结合起来,也许在国内能做一些真正实现源头创新,颠覆现有生物制造技术的工作。
《中国科学报》:此前,国内是否有其他学校邀请你加入?为什么选择西湖大学?
曾安平:
是的,也有过其他学校邀请,但施一公校长的情怀和几句话很打动我。我问他对我有什么期待,他说,我对你没有期待,只希望你能做自己最想做的事。而我刚好有些最想做的事。就这样机缘巧合!
还有一点,就是西湖大学的建校理念。我回国前是德国华人教授学会主席,对国内外高等教育一直很关注。在和施校长第一次联系的时候,我正在组织一个关于德国大学变迁的学术会议,颇为感慨。
19世纪初德国教育的改革,造就了德国大学的百年辉煌,使其涌现出大批杰出学者,20世纪初德国科学家曾囊括全世界近40%的诺贝尔科学奖,比如建在德国一个小镇上的哥根廷大学就培养出40多位诺奖得主。
中国的人才资源很丰富,但尚未培养出这种有世界级影响力的人。我很高兴有机会助力建设一个西湖理念的中国新型研究大学,为国内的人才培养出点力。
总在“变”
《中国科学报》:你的硕士专业是石油及化学工程,导师是我国石油化工事业的开拓者林正仙先生。但即将读博时,你为何跨到陌生的生物技术专业?
曾安平:
硕士毕业那会儿我21岁,可能因为年轻,林先生就建议我改学生物技术,将来用生物化工为“夕阳工业”的石油化工产业开辟新道路。
我也觉得自己还很年轻,改行应该不算晚,而且我也把改行看成是一个新的机会。
《中国科学报》:博士期间,你“擅自”更换了导师布置的第一个课题,研究结果还颠覆了关于氧气利用生物能学效率一个教科书般的定论。你怎么看待这种“叛逆”?
曾安平:
一方面导师布置的课题确实不是我兴趣所在,另一方面我觉得就算做了,在当时也肯定不会有大的突破。
我觉得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很重要,而不是盲从。德国的博士生培养以前是很“放羊”式的,非常注重个人的独立思考,有选择的自由,这也是他们培养人才的一个优势。
《中国科学报》:你对想更换研究方向的学生有什么建议?
曾安平:
换专业最重要的是兴趣,而不要因为赶时髦或者就业,这样才有持久的内驱力。同时还要看到自己的长处所在。下定决心以后,就得能吃苦,从基础入手,不能眼高手低,好高骛远。
《中国科学报》:在德国竞聘教授很难。你的主业是工业生物技术,但竞聘时又开辟了生物医学技术的新领域,最终获得这两个领域的教授。你担心开辟新方向会影响主业,影响教授竞聘吗?
曾安平:
两个方向都是兴趣所在,都放不下,所以干脆就都做了。而且我当时是在做教授资格的研究,在德国一旦成为教授,往往很难有精力开辟新方向,所以我就趁着还不是教授时,静下心来抓紧做感兴趣的事。
打破学术权威意识
《中国科学报》:你是如何选择学校和导师的?
曾安平:
德国国家生物技术中心(GBF)当时在生物技术领域国际领先,我申请的导师是很有名气的GBF院长Klein教授,但最后收到的却是没有听说过的GBF生物化工部主任Deckwer教授的来信。他也是刚从化学工程转道到生物化工领域的。
在学术上,我的导师对我的影响起初似乎并不大,倒是GBF的多学科交叉和活跃的国际学术气氛使我大开眼界,受益匪浅。
Deckwer教授很严谨、勤奋、平易近人,最重要的是对我比较“放任”和信任,我很庆幸能在他的大力支持下自由地做真正感兴趣的课题。
《中国科学报》:你对学生选择导师有怎样的建议?
曾安平:
有句话说“事在人为”,尤其是年轻人,不要光看导师的“帽子”,光想着导师要我做什么,要主动思考自己想做什么,看导师的研究方向是不是自己感兴趣的。
导师课题组及所在的研究机构的学术气氛也很重要。我认为,环境甚至比具体的导师更重要。
《中国科学报》:回国后,你是如何教育学生的?
曾安平:
我在国内带学生,一直注意打破束缚学生思维的学术权威意识,不要盲从书本和文献。
我总跟学生讲,我们在学术上是平等的,在一些具体课题上,学生要尽快走到老师前面去,提出自己的想法,老师更多时候应该是引导,质疑,和学生一起分析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另外我会给学生比较大的自由。这点我在国外深有体会,很多到我研究所来的中国学生,不一定是来自清华北大这些一流高校,但几年后却做得相当出色。我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一个专心做学术的环境和气氛。
中国的人才资源潜力很大,我这次回来,也是希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营造一种有利于人才潜力充分发挥的学术氛围和环境。
《中国科学报》:如果对青年科研人员说几句话,你最想说什么?
曾安平:
首先肯定是要静下心来,扎扎实实,心无旁骛地做研究。创造力是有黄金期的,可能不到十年,年轻人把这段黄金时间好好用在科研上非常关键。
另外因为现实原因,很多年轻人可能很早就开始考虑买房、孩子上学这些事,被迫作出妥协,放弃自己的事业和梦想,这是非常可惜的。
当然我知道青年科研人员很不容易,但我还是希望年轻人先树立好事业,而不是本末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