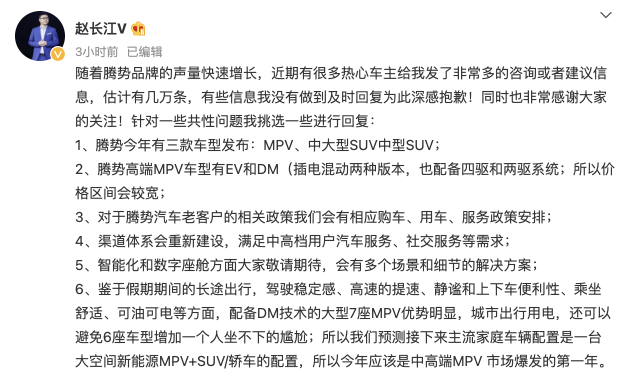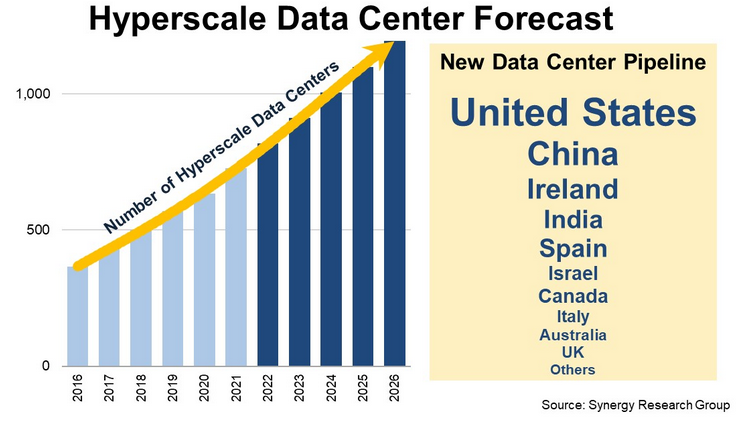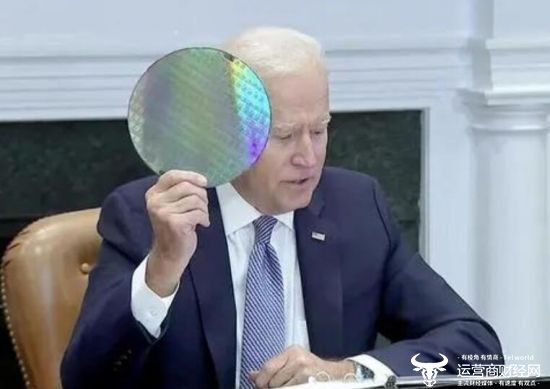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孟郁是一名孤独症人士的父亲,他的儿子禾禾3岁时被诊断为孤独症。“18岁生日后,禾禾出现了严重的情绪和行为问题。现在他的个头比我还高,体重200多斤,一旦出现行为问题,抱都抱不住。”孟郁说。
像禾禾这样的大龄孤独症人士不在少数。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没有独立行为能力,存在严重的社交障碍,缺乏自理能力。随着年龄逐渐增大,相关机构不再接纳他们。目前国内对学龄前和义务教育阶段的心智障碍权益尚有政策支持,但面向18-59岁心智障碍人士的专业服务非常稀缺,很多成年后的孤独症人士只能常年待在家中,由父母照顾。
未来如何托养他们的孩子,成了横亘在家长们心中一道过不去的坎儿。
无处可去
孤独症人士,也被称为来自“星星的孩子”。他们中的大部分有着自己独特的精神世界,孤独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很难融入周边的社会环境中。
大多数人对孤独症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一些影视作品中,例如《雨人》、《自闭历程》等。在很多类似的影视作品中,孤独症人士被刻画成某种天才。但真实情况是,孤独症是一种从儿童发育早期就开始出现并持续终生的障碍,除了少数特例之外,大多数都需要他人的照护。
2002年出生的禾禾今年已经年满19周岁,目前在北京海淀区一所特殊教育职高就读。这两年因为疫情,学校时常停课,加上不久前家里常年照顾禾禾的阿姨突然出了车祸、禾禾步入青春期等因素,18岁之后,他开始出现撕碎书本及海报、“轰人”、到小卖部疯狂购物等怪异的行为。
经过家人的耐心陪伴和一些服务机构的干预,现在禾禾的情绪问题有了明显改善。不过,从小到大,他从未自己独立生活过。“要么是我和家人照顾,要么是保姆照顾,自己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楼下的理发店,全程我都悄悄跟在身后。”孟郁说。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康复医院主治医师周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她所接触的孤独症人士中,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到医院做康复的频率会下降,更多的是待在家中。有很多孤独症人士还存在共患病的问题,比如同时患有癫痫、情绪障碍等疾病,照顾起来很麻烦。对家长和孤独症人士而言,生存质量都不好,亟需社会的关注。
居住在上海的凌峰,也是一名孤独症人士的家长。他的孩子祺祺今年24岁,同时患有癫痫。祺祺1岁8个月时,凌峰和妻子发现孩子目光无法与人对视,语言方面进展缓慢,他们很快带孩子到上海的各大医院就诊,最终被诊断为孤独症。
妻子当时毅然放弃了年薪百万的工作,成了一名家庭主妇。他和妻子曾带着孩子去上海各大医院做儿童训练,也尝试过针灸等其他方式,“回过头来看,当时如果不去做这些干预训练,现在结果可能会更糟糕。”凌峰说。
16岁以后,祺祺开始频繁出现情绪爆发,甚至是攻击和自伤行为,有时用头猛撞地板,有时会把自己的手咬得坑坑洼洼,有时连着搓手二三十分钟,直到搓出血。
看着这些,凌峰和妻子却无能为力。一是年龄和体力不允许,拦不住;二是到底是顺着孩子由他发泄情绪,还是阻止他的这种行为,他和妻子也没有达成共识。
祺祺从特校毕业后,凌峰和妻子基本上每周抽2天时间,带他在慧灵智障人士服务机构(国内最早的针对成年智障人士的公益组织之一,以下简称慧灵),其余时间会安排一些打球、溜冰等活动。但疫情后,这些活动基本都停了。
“孩子从特校毕业之后,问题就出现了——没有地方可去。”凌峰说,目前对于成年孤独症人士而言,国内没有专门的机构对他们进行托管和照护。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副主任医师李雪常年研究精神疾病康复这个领域,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接触的孤独症人士中,成年人占比不少。很多家庭的经济条件没那么好或者家长不重视,导致孩子很晚才被诊断出来,使得这些孤独症人士很难得到有效干预,再加上他们中的一些人存在行为问题,一部分人没办法回归社会生活,只能常年待在家中。
2019年,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孤独症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五彩鹿孤独症研究院院长孙梦麟在《中国孤独症教育康复行业发展状况报告Ⅲ》发布会上指出,孤独症发生率逐年增长,按保守估计的1%计算,中国有超过1000万的孤独症人群,200多万孤独症儿童,孤独症儿童的数量每年以接近20万的数字递增。
更严重的是,孙梦麟说,“现在国内能诊断出来的孤独症孩子大部分是中重度,很多症状较轻的孩子还在幼儿园和学校,没有被发现。”
2020年6月,《神经科学通报》(Neuroscience Bulletin)在线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首次全国性孤独症流行病学估测研究的论文。该研究由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的科研团队领导开展,于2014年7月-2016年12月对8个代表性城市的12万余名6-12岁儿童中进行调查,估测出国内孤独症的流行率为0.7%。这意味着,大约每143名儿童中就有1名孤独症儿童。
“究竟国内目前有多少孤独症人士,整体准确数据是缺失的。”上海闵行区慧灵社区助残服务中心服务主任陈戎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医生和相关从业人员对孤独症缺乏了解、一些家庭出于社会歧视、就业等因素放弃为孩子领残疾证(无法被收录数据),这些因素都会导致漏掉很多孤独症人士。
据他介绍,在上海闵行区这样一个积极进行孤独症关爱援助的地方,经过多年的努力,所了解和触及的孤独症家庭也仅仅五六百家,而这显然不是全部。
托养何解?
孤独症的诊断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40年代。1943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儿童精神科医生里奥·凯纳(Leo Kanner)首次报道了孤独症,并将其命名为“早期婴儿孤独症”。国内迟至1982年,南京脑科医院的陶国泰教授才在论文中首次报告了4例“婴儿孤独症”。
如果按照1982年陶国泰教授首次确诊4例孤独症病例来计算的话,早期诊断出的这批孤独症已步入中年,他们的父母已步入老年。
然而,没有一个家庭可以为孤独症孩子的降临做好准备。现在,这群大龄孤独症人士的家长正面临或即将面临老无所依的困境,同时还面临着他们的终极焦虑——当无力照看时,他们的孩子能去哪?无数家长都在寻找答案。
生活在北京的苏琳是一名科研工作者,她的女儿曼曼小时候被诊断为智力发育迟缓,“但现在越来越自闭了,自己1个人可以待一天,有时候还会自我对话。”苏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小时候状态还不错,2016年从特校毕业后,曼曼的状态就直线下滑。从那之后,我一直在为她找出路。”
这几年,苏琳走访了很多机构,包括温馨家园(由社工组织运营的一个服务窗口)。这些机构大多在郊区,离苏琳住处很远。大约几年前,苏琳曾了解到,温馨家园对于这类心智障碍人士,每天有2个小时的照看时间,但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苏琳希望能找一个安心托付孩子的地方,可以保证她能正常上班,距离远一点也行。2019年,中科院和北京健翔学校共同搭建的职业康复中心成立,专门为北京海淀区残障人士提供看护和照顾服务。“中午管饭,还有老师教一些知识。这样的帮扶真的已经很到位了,希望这样的机构能够多一些。”苏琳说。
事实上,近年来,关于大龄孤独症人士的托养问题已有不少讨论,包括广泛被提及的“双养”模式(同时对家长和孤独症孩子进行照护)、孤独症家庭依托社区近距离搭建的社区帮扶体系、集中托养机构等。
“双养”模式虽被广泛提及,但目前没有明确的支持政策。苏琳说,她这辈子都被“拴”在孩子身上了,“双养”于她而言是别无他法之选,因为没有一个让她可以放心“托养”孩子的地方。苏琳咨询了很多大型的养老机构,并不允许孩子和家长一起入住养老。
北京市晓更助残基金会发起理事李俊峰认为,理想的状态是家长老去或去世后,心智障碍者依旧能够居住在他们熟悉的社区中,最大程度上维持原有的生活状态,有专门的社工人员负责提供生活的部分支持。但就现在来看,这种模式成本投入比“双养”模式更大,公共服务也更难企及。
“成年孤独症人士的家长,并不是都在被动等待。我们意识到了服务机构的重要性,正在发起与一些智障人士服务机构的合作,支持他们的社区化生活模式在北京有更大发展。”孟郁说。
也有一些家长开始了做新的尝试,被视为“民间自救”,例如安徽金寨的“星星小镇”等。
在中国,大龄孤独症人士的照护和托养问题仍是孤独症家庭在承担。义务教育阶段结束之后,他们很难寻得专业的资源和相应的机构。“孤独症目前被纳入精神残疾范畴,但孤独症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医疗问题,更多的是一个社会问题。”李雪说。
在李雪看来,要想实现对大龄孤独症人士的托养,需要一环扣一环的完整体系,并非一个家庭、一家医院或一个机构就能解决的。相应的专业机构又需要专业的管理人员、护理人员、社工,还需要医生定期查看孤独症人士的身体状况;此外还涉及到监护人权利等一系列伦理、法律方面的问题。
作为国内老牌的心智障碍服务机构,慧灵目前已在24个省、42个城市开展相关服务,有2000多个日常服务对象。据了解,其中差不多1/3是孤独症人士,有500多位工作人员。“这个数据意味着,社区化服务模式是可以真正落地的。”陈戎东说。
不过,即使是慧灵这样的机构,近年来也仅勉强营生。据财新报道,慧灵创始人孟维娜坦言,慧灵创办20余年,基本未实现盈利。
特需信托的兴起
对孟郁、凌峰、苏琳而言,他们的资产状况足够支撑孩子的生活开支,但他们也面临一个现实的问题:当他们无法陪伴孩子的时候,家庭资产由谁来管理、怎么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孩子身上。
特殊需要信托(以下简称特需信托)因其具备财产隔离、权力制衡、以受益人为核心等优势,正成为这些家长的选择之一。
据悉,特需信托的受益人是心智障碍孩子,由机构做监护人,需求是让资金转化为对孩子的支持服务。其中,信托公司管理资产而无使用权,监护人有决定权但不接触资金,专业服务商提供服务但没有资金的所有权。
“对大龄孤独症家长而言,特需信托是大的趋势。”凌峰分析,如果没有特需信托,家长的财产大概率要托付给亲戚。但这还面临很多现实问题,毕竟在亲戚享有财产的情况下,这些家长的孩子是否能享受较好的照顾和生活,存在不确定性。
据报道,目前在北京,已有三位特殊需要人士家长与光大信托签署了特需信托的协议。
凌峰长期从事信托相关工作,他坦言,这条路走起来并不容易。对于特需信托而言,国内机构的公信力不够,缺乏政府背书。
此外,孤独症人士因自身的特殊性——无法管钱,所以如果交给信托公司来做专业理财和资产隔离,他们的未来必定绕不过监护人。
一名资深保险人士、同时也是一名心智障碍者家长表示,不论法定、遗嘱继承还是寿险,留给孩子的财产都是一次性给到了监护人手里。未来家长的资产也是孩子的资产,孩子的资产也是监护人的资产,孩子的资产很难与监护人的资产隔离。
这样一来,监护人要兼顾管事和管钱,权责过重。前述资深保险人士表示,就算家长把钱留给孩子,提供了资金的保障,但是他们还缺相应的服务。目前大龄心智障碍孩子的服务机构严重不足,而且照顾特殊孩子的时间跨度大,服务内容繁杂,不是一家机构能够全面覆盖的,更缺乏对服务的监督机制。
在孟郁看来,把成人孤独症的特需信托体系搭建起来,让家长们现在就能看到它的运行,看到体系中的各个角色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这是最大的价值。“现在在努力推动家长组织做监护人,家长组织因为比较能感同身受,可以互相制约和监督。这样一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建立完善的被监护者个人档案。”他说。
不过,在特需信托的框架里,监护人、监察人、服务枢纽,以及第三方服务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更多的家长仍在观望。
“光大信托开启的特需信托,是一件积极的事。但希望今后还是尽量走慈善途径,避免商业化。一旦商业化,孩子的照护必定不会太理想。”凌峰说,如果政府今后能参与其中,为特需信托背书,加上家长和机构的资源的整合,共同解决大龄孤独症人群乃至更大范围心智障碍人士的养老问题,无疑是一件多赢的事情。至于是社区化还是机构化,还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探讨和摸索。
“作为家长,我的终极目标就是,孩子有地方去,我也有地方去。”苏琳说,就政策层面而言,国家并非完全没有托底,家里完全没人照顾的情况下,政府也是有托底的。但是,在这些“托底”机构或者某些养老机构,孩子是否还能生活得有尊严、有质量,苏琳也打了个问号。在她看来,硬件不主要,收费贵点也没关系,只要照顾服务跟得上,有专门的机构或人员对照顾人员进行监管。
孤独症群体没有一位是自愿孤独的。陈戎东说,他们渴望被看见和听见,也愿意看见和听见别人。如果只是把这个人群当做照顾的负担,那么最终会演变为政府、家庭或家长的博弈,依然无法解决问题。
随着父母老去,大龄孤独症人士的未来在哪里,恐怕目前的答案仍是无解。但可以肯定的是,一名大龄孤独症人士的全生命周期服务的构建,仍需要政府、社会、家庭多方合力。
(文中孟郁、凌峰、苏琳、曼曼均为化名)
欢迎提供线索
作者邮箱:[email protected]
值班编辑:王琳